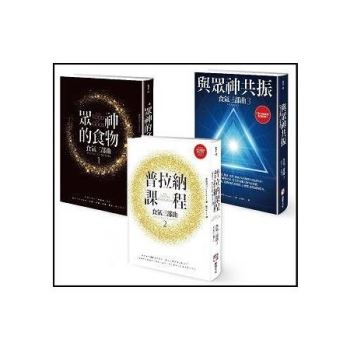代序
黃碧雲.處境
寫是我的狂歡節。
─黃碧雲
我有一張黑白照片,右手支頷皺緊眉頭抿嘴以15度角斜視側方,一九八三年,在明星咖啡屋,黃碧雲拍的。我們第一次見面,(她剛剛開始寫作)總之一杯咖啡沒喝完,我們就沒話說了。(桌上半杯咖啡,時光沉澱似的有種神秘難解的狀態,一如我的表情。「聽和沉默都構成話語」,海德格。)我是一個沒經驗的受訪者,(我後來知道了)她是一個不導引話題缺乏好奇(且一切看在眼裡)的記者。我認為我們不會再見了,卻沒想到這樣的相識之初,成為日後二十多年來我們之間的相處模式。
一九八七年,她交出了《揚眉女子》,之後的《溫柔與暴烈》、《七宗罪》……編織出她獨特的小說美學風格:溫柔與暴烈。沉默者。
等她再來台北,身分顛倒,她作家,我報社《讀書人》主編,有時候,我寫訪問稿,有時候別人寫。不變的是,我們在吃飯、喝酒、隨性漫遊的動線裡,我們見面,我們不交談。我猜想並且確定,該問該回答屬於寫作的,都已經歷完成,反之亦然,她的問題就是我的問題,我的答案就是她的答案,這些年過去,並沒有起太大變化。還有,我同樣對人不好奇。至少對她不好奇。不是因為她沒什麼,而是別的。
譬如,二十世紀末,我去香港,她帶我搭火車往深圳玩,主要可以坐掉一些時間吧?下了車,她拿回鄉證我台胞證,我們走不一樣的入出關口,人潮迅速把我們分開,但我們一路沒失散,不是我一個轉彎就看見她神閒氣定等在那裡,就是我等她。人事無可驚。我們循序走完見面公式:江浙菜、逛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名牌仿冒商場、按摩。我們被安排在一個房間。(我找到了一個黑暗房間,沒有聲音,沒有言語;靈魂在黑暗之中遊蕩尋覓。──〈暗啞事物〉)沉默持續。這點不會讓我有一絲絲不安。人人說黃碧雲酷,她只是消減。(我的人生也從此進入省減時期:真的不需要那麼多。〈虛假和造作的〉)
二十一世紀初,我去香港,找了碧雲、黃寶蓮、聞人悅閱幾位朋友午餐,先約在荷李活道電梯步道下碰頭,突然吹起一陣陣狂風,我們個個東倒西歪,碧雲出現了,完全不受狂風影響,一路朝我們走來,面露少見的燦爛笑容,亮麗時髦披肩長髮,無袖黑洋裝垂吊形大黑包,總之有點不太一樣。這次,我們配潮州館子。之後和寶蓮、悅閱去不遠伴石階而上大門敞開的小咖啡館說話,她們談得熱烈,碧雲跳佛郎明哥舞般動作很大,她那時已度過西班牙西維爾(seville)練佛郎明哥舞、香港來去出版《沉默。暗啞。微小》(他們說你不要寫了,讀者都不明白你在寫什麼。我就覺得很絕望。〈沉默詛咒〉)進了律師樓工作又放棄,遂生成眼前西班牙、香港兩地居住模式。我忍不住拍了幾張相片,鏡頭裡的她們嫵媚智性發光,非常動人。我們街頭散了之後,寶蓮說,黃碧雲其實是想跟妳單獨見面。我停頓一會兒,也只說,沒事。不久前我先生過世,碧雲得到消息已經回過話:「其實我一直在等這封信,無論它以甚麼形式出現:要發生的終必發生。這也好,或許進入痛定思痛的處境,痛就不那麼令人憤怒和恐慌了。」
命運以這樣的節奏牽引人生,痛定思痛的處境究竟是什麼呢?個人顧餘生,這刻,以更沉默的寫作。之後我們幾乎年年見面,任何人問起為何好久不寫了,都只得到一句:「噯呀!寫什麼喲!」根本不是答案,是處境「選擇了我並且不那麼費力的就贏了我」,是姿勢:「輕微或許根本就不成為一個姿勢」,所以,人家重口味,她重動作:「讀就讀,不讀就拉倒。〈沉默詛咒〉」一切如此。不這樣,她就不是黃碧雲,但「從一邊轉到另一邊,她人還是那個人。……當我從過去的時間離開,不因為這樣的緣故,我就不是原來的。〈微小姿勢〉」痛定思痛,黃碧雲處境。
很快的來到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將結束的二○○九年,我重返台南在成大教書,碧雲來,旅程公式,漫走成大校園,停在有名的老榕樹前,她想一個人畫畫,當然由她。稍晚我去找她,站背後看她收筆,榕樹主題,印象派點描法,梵谷氣質。反沉默話語。她突然說起寫了篇小說〈晚蛾〉,(我當時其實很激動,但已經習慣不在她面前有情緒。)回香港就寄過來。
〈晚蛾〉是一個獨立的故事系,文句更減省斷裂,強烈的黃碧雲主導。(我從來不容許觀眾、讀者、編輯,或任何人決定我的作品。──〈虛假和造作的〉)異國情調種族人名,在一個稱之為空間的酒店糾葛返覆,賦格音樂,記憶主弦律。我特別印象深刻的是,小說中,她形容貝多芬晚期作品《莊嚴彌撒曲》裡《聖本篤》樂章:「以一段小提琴獨奏開始……提示,展開,回答,重現,結束,成為樂章最婉轉的敘述者。」而最終樂章《大賦格曲》:
終章並不總結,也不回應。終章憤怒,粗暴,突兀,回歸卻不馴服,與過往決裂後者無追,枯燥無華采,無人理解也厭惡理解,成為老孩子玩自己一個人的遊戲,並一手將城堡與房子推倒;終章無啟示,無永世,亦無再。
是的,小提琴和黃碧雲的寫作風格比擬,《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裡班雅明(Benjamin)引瑞赫特(Gamille Recht)的話形容小提琴家的魔術技藝,我認為十足貼切指出黃碧雲的一字一句一個意象點描法手法:「小提琴家必須自己創造音調,要像閃電一般快速找出音調,而鋼琴家敲按琴鍵,音就響了。」
班雅明延伸解釋,畫家的調色,對應的是小提琴家的塑音,攝影家則像鋼琴家。那麼,小說家呢?有的是小提琴家,有的是鋼琴家或其他。黃碧雲對酒店(告解室?肉身?)空間人物故事的塑音手法,明顯的延伸到《末日酒店》。
人人有一個城堡與房間,黃碧雲、〈晚蛾〉1367號,《末日酒店》107號。卡夫卡:拆生命的房子,拿這些磚塊蓋小說的房子。因此,黃碧雲的小說,從來不是好不好的問題,她總是創造或把自己推向一個處境(我是那麼一個驕傲而造作的人,所有的追求不過一個姿勢。──〈虛假和造作的〉),那過程,宛若對儀式或祭典的追求。(以火以水,以鬥牛,以煙花,以音樂及可消逝之時間所祭……在一個狂歡節裡面,我不再是我。〈與D先生跳舞〉)於是,她調度筆下的鬥牛士揚起、刺殺及Flamenco舞排、試、唸、停頓、轉身、擊掌。找出音調。
其實我早知道,這樣一名小說家,不管沉默多久,都會繼續寫下去。現在,她出書了,即使距離上本《沉默。暗啞。微小》已經七年過去。所以,黃碧雲處境是什麼呢?
寫是我的狂歡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