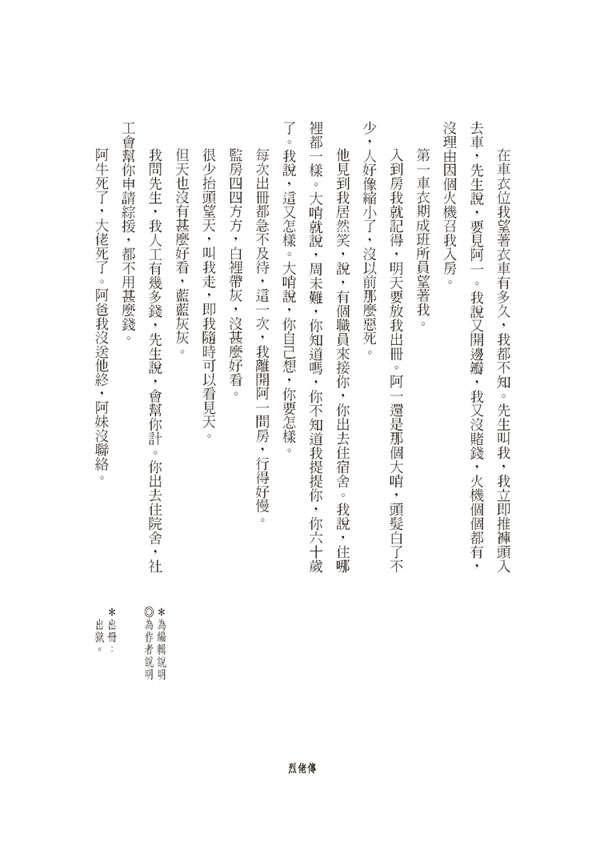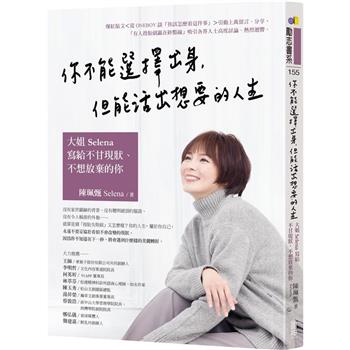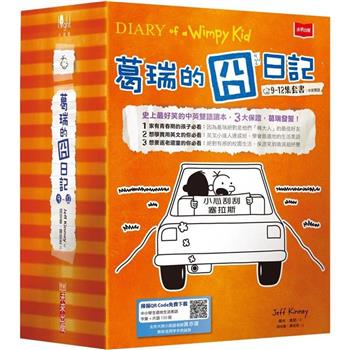黃碧雲在《烈佬傳》的封底文字這樣寫著:
小說叫《烈佬傳》,對應我的《烈女圖》。小說也可以叫《黑暗的孩子》,如果有一個全知並且慈悲的,微物之神,他所見的這一群人,都是黑暗中的孩子。小說當初叫《此處那處彼處》,以空間寫時間與命運,對我來說,是哲學命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裡面,人的本性就是命運。時間令我們看得更清楚。
我曾經以為命運與歷史,沉重而嚴厲。我的烈佬,以一己必壞之身,不說難,也不說意志,但坦然的面對命運,我懾於其無火之烈,所以只能寫《烈佬傳》,正如《烈女圖》,寫的不是我,而是那個活著又會死去,說到有趣時不時會笑起來,口中無牙,心中無怨,微小而又與物同生,因此是一個又是人類所有;烈佬如果聽到,烈佬不讀書不寫字,他會說,你說甚麼呀,說得那麼複雜,做人哪有那麼複雜,很快就過---以輕取難,以微容大,至烈而無烈,在我們生長的土地,他的是灣仔,而我們的是香港,飄搖之島,我為之描圖寫傳的,不過是那麼一個影子。
【編輯推薦】
再一次溫柔與暴烈/大田出版儀主編
每一次讀黃碧雲的作品,第一回總是艱難的,但很奇妙的是,讀過一遍之後,你再也不會覺得有什麼難?難在哪裡?你還會中毒般地,不知不覺地默默守候成為她的忠實讀者……
《烈佬傳》是黃碧雲在大田出版的第9本作品。
她一開始即言明,這是一本用廣東話語法書寫的小說,如果在台灣出版是否要注解廣東話,還沒有定論,她說在香港也是讓讀者去猜……
最後,作為一個編輯,我還是幫讀者做了些功課,在書中區隔了編注與作者注,放在版型的下半段,不會對閱讀有所影響。
每次核對文稿,便又一次震懾黃碧雲輕輕描述,輕輕放下的無謂感,每次對稿結束,好像生命又被狠刮了一頓,可以輕省的,無論你多麼沉重;可以沉重的,無論你多麼不在乎。
黃碧雲作品的題材從不重複,每推出一本小說,便是一個新的視界,在這個小說的寬度與廣度裡,她爬梳的文字無人可預測,她鋪陳的中心思想,無人可譬喻,我在十幾年前編輯她的小說,十幾年後再度捧起文稿讀著,仍然莫名存在一種攝魄感,那往往令人讀畢之後,會掩卷嘆息的。
而編輯多年,我總愛她字裡行間的詩意,像這次摘選出來當作封面文字:有一天,你會發現你一無所有。前後有文,但當你讀到這句,你會明白,這文字絕望與希望的力量有多麼劇烈,我總在這些劇烈之中,去喜愛這個作者的作品。
有一回和美術設計談到兩本前後作品,我說《末日酒店》是有寫作技巧的,所以濃烈,而《烈佬傳》平鋪直敘,卻後勁十足,我往往承受不住這衝擊,每讀一遍就沉默一回,一世人流流長,而小說中的烈佬就這麼無所謂地過了這一生。
◎更多精采線上預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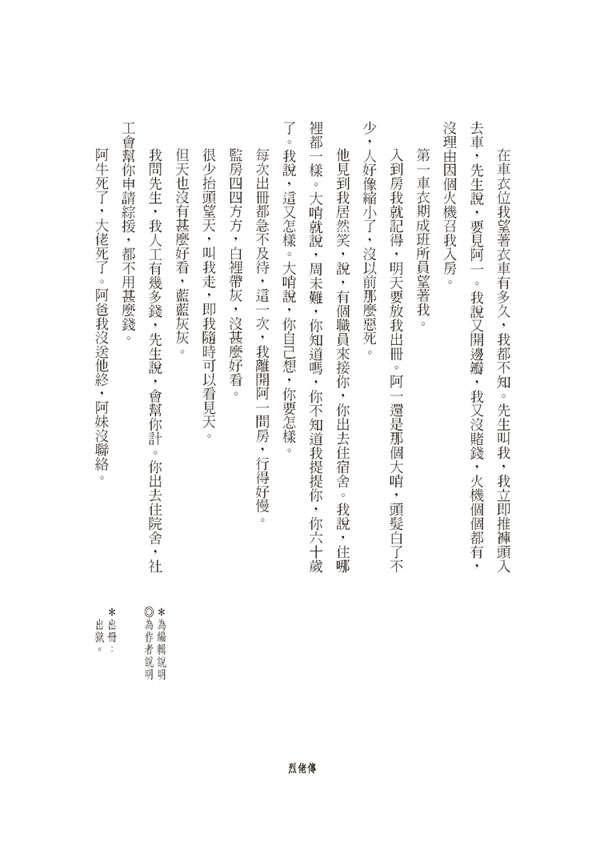
作者簡介:
◎【特刊】 再一次溫柔與暴烈
黃碧雲
香港大學社會系犯罪學碩士,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法律專業文憑。曾任新聞記者。為合格執業律師。
她的小說創作深具特色與驚嘆,長久以來重量級的溫柔文字觸動讀者,教人願意追索與守候其作品。
黃碧雲得獎紀錄與出版作品--
第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小說獎
第四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獎
第一屆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新秀獎
第一屆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小說首獎
聯合報、中國時報十大好書年度獎
1987年香港當代舞蹈團單人表演「一個女子的論述」
2000年香港讀書小劇場「媚行者」
2004年香港牛池灣文娛中心、台北牯嶺街小劇場「沉默‧暗啞」
章節試閱
在車衣位我望著衣車有多久,我都不知。先生叫我,我立即推褲頭入去車,先生說,要見阿一。我說又開邊瓣,我又沒賭錢,火機個個都有,沒理由因個火機召我入房。
第一車衣期成班所員望著我。
入到房我就記得,明天要放我出冊。阿一還是那個大哨,頭髮白了不少,人好像縮小了,沒以前那麼惡死。
他見到我居然笑,說,有個職員來接你,你出去住宿舍。我說,住哪裡都一樣。大哨就說,周未難,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提提你,你六十歲了。我說,這又怎樣。大哨說,你自己想,你要怎樣。
每次出冊都急不及待,這一次,我離開阿一間房,行得好慢。
監房四四方方,白裡帶灰,沒甚麼好看。
很少抬頭望天,叫我走,即我隨時可以看見天。
但天也沒有甚麼好看,藍藍灰灰。
我問先生,我人工有幾多錢,先生說,會幫你計。你出去住院舍,社工會幫你申請縱援,都不用甚麼錢。
阿牛死了,大佬死了。阿爸我沒送他終,阿妹沒聯絡。
灣仔修頓那班兄弟,行正的行正,老的老,一身病,斷手斷腳,死的死一個少一個。後生的我都不認識。
在漆咸道公園如果沒識到阿生,沒和阿生去踩單車,我沒去到灣仔,我留在尖沙嘴,不知我會不會和阿爸一樣,做裁縫,上海師傅。
和我一起玩那個大衛仔,我識到阿生後,沒跟我們去踩單車,後來他阿爸送他去巴黎,學剪頭髮,後來在中環開了間飛髮鋪,一定收得很貴,那些地方。他住在灣仔星街,有一次我在灣仔碰到他,他還認得我,叫我小難。阿爸來公園接我回家,大衛仔見過阿爸,聽到阿爸這樣叫我,他跟著叫。
我在柯士甸道漆咸道口那間言教小學讀書,留級再讀一年級,第三天上學,無法坐得定,便逃學,回到漆咸道公園玩。這時阿生從澳門偷走回香港,在公園和我打波子,他晚上在公園睡。
我一天阿爸給我和阿妹五毫子吃飯,我和阿生兩份,一個麵包兩個人吃,一支汽水兩個人飲,到下午三點幾便肚餓,賭波子我輸了給阿生,阿生說,我們去天星碼頭開車門,賺到錢,你還我。
有班小孩在開車門,開車門是要打的,我走過去將帶頭那個小孩推開,扭在地上,打了一陣,阿生在叫,走吧走吧,警察來了。其他的小孩聽到警察來了,都散走。
有個金髮鬼婆,見我們打交,很好人,每人給我們一元。
有二元,買個麵包兩毫,還有錢租單車,一元按金,五毫一個鐘,要留下證件,阿生偷走帶到兒童證,就放下給單車舖。我們在公園踩幾踩,阿生帶我坐渡海輪,過海一毫,兩個人推一架單車,坐樓下,好大風,海好藍。去到灣仔,阿生識路,他阿叔有個兄弟,在灣仔搵食,有條叫阿牛,去酒吧搵到阿牛,阿牛說,不如跟我們搵食。那晚我便和阿生阿牛,在酒吧睡,沒有回家,回家阿爸都是睡,不知我有沒有回家,阿妹好乖,天天返學,聽阿爸話,放學便在房間做功課。單車也沒有還,以後有單車用,阿生兒童證掉在單車舖不要。我身上還穿著言教學校的校服,白衫藍褲,那年我十一歲。
在上海已經讀到二年級,來到香港,不會講廣東話,沒讀書。到學會廣東話才返學,讀一年級,但我不喜歡返學。
阿牛說,入得酒吧,要見大佬。跟大佬搵食,有班兄弟,有吃有住,有錢賺,有人一齊玩。阿牛說要收我三十六個六,給大佬的入門利是,我說和阿生兩份行不行,我們哪裡有錢。阿牛就給我和阿生各一個利是封,說,你們出糧要還,小姐會給你打賞的,一個月總共會有六七十元。原來可以賺那麼多錢,怪不得還有一個阿物,不知他哪裡玩的,都要入會。
酒吧黑漆漆,無日無夜,阿生說,你們打開門掃地。大佬今天下午會回來。
掃完地沒甚麼做,阿生教我玩啤牌,酒吧檯很高,我們坐在地上,拖一個紙皮箱玩,沒錢,玩火柴,每人分五十開始。
阿牛踢我們紙皮箱,說,大佬回來了。我卻見到兩個人走入來,不知哪一個是大佬。
原來兩個都不是。這時有個男人,頭髮長長,穿一件花恤衫,頸上戴一條粗金鍊,一個金牌,手上又戴另一條粗金鍊,戴著一個金絲太陽眼鏡走進來,酒吧黑漆漆,那個人眼鏡也不除。阿牛說,叫大佬,我和阿生便叫,大佬。那個人望一望我,說,做乜還著一套校服,阿牛你去和他買套恤衫西褲,買對皮鞋,就從褲袋掏出一個銀包,抽出一張紅底。阿牛問,買一套還是兩套。大佬又抽多兩張紅底,指著阿生,說,也給他買一套,你不是說想買牛仔褲,大佬將錢給阿牛,說,你也買條新褲。阿牛說,多謝大佬,又拉我,說,你站在這裡粒聲不出做乜,我講乜你講乜,我便說,買一套還是買兩套,大佬便笑了起來,說,醒啲喇,講啲乜話,是不是上海仔。
在灣仔他們就叫我上海仔,我真名都沒人知。
後來還有一個大上海,見習騎師。
那場大戲,好恐怖,有個壇,有個壇主,著件白袍,頭縛紅結繩,似茅山師傅,幫死人打齌。
在酒吧做了幾個月,開門關門,有人打交,一地玻璃便掃地,日頭睡覺,睡到下午兩點,出去吃碗麵,回來拉個紙皮箱,開檔玩十三張,五點鐘酒吧便開門,小姐七八點才返工,有個灰嫂,看收銀機,她回來便叫我們做乜做乜,又洗廁所,又抹杯,總之不讓我們白坐,說你們收人工的,又後生。大佬不是天天回來,回來也沒有定時,有時下午,有時大佬回來我們已睡,酒吧關門,我們開張帆布床,推開高檯高凳,睡時已天光。
一天阿牛叫我,明天要穿大佬給錢買那套衣服,去飛個髮,叫師傅要吹好,落髮蠟,阿生阿物都一樣。原來是要做大戲。
帶到我們去李節街,樓下士多,士多裡面好多人躺著,滿地針筒錫紙,果汁樽,穿過去可以上二樓,二樓空蕩蕩,有幾張摺椅,有個神位,紅色燈膽,有個關公,有香爐,點著香,供有生果,生果不知放多久,皺皮又褪色。壇上掛著對聯,寫著「有忠心方可入門 無義氣請勿拈香」,祭壇中間有個木斗,桌上有燈有紙,有個紅盤,裝著花生,有針,有木籤筒,簽筒裡有黃紙。阿牛問過我生辰八字,我說我怎知,他說不知便亂寫,反正有幾個字,戊子年八月五日,阿牛說會叫秋哥寫,黃紙寫有我名,字,生辰,壇上還有單刀,筆墨,紅燭,荷包,剪刀,鏡,木拍板,念珠,有酒有糖,堆到滿一滿,壇後掛旗,還掛著藍燈籠,壇下縛著一隻雞,咯咯叫。
阿牛叫我們三個,穿白袍,著草鞋。
那個主持叫秋哥,瘦瘦小小,穿一件黑袍,阿牛說,他叫你做甚麼便做甚麼,沒事的。
那個秋哥,叫,傳新人,其實我們都在房間裡面,使乜傳,果然是做戲。
還有一個,阿牛後來說是紅棍,叫灰哥,黑黑實實,頭髮長長,用刀背拍我三個背脊,點了香,燒了蠟燭,叫我們拜教主。這時秋哥開口唱詩,他唱一句,「義板橋頭過孟君,左銅右鐵不差分,朱家設下洪家過,不過此橋是外人」,我們唱一句。又叫我們發洪門三十六誓「自入洪門之後,爾之父母即我之父母,爾之兄弟姊妹即我
之兄弟姊妹,爾妻我之嫂,爾子我之姪,如有違背,五雷誅滅」「兄弟貨物,不得強買爭奪,如有恃強欺弱者,死在萬刀之下」「立誓傳來有奸忠,四海兄弟一般同,忠心義氣公侯位,奸臣反骨刀下終」。最得人驚是大刀斬雞頭,公雞沒頭,身還在跳,血滴在酒杯,灰哥又燒黃紙,刺我們指頭,滴血入聖杯,一人喝一口,又腥又苦。
我頭暈身熱,幸好飲完血就做完。
大佬叫我們脫下白袍,說,以後大家是兄弟,你們不要成天在酒吧睡覺打啤牌,要出去賣嘢。原來賣那啲「嘢」,是白粉。
─摘自大田出版黃碧雲《烈佬傳》
在車衣位我望著衣車有多久,我都不知。先生叫我,我立即推褲頭入去車,先生說,要見阿一。我說又開邊瓣,我又沒賭錢,火機個個都有,沒理由因個火機召我入房。
第一車衣期成班所員望著我。
入到房我就記得,明天要放我出冊。阿一還是那個大哨,頭髮白了不少,人好像縮小了,沒以前那麼惡死。
他見到我居然笑,說,有個職員來接你,你出去住宿舍。我說,住哪裡都一樣。大哨就說,周未難,你知道嗎,你不知道我提提你,你六十歲了。我說,這又怎樣。大哨說,你自己想,你要怎樣。
每次出冊都急不及待,這一次,我離開阿一間房,行得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