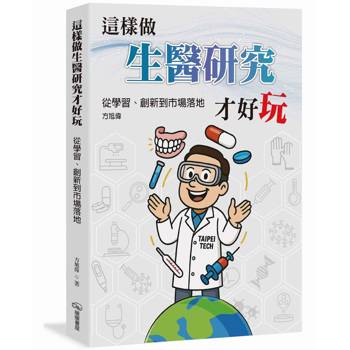在晴空萬里的青春裡翱翔,
在心動不已的戀情裡高飛,
在離情依依的不捨中徘徊,
現在,26篇想念,好像一次告別,
不管是否幸福,我們都曾那麼義無反顧,與快樂。
出版過兩本詩集《下雨的人》《那些最靠近你的》,陳繁齊這次寫散文。他以最習慣抒發原始自我心境的文體,圍繞著詩意旋風,再一次和讀者對話。
陳繁齊2016年在出版浪潮上嶄露頭角,希望未來產量是一年一本的創作,算是對自己的期望。而為什麼是一年?他說:「一年是看見一個人改變的最小單位。一年,不會太細碎,也足以改變。」
只是,這「一年一本」的期許,卻帶來一次無法言喻的衝擊。
交出文稿後,他沒想到被總編輯「退稿」了。他坦言寫了不少,但僅僅只拿出一半的量,竟然就被砍了四分之三……他決定全部重寫。
在重寫的三、四個月裡,他每天下午一點開始,乖乖坐在電腦前,可能發呆什麼都沒做,可能重覆翻著筆記本,或者聽過一張又一張Spotify上的專輯,他強迫自己去面對。
創作的盲點,是一個極具殺傷力的敵人,而陳繁齊遇見了這個敵人,又殺死了這個敵人。
他以為散文就是要詳細描述細節,譬如描寫一本書頁就要極盡所能地描述所有細節──折角、破損、泛黃,甚至書名、頁數。但他忽略了這些細節後面是有情感連結的,於是被打掉重練的這一批文字,他重新挖掘躲在文字後面的那些情感。過去大學時封閉狀態中鉅細靡遺描寫細節的盲點,也並非毫無可取,那些過程等於示現了最原始的陳繁齊。
莫名與淚光,任性與純情,在他的筆下,曾經瘋狂和無端情緒,在時間的滾軸中一一「告別」,回望「告別」,雖然教人感傷,卻隱藏著一種不得不記錄的衝動,於是《風箏落不下來》就成了時光中最深刻的印記。
在這本新書裡,讀到很多句子充滿詩意。陳繁齊在兩種文體之間遊走,彷彿詩與散文的距離,被風化了。
文字成為陳繁齊意想不到的發聲工具,他承認,但用「工具」兩字太冰冷,當他為一些議題或身邊的人事物提出看法與想法時,「感性」是他永遠的功課,而這也終將成為「陳繁齊式」的風格。有讀者說因為他的文字被療癒了,這樣的說法讓他覺得意外也欣喜,向來只是圍繞著自己寫而已,竟也能被他人承接。在某些時候陳繁齊的自卑感,仍令他難以相信自己真的擁有那些能力──治療、理解他人,對他而言,都是人際關係中較為柔軟的體現。
為什麼新書書名叫《風箏落不下來》,一次在回答總編輯的提問時,他說:「風箏可以意指過去的時光,也可以直指思念,或指一種目光、一種因他人而起的改變。 落不下來,大概就是這整本書的書寫狀態。或者說,書寫過程是要讓它落下來。畢竟一起放風箏的人已經不在身邊了。」
我們期待,陳繁齊的文字再一次讓不同世代的讀者,有著溫柔的共鳴,而這共鳴不是要如何定義這位年輕的創作者,而是我們從他的文字中找到了理解的階梯,一步一步理解自己。風箏有一天會落下來,落到我們的心裡。
本書特色
26篇想念 隱藏著生命的詩意
起初只是假裝自己不再需要,
最後卻真的再也不需要了。__〈火柴〉
如果我們沒有約定好不再回頭,
那麼彼此都是不告而別的人。__〈你怎麼就這樣消失了呢?〉
我們就是那麼健忘,
終於修復好的時候,
又忘記殘破的樣子了。__〈易遺忘體質〉
承擔失去後開始越來越老。__〈折舊〉
當你已經跟不上
一個人事物的節奏時。
就會覺得遙遠。__〈距離〉
我始終是一個想太多人的人,從愛一個人開始,
就會假想無情的可能。__〈花〉
那時候,一天是一天,
所有的明天都是從容的。__〈閉館〉
青春是恬不知恥的詞彙,是不容異議的詞彙,
我不應該再使用它。__〈趕路〉
成長是否就是想像本身?__〈不符〉
| FindBook |
有 15 項符合
風箏落不下來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風箏落不下來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繁齊
1993年生,臺北人,國北教語創系畢業。喜歡貓狗、喜歡冬天。喜歡彈吉他自娛、喜歡拍照。著有《下雨的人》、《那些最靠近你的》。
Facebook:陳繁齊
Instagram(writing):dyingintherain
Instagram(album):circa_fc
陳繁齊
1993年生,臺北人,國北教語創系畢業。喜歡貓狗、喜歡冬天。喜歡彈吉他自娛、喜歡拍照。著有《下雨的人》、《那些最靠近你的》。
Facebook:陳繁齊
Instagram(writing):dyingintherain
Instagram(album):circa_fc
目錄
卷一
008 時差
016 距離
028 相似
034 鹿男
044 17
054 花
064 火柴
068 閉館
072 信徒
078 你在聽哪首?
084 你怎麼就這樣消失了呢?
092 易遺忘體質
098 光之死
卷二
108 如何成為一個男生
116 更安全的辦法
120 不符
124 擲
132 趕路
136 起風
144 離家
154 流星
162 晚安
170 年
178 聖誕節之前
182 變少
190 折舊
196 後記
008 時差
016 距離
028 相似
034 鹿男
044 17
054 花
064 火柴
068 閉館
072 信徒
078 你在聽哪首?
084 你怎麼就這樣消失了呢?
092 易遺忘體質
098 光之死
卷二
108 如何成為一個男生
116 更安全的辦法
120 不符
124 擲
132 趕路
136 起風
144 離家
154 流星
162 晚安
170 年
178 聖誕節之前
182 變少
190 折舊
196 後記
序
後記
坐在咖啡廳靠窗的位置,窗外的雨下了又停、又下,像偏執的小孩間歇地發脾氣,屢勸不聽地打翻整缸的水。
我不知道該點熱的還是冰的飲料,大概就如同我無法確定下雨是不是好事。濕漉漉的柏油路面很漂亮,車燈打在地上像碎掉的玻璃瓶,我懷疑那是不是只原本裝著信的玻璃瓶,只是信已經漂走了。
秋天大概就在這種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悄悄死去,九月、十月、十一月,表定的時辰輕易地來了又走。有人說台灣的氣候沒有秋天,有時我倒覺得這座小島的秋天,像緩慢滲血的傷口,在不知覺時滿溢,又在不知覺時復原。
我想起S就是在這個季節,靜靜地捎來一封信。比當時疼惜的心情還要靜。所以我讀完才會知道,我們要回歸無聲了,不再有對話也沒有情緒,沒有為我們喧囂的馬路、也沒有熟稔的服務生宣讀菜單的細條。我們必須讓其他聲音重新加進來,我們必須保持距離,寂靜才有空隙。像是先後乘上不同班的電梯。最後我們一起在酒吧搖頭晃腦,慶賀不合時宜的節日。「你還好嗎?」「沒事,才這點程度。」在數杯酒下肚後,那樣的對話已經趨近我們晦暗的極限。那一年的秋天非常非常短,像是一場未經規劃的夢,或是像一首幾分鐘的情歌,唱完就沒了。在寂靜還沒復原之前,樹就已經光禿,以至於我絲毫沒發現冬天來臨。告別一個人像告別一個季節。
「冬天來了,請你走吧。」
記得有次曾一起步行穿越車水馬龍的大橋,行至中處,S把手機舉得高高的,照了幾張相,回頭看我一臉詫異。「幹嘛?我只是覺得平常住在市區裡,不太有機會看到這麼大片又完整的天空。」S非常珍惜地滑著手機,確保適才的幾張照片沒有拍壞。有一瞬間我以為天空真的變低了,我們都碰得到星星。
從那之後我的手機裡也充滿天空的照片。S教會我在擁擠的街衢裡放隱形的風箏,一直到S已經不在身旁,高處的風還是一直吹著,風箏落不下來,若有似無的釣魚線,持續拉扯著後來的我。
我也想起前年一月夜晚,將N的謊言拆穿後,N在身旁啜泣,我卻一點也不生氣。對不起,我不知道我怎麼了,也許我故障了,或是我執意讓自己故障,諸如那類的話語,從N抽抽噎噎的聲音裡,擠壓出了幾句,水位漸低,水底的凌亂都顯出來。那是很俗濫的公式,我說我理解,雖然我心裡清楚,理解不代表接受,卻別無他法,一個人在憐憫他人之時是最脆弱的。
冬末的氣溫,讓人以為只要足夠溫暖,就能融化一切窒礙。
N說那是善良,我沒有同意,只是將善良和暴露自己的脆弱,畫上等號。那幾年拚了命在理解別人,動機也許來自於彼此無法掌握的變動。像是面對網路世代商家們喜愛的GIF圖片行銷,數十張圖像在幾秒內閃動,我總是很想停在每一張圖上看清楚。我害怕下一秒,這一切就變成截然不同的模樣了。
我還想起更多人,更多像霧的人,他們的身體已經完全逸散,沒有形體,無法被留下。告別一個人可能就是這樣吧,將圍繞著那個人所發生過的事,片片拆下,拆到一片也不剩,拆到他已回歸你最初看過的模樣,甚至拆至已經看不見他,這時候就可以說,我不認識你了。但仍然記得他。記得他的輪廓、語氣、價值觀、小動作,包括天氣、頭頂的音樂、共餐地點的裝潢。因為知道那些獨特都不會再發生了。
只是獨特並不代表永久居留。
「勇敢成為他人的過去,才是個成熟的大人喔!」
—《比海還深》
這陣子我像是走在一棟由記憶築成的大樓,每一個曾經過的人都成了房間,沒有語言也沒有眼神,只剩我偶爾寫信給他們,和他們說話;有時我自己讀自己的信,或僅是獨自進到房裡擦拭灰塵。有時候是生活寄信來了,繁多至塞滿信箱,我不得不去整理,一張張攤開終於都讀懂了,但自己卻又變得難以解釋。
也許這些人與事我還會再提數次,數十次,甚至上百次,但那又怎麼樣呢?每提及一次,都變得更遠一些。我的語氣一直在推送它們,越是想念推得越用力,推到二十五歲的邊緣,有沒有墜落我並不能確定,如果墜落,我必須相信,它們都落到一個很好的地方了。
坐在咖啡廳靠窗的位置,窗外的雨下了又停、又下,像偏執的小孩間歇地發脾氣,屢勸不聽地打翻整缸的水。
我不知道該點熱的還是冰的飲料,大概就如同我無法確定下雨是不是好事。濕漉漉的柏油路面很漂亮,車燈打在地上像碎掉的玻璃瓶,我懷疑那是不是只原本裝著信的玻璃瓶,只是信已經漂走了。
秋天大概就在這種猶豫不決的情況下悄悄死去,九月、十月、十一月,表定的時辰輕易地來了又走。有人說台灣的氣候沒有秋天,有時我倒覺得這座小島的秋天,像緩慢滲血的傷口,在不知覺時滿溢,又在不知覺時復原。
我想起S就是在這個季節,靜靜地捎來一封信。比當時疼惜的心情還要靜。所以我讀完才會知道,我們要回歸無聲了,不再有對話也沒有情緒,沒有為我們喧囂的馬路、也沒有熟稔的服務生宣讀菜單的細條。我們必須讓其他聲音重新加進來,我們必須保持距離,寂靜才有空隙。像是先後乘上不同班的電梯。最後我們一起在酒吧搖頭晃腦,慶賀不合時宜的節日。「你還好嗎?」「沒事,才這點程度。」在數杯酒下肚後,那樣的對話已經趨近我們晦暗的極限。那一年的秋天非常非常短,像是一場未經規劃的夢,或是像一首幾分鐘的情歌,唱完就沒了。在寂靜還沒復原之前,樹就已經光禿,以至於我絲毫沒發現冬天來臨。告別一個人像告別一個季節。
「冬天來了,請你走吧。」
記得有次曾一起步行穿越車水馬龍的大橋,行至中處,S把手機舉得高高的,照了幾張相,回頭看我一臉詫異。「幹嘛?我只是覺得平常住在市區裡,不太有機會看到這麼大片又完整的天空。」S非常珍惜地滑著手機,確保適才的幾張照片沒有拍壞。有一瞬間我以為天空真的變低了,我們都碰得到星星。
從那之後我的手機裡也充滿天空的照片。S教會我在擁擠的街衢裡放隱形的風箏,一直到S已經不在身旁,高處的風還是一直吹著,風箏落不下來,若有似無的釣魚線,持續拉扯著後來的我。
我也想起前年一月夜晚,將N的謊言拆穿後,N在身旁啜泣,我卻一點也不生氣。對不起,我不知道我怎麼了,也許我故障了,或是我執意讓自己故障,諸如那類的話語,從N抽抽噎噎的聲音裡,擠壓出了幾句,水位漸低,水底的凌亂都顯出來。那是很俗濫的公式,我說我理解,雖然我心裡清楚,理解不代表接受,卻別無他法,一個人在憐憫他人之時是最脆弱的。
冬末的氣溫,讓人以為只要足夠溫暖,就能融化一切窒礙。
N說那是善良,我沒有同意,只是將善良和暴露自己的脆弱,畫上等號。那幾年拚了命在理解別人,動機也許來自於彼此無法掌握的變動。像是面對網路世代商家們喜愛的GIF圖片行銷,數十張圖像在幾秒內閃動,我總是很想停在每一張圖上看清楚。我害怕下一秒,這一切就變成截然不同的模樣了。
我還想起更多人,更多像霧的人,他們的身體已經完全逸散,沒有形體,無法被留下。告別一個人可能就是這樣吧,將圍繞著那個人所發生過的事,片片拆下,拆到一片也不剩,拆到他已回歸你最初看過的模樣,甚至拆至已經看不見他,這時候就可以說,我不認識你了。但仍然記得他。記得他的輪廓、語氣、價值觀、小動作,包括天氣、頭頂的音樂、共餐地點的裝潢。因為知道那些獨特都不會再發生了。
只是獨特並不代表永久居留。
「勇敢成為他人的過去,才是個成熟的大人喔!」
—《比海還深》
這陣子我像是走在一棟由記憶築成的大樓,每一個曾經過的人都成了房間,沒有語言也沒有眼神,只剩我偶爾寫信給他們,和他們說話;有時我自己讀自己的信,或僅是獨自進到房裡擦拭灰塵。有時候是生活寄信來了,繁多至塞滿信箱,我不得不去整理,一張張攤開終於都讀懂了,但自己卻又變得難以解釋。
也許這些人與事我還會再提數次,數十次,甚至上百次,但那又怎麼樣呢?每提及一次,都變得更遠一些。我的語氣一直在推送它們,越是想念推得越用力,推到二十五歲的邊緣,有沒有墜落我並不能確定,如果墜落,我必須相信,它們都落到一個很好的地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