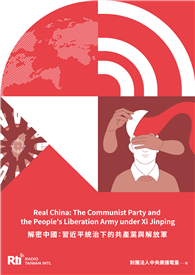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和新井一二三一起讀日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24 |
散文 |
$ 253 |
Books |
$ 272 |
社會人文 |
$ 281 |
中文書 |
$ 282 |
日文 |
$ 282 |
Others |
$ 288 |
文化研究 |
$ 288 |
日本文化/民族 |
$ 28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和新井一二三一起讀日文
我們愛日文,愛日本名詞,愛的就是那熟悉中帶著神祕感的味。
日本名詞,躲著味道。
玉子,春雨,蕎麥,牡丹肉……
可愛優雅的外表下,是樸實的味覺。
日本名詞,收納異國情調。
露西亞,彷彿流轉魚子醬光澤。
南蠻,傳現當年紅毛人的霸氣。
日本名詞,統整群體的憂愁。
就活,婚活,終活;福島,在日,風評被害……
社會現象與災難被語言理解,人心只能循規前進?
那些左右議題的人名,就是名詞。
(木尾)原一騎,上野千鶴子,孫正義,山口百惠,
他們各自代表了一個時代,幾種信念。
漢字中夾雜著平假名與片假名,留下了想像空間,形成獨特美感。
曖昧又美麗的語感,即是日文的魅力。
暫別中文的世界,新井一二三回到自己的母語裡悠遊,
新井一二三的快活,在字裡行間不時俏皮輕鬆的呈現。她說:
歡迎你參加新井一二三日文旅行團。
現在,我們就往日文的知識和感官世界出發啦!
本書特色
春雨≠春天的雨
玉子≠高級的玉石
狐蕎麥、狸烏龍、在日、南蠻……
這些日文漢字的真實意思是甚麼?
作者簡介
新井一二三
生於東京。明治大學理工學院教授。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留學北京外國語學院、廣州中山大學。
任職朝日新聞記者、亞洲週刊(香港)特派員後,躋身為中文專欄作家。
日文作品著有:《中国語はおもしろい》(講談社現代新書)、《中国‧中毒》(三修社)、《中国・台湾・香港映画のなかの日本》 (明治大學出版會,以林一二三之名義)。
中文作品:《心井‧新井》《櫻花寓言》《再見平成時代》《臺灣為何教我哭?》《獨立,從一個人旅行開始》《媽媽其實是皇后的毒蘋果》《我們與台灣的距離》《這一年吃些什麼好?》等三十部作品〈皆由大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