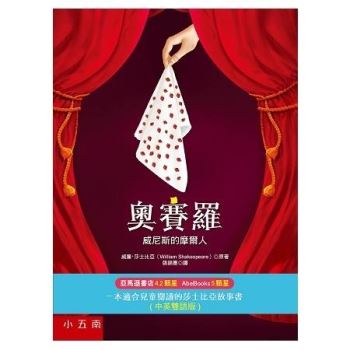第十九屆群像新人獎
第七十五屆芥川龍之介賞
日本銷售超過三百五十萬本
村上龍成名小說!
24歲即奠定大師地位的代表作!
影響日本許多知名作家的驚人之作!
譯者張致斌依據原版重新翻譯的完整正確譯本!
1976年出版立刻引起話題,並獲得日本文壇最高榮譽芥川獎!
你到底是什麼人?
你到底在懼怕什麼?
你是如何變成一具任人玩弄的人偶的呢?
濃烈的感官體驗,狂亂了青春;
脫序的生活,譜成了迷幻的歌;
基地裡那年輕失落的靈魂,
麻痺自己只因不想再感傷,
戲謔人生是為了反抗對他嗤之以鼻的社會。
他其實想化作那出現在黎明時,近乎透明的光暈。
那彷彿能反射出真實的他,無限透明的藍光。
如同詩句韻律般優美起伏的,
接近無限透明的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