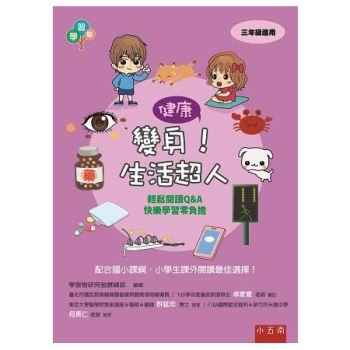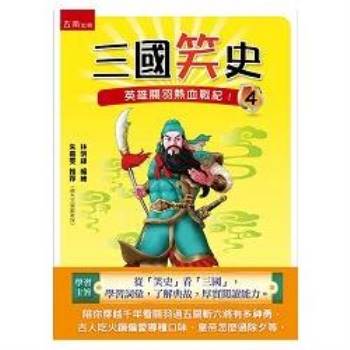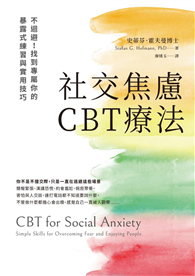1.初秋他們說,再過10天,大片的紅與黃,才是北疆最美的時分。但我猜,無論哪天哪時到,總有甚麼在那裡等著。上弦月的盈滿,就叫上弦月。青黃是有的,但沒有不接。我來,盛滿了眼界與感受;我走,又一層的變幻正要開始。我說,這次,這樣就夠了。初秋的確定,是一片由綠轉黃或轉橙的樹葉,然後兩片、三片、四片�遍紅的那片落下,明天,還有更紅的一片會落下。林葉使勁的黃吧、紅吧,努力的理由,不必是為了滿足旅人的眼,是因著天命。初秋走入喀納斯湖邊的森林,由於燦爛的風華,陽光說:「寧駐青黃一株,勝過綠樹千畝」。
湖邊的枯木說:「我非胡楊,倒下不朽不必一千年。側枕一季的青黃,來年不必有我」。
最西初秋的穿著大致是這樣:天空穿著一身藍,低密度地印著白雲;草原穿著綠衣兩季後,開始泛黃;雪嶺雲杉一身蔥綠,但跟在後頭的白樺樹林,可能整片鵝黃,一陣風吹來,沙沙作響,讓馬客沐浴在千片葉落中;至於旅行的人,白天短衣薄衫,晚上稍涼得添外衣。這個時節,看見最西的甚麼趕時節的,北疆,彩色,是白哈巴村四周山頭的容顏。樹與樹靠得很近,右邊秋黃的樹看著左邊的綠樹,有時以為是自己;但顏色實在分明,相似的,只是一同迎接這個秋天;對,是迎接,沒有擁有。等十月大雪封山後,大家都一樣,只讓白了頭。來到吉力湖邊,一片靜謐無聲,天鵝已在八月走遠,還留在那邊的,只有枯黃蘆葦。天山東路,吐魯番葡萄溝南北八公里,茂密的葡萄葉中,只有幾串果實垂掛。在南疆帕米爾高原,雪山下的青稞田走向金黃;海拔三千五百米的喀拉庫里湖前,柯爾克孜人的氈房還沒撤去,喀湖水色,還隨太陽位置一日三變著。
再說些不變的:孩童,維吾爾的、哈薩克的、圖瓦的、塔吉克的,在烏魯木齊城市巷弄、在喀什高台民居、在吐魯番高昌故城、在喀納斯山區、在烏帕爾鄉巴扎、在塔縣石頭城笑鬧著;鴿子,在喀什老城區日復一日起飛、降落;帕米爾七千米冰山座座,不畏蔥嶺一日九日出,四季猶白著頭;新疆秋冬春夏,流轉更迭著。最西太饒,初秋來到這裡,領略了幾道時節味,留下更多的未嚐。最西太大,短期的旅程望不盡,行止到不了每一個夢繫的地方。罷了,留給往後的拜訪。胡楊,長於沙漠,耐旱。自古即說胡楊「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
2002年開始,每年十月,南疆的輪台縣舉辦塔里木胡楊節,裡頭的重頭戲是攝影大賽,屬於深秋的絕對金黃,是沙漠中最教人動容的活化石。
再說些不變的:孩童,維吾爾的、哈薩克的、圖瓦的、塔吉克的,在烏魯木齊城市巷弄、在喀什高台民居、在吐魯番高昌故城、在喀納斯山區、在烏帕爾鄉巴扎、在塔縣石頭城笑鬧著;鴿子,在喀什老城區日復一日起飛、降落;帕米爾七千米冰山座座,不畏蔥嶺一日九日出,四季猶白著頭;新疆秋冬春夏,流轉更迭著。最西太饒,初秋來到這裡,領略了幾道時節味,留下更多的未嚐。最西太大,短期的旅程望不盡,行止到不了每一個夢繫的地方。罷了,留給往後的拜訪。
9月12日晴/雨,第十一天。原來硬臥也很好眠。 N946是雙層列車,昨天下午準15:51從烏魯木齊開出,我的臥位在10車下層19號下舖。
19號室在這10車的最前頭,旁邊就是可上下的樓梯。這號室人口簡單,非常好,臥位只有單排上下兩個,不像其他號室,一般會有雙排六個。更好的是,遇到曾在喀什度過19個年歲的室友,叫曉瑩,聊得暢快,熱心的她,還介紹了喀什的老同學幫我安排住宿、地陪一程。
10車上,有幾個維族的小孩,大大圓圓的眼睛,光頭的、戴花帽的,很是可愛,時而安靜,時而上下層追逐。通常,這些天使,就是維、漢大人們同室聊天的起點與焦點。一車的維、漢乘客,硬臥無門,在走道上站一會,不用太仔細傾聽,就不難察覺漢族擅喜高談闊論,而維族大部分時刻,則傾向安靜,即使交談,也是聲音壓低。
「小伙子,把那圓圓的日出給拍起來」,日出時分,走道上我拿著相機,在走道壁椅坐著的大叔喊我。
「不好拍,大…叔」。
倒是維族小花帽夏熱帕,先是自然揉眼,而後在媽媽指導之下,擺了微笑、歪頭、吐舌的姿態,在晨光穿透的走道邊,留下幾幅童真的模樣。對照著烏市買來的新疆交通圖冊,在札記本畫出:烏市→(236)吐魯番→(380)庫爾勒→(541)阿克蘇→(442)阿圖什→(34)喀什絲路中道,公路里程全長1633公里,而鐵路大致是跟這些串聯的公路平行的,火車以平均70公里的時速前進著。阿克蘇到了,曉瑩此行出差,下車即開工,臨走前,至性盛情,留了內蒙製的香酥饃片、西域春牛奶、梨、蘋果給我,說是難得遇到台灣同胞,相談愉快。欣然接受,足不出室,也就是一餐了。遇到一匹馬,牠也對我凝視,眼神說著:這裡不是我的家,旅人來到這裡的時候,沒有風,我也沒有為你奔馳一場,所以揚不起一點風沙。我隨鏡頭而凝視,就說是朋友,太輕易;你走了,還有我留下。額爾濟斯河/布爾津段額爾濟斯河,是中國唯一流向北極冰洋的西向長河,進出喀納斯咽喉、北疆要地布爾津,額爾濟斯河,是必然的觸動。在初秋落日時分,車子特意停在布爾津橋前,讓旅人步行過橋。凝視東邊,一波不興,整城落入墨的休靜。過客帶來的旅情騷意,連樹葉一片也不能擾動;凝視西邊,「遠樹帶行客,孤城當落暉,吾謀適不用,勿謂知音稀」,摩詰先生,你一千二百五十年前見容的「長河落日圓」,我今日也看到了。額爾濟斯若黃河,一向北,一向東,日落皆有圓。一條長河,千里落日。如果水靜止了,日會停下沉入的腳步嗎旅人縱使在水面上以突破音障的速度狂奔,亦不能抵禦光線的消褪。精神矍爍的圖瓦老奶奶招我們進屋,給了 Steven一塊乳白的酸羊奶酪,他嚐了一口,扒下一半給 Tony; Tony接過後,也嚐了一口,又扒下一半給我;照例,我嚐了一口,又扒下一半,但那八分之一塊,不知要遞給誰眼光巡弋著, Jason竟一個人吃完一整塊。要跟圖瓦成一家親,也不用這麼盛情吧啟程之前,對於最西的飲食印象是這樣的:各邊疆民族大多信奉伊斯蘭教(回教),所以除非找著漢餐館,否則最好將大肉(豬肉)暫時忘卻。肉食以羊、牛、雞為主,尤其是羊,做成餡,是羊肉包子;鐵條串起五、六塊,灑上孜然,是烤羊肉串;現擀麵條炒上洋蔥、各式的椒,是過油拌麵,羊肉的最對味;抹上鹽,掛在山區的氈房前,是風乾中的羊肉;整隻香脆金黃,那是烤全羊。還有多達五十幾種樣式的饢,聽說不小心吃上一個,足以飽上一整天。大盤雞料好汁開胃,幾碗飯很容易送服下肚。從最西回來,台北幾家新疆風味的餐館再嚐過,終於知道,那是讓無緣親身帶舌到最西的人臨摹用的。總之,想像成就美好,地道不必計較。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最西‧新疆記憶的圖書 |
 |
最西.新疆記憶XINJIANG-嬉.生活011 作者:蔣居裕 出版社:高寶 出版日期:2006-01-03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76頁 / 16.5*20. / 普級 / 全彩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29 |
社會人文 |
$ 247 |
中國遊記 |
$ 255 |
中文書 |
$ 255 |
中國歷史 |
$ 261 |
中國遊記 |
$ 261 |
中國 |
$ 261 |
亞洲旅遊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最西‧新疆記憶
一塊佔了中國六分之一的西域疆土,可以充滿多少想像歐陽峰說:「我只是想知道,沙漠的後面是甚麼」我也想知道。西邊的沙漠即使沒有傳來駝鈴聲,一樣能輕易引領旅人進入純粹的境界……不出陽關,不覺天地之悠遠不到新疆,不知中國之遼闊沙漠的背後究竟是什麼最西的天使究竟在哪裡新疆有全中國最大的沙漠;全中國最熱的地方;全世界離海最遠的城市;全世界最長的沙漠公路……;還有壯麗的高原、雪山、湖泊。這些,都只是新疆吸引人的其中部分。說人,那歷史承載的神秘面紗,古樸的老城面貌,豪邁好客的塞外民族;說景,那綺麗萬千的天地色彩,如纖波列的細沙,日落餘暉不盡的長河;說物,那粗曠飲食與甜美瓜果:過油拌麵配大盤雞,餐後再剖大紅西瓜。在眼裡、心底,在鏡頭下的最西,閃耀著無比風華,令人凝視、況味,久久無法忘懷。新疆中國之最‧面積最大的省區‧對外開放山峰最多的省區‧航線最長、航站最多的省區‧鄰國最多、邊境線最長的省區‧最低的陸地‧最長的內陸河‧最大的內陸盆地‧最大的內陸淡水湖‧最大的自然保護區‧最大的天然胡楊林‧最大的冰川‧最深的凍土層‧最多晴天的地方‧最長的地下灌溉系統‧最早的石窟寺
作者簡介:
蔣居裕,1969年生於高雄小港,現居淡水。喜歡讀字、寫字,在城市中習以捷運擺渡,總能找到安靜的一角看書。現任台灣某軟體公司行銷長,十五年的軟體產業理性生涯,一輩子的感性恣意生命。在旅行中內在敏感參詳,外在奮勇交流,足跡踏過希臘、西班牙、美國、中國(北京、上海、武漢、雲南、青島、濟南、新疆)。個人網站http://www.fred.idv.tw。
章節試閱
1.初秋他們說,再過10天,大片的紅與黃,才是北疆最美的時分。但我猜,無論哪天哪時到,總有甚麼在那裡等著。上弦月的盈滿,就叫上弦月。青黃是有的,但沒有不接。我來,盛滿了眼界與感受;我走,又一層的變幻正要開始。我說,這次,這樣就夠了。初秋的確定,是一片由綠轉黃或轉橙的樹葉,然後兩片、三片、四片�遍紅的那片落下,明天,還有更紅的一片會落下。林葉使勁的黃吧、紅吧,努力的理由,不必是為了滿足旅人的眼,是因著天命。初秋走入喀納斯湖邊的森林,由於燦爛的風華,陽光說:「寧駐青黃一株,勝過綠樹千畝」。
湖邊的枯木說:...
湖邊的枯木說:...
»看全部
目錄
一、 前言
二、 行止‧初秋‧北疆‧南疆
三、 記憶‧凝視‧況味‧渡沙‧侶遊‧日原‧天使‧老城‧清真‧口腹
四、 尾聲
五、 附錄 ‧新疆地圖‧交通安排‧我的整備‧我的資訊‧預約下次的行程
六、 索引
商品資料
- 作者: 蔣居裕
- 出版社: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出版日期:2007-01-04 ISBN/ISSN:9861850244
-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6頁
- 類別: 中文書> 歷史地理> 中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