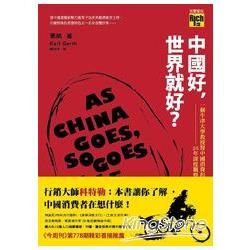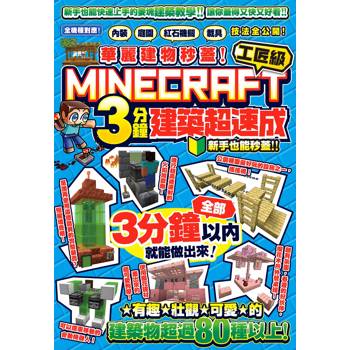十幾年前,有很多臺灣人跟中國人會問我:「你為什麼對亞洲感興趣?令尊是生意人?政府官員?還是祖母是傳教士?」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很少問我這類問題。因為美國的中國熱就跟一九八○年代吹起日本風一樣,這些對異國有興趣的美國人多想從中尋求商機,或是為事業鋪路。不過我並不是因為這些原因才來研究中國歷史。當時(一九八五年)我還是一個懷抱理想主義的年輕小伙子,中國也不像現在那樣富強!
從小我就愛看《星際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在《星際大戰》首部曲的最後,天行者路克(Luke Skywalker)成功摧毀銀河帝國的「死星」。但是二部曲一開始,大家就會發現死星並沒有被徹底摧毀,只是多了一個大洞,呈現出一個只有三分之一的星球,這個不完整的世界景象深深烙印在我心裡。
上大學的時候,我開始學習了解整個世界,我突然領悟到,原來我對這個世界一知半解,跟沒被徹底摧毀的死星一樣不完整。於是,我想辦法填補心智世界中不見的那三分之一。
我在一九七○、八○年代的冷戰期間成長,在那時我不記得自己學到什麼跟中國有關的事,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當我還是青少年時,雷根總統把蘇聯說成是「邪惡帝國」(the Evil Empire),叛逆的我對於年長當權者說的任何「邪惡」事物都很有興趣!而且學校告訴我們,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死對頭,我想了解跟自己所知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我最先研究的國家是蘇聯。但是在整個暑假浸淫書海後,我得到一個結論:蘇聯跟歐洲其它國家很像,是歐洲內部一個派系,並不是一個徹底相反的世界,而且那時我再也不相信冷戰宣傳,不相信正邪兩立的說法。所以,我繼續尋找遺失的部分世界。
很幸運的是,我在芝加哥附近的大學城長大,那裡書店林立,還有一間擁有豐富中國相關書籍的書店,我曾經花整個下午的時間瀏覽這間書店的每個角落,這些角落讓我更加感受到自己有多麼無知。不論是對中國歷史,還是中國武術,我都一無所知,我也沒聽過唐詩或看過青銅時代的禮器,更沒讀過中國小說,像是《紅樓夢》,也應該沒吃過中國菜。而且,我跟許多老美一樣,連「臺灣」跟「泰國」都分不清楚!
我決定從上下二冊的中國哲學英譯本開始研究,我念到的第一句話是:「道可道,非常道」!我當下為之懾服。對懷抱理想主義的學生來說,這類閱讀是不可多得的心靈慰藉。我還買了一本小冊子,開始學習中文。暑假過後回到學校,有次在學校看電影,我發現自己坐在一名中國學生旁邊(我們學校的中國學生寥寥無幾)。我小聲跟他說:「我信道教,你也是嗎?」我很自豪自己竟然知道「道教」。那名中國學生很有禮貌,只是對我微笑。
幸運的是,那年我念的大學開辦中文課,我成為第一批選修中文的學生,我必須先在學校學一年中文,才有資格交換學生到中國唸書。隔年,我如願前往南京大學唸一學期的書,然後再到北京大學念完另一學期。
當時,我有兩個室友,其中一個是中國人。現在我終於可以找中國同學問相同的問題了,「你是道教徒嗎?」,而我也的確這麼做了。我的室友王建寧思想開放,也和我一樣懷抱理想主義,他熱心回答我所有的問題。有些老外抱怨中國人老是問一些不該問的問題,好比說:你結婚了嗎?有小孩嗎?賺多少錢?等等。但這正是我特別喜歡中國的一個原因,這表示我也能拿任何問題問他們。可是,他們給我的答案反而讓我產生更多的問題,中國老是讓人有這樣的感覺。我指導教授的老師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自傳中寫到,了解中國就像了解一個不斷擴大的圓圈,圓圈裡面是對中國的了解,圓圈外面是對中國的疑問:了解中國愈多,疑問就會愈多,也就明白自己對中國了解不多。二十五年前王建寧教我「難得糊塗」這個詞或許就能說明這件事。研究中文讓人變得謙虛,因為我的心智世界有好多「坑洞」有待填補。
我很天真,以為在中國念一年書就能把中文學好,然後就能繼續進行拼湊完整世界的夢想。現在,我還在拼湊我心中那個地球。要學好中文,一年的時間當然不夠(我已經花了二十五年),除非把中文學好,否則我不打算回美國完成大學學業。可是我沒有錢。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在一九八○年代,外國學生可以到臺灣教英文過活。所以我到臺灣教了一年英文,再繼續學業。這段期間我又回中國旅遊幾次,幾乎遊遍中國大江南北。我親眼看到發生巨大改變前的中國,讓我得以比較對過去與現在的中國到底有何改變,這也是我想要在這本書告訴讀者的事。我還記得雲南陽朔和麗江還沒成為中產階級度假勝地的景象。一九八○年代,那些是很難抵達的偏遠村落,除了享受與世隔絕的寧靜和夜晚星空外,實在沒有什麼事情可做。
後來我進了研究所,選了適合自己的哈佛大學。以我教學的牛津大學來說,我們會希望研究生在入學時都能清楚自己想研究的主題。不過,我剛進哈佛大學念研究所時,我沒有任何一點明確想法。但是指導教授孔復禮(Philip Kuhn)和柯偉林(William Kirby)很支持我,也很信任我做自己想做的研究。從蒙古帝國到毛澤東時期的中國史我都研究過,不像大多數同學都對傳統史學主題比較有興趣(像是研究總理衙門這類的機構史),我卻對中國城市的社經生活比較有興趣,指導教授也允許我依照自己的興趣做研究,這讓我由衷地感激。這也是為什麼我每年會捐款回饋這間全球最有錢的大學。
我的博士論文最後成為我的第一本書《製造中國:消費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創建》(China Made: Consumer Cultu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Nation),我引以為傲,這是我花了將近十年的嘔心瀝血之作。我走訪中國、臺灣和日本的史料保存處。中譯本的問世更讓我感到自豪,感謝中國清華大學傑出學者黃振萍翻譯這本書。也許有一天,英文會像現在的法文一樣,中文會像現在的英文一樣,變成最重要的世界語言,所以我也感謝臺灣譯者陳琇玲小姐,讓這本書得以用新世界語言跟廣大讀者見面。
我本來沒打算寫《中國好,世界就好?》這本書,而想寫一本探討中國自一九○○年以來消費主義的學術著作。通常,史學家從古代開始研究,並提筆論述,但是我決定以當代為起點,先思索現在什麼問題最重要,決定問題後再開始回溯歷史。我也碰到所有學者最常碰到的一個問題:對於中國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發展,我有太多話要說。所以,我打消撰寫學術著作的念頭。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本書主題很重要,也希望寫一本不那麼學術、對更多人有益的書。
我在這本書的〈結論〉提出非常重要的要點,基於不同的理由,我要在此說明。這本書大多引用中國的資料和中國人的說法,我向美國讀者提出這一點是要讓他們知道,許多中國人都清楚本書所探討的問題有多嚴重和複雜;我在繁體中文版作者序中提及此事,則是要提醒讀者,本書的內容不是一位外籍人士的胡亂推理及奇怪看法。相反的,我認為因為我是外籍人士,所以有旁觀者清的優勢,能夠看到更全面的關聯性,畢竟身在其中就有見樹不見林的盲點。
我很慶幸自己花二十五年時間遊遍中國和臺灣,並進行研究,我曾以傅爾布萊特學者的身分在臺灣大學當過一年客座教授。跟東亞人一樣,東亞地區的生活有時讓人疲憊受挫,但卻一點也不無聊。我想我跟其他外籍人士一樣,也希望自己待在中國和臺灣時能有所獲,從二十五年的歲月中獲得啟發。我認為要求或指望中國解決這本書裡提出的問題並不公平:中國如何在不讓全球問題惡化的情況下,享受這幾十年來個人、家族和國家以種種犧牲換來的成果?有時我不禁這麼想:中國人為什麼必須幫忙收拾其它國家製造的麻煩?但是,如同臺灣人曾協助中國建立消費文化一樣,我希望臺灣人也能再次出手相助,創造一個讓我跟全世界都刮目相看的中國。
葛凱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