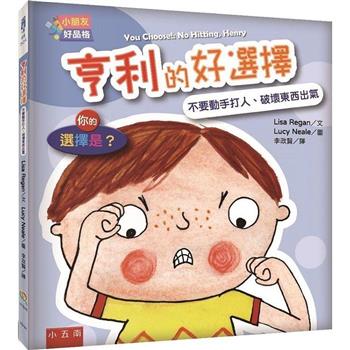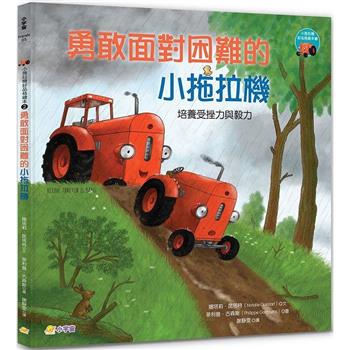序幕
她要在釣鉤上,把愛情的香餌偷食。
既是仇人,他無法能像情人一般向她海誓山盟的獻媚。
她同樣的情深。
可是更感困難,無處去和她的新歡幽會。
兩方仇視的家族成員,絕不可能在一起。
摘自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二幕‧序詩(8-12)。
教宗廳的秩序亂成一團。
芬徹城內居然發生這類褻瀆教義的事情,這對於兼任教宗的皮斯伯爵而言或許不算什麼危機,但對於立足於大陸上的芬徹來說,事態實在是過於嚴重了。
也因此,駐芬徹的主教開始過問這個月發生的事情。
然而,繼上次的殺人行動已經過了兩周,那神秘的黑影就像是人間蒸發了一樣,沉寂無蹤,芬徹街上又回復了興興向榮的景象,各式攤販及店家,也像是沒發生事情般依舊致力營生。
一切如昔。
至於那黑影為什麼沒有再殺人了?
不論教宗廳的哪位主教都無法推測對方的行動,光是交頭接耳地爭論,到底也沒個準確的答案。
不過,至少他們知道了一件事,那便是當教宗開始行動之時,那黑影立刻也停止了殺人。
時機點確實很巧。
但說是單純的巧合,似乎又太過火了。
所以為了查證時間點,芬徹議會立刻召回了夏依,登臺進行報告。
夏依在議會上表示,最後的受害者出現時,皮斯伯爵立刻在城內發布了緊急戒嚴,透過密集的巡邏,讓黑影的行蹤能在每半刻鐘內就被回報一次。
「當然,這也必須是在黑影露面的條件下,才能實行的防禦措施。」夏依輕描淡寫地解釋,又簡單地闡明了相關防務的部屬。
透過這段報告,議會也總算勉強得到了唯一能確認的情報。只不過光是這樣,還是無法滿足這群噬血的豺狼,弭平那些嚴苛的審問與批判。
「那道黑影是城內的人。」芬徹議會裡頭,加斯羅德議長首先開炮,態度悍然而且堅持己見。
「我說了好幾次了,議長。絕不可能是城內的人!」夏依不卑不亢地提出辯駁。
深知對方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強硬,無非也就是「不讓大陸議會知道這件事」的理由,她也只能選擇隱忍。
一時,此起彼落的議論聲交雜而起。
四面環繞連綿,每一面至少有四、五階都坐滿了人的長桌一陣騷動,議會上的秩序可以說是蕩然無存。
而加斯羅德緊盯著夏依,銳利而深沉的目光彷彿能劃開一早瀰漫灰塵的空氣,將臺上的夏依狠狠地印在瞳孔上。
「年輕的行政事務官,我相信妳也知道緊急戒備動用的,是戰爭用的軍隊,如果不是城內的人,根本無法立刻知道的。」
以一種咄咄逼人的傲慢,他冷冷地詰問道:「伯爵下了令,如果黑影還是殺了人,那自然能證明他是個外來者,但他沒那麼做,這就不免讓人懷疑城內出了叛亂份子,或者……我想,會清楚緊急戒嚴的程序的,只有近衛隊、軍隊,以及一定權力的人吧?」
加斯羅德的指控,很明顯地就是企圖給予夏依壓力,藉著讓夏依認為「自己被指控為黑影」,想讓她因為害怕而露出馬腳,變得無所遁形。
當然事實上,也的確對她抱持著懷疑。
但,夏依畢竟是皮斯伯爵的心腹。
對此,親教宗派的議員自然不會悶聲不吭,立刻就進行了反擊。
一時,吵雜的漫罵沓然而起,讓夏依的耳根片刻也得不到清靜。
這幾周,光是應付教宗廳的主教們就已耗費她不少精力,還得來議會報告,面對「鬼議長」加斯羅德……他那咄咄逼人的口氣以及石像般的僵臉,實在是太符合這綽號了。
夏依暗暗在心底嘲諷。
「沒話說了?還是等著要被撤職?我記得妳父親可沒這麼軟弱!」面對她的緘默,加德羅斯冷笑:「我早向皮斯說過別讓個沒用的毛丫頭繼任事務官,可那傢伙死都不聽,實在是咎由自取!」
「很抱歉沒逮住兇犯,但是議長……」
「拿妳道歉的口水去跟皮斯討安慰吧!小女孩。」加德羅斯冷喝。
夏依低著頭,暗自慶幸議會桌前有做遮蔽設計,擋住了她握緊而陷入肉內的手。
她知道對方決不好惹,儘管懊惱與憤怒各種情緒竄上心頭,但也只能咬牙忍下。她深吸了口氣,試圖再為自己提出辯駁。
而就在這時,門外的衛兵一臉驚恐地奪門而入。
「放肆!」加斯羅德厲聲怒斥,臉色如地獄修羅般可怕。
議會在進行重大決議,也就是外界所稱的「閉門會議」之時,是不允許閒雜人等任意闖入干擾的,這名衛兵的行徑,等於是直接衝撞議會羞辱了議會的權威。
然而,面對加斯羅德的憤怒,那名衛兵只是一個勁地嚷嚷著:「骸骨……骸骨之鳥……議長!議長!伯爵宅邸裡的骸骨之鳥動起來了!」
「那又如何?」加斯羅德眼神如刀,仍是一臉鎮靜。
其他在場的議員們卻同時色變,不論是親教宗或是親議長,不管哪派的臉上,都不約而同多露出了幾分驚恐之色。
那衛兵吞了下猶豫的口水,想繼續接著說,但就在這時,轟然震耳的雜音冷不防蓋過了他的聲音。
只見議會堂的拱頂像是遭逢了地震,先是幾根飾柱,隨即裂痕延展,分成好幾塊巨石跟著落下,將桌椅砸了粉碎,一時,原本就秩序混亂的議場更加失序,議員們到處閃避,有些甚至不顧「閉門會議」直接奪門而出,為了逃命,甚至連情勢也不管了。
「什麼玩意兒……這玩意兒竟然會動?」加斯羅德沒有逃跑,順勢退到了角落。
而夏依同樣不敢置信地看著從壯麗拱頂的裂痕中,像是根縫衣針般貫穿而入的巨喙,雖然,大陸上的確還有活著骸骨之鳥存在,但伯爵宅邸裡的那隻不過是展示品的死物,居然在這個時刻又復活了?
夏依還來不及細想,骸骨之鳥的巨翅轟然振垮了拱頂,她幾乎是第一時間護著議長,躲開持續落下的碎石。
「議長,沒事嗎?」拔劍做出防衛姿勢,夏依頭也不回地問被她護在劍圍內的加斯羅德。
雖然放著這討厭的傢伙不管的話,搞不好以後都不用再來聽審受拷問了,不過,這可不行。類似像這樣的玩笑話,夏依也只能悶在心裡。
「還好……」加德羅斯拉起斗篷擋住瀰漫的煙塵,漠然看著夏依,「這玩意兒到底是什麼?妳難道不知道牠是活的嗎?」
……怎麼可能會知道?
對加德羅斯愚蠢的提問不予理會,夏依逕自揮開了四周濃厚的幾層灰塵,小心翼翼地越過腳下斑駁、雜亂的碎石堆,利用滑步緩緩地靠近骸骨之鳥。
此時,骸骨之鳥雙眼的窟窿就像鑲了顆朱紅寶石般變得鮮艷發亮,血紅色的眼孔盯著夏依不動,兀自甩動空空如也的身體,做著整理羽毛的動作。
明沒有羽毛,它卻煞有其事地彎下頭、動著鳥喙仔細梳理,這情況在夏依看來,非常滑稽。
忍著笑意,她面無表情地再向前滑動幾步。
骸骨之鳥立刻抬起頭瞪視著她,接著出乎意料地,就像是望見老朋友般縮起身體,如木柴細小的雙肢跪臥下地。
「你……」夏依看出來了,牠是在向自己行「希德教派」的禮儀,不由滿腹疑問。
那骸骨之鳥自然不會應答。
牠只是張開了喙,從嘴巴裡吐出了一本牛皮紙書頁裝訂的泛黃書冊。
「去把那東西取回瞧瞧。」骸骨之鳥昂著頭,眼神彷彿這麼告訴夏依。
夏依看了加斯羅德一眼,再次確認骸骨之鳥對自己沒有敵意後,收回劍,不疑有他地走了過去,將那本子拿起。
陡然,一股溢滿悲傷的鳴叫從那沒有內在的骨骼間,完成了任務的骸骨之鳥展開沒了羽毛的翅膀,從巨大的破洞中飛向天空,只留下這本堪舊的本子。
夏依拍拍上頭的塵埃,望著書封上的文字──骸骨之鳥/凱特妮‧德莫格。
是本不見經傳的歌劇,但著作人的名字在這片大陸上卻是如雷貫耳──初代的紅髮女巫,凱特妮。
第一章 沉睡在記憶裡的故事
在這之前,普羅亞並不是這副模樣的……
長著一頭烏黑細髮、鼻頭隱隱沾上了塵埃的少年,茫然地環顧著灰壁砌成的屋子裡,再低頭看了看長期搬動石塊而長滿了厚實皮繭的雙手,緊緊地抓牢了手上破損、老舊的陶碗。
普羅亞只是塊小土。
然而,面對存在百年以上的三大領地卻自有一套治理策略。
賴生於這塊土地上的平民們透過制定的制度分配了財產,而後,開始為拓展土地而持續向外斡旋,不斷把邊境越來越往外推移,一方面不斷進行各種建設,一方面也必須與四周的領地展開零星衝突。
這是必然的過程。
凡是想要生活過得更加幸福或得更多安穩,就免不了必須經歷各種的磨合與抗爭。生活在普羅亞這塊土地上的人們都不懼犧牲,更相信自己的努力是為了收穫更豐盛的未來。
然而這些,也這不過就是幾年前才有的榮景。
現在的普羅亞,早已成為貴族們盲目剝削與鬥爭之下的犧牲品。
以「自由是建立在擁有資本的前提下」為號召,上層的貴族們聚集了無數的平民志願者,大肆往領地外圍進行了開墾。數百家庭在豔陽底下耕耘,汗水成為了土壤的肥沃養分,在細小的循環中持續擴展普羅亞的勢力。
然而,似這種只為了成就家族利益而進行擴展的領地拓張,在上層貴族之間各種利益算計與內耗鬥爭下,越漸紛亂,完全毫無向心力可言,根本無法與外圍其他的領地作抗衡,再加上領地擁有者的家族只要略一式微,就會毫不猶豫地採取殺雞取卵的手段,榨乾所屬領地的最後一分資源後,立即捨棄領地斷尾求生,而被遺留下的平民們失去貴族支援,只能臨近強權的侵襲下苟延圖強。
於是,平民們舉起耕鋤當作武器進行反抗。
而諷刺的是,貴族們的軍隊卻變本加厲地肆虐於普羅亞中央。
不斷的鬥爭、持續的內耗,伴隨著變本加厲的盤剝,瀰漫覆蓋了這塊原本豐饒美好的土地好幾年,而早時的榮景,早已在戰火與絕望下燒成灰燼了……
不該是這樣子的……
少年心想,眼神除了忙然更多了不符年齡的困乏。
「今天看起來沒什麼元氣啊……兒子。」坐在餐桌對面的男人放下碗,眼神關切地望著少年。
他是少年的父親。
雖然那不過是個「稱謂」,他說穿了也不過就是與那少年一起生活的一名男性,但少年的確是從小就只叫他「父親」。他們是兩個沒有名字的人,僅僅以「父親」與「兒子」作為代稱罷了。
至於少年的母親,說起來就更沒什麼了……
在少年的腳還不能站穩、記憶最模糊的年歲時,那個他該叫做「母親」的女人,就在普羅亞的某場抗爭中因遭到貴族鎮壓而犧牲了。當時,每天在替貴族建造的建築擔任搬運工的父親,在貴族的壓迫下除了多挨上幾鞭,哪有力反抗?!
除了把自己淌進一場渾水中,想救起男人的妻子、少年的母親,說什麼也是辦不到的吧……這點,少年非常清楚。
總之對他而言,母親就是個可有可無的存在。偶爾在某些時刻,某些想像中的畫面隨著某種窒咽的情緒冒出,也就像突然從灰土裡探出頭的老鼠,根本就沒什麼重要的,只要幾個深呼吸後,他就不會再去理睬。
對少年來說就是如此,對那個他叫做「父親」的男人想必也是。
然而,或許是內心仍不免有一絲寂寞之感,少年對於女性的嚮往,隨著歲數增長而漸強。母親的縮影,彷彿就在他身邊。
男人自顧自地絮絮叨叨著。
而少年始終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地低著頭。
男人倦怠的眼神多了分苦悶,正要抱怨,一道鮮豔的聲音輕輕替代了少年開口: 「叔叔,今天的工作可比平常還多啊!您不能這麼說他。」
除了少年與中年男性外,裂出幾條縫的餐桌上還坐著第三人,一名荳蔻年華的小姑娘,算得上姣好的笑靨,在環繞的灰壁映襯下顯得格外很搶眼。
她名叫艾希蒂,在出生的時候便失去了雙親。
只不過她的景況,比少年更加悽慘。
少年出生時,看到的至少是雙親的面孔,而她打從出生第一眼開始,看到的就是雙親的屍體,感受到的便是赤裸裸、猙獰的死亡。
她恰好在母親慘遭貴族軍隊刑求之時被產下,又巧合剛剛在那堆屍體聚集一起,就要一把火燒掉之時,意外讓少年的父親發現,悄悄救下。
她活了下來,與她兩名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莞爾微笑,她探手摸索著端起男人放下的碗,熟練地添上一勺清湯。
男人張了張嘴,終究是沒說什麼,接過碗,只說了句:「他老是和妳鬼混,當然會不專心!力氣也跟著使不出……再這麼下去的話,萬一……」
艾希蒂眨了眨眼,也不反駁。
少年抬起頭,看著自己的父親。
「好吧,我懶得再多說什麼……」男人呼嚕嚕,放下碗,起身離開餐桌,「今天輪到我去上工,你們兩個自己在家小心點,出門時,記著千萬別招惹軍隊。」
「好。」 少年首度給了回應,與艾希蒂同聲說道。
男人含含糊糊地又講了幾句話,抱怨著住屋的狹小與年久失修,而後戴上毛帽,打開木門走出後,抬腳踢上,在寒冷的冬雪紛飛下隱沒了背影。
「今日是輪到伯父去上工,我們應該能獨處好一陣子了吧?」
聽著門砰一聲被關上後,艾希蒂偏頭朝少年笑了笑。
「是啊,不過要做些什麼呢?」少年收回看著窗沿的視線,轉過頭看著艾希蒂。
她的頭髮,是稀有的紅色,在普羅亞的住民中非常特別,彷彿是一群野草中滋長著一朵紅色的鮮花,高貴又有氣質。
然而,她那雙橙色像是燃燒火焰的瞳孔卻沒有焦距。
她沒有視力。
因生母長期地被貴族軍隊壓榨,產下她時又不慎壓到了眼球,她的眼瞳,總是目視著別的地方,雖然聲音代替了眼睛,可以讓人發現她到底對誰說話,住在少年家中一段時間後,也沒有當時那種扭曲的目光,但,艾希蒂就是個天生的瞎子,自從在屍體堆內被救出來時便已注定是如此。
「如果妳的眼睛不會痛的話,那,要不要站起來走動、走動?」少年望著那雙沒有焦距的眼睛,神情說不出的溫柔。
「好啊,要到哪裡呢?」艾希蒂笑著反問。
「到這來吧……妳應該會想更盡情地觸摸這世界吧。」少年牽過她的手,來到窗前。
儘管四面垣璧,簡陋的灰磚屋還是砌出了一扇窗。窗外景緻雪白如洗,跟艾希蒂那沒有任何髒污的皮膚非常搭襯。
「妳一直想看雪吧?」少年由衷想著,牽引著她的手探出那隔絕一方天地,小小的、四方的框,「雖然父親老叫我別讓妳露臉,要是知道我讓妳露臉,恐怕會把我打個半死,不過,我還是想讓妳知道外頭真正的世界。」。
這是他心中早就有的想法,只是遲遲卻未能付諸行動。
在普羅亞中,沒有勞動能力的男性平民,只能被當作奴隸,而女人……在貴族強權統治下的普羅亞淪為玩物,更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了。
但少年父子倆,都不忍心讓無法窺見光明的艾希蒂再受到如此的污辱。
少年的父親,或許是出於當時只能眼看著妻子被凌虐致死,即使咬破嘴唇,流出的鮮血落在雪地上綿延,也救不回妻子的悔恨,而少年則是把她看作妹妹,或許還有更深的意涵,也有可能是日子久了產生愛慕……不管是為了哪個原因,他父子倆都格外珍惜這個從劫後餘生的災難中誕生的少女。
所以,不是不知道艾希蒂對於自由的渴望,但除了藏匿,再也沒有更安全的方法。
眼盲的艾希蒂,絕可能讓別人發現她的存在。
「這就是雪啊……好冷!」艾希蒂好奇地瞠圓了眼睛,口中呼出一道白色的霧氣,「原來所謂的雪,是這樣冰冷呢!」
「嗯,普羅亞一年中有三季都在冰雪覆蓋之下,妳是第一次見到,我跟父親早就習以為常了。」少年湊到艾希蒂旁邊,與她一同從窗框中探出頭,望著四季中有大半時間都處在冰雪中的家鄉。
雖然窗戶只拉開了一半,但刺骨的寒意使得他們不自覺蜷縮著身體。艾希蒂探著手尋找少年的方位,冰涼的掌心貼上他的臉頰,「即使有觸覺,卻全沒有實際的印象,我沒有辦法感受活著。如果能出去就好了,我想再多觸摸一些、多一點感受的話,或許,我還有依靠觸覺活下去的動力。」
持續落飛的白雪,像是夏天的蝴蝶輕舞飄在她的手上、鼻頭上。雪的溫度慢慢地加寒,但艾希蒂卻不感到冷。
對她而言,溫度,或許是她認識這世界的唯一方法了。既使什麼也看不到,純淨的雪落在她手心時,彷彿就會與皮膚一起融化似的觸感,。
「看不見,或許也不是什麼壞事。」沉默了良久,他幾不可聞地說道。
現在的普羅亞,根本不值得去記住,更不值得當作故鄉一樣深深留戀。上層的貴族們實在太殘暴了,只知道利用平民的窮困造就自己家族的利益,平民們越是為了幸福而拼命去努力,積累的財富就越是導引出貴族們無窮的欲望。
到頭來所謂的平等,終究變成了高壓統治。
他們太容易相信號召,卻沒想到未來會變成這樣諷刺的景況,只不過是被利用,卻要為了連鋤頭都拿不動、只會不斷剝削、掠奪他們的貴族去做苦役。
對此,少年老早已積累了不少怨氣。
不只是他,整塊普羅亞的領轄中都是如此。
但,卻沒有半個人敢反抗。
一念及此,少年整個人沉寂了下來。
他不說話,艾希蒂也只是靜靜地靠著他。
她沒告訴少年的是,雖然她根本分不清楚四季,但普羅亞在她心中卻是四季如夏。原因不是她看不見,而是因為他身邊有著熱情如夏的少年父子。
為了養活沒有血緣的她,父子倆窮盡了心力,努力地籌措著她的醫藥費以及多出的那份伙食費,正由於這份觸手可及的溫暖, 所以對她而言,普羅亞每天都當是夏季。
手心上的雪隨著時間流逝逐漸融化, 在艾希蒂的掌心上留下一道道冷冽的水痕。
察覺到她的手溫變冷,少年回過神,輕喊了她一聲,打算要領著她離開窗前。
回應著少年的呼喚,艾希蒂忽然想起什麼似地,熱切地望著少年:「你還沒告訴過我你的名字。」
「我沒有名字?」
「為什麼?」
「父親跟我並不想以名字互相稱呼,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少年淡淡地說道:「 正是知道母親的名字,她的死才讓父親感到悲傷。父親是這麼跟我說的。」
「因為名字就是代表這人的象徵吧……」艾希蒂咬了咬唇,搖搖頭,「我可以理解叔叔的感受,但叔叔的決定,我不喜歡。」
「為什麼不喜歡?」少年淡淡地說道:「我認為沒有名字,反倒容易忘記已逝去的人。」
「總之,我想幫你取名字就是了,別管那麼多。」艾希蒂嘟起嘴重申,帶點撒嬌與任性的語氣,難得顯露出孩子氣的神態。
少年撓了撓鼻心,神情格外地溫柔。
「好吧,那要取……」
迎面而來的狂風,打斷他還沒說完的話,紛飛的雪花驟然飄得更急,艾希蒂與少年下意識地用手臂擋住視線。
「是誰?應該不是軍隊吧?」 門板遭到風的無情敲打而變得脆弱不堪,艾希蒂惶恐地抓著少年的肩膀,手指掐得很緊。
「是正在邊境攻打普羅亞的聯軍嗎?不可能打到這裡!這實在太快了!」門上的敲打聲變得更急,結實的敲擊不像是風乾扁的節奏,更像是帶著憤怒及戰慄的金屬。
不祥似乎已經降在這裡。
少年的預感讓他開始顫抖, 而彷彿是為了呼應他的恐懼,只見門應聲破裂,碎裂的木屑隨著龐大的黑影直驅而入,那非常熟悉的身影不是別人,正是少年的父親。
少年一個箭步衝向男人。
「怎麼了?!這到底是怎麼了?!」在一旁的艾希蒂焦慮地詢問。
她雖然眼睛看不見,但聽到兩人的對話便足以揣測出大概的情況,焦急地探著手,想確認少年與男人的位置。
這時,大風撞開了門扉。
隨著大雪從門外頭踏進來一個士兵。身上披著帶有布料的盔甲,盔甲上頭還綴有不少紡緞紗布料,很顯然是隸屬於貴族軍隊。
「我就覺得奇怪,為什麼從窗外看到一位從未見過的少女?」斜舉的劍鋒上還滴著血,眼神貪婪地盯著少年身後的艾希第,他臉上的神情,顯然已不是人類的範疇,「原來是你們玩暗的,有這樣可愛的女孩,竟然不說而且隱匿了她!」
「走,快走!」瘦弱的胸膛泊泊滲出鮮血,一頭栽倒在少年懷裡的男人發出痛苦的呻吟,不斷胡亂地張擺著雙手、雙腳,無力地推著少年催促。
就在少年還來不及反應的一瞬間, 滴著血劍鋒毫不留情地插入了男人的背後!
那張因疼痛難耐而猙獰的臉孔,還明白顯露出的對現況的憂慮與恐懼,但男人就徹底斷氣了,死在自己的兒子面前。
「老鬼,也太不識相了!」一揮劍甩去劍峰上的血跡,那士兵俯瞰著少年嘿然冷笑,「小子,這情況我可必須上呈,在這之前你最好別試圖抵抗。」
一腳踢開擋路的少年與他父親橫倒在面前的屍體,他肆無忌憚地走向那引人遐思的獵物,「讓普羅亞少了個好用的工具,那怎麼行呢?」
艾希蒂無助地站在原地,轉著頭,從鼻翼間清晰傳來的血氣試圖判斷少年的方位。
逼近的敵人臉上帶著怎樣的表情,目盲的她並不知道。
但那光從聲音判斷,就可以知道她將面對的是隻凶惡的禽獸,是個被利益及名望薰心的人渣,她無從得知自己的下場與未來,唯一記掛的是兩名親人的安危。
那是場充滿殘虐與惡意的凌辱。
少年倒在地上,呆呆地與父親睜大而沒有焦距的瞳孔對視,瞬間知道了死亡的定義,那便是將失去所有的一切,也就代表身邊的人永遠不復返!
噴濺的鮮血,染紅了少年的頭臉。
面對眼前猙獰的敵人、殘酷的兇手,他不知道自己還能怎麼辦?腦中只記得自己已是一無所有,而那即將被可怕命運吞噬的、無力殘喘的少女是他最後的、唯一的寶物,他必須守護她,守護著艾希蒂。
「滾開!」
猶如野獸般地嘶吼爆發,少年抓起身下被撞碎的瓷碗飛撲而去,以碎片尖銳的那一面用力刺入那貴族士兵的脖子!
血花四濺。
那毫無防備、不曾將眼前殘弱的螻蟻視作威脅的士兵按著出泊泊血的頭部,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身體一陣扭曲抽搐後砰然倒地。
少年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
他衰弱的意志,僅靠著一股必須保護艾希蒂的支持著殺戮的勇氣,他的手,卻克制不住地為沾染的鮮血而顫抖,直到一雙柔軟而溫暖的手,捧住了他失去血色、冰冷的臉孔。
他失焦的眼神,映入眼簾的是孰悉的少女的身影,沾滿了污痕與塵土不再乾淨無暇,猶如破損的娃娃,但雪白的臉上卻彷彿被罩上了一層面具,看不見恐懼沒有任何表情。
「艾、艾希……沒……沒事了,我們……」少年的心在淌血,臉色比死亡還要可怕。他深吸了幾口氣,強迫自己穩下急迫、紊亂的呼吸。
艾希蒂輕眨了下眼,陡然,早已乾涸的淚水跟著眼內的瘀血一起流了出來,在她雪白的臉孔劃下兩道紅色的水痕。
乍現的光線照亮了她。
她終於看見了少年的模樣。
她望著少年,臉上綻開了一抹笑,手指輕輕觸摸著少年俊俏的臉孔,而後,幾不可聞地開口:「殺了我吧!」
「艾希蒂!」少年痛苦地嘶吼,儼然是負傷的野獸。
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已奪去他人生中僅有的親人,而他不惜背負殺戮去守護的這名少女,卻要求自己殺了她!
「你帶著我跑肯定會被抓到的。」艾希蒂握著少年的手,血色的淚痕與冷靜的笑容形成強烈的對比,「我不想被當作性慾的工具。」
少年的憤怒與無奈形成了淚水,對「殺人」這件事還反應不過來的手依舊顫抖著,卻彷彿有自己的意識般,握著奪取敵人性命的那片凶器,貼上少女雪白、纖細的頸項。
「艾希蒂……不要!」少年的嘴唇不住顫抖著,幾乎什麼聲音都發不出來,臉色比死亡還要可怕,因奮力而扭曲泛白的手指,在那雙如火焰的橙色眼眸注視下,準確而穩定在少女的脖子上劃開一道鮮豔的血痕。
「你的名字是……莫寧。」少女長吐了一口氣,安然地閉上了眼睛。
沾血的兩手恢復自由,少年踉蹌地爬起身,頭也不回地奔離那被死亡與悔恨的陰影所覆蓋、籠罩的場所。
他在大雪中拼命地奔跑,在悔恨中不斷回想起少女斷氣的臉,最後,一望無際地黑天白地剩下的只有他孤身一影,而他卻失去了最後的寶物,剩下的是「一無所有」。
「……艾希!」
莫寧從床上醒來,額頭上的汗水流經眼瞼沾濕了睫毛。
他茫然環顧著四周,裝飾華美的屋宇取代了四面灰壁,是夢啊……這段記憶,有多久沒被想起了?
莫寧頹然倒回枕上。
棉絮充填的床上布滿了花香,這種大概是還在德莫格那才有的待遇,許久不能感受的安詳生活,讓他整個人彷彿少了些動力,大概,算是一股對於生存的渴望吧……
所以,自黑影沒有動靜後,他越發期待著能理解對方的殺人目標。
他總覺得,那黑影的舉動有股與他自己相像的報復意味。莫名地,自從那道黑影出現,他總是在夢中回溯起過往的那段記憶。
「……沒事吧?」清脆悅耳的聲音陡然響起,有點急促,透著隱隱的關切。
他轉過頭。
莉梵就坐在一旁,正用一把精美的袖刀削著顆豔紅的蘋果。
「我怎麼了?」面對她探究的眼神,莫寧避重就輕地反問,反手摸了額頭的溫度。
「水土不服吧……」莉梵叉起了一塊蘋果肉,湊到莫寧的嘴邊。
「做什麼?」莫寧皺著眉。
「當然是餵你吃啊,不然呢?」
莉梵舉著叉子,在莫寧面前晃了晃,語氣上聽起來,像在諷刺莫寧,實際上躍躍欲試的眼神卻顯然不是這麼回事。
莫寧無奈地奪過那把叉子,直接將那塊蘋果給咬進嘴裡。
「真不可愛!」莉梵狀似十分不滿地哼了哼,轉過頭,繼續削著蘋果。
莫寧自然沒把她的抱怨給聽進去,兀自把玩著手上的叉子,索性也枕在床上先不起身。大概是跟他從小生長在普羅亞,四季有三季總是被冰雪覆蓋有關,他反倒不大適應溫暖、多變的天氣,每當季節交替之時,身體總像是被束縛般地不聽使喚……
「抱歉,沒打擾到你們吧?」
輕扣了幾下門板,皮斯伯爵正倚著門板、站在門口。
「不,怎麼會呢?」莉梵放下刀起身,朝伯爵屈膝行了一禮。
伯爵揮揮手,神情顯得有些急迫卻又帶著幾分猶豫。
黑影的事件已過了幾周,他的臉色原本已有了很大的好轉整個人變得神清氣爽,可此時又像被重新打落谷底,肉體與精神的疲憊似乎正雙重摧殘著皮斯伯爵,讓他原本可算是端正的臉孔,彷彿像是要裂開的石膏面具般蒼白、憔悴。
莉梵與莫寧對看了一眼,覺得事情似乎頗不單純。她主動開口:「皮斯叔叔,是不是城內又出了什麼事情?」
,「嗯,的確是有事想請妳幫忙 ,可以嗎?」
「當然可以,到底是什麼事?」莉梵毫不猶豫地說道。
「那黑影又出現了?」莫寧下了床,套上襯衫、紮好領結,與莉梵一起走向皮斯伯爵。
「也不是……不過,卻是差不多嚴重的事情。」
皮斯伯爵倚著門板,從懷裡取出一本泛黃的書遞過去,「一刻鐘前,我宅邸內的骸骨之鳥動了,銜著這本書飛到議會,而且還震破了屋頂。夏依將劇本帶回,現正在追查鳥的下落。」
……這事情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莫寧才剛想這麼反問,但劇本一到了莉梵手上,他平時常顯得十分嚴肅、淡漠的臉孔瞬間變色、扭曲。
他退了幾步、搖搖頭,劇本上的名字「凱特妮.德莫格」,讓他連聲音都出不來!
「凱特妮是德莫格家族的人嗎?」
「我知道你很難相信,不過,我想不用我再承認第二次了吧……」皮斯伯爵有些無奈地說道。
「為什麼這件事不早點跟我們說?」莫寧低著頭問道,深吸了幾口氣,試圖甩掉腦海中德莫格的陰影。
而莉梵則是望劇本的封面望得出神。
封面沒有精細的美工,僅有這齣歌劇的名字以及作者──凱特妮.德莫格……從這姓氏看來,當時擔任教宗的德莫格不就是她的父親嗎?
這下,她也總算搞清楚了。
看樣子,皮斯伯爵始終未詳細說明上一回巫妖聚會的情況,為得大概就是想隱瞞凱特妮的身分,只不過……巫妖聚會到底還牽涉到多少秘密?
自從觸摸了「眾影書」後,她對其中糾結複雜的依舊真相無法知曉透徹,深埋在其中的秘密,像是一池混濁的汙水,明知道是水卻也無法看清底下的事物,而在那混濁又讓人避退的表象之下,真不知道還埋藏著多少悲傷與痛楚?
撫摸著書封上的字跡,莉梵略想了想後問:「叔叔,這劇本是她親手寫的?」
「這……」皮斯伯爵像是被問倒了,略遲疑了下苦笑道:「應該是。事實上,她本身是劇作家,而這劇本,恐怕是她第一次以真名署名,其餘作品都是使用筆名。」
「嗯,我知道了。」莉梵不置可否地點點頭,又問:「那麼叔叔想拜託我什麼呢?」
「其實……」
「等一下!」
搶先一步打斷伯爵的話,莫寧不怎麼高興地看著對方的笑臉,「您為什麼拿這劇本來?有什麼目的?」
「過這麼多天了,你還是保持著戒心啊……」伯爵站直了身體,似笑非笑地看著莫寧,「任何時刻都得保持冷靜與理智,是吧?真該說是德莫格那傢伙教得好啊!」
莫寧一聽,神色登時又冷沉了幾分。
對於他跟莉梵兩人之間的狀況,皮斯伯爵自然早就知曉了,他跟莉梵的心結,正是源於「德莫格」這姓氏,如果伯爵打算利用這劇本打擊、潰散莉梵的信心,那他不可能輕易讓伯爵得逞!
即使不計前嫌讓他也住在宅邸內伴隨著莉梵,但皮斯伯爵的心裡當真就這麼單純,沒有一絲算計嗎?莫寧根本不相信這類天真的想法。
只世上只有莉梵的存在能讓他迷惘,甚至讓他動搖了長久的冰冷心牆之外,生活給的教訓,從來教導他疑心,永遠是他不該拋去的防衛。普羅亞的經歷,更讓他可沒辦法將人的善心擺在第一位。
所謂的領地領導人,不就與普羅亞的那群自傲的貴族相似!
除了家族與利益之外,又有什麼事、什麼人能獲得他們一絲憐憫的慈悲與溫柔。
氣氛一瞬間有些劍拔弩張。
莉梵有些苦惱地看著在場的兩個男人。
皮斯伯爵先是笑了笑,雙手背在腰後自若地說道:「抱歉,我沒有惡意。真要說目的,只能說我非得拜託莉梵不可,只有她做得到這件事。
「叔叔的意思是……」莉梵將劇本翻開,若有所思地注視著內頁,「沒有字?!叔叔,這本劇本沒有字呢!」
「是啊。」伯爵輕咳了幾聲,方道:「正是因為沒有字,所以才來找妳。事實上,除了妳之外的人,根本沒辦法將劇本翻開,甚至無法利用透光去窺探裡頭的內容。
我不是推卸責任。事實就是任何人都無法翻閱它,只要一根食指嘗試翻起頁邊,莫名的焦熱會立刻從指甲縫攢流而上。」
……燒灼的感覺嗎?若有似無燒灼、竄流全身的力量,這跟莉梵當時失控的情況,倒非常地類似。
莫寧想了一會兒猜測是某種巫術,或者與其說去探討是某種不知名的奇異力量所致,對他而言,倒不如相信身邊早有過印證的人事,他覺得在這劇本裡頭,一定存在著某些暗語,又或者是在上頭施了巫術做障眼法。
「作者是凱特妮的話,肯定在裡面藏了什麼吧?會是甜言蜜語,或者僅是單純的劇本呢?」
莉梵的想法,顯然也與他不謀而合。
她看起來挺有興趣地瀏覽著,接著很快地又翻開了第二頁。書頁上依舊是存留著歲月的痕跡,上頭還沾有些許骸骨之鳥的骨粉,點點分布於泛黃的紙稿間。。
「這東西,是一直藏在那隻鳥嘴裡嗎?」就一本跨越了百年以上的書卷而言,這劇本的保存狀況意外地良好,莫寧越覺得滿腹疑問。
「不,那骸骨之鳥的周圍定期都有侍僕負責清掃,每年度的骸骨之鳥日也會特別整理一番,從內部到外部徹底清理,將灰塵掃得乾乾淨淨,不過我們從未發現過劇本的存在。」
頓了一頓,皮斯伯爵又道:「今日早晨,正好是一年一度的骸骨之鳥日,但那侍僕正準備要進行例行的清理工作時,骸骨之鳥就突然動起來了。」
「確定那隻鳥的骨骼完好如初嗎?」莫寧追問。
「那是當然。」皮斯伯爵十分肯定地說道。
對他的謹慎,莫寧是早就知道的,若是鳥嘴裡真的藏有劇本,一定不可能直到現在才發現,那麼先前劇本到底藏在哪?那骸骨之鳥又是如何去藏匿劇本?
對於這點,莫寧實在想不出個所以然來。
誠如皮斯伯爵所說的,這劇本內隱含著會螫人的神秘力量,任何人嘗試翻閱便會遭到火燒之苦,從一開始,凱特妮便將巫術的觸發方式更改成「除女巫以外任何人不得翻閱,但可以觸摸」,換言之,只要劇本交付的人不是女巫,一旦想翻閱肯定會碰上書上設下的巫術。
這樣一來,不管書本落到什麼人手上,最終都可以透過他人之手傳遞給下一個的女巫。
這劇本如果真是凱特妮所寫下,那麼單就這一點來說,莫寧還真不得不挺佩服她細膩的心思,同時,也對這麼大費心思的計畫感到十分地訝異,究竟上一回的巫妖聚會到底怎麼了?
凱特妮如此大費周章、殫精竭慮為這一切都布好了局,目的到底是什麼?
「真的整本都沒有字啊……」莉梵微瞇著眼,緩緩抬起細嫩的手掌,將手心置於胸前。
頃刻間,只見一股微弱的風緩緩颳起,然後像是突然加大了力道轉為劇烈,風中帶點灼熱,靠近莉梵手邊的灰塵及蚊蠅像是撞到無形的火牆,瞬間燒成焦炭散於地面。
就在這一瞬間,空氣中浮現出五芒星,眾影書也同時從莉梵掌心捲起的火焰中誕生。
莉梵迅速翻開至某頁,吟誦出有關於「隱藏」與「現形」的咒語:「公主的美麗,誰也不知道;國王的威嚴,躲藏在權力之下,童話有如假面;寓言有如裝飾。執起風的掃帚,
將那層輕薄的唇蜜拭去,拭去那令人厭惡的阻礙!」
須臾,一串串字從內部開始浮現,彷彿剛寫上去的墨水焦亮且透著光。
「好了。」莉梵收回「眾影書」,將劇本回遞給皮斯伯爵。
「是巫文……」皮斯略看了一眼,有些苦惱地沉吟著。
看情況,這劇本還是只有身為女巫的莉梵能夠解讀。
她也不等伯爵授意,拿回劇本,退了幾步往床上大方坐下,雙腿合攏並將劇本擺在大腿上,開始閱讀起第一頁。
伯爵略鬆了口氣,喊了管家菲爾庫讓他送來幾杯溫熱的紅茶,而後,便跟莫寧坐在一旁寬敞的沙發椅上,準備聆聽這段跨越百年以上的故事。
那是發生在一百六十五年,殘酷且美麗的故事。
當時,芬徹有兩大家族。
德莫格家族現任的當主,正是教宗芬徹.德莫格。芬徹並不是他的名字,只不過傳統以來任何繼位教宗的家族成員,都必須承襲這個名字。而皮斯家族則是世襲著行政事務官的位子,世代與親教宗派的德莫格家族對抗。
兩大家族有著相等的聲望,至於對抗之源,或許只不過是他們擁有相同的地位,而各自想要稱霸……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貓爵(2)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73 |
幻奇冒險 |
$ 194 |
中文書 |
$ 194 |
奇幻小說 |
$ 198 |
奇幻/科幻 |
$ 198 |
文學作品 |
$ 198 |
科幻/奇幻小說 |
$ 289 |
小說/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貓爵(2)
黑影刺殺事尚未落幕,被驚動芬徹議會立即召開了「閉門會議」。
皮斯伯爵與夏依同時成為議會鎖定與針對的目標,夏依更單獨被議會召喚,必須針對所謂「褻瀆教義」的影響,向議會進行報告,並接受審查!
而就在「閉門會議」如火如荼進行之際,皮斯伯爵宅邸中沉寂多年、本為死物的骸骨之鳥,居然再次震動雙翼!
骸骨之鳥沖天而飛,隨之展露在世人眼前的,是埋藏在伯爵府中,出自女巫凱特尼之手的詠嘆歌劇《骸骨之鳥》……
久遠的劇曲,沉默地歌頌著遠古的歷史、記錄當代,更描摹著遙遠的未來,巫妖聚會,到底擁有多少秘密?
被捲入其中的莫寧跟莉梵,不斷抽絲剝繭試圖還原佚失的劇本,找尋失落的歷史真相,然而……
作者簡介:
Hadiel
作品以奇幻、推理為主。愛喝咖啡,特別喜愛有酸味的;雖然住在台灣,但內心卻嚮往十九世紀末的歐洲,尤其是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與自然主義盛行時的法國。涉獵世界歷史與神祕學居多,所以作品中完全沒有中華文化色彩。西方作家中,喜歡的是菲力普‧普曼;東方則是韓國女作家-全民熙、日本推理作家-北村薰。
入圍過台灣推理作家協會獎後,近期也跨往輕小說方面創作中。
畫者簡介
YO~大家好^q^~這裡是SR!平常喜歡打RPG跟看動漫的我,第一次負責輕小說的封面真的很ドキドキ!!希望大家多多支持Hadiel桑的小說喔!
感謝您看這一版(喂) 大家好我是Rei~第一次參與輕小說的製作!真開心喔XD!嘛~然後請大家慢慢細閱本小說吧'u')!!!
以下是我們的噗浪 ^q^
有興趣的不妨來看看~(?
SR: http://www.plurk.com/amksr417
Rei: http://www.plurk.com/Euthvil
章節試閱
序幕
她要在釣鉤上,把愛情的香餌偷食。
既是仇人,他無法能像情人一般向她海誓山盟的獻媚。
她同樣的情深。
可是更感困難,無處去和她的新歡幽會。
兩方仇視的家族成員,絕不可能在一起。
摘自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二幕‧序詩(8-12)。
教宗廳的秩序亂成一團。
芬徹城內居然發生這類褻瀆教義的事情,這對於兼任教宗的皮斯伯爵而言或許不算什麼危機,但對於立足於大陸上的芬徹來說,事態實在是過於嚴重了。
也因此,駐芬徹的主教開始過問這個月發生的事情。
然而,繼上次的殺人行動已經過了兩...
她要在釣鉤上,把愛情的香餌偷食。
既是仇人,他無法能像情人一般向她海誓山盟的獻媚。
她同樣的情深。
可是更感困難,無處去和她的新歡幽會。
兩方仇視的家族成員,絕不可能在一起。
摘自莎士比亞《羅密歐與茱麗葉》第二幕‧序詩(8-12)。
教宗廳的秩序亂成一團。
芬徹城內居然發生這類褻瀆教義的事情,這對於兼任教宗的皮斯伯爵而言或許不算什麼危機,但對於立足於大陸上的芬徹來說,事態實在是過於嚴重了。
也因此,駐芬徹的主教開始過問這個月發生的事情。
然而,繼上次的殺人行動已經過了兩...
»看全部
目錄
序幕
第一章 沉睡在記憶裡的故事
第二章 骸骨之鳥
第三章 家族的秘密
第四章 第二幕
第五章 歷史的骸骨
第六章 真相的背後
尾聲
第一章 沉睡在記憶裡的故事
第二章 骸骨之鳥
第三章 家族的秘密
第四章 第二幕
第五章 歷史的骸骨
第六章 真相的背後
尾聲
商品資料
- 作者: Hadiel
- 出版社: 三日月 出版日期:2013-03-20 ISBN/ISSN:9789861857817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08頁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奇幻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