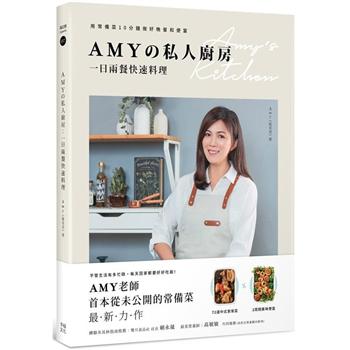全球銷售超過250萬冊!版權售出30國!
《分歧者》系列電影預計2014年搬上大銀幕!
Amazon網路書店年度百大!
Goodreads 網站讀者票選最愛小說!
NPR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年度百大!
紐約時報2011年度百大小說!
獲美國青少年選擇獎提名!
另一本讓人上癮的精彩故事:滿滿的經典橋段、心碎與羅曼史、還有劇力萬均的人性描述。
――《紐約時報》
作者深諳寫作之道,故事中的情感、複雜的情節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設定,這本續集將會讓第一集的讀者更加死忠。
――《出版人週刊》
又是一本精彩且吊人胃口的作品,看了第一集的人會渴望著第二集,然後等不及要看結局!
――《科克斯書評》
《叛亂者》探討了很多爭議性的主題,值得一讀!
――《圖書館週刊》
革命必定伴隨死亡、毀滅必定帶來新生,
但誰能斷言謊言背後必有真相?
搗毀舊世界的秩序後,美好的新世界卻仍離他們很遠。
在躲過追殺後,翠絲和托比亞等一行人逃往友好派尋求協助,但在輾轉流亡的過程中,殺死朋友、失去親人的痛苦回憶幾乎壓得她喘不過氣。翠絲不再確定自己想要什麼,也不在意未來世界會變成怎樣。在友好派的住所中,翠絲感受到一股猶如毒藥般的安逸感。雖然明知不可能永遠躲避下去,但她好希望有那麼一次,讓別人去肩負重任,因為她已經筋疲力盡,似乎再也無法擔任那個揭開陰謀、領導革命的人。
而在這趟充滿猜疑與危險的逃亡之路上,她以為自己對於背叛已司空見慣,但翠絲怎麼也沒想到,與她關係最密切、感情最親近的他,竟然是一名背叛者。這是她寧可被謊言遮蔽雙眼也不願接受的真相,也是傷她最深最痛的一場騙局……
在這個失去秩序的世界裡,你必須重新定義自己;
重新定義虛與實、還有錯與對……
作者簡介:
薇若妮卡.羅斯〈Veronica Roth〉
紐約時報暢銷小說《分歧者》作者。她在書寫三部曲的第一本時,還是個大學生。現在則是全職作家,目前與丈夫居住在芝加哥。
官方網站:www.veronicarothbooks.com
作者推特:Twitter (@veronicaroth)
譯者簡介:
簡秀如
台灣桃園人,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法文系。曾任多年美語教師及英語雜誌社執行編輯。目前擔任科技軟體公司之技術文件中英文撰寫員,並從事HBO及Discovery等頻道之字幕翻譯。平日喜愛旅行,閱讀及翻譯。
章節試閱
「真相一如野生動物,任何牢籠都箝制不住。」
――節錄自直言派宣言
【追捕】
我一面跑,一面數我跑過了幾排樹木。七、八。樹枝沉沉地下垂,剛好僅容我通行。九、十。我越跑越快,將右手抱在胸前,每跑一步,肩上的槍傷便抽痛一次。十一、十二。
跑到第十三排時,我猛地向右拐個彎,沿著一條小徑繼續跑。第十三排的果樹長得很緊密,枝葉交錯生長,形成一片由樹葉、細枝和蘋果所組成的迷宮。
我的肺部因為缺氧而刺痛,但是我就快跑到果園盡頭了。汗水滲進我的眉間。我跑到用餐大廳,用力推開門,橫衝直撞地穿過一群友好派男子,他就站在那裡;托比亞在餐廳的盡頭,和彼得、迦勒及蘇珊坐在一起。我的視線模糊,幾乎看不清他們,但是托比亞撫著我的肩膀。
「博學派。」我只說得出這句話。
「他們來了?」他說。
我點頭。
「我們有時間逃跑嗎?」
這我就不確定了。
這個時候,坐在桌子另一頭的克己派成員也都注意到了。他們圍繞在我們身旁。
「我們為什麼要逃跑?」蘇珊說:「友好派都把這個地方設為庇護所了,這裡不允許衝突發生。」
「友好派必定會發現這項政策根本有執行上的困難。」馬可斯說:「妳怎麼能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阻止衝突發生?」
蘇珊點頭。
「但是我們不能離開。」彼得說:「我們沒時間了,他們會發現我們。」
「翠斯有一把槍。」托比亞說:「我們可以殺出一條生路。」
他開始往寢室走去。
「等等。」我說:「我有個主意。」我掃視克己派群眾。「偽裝。博學派其實不確定我們是否還在這裡,我們可以假裝成友好派。」
「那麼,不是穿友好派服飾的人應該先回去寢室。」馬可斯說:「其他人把頭髮放下來,試著模仿友好派的舉止。」
身穿灰衣的克己派成群離開用餐大廳,穿越中庭回到客用寢室。我一走進寢室區便衝進我的房間,手腳著地跪在床邊,伸手到床墊底下去取槍。
我摸索了一會兒才找到。一旦找到了槍,我便感到喉頭緊繃、無法吞嚥。我不想碰那把槍,再也不想碰到它。
撐著,翠絲。我把槍塞在紅色長褲腰帶的後面,幸好長褲很寬鬆。我看到床頭櫃上的藥膏玻璃罐和止痛劑,於是一併塞進口袋裡,以防我們真的打算要逃跑。
接著我又去拿抽屜櫃後面的硬碟。
假如博學派抓到我們――而且這種可能性不小,他們會搜身,我不希望就這樣把攻擊模擬實境再次交出去。但是硬碟裡還有攻擊事件的錄影,那是我們慟失親友的紀錄,其中包括我父母的死,這是他們唯一留下的身影,因為克己派不拍照,這是唯一記錄他們模樣的檔案。
隨著時間流逝,我的記憶會淡去,到時我要如何記得他們的容貌?他們的面容會隨著我的記憶改變,我將再也看不到他們。
別傻了,這不重要。
我緊緊攢著硬碟,直到手心發疼。
那麼,為什麼它讓人感覺如此重要?
「別傻了。」我大聲說出來。我咬緊了牙,抓起床頭櫃上的檯燈,把插頭從插座上用力扯下,燈罩扔在床上,然後俯身看著硬碟。我忍住盈眶的淚水,拿起檯燈底座往硬碟砸下去,砸出了一道凹痕。
我繼續往下砸,一次又一次,直到硬碟破裂,碎片散落了整個地板。我把碎片踢到抽屜櫃底下,檯燈放回原位,然後走到走廊上,用手背揩了揩眼睛。
幾分鐘之後,一小群身穿灰衣的男男女女(包括彼得在內),全都站在走廊上,將一疊衣服分門別類。
「翠絲。」迦勒說:「妳還穿著灰色衣服。」
我抓緊父親的襯衫,有點遲疑不決。
「這是爸的,」假如我把它換掉,就無法帶走它。我咬著脣,藉著痛楚讓自己鎮定下來。我必須扔掉它。這不過是件襯衫,如此而已。
「我把它套在衣服下面好了。」迦勒說:「他們不會發現的。」
我點點頭,從衣堆中抓起一件紅襯衫。襯衫大到足以遮住槍枝的隆起。我躲進鄰近的房間去換衣服,出來之後把灰襯衫遞給了迦勒。房間的門開著,我看見托比亞將克己派的衣服塞進垃圾桶。
「你認為友好派會說謊掩護我們嗎?」我倚著敞開的門口問他。
「為了避免衝突嗎?」托比亞點頭。「當然會。」
他穿著一件紅領襯衫和膝蓋磨損的牛仔褲。這樣的組合在他身上看起來很可笑。
「襯衫真好看。」我說。
他對我皺鼻子。「只有這件才遮得住我的頸部刺青,好嗎?」
我緊張地笑了笑。我忘了我有刺青,但上衣遮掩得很好。
博學派的車離住所越來越近,一共五輛,全都是黑車頂的銀色汽車。車輪在不平的路面顛簸前進時,引擎似乎發出了低沉的顫動聲。我溜進大樓內側,任憑大門敞開,托比亞則忙著栓好垃圾筒。
車子停下來,車門打開,出現了至少五名身穿博學派藍衣的男女。
另外還有十五名身穿黑衣的無畏派。
無畏派的人走近時,我看見他們的手臂上綁著藍布條,象徵他們擁戴博學派――那個奴役他們心智的派別。
托比亞握住我的手,帶我走進寢室。
「我沒料到我們的派別會那麼愚蠢。」他說:「妳有帶著那把槍吧?」
「有。」我說:「但是我不敢保證用左手開槍能射中什麼。」
「那麼妳應該加強這部分。」他那指導員的模樣又出現了。
「我會的。」我有點發抖地又加上一句。「假如我們活得成的話。」
他的手輕拂過我赤裸的雙臂。「走路步伐輕快點。」他吻了一下我的額頭。「假裝妳很怕他們的槍。」又一個吻落在我的雙眉間。「裝出一副妳永遠裝不像的那種害羞小女生模樣。」一個吻落在我的臉頰。「這樣就沒問題了。」
「好。」我抓住他的襯衫領口時,雙手在顫抖。我將他往下拉,讓他的脣貼上我的脣。
鐘聲響起,一次、二次、三次,召喚大家前去用餐大廳。如果聚會目的不像我們上次參加的那麼正式,友好派應該會在這裡召開會議。我們加入克己派偽裝的友好派人群之中。
我將別在蘇珊髮際的髮夾拿掉,那種髮型對友好派來說太過嚴肅。她給我一個感激的淺笑,秀髮飄散在她的肩頭。我不曾見過她這副模樣,她方方的下巴線條因此變得柔和。
我應該要比克己派更勇敢一些,但是他們似乎不像我這麼擔憂。他們對彼此微笑,安靜地走著,有點太過安靜。我從人群之間擠過去,在一名年長女子的肩頭戳了一下。
「叫小孩子玩鬼抓人。」我對她說。
「鬼抓人?」她說。
「他們太有規矩,而且……像僵屍一樣。」我吐出這個無畏派給我的綽號時,不禁畏縮了一下。「友好派的孩子會大聲喧鬧。照做就是了,好嗎?」
那名女子碰了碰一個克己派孩子的肩膀,低聲囑咐了一番;不要多久,一小群克己派的孩子便在走廊上奔跑,閃避友好派的腳步,並且大喊。「抓到你了,你當鬼!」「才沒有,你是摸到我的袖子。」
迦勒追上去,戳了一下蘇珊的肋骨,害她閃躲著並笑了出來。我設法放輕鬆,聽從托比亞的建議,讓腳步輕快些,轉彎時手臂也隨之晃動。對此,我大感驚訝,假扮另一個派別居然能改變一切,甚至是我走路的姿態。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我輕易地擁有三種派別傾向一事才顯得那麼奇怪。
穿過中庭前往用餐大廳時,我們追上前面的友好派,混入人群之中。我不讓托比亞離開我的視線範圍,不想離他太遠。友好派沒有提出質疑,就這樣讓我們融入了他們的派別。
兩名無畏派叛徒守在用餐大廳門口,手上握著槍,我渾身僵硬了起來。忽然間,這一切感覺如此真實,我沒有攜帶武器,便被趕進了博學派和無畏派包圍的屋內。假如他們發現我,我根本無處可逃。他們會將我一槍斃命。
我考慮逃跑,但能跑到哪裡?哪裡他們才抓不到?我盡量正常呼吸,幾乎要走過他們身邊了。不要看,不要看。現在剩幾步的距離。移開視線,快移開。
蘇珊把她的手套進我的臂彎。
「現在我正在跟妳說一個笑話。」她說:「而且妳覺得很好笑。」
我用手掩住了嘴,擠出一種音調高又陌生的咯咯笑聲;不過依照她給我的微笑來判斷,我裝得很像。我們和友好派女生一樣拉著彼此不放,偷偷看著無畏派,然後又咯咯地笑了起來。我很訝異自己在如此沉重的心情下居然還能辦得到。
「謝謝妳。」我們一進到裡面,我便低聲對她說。
「不客氣。」她回答。
托比亞和我在一張長桌上對面而坐,蘇珊坐在我旁邊。其他的克己派分散在各個角落,迦勒和彼得則跟我隔了幾個座位。
我的手指在膝蓋上輕敲著,一面靜等接下來的狀況。有好一段時間,我們光是坐在那裡,我假裝在聽左手邊一個友好派女孩講故事。但不時看著托比亞,他也看著我,彷彿我們不斷往返傳遞恐懼。
喬安娜終於和一名博學派女子一同走進來。她的亮藍色襯衫在深棕色肌膚的襯托下顯得閃閃發光。她和喬安娜說話的同時,眼光梭巡著室內;目光掃到我身上時,我屏住了呼吸;當她毫不遲疑地移開眼神,我才吐出了氣。她沒有認出我來。
至少還沒有。
有人重擊桌面,整個大廳都安靜下來。時候到了,她若是沒有在此時把我們交出去,我們就安全了。
「我們的博學派和無畏派友人在找某些人。」喬安娜說:「幾位克己派成員,三名無畏派成員,還有一位前博學派新生。」她面帶微笑。「在答應會全力配合的前提下,我告訴他們,他們要找的那些人原本在這,但後來離開了。他們想要得到許可搜索這裡,因此我們必須投票表決。有人反對搜索行動嗎?」
她聲音中的緊張情緒暗示,如果有人反對,最好別出聲。我不知道友好派的人是否會了解這種事,但的確沒有人作聲。喬安娜對那名博學派女子點頭示意。
「你們三個看著這裡。」那名女子對聚集在入口處的無畏派守衛說:「其他人搜索所有建築,有任何發現立刻回報。開始行動。」
他們可能找到的線索有很多:硬碟碎片、我忘了扔掉的衣物,還有我們的寢室相當可疑地缺少許多小飾品和裝飾物。當那三名無畏派士兵在我背後的桌子之間來回走動,我的脈搏猛烈跳動。
其中一名士兵走到我背後時,我感到頸背的皮膚隱隱刺痛,他的腳步聲既響亮又沉重。這時我再度感到慶幸,我的身材瘦小又平凡,很少會吸引別人注意的眼光。
但是托比亞就不一樣了。他有一種掩不住的自信神態,眼神中霸氣十足。這可不是友好派的特徵,絕對是來自無畏派。
那名朝他走過去的無畏派女子立刻盯著他看。她走近時瞇起了眼,然後在他的正後方停下來。
真希望他的襯衫衣領再高一點,希望他沒有那麼多刺青,希望……
「就友好派來說,你的頭髮倒是挺短的。」她說。
他沒有把頭髮剪得像克己派一樣。
「天氣很熱。」他說。
假如他知道要用什麼口氣說話,這個藉口可能說得過去,但是他卻用了頂撞的口吻。
她伸長手,用食指拉開他的襯衫領口去看那些刺青。
然後托比亞採取行動。
他抓住那女子的手腕,將她往前猛地一拉,讓她失去平衡。她一頭撞上桌緣,然後便倒了下去。大廳另一端有槍聲響起,有人放聲尖叫,大家都躲到桌子底下,或者是趴在長凳旁。
每個人都如此,除了我之外。我坐在槍響前方的那個位置,緊抓住桌緣。我知道自己身在何處,眼中卻看不見餐廳的存在:我看見在母親死後我拔腿狂奔的那條小巷,我盯著手中的槍,槍口抵著威爾雙眉間的平滑肌膚。
我的喉嚨發出一陣咯咯輕響。要不是我的牙關緊閉,那聲音會變成一記尖叫。記憶的片段漸漸淡去,我卻依然動彈不得。
托比亞抓住那名無畏派女子的後頸部,拖著她站起來。她的槍落到他手上。他拿她當人肉盾牌,從她的右肩上方朝大廳另一端的無畏派士兵開槍。
「翠絲!」他大叫。「幫我!」
我將襯衫往上拉,剛好能伸手去抓槍柄,然後我的手指碰到了金屬。金屬的感覺好冰冷,刺痛我的指尖;但不可能啊,這裡很熱。一名無畏派男子站在走道盡頭以左輪手槍瞄準我,槍管盡頭的黑點在我眼前不斷擴張;除了自己的心跳聲,我什麼也聽不見。
迦勒衝上來抓住我的槍,他雙手握著槍柄,射中離他數英尺遠的一名無畏派男子膝蓋。
那名無畏派男子哀嚎著倒下,雙手抱著腿,托比亞便趁此機會往他的頭部開一槍。他的痛苦並未持續太久。
我渾身顫抖,無法自制。托比亞仍然制住那名無畏派女子的喉頭,但是此時他的槍瞄準那名博學派女子。
「再多說一個字。」托比亞說:「我就開槍。」
博學派女子張開了嘴,但是什麼也沒說。
「同伴們,該逃跑了!」托比亞說,他的聲音在大廳迴盪。
【直言】
奈爾斯站在大廳中央,手上拿著針筒。他上方的燈光把針筒照得閃閃發亮。圍繞在我身邊的是無畏派和直言派,他們等待我走上前,在他們面前傾吐我的一生。
我心裡又出現那個想法:也許我可以對抗血清。但我不知是否應該放手一試。假如我能把話說出口,也許對我愛的人來說會比較好。
托比亞離開時,我僵硬地走到訊問室中央。當我們經過彼此身邊時,他拉住我的手,緊握一下我的手指,然後走開。現在只剩下我、奈爾斯,還有針筒了。我用消毒棉擦拭了頸側,不過在他把針筒湊過來時,我往後退開。
「我情願自己來。」我說,並且伸出了手。我不會再讓別人在我身上注射什麼,尤其在我最後一場測試結束後,我讓艾瑞克給我注射了攻擊模擬實境血清。自己動手注射是無法改變注射器的內容物,但至少這麼做,是由我自己來毀了自己。
「知道要怎麼做嗎?」他揚起一道濃密的眉。
「知道。」
奈爾斯把針筒交給我。我將它擺在頸部的血管上方,把針頭戳進去、壓下推桿。我幾乎沒有察覺到刺痛,我的腎上腺素飆得太高了。
有人拿了垃圾桶過來,我把針筒扔進去,感覺到血清立即起了作用。它讓我的血液變成鉛一般在血管流竄,我幾乎要在走向椅子的途中倒下去,但是奈爾斯抓住了我的手臂,帶我往前走到椅子旁。
過了一會兒,我的頭腦安靜下來。我究竟在想什麼?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沒什麼好在意,除了我坐著的椅子,以及坐在我對面的那名男子。
「妳叫什麼名字?」他說。
他一問完這個問題,答案就從我的口中蹦出來。「碧翠絲.普里爾。」
「但是叫妳翠絲也可以?」
「是。」
「妳父母親的名字是什麼,翠絲?」
「安德魯和娜塔莉.普里爾。」
「妳也是派別轉換者,是嗎?」
「是的。」我說,但是心中響起了一種新的聲音。也是?這代表還是有別人也一樣,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那個別人就是托比亞。我皺著眉,試圖想起托比亞的影像,但很難在心中看清楚他的模樣――但也不至於辦不到。我看見他,然後又看見一道影像,他就坐在我這張椅子上。
「妳是來自克己派、然後選了無畏派?」
「是的。」我再次回答,但是這次的回答聽起來很簡潔。我搞不清楚是為什麼。
「妳為何要轉換派別?」
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是我依然知道答案。我幾乎要脫口說出我對克己派來說不夠好,但是另一句話卻起而代之:我想要自由。這兩個答案都是真話,我想把兩種答案都說出口。我用力握緊椅子的扶手,想記起自己究竟在什麼地方、正在做什麼。我看見周圍有很多人,但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全身緊繃,就像參加考試時,幾乎記得問題的答案,但是卻一時想不起來。我以前會閉上眼睛回想課本上有答案的那一頁。我掙扎了幾秒鐘,還是辦不到。我記不起來了。
「我對克己派來說不夠好。」我說:「而且我想要自由。所以我選取無畏派。」
「妳為什麼不夠好?」
「因為我以前很自私。」我說。
「妳以前很自私?現在不會了嗎?」
「我當然還是,母親說每個人都是自私的。」我說:「但是我在無畏派變得比較不自私。我發現有些人值得我去奮鬥,甚至犧牲生命。」
這個答案讓我大吃一驚,但為什麼?我緊閉著嘴脣一會兒。這些話是真的,假如我在這裡說出這種話,那就一定是實話。
那個想法幫我連結起事物,補齊了我想要釐清的那個思緒。我是來這裡做測謊的試驗。我說的每件事都是真的,我感到汗珠滑下頸背。
測謊試驗。吐實血清。我得提醒自己,實話很容易會說過頭。
「翠絲,可否請妳告訴我們,攻擊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我醒來。」我說:「發現大家都受到模擬實境的控制。所以我也跟著假裝,直到找到托比亞。」
「妳和托比亞分開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珍寧想要殺了我,但母親救了我。她以前是無畏派,所以知道該如何用槍。」我的身體感覺更沉重,但不再感到冰冷。我覺得胸口有種情緒在翻騰,比悲傷還要糟、比後悔還要糟。
我知道接下來的事情:我母親死了,我殺死威爾;我射中他、殺死了他。
「她引開無畏派士兵的注意力,我得以逃走,但是他們殺了她。」我說。
那些人在追我,我殺了他們。但是我身邊的人群中有無畏派的人,無畏派,我殺死了一些無畏派的人,我不應該在這裡提到這件事。
「我一直跑。」我說:「然後……」然後威爾追著我、我殺了他。不行、不能說。我感覺到髮際線都汗溼了。
「然後我找到父親和哥哥。」我的聲音緊繃。「我們想出一個計畫來摧毀模擬實境。」椅子的扶手邊緣戳著我的手掌心,我隱瞞了部分事實,這當然算是欺騙。
我打敗了血清,在那短短的一瞬間,我贏了。
我應該感到勝利,然而我做過的事卻再次沉重地擊垮了我。
「我們滲入了無畏派住所,父親和我前往控制室。他擊退無畏派士兵,卻犧牲了自己的性命。」我說:「我順利抵達控制室,托比亞就在那裡。」
「托比亞說妳和他發生打鬥,後來卻住手了。為什麼那麼做?」
「因為我明白我們之中必定要有一個人殺了對方。」我說:「而我不想殺死他。」
「妳投降?」
「不對!」我生氣地搖搖頭。「我不算投降。我想起在無畏派新生訓練時在恐懼之境所做的一些事:在模擬實境中,一名女子要我殺死家人,而我要她取而代之殺了我。當時我順利過關。於是我想……」我捏著我的鼻梁,頭開始痛了起來,我失去了控制,腦中所想就這麼脫口而出。「我感到悲痛不已,但是我只能想著:一定有辦法,這其中一定有某種力量;我不能殺他,所以必須放手一試。」
我眨眼,把淚水忍回去。
「所以妳從未受到模擬實境的控制?」
「沒有。」我以掌根壓住眼睛,把淚水擠出來,以免順著臉頰流下來,讓大家都看見。
「沒有。」我又說了一遍。「我沒有,因為我是分歧派。」
「讓我弄清楚。」奈爾斯說:「妳是說,妳幾乎被博學派的人殺掉,卻一路殺進無畏派的住所、並且摧毀了模擬實境?」
「沒錯。」我說。
「我想我可以代表全體的人表示。」他說:「我認為妳為自己贏得了『無畏』之名。」
左邊的大廳傳出陣陣喊叫,我看見模糊的拳頭影像在黑暗的空中高舉。我的派別正在對我呼喊。
但是,錯了,他們都錯了。我不勇敢,不勇敢,我殺了威爾卻不敢承認,我連承認這點都做不到。
「碧翠絲.普里爾。」奈爾斯說:「妳最後悔的是什麼?」
我後悔什麼?我不後悔選取無畏派或是離開克己派。我甚至不後悔槍殺控制室門外的守衛,因為我非要通過他們的防守不可。
「我後悔……」
我的眼睛離開了奈爾斯的臉,掃過大廳,最後落在托比亞臉上。他的臉上毫無表情,嘴巴緊閉成一條線,眼神空洞;他雙手在胸前交抱,緊抓著手臂,以至於指關節泛白。站在他身旁的是克莉絲汀娜。我的胸口緊縮,不能呼吸。
我必須告訴他們,必須說出實情。
「威爾。」我聽起來像是倒抽了一口氣,這聲音好像是從我的胃裡直接吐出來。現在我沒有回頭路了。
「我開槍殺死了威爾。」我說:「他受模擬實境的控制,於是我殺了他。他原本要殺我,但我殺了他。我殺了我的朋友。」
威爾。他的雙眉之間有著皺紋,有一雙芹菜般的綠眼睛,還能憑記憶引用無畏派的宣言。我的胃部傳來強烈的痛楚,讓我幾乎叫了出來。想起他帶來的極大痛楚,我身體的每個部位都好痛。
而且,不只如此,還有一些我之前沒想過的問題。我情願死也不願殺死托比亞,但遇上威爾我卻不曾有這種想法。我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便決定殺了威爾。
我感到無所遁形,不知道原來我把祕密當作盔甲,直到祕密消失,現在每個人都看見了真實的我。
「謝謝妳誠實以對。」他們說。
但是克莉絲汀娜和托比亞什麼也沒說。
「真相一如野生動物,任何牢籠都箝制不住。」
――節錄自直言派宣言
【追捕】
我一面跑,一面數我跑過了幾排樹木。七、八。樹枝沉沉地下垂,剛好僅容我通行。九、十。我越跑越快,將右手抱在胸前,每跑一步,肩上的槍傷便抽痛一次。十一、十二。
跑到第十三排時,我猛地向右拐個彎,沿著一條小徑繼續跑。第十三排的果樹長得很緊密,枝葉交錯生長,形成一片由樹葉、細枝和蘋果所組成的迷宮。
我的肺部因為缺氧而刺痛,但是我就快跑到果園盡頭了。汗水滲進我的眉間。我跑到用餐大廳,用力推開門,橫衝直撞地穿過一群友好派男子...


 2013/04/01
2013/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