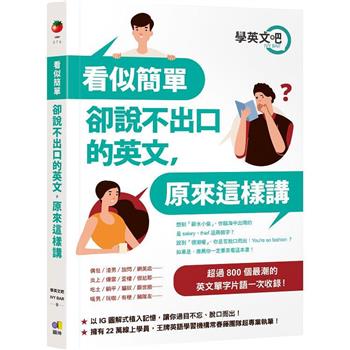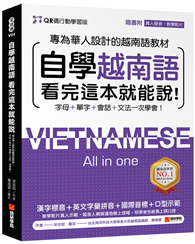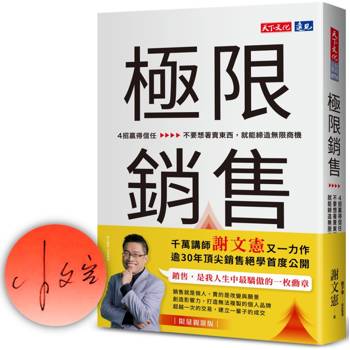符籙、虎爪、靈玉、鎖魂結、引魂燈、聚陰地、修仙、崑崙……道家源流傳承千年,未必一切只是傳說!
四十多年的道士生涯,三十七件精彩Case,風靡兩岸讀友的術士人生!
因為踩著正午十二點出生擁有天生的童子命,讓嬰兒時期的我被百鬼纏身,父母尋訪了村子裡的高人,我的師父── 一個高深莫測的真正道士,註定了我這輩子要做道士。跟著師傅修練闖蕩,遇見冤魂、厲鬼、蛇靈、餓鬼墓……此乃區區小事,苗疆蠱術、神秘的川地南部養屍地、人人聞之色變的滅村傳說……原來平常保衛國家的,除了軍人之外,還有道術的山、醫、命、卜這些派系傳人,玄學世界的神秘面紗即將被揭開……
《我當道士那些年》
卷一:少時驚魂,2013.07出版
卷二:山中修行,2013.07出版
《我當道士那些年》集集精彩,即將推出敬請期待:
惡鬼迷霧
南部養屍地
苗疆風情畫
城中詭事
江河湖海
神仙傳說
(暫定篇名)
本書特色
天涯論壇超級紅帖,百萬人追捧,點擊率超越1500萬次!
長踞磨鐵中文網點擊率榜與付費訂閱榜第一名!
繼《鬼吹燈》《盜墓筆記》之後最精彩的半自傳冒險小說!
帶你一窺神秘的道家世界,請別把我跟神棍混為一談!
卷一、卷二 口碑推薦特價:99元!
作者簡介
仐三
(仐:音同傘)
最早於二○一二年八月在天涯社區發帖,內容後經整理成《我當道士那些年》,同年九月在磨鐵中文網發表。 性格隨和,幽默,正直。有著獨特而豐富的人生經歷,作品《我當道士那些年》與神秘道家文化結合緊密,揭示了一個神秘的道家世界,猜測帶有部分自傳性質,給讀者展示了一段充滿神奇的人生經歷和打開了一扇和現實世界不同的大門,字裡行間常流露出對道及人生的感悟,以及動人之真摯感情,他也被書友親切地稱為「三叔」、「三哥」 「三娃」 「三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