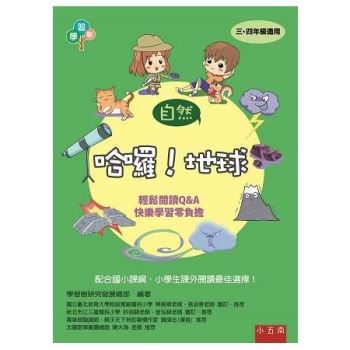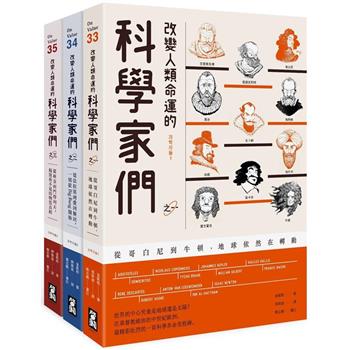永遠別在謀殺案中代入摻私人情緒。
是警官操弄證據,陷無辜之人入獄?
或是心理醫師操弄人心,引發一場復仇計畫?
誰是真凶? 誰是無辜? 誰是真正的受害者?
亞琛市刑警接到一通匿名報案電話:一名小女孩失蹤了。在偵辦此案時,賽菲特和曼克霍夫驚訝地發現,失蹤女孩的父親正是多年前因謀殺兒童案被他們逮捕的心理醫師約希.利希納。當年在經歷了壟長的調查後,利希納被判處多年有期徒刑。當兩名警官再次與利希納狹路相逢時,利希納表示他根本沒有小孩。他堅稱自己一如當年是清白無辜的。難道是警察要再次誣陷他從沒犯過的罪行嗎?為何在多年之後,曼克霍夫警官仍如此痛恨利希納,一心想將他再次繩之以法?過去的噩夢再度輪迴。
一場心理醫師與刑警間的鬥智之戰即將展開……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52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力,找回專注力[靜心升級版] 如果停不下來,就先學會慢下來:52種簡單易行的正念練習,幫你化解壓力,找回專注力[靜心升級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17/2011760340723/2011760340723m.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