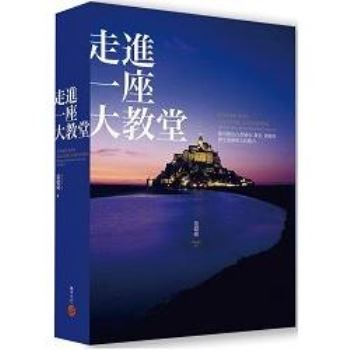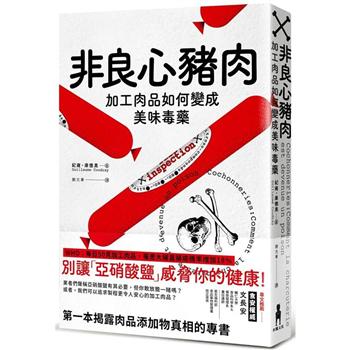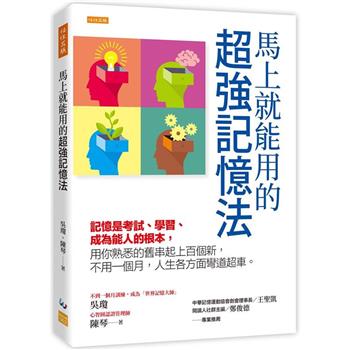CHAPTER 1
神代宗近察覺弟弟薄綠的異狀,至今已經兩個月了。
但最大的不可思議之處,就是察覺異狀的只有自己的這個事實。
跟薄綠住在都心這間半新不舊的公寓生活已經邁入第四年,自己會這麼早購房也是意料外的事,四年前全國在不景氣的狀況下,即使連過去號稱寸土寸金的都心房價也跌得亂七八糟,房地產業難過,「要是再作不出業績的話就只能上吊了啊——」高中時期的好友跑來他面前下跪哭訴。
看來不知道是從哪裡打聽到他成為國家公務員,再怎麼說都有份穩定薪水,付貸款到一半突然落跑的機率較小吧。
「拜託你買下這間公寓吧?在都心喔、都心,旁邊就有附超市的賣場,很方便對吧?而且這區有很多明星學校,以後要是結婚生子,絕——對不會後悔的啦!啊、打開窗戶就能看到那座紅色鐵塔,衝著這點就不知道有多值回票價!」
並不是因為老同學的哀兵策略與三吋不爛之舌而動搖,只是機緣巧合,在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父親被逼著從專務的位置上退休,雖然退休金還算夠用,但也因為自己成為公務員的契機,兩老決定賣掉位在郊區的獨棟平房,跟母親搬回神戶老家,跟那邊的兄弟合作點小生意,賣掉房子的錢三分之一繳了現在住的公寓頭期款,算是他們送給長子宗近的就業大禮。
而還差一年就大學畢業的次子薄綠,也因為新公寓離學校更近的緣故,自然搬來跟大哥一起住。
雖然偶爾會因為無聊的事情起爭執,基本上還算過得平順的兄弟倆,直到三個月前薄綠被捲進一起案件中受了重傷……
在薄綠的傷癒後,宗近卻明顯地發現,「這個」不是自己的弟弟。
「宗,早餐。」
薄綠在宗近發呆時,將早餐端了上來。
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身為忙碌的現代人會在自家早餐吃的東西,白飯、蛤蠣湯、配菜則是味噌鯖魚。
「我要開動了。」薄綠闔掌後,開始用自己的那份。
宗近端起碗筷,扒飯進口。非常好吃……不、應該說完全超乎家庭料裡的水準,柔軟的魚肉完全吸取了紅味增的甜味,配上爽口的薑絲更增添了足以讓昏沉腦袋清醒過來的鮮辛;蛤蠣湯也是精心之作,昆布為底的湯內還加了新鮮香菇、木芽與筍片。
正因為太好吃了,已經連續兩個月的早餐都這麼好吃了!所以宗近才更加確定,眼前這個跟薄綠長得一模一樣的傢伙絕對不是自己的弟弟!
薄綠早上有低血壓跟壞脾氣,基本上只喝咖啡而已,平時如果還願意大發慈悲地順便幫他泡一杯來就謝天謝地了。
另外、薄綠雖然偶爾也會進廚房,但廚藝低落到讓品嚐者會因為過於同情而忍不住全部吃完,炒蛋一定會有蛋殼混入、咖哩的馬鈴薯從沒削過皮,甚至有忘記放咖哩塊的紀錄。
雖然聽說有那種接受移植器官的人在恢復健康後吃飯的口味跟習慣會變得跟以往不同,但薄綠這種簡直像是變了一個人的狀況實在是匪夷所思。而且,他也沒移植什麼器官,只是輸血輸多了點而已。
「你不喝咖啡了嗎?」宗近推了下鼻梁上的粗框眼鏡,試探地問。
「咦……」薄綠抬起頭,像是思索了下,最後道:「你說那個又苦又酸的飲料嗎?」
「……為什麼說得一副好像第一次喝到咖啡的口吻……」宗近挑了下眉。
薄綠果然變得很奇怪。
「對、對了,是那個,突然不喜歡喝了。」薄綠像是一秒鐘前才剛想到理由似地道:「而且空腹喝咖啡對身體不好,宗以後也得少喝。」
「你管太多了。」宗近抿了下唇。
這種超級不自然的態度……還有、在那之前,薄綠都是稱呼自己「哥哥」,而不是什麼「宗」。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果然還是應該要問清楚才對吧。可是、要是薄綠他……
兩人沉默地吃著早餐,一會兒,薄綠像是企圖挽回氣氛地開口:「宗,那個,晚餐想吃什麼?」
一邊吃著早餐然後討論晚餐的事嗎……宗近在內心默默地嘆氣,隨口道:「漢堡排。」
薄綠像是又思考了會兒,說了:「我知道喔,就是那個像肉團子一樣東西吧。」
之後,雙眼發光,似乎想讓宗近稱讚他。
「啊啊,嗯,就是那個。」所、以、說……到底為什麼要用那種好像從來沒吃過這道料理的口吻說呢?而且漢堡排對「以前的」薄綠還說太難了,肯定做不出來。
話題又這樣停了下來,雖然兄弟本來在早晨的飯桌上話題就不多,但氣氛變得如此尷尬倒是少見。
在終於把早餐吃完後,宗近像是鬆了口氣般離坐。薄綠趕著把最後一口湯嚥下,非常俐落地將兩人的餐具收到廚房。
「我出門了。」宗近背起肩包。
「等等、一起走到車站吧。」薄綠在廚房喊。
宗近只好等。
以前的薄綠不喜歡跟自己出門,正確來說,不喜歡跟自己走在一起。
因為薄綠長得很顯眼,大眼睛、有著透明感的白皮膚,以男人來看的確是過於秀氣了些……跟自己完全呈反比。
——你們是兄弟?哈哈,不如說兄妹吧?而且長得完全不像耶。
已經不只一次被別人這麼說過了,宗近也不想自己長這麼高,而且他又是容易長肉的體質,稍微不注意就會變胖,為了外觀著想,只有奮發鍛鍊身體一途……結果在外表上就跟薄綠相差越來越大。
之後甚至有被說過「好像偶像歌手跟保鏢」。總之、薄綠跟自己走在一起時,受到注目的程度會比只有一人時要來得更高,所以盡可能地避免這種機會吧。
兩人出了公寓大門,往車站的方向走去,一臺墨綠色的三菱房車在兩人走出一段路後,在後面緩緩跟隨滑行。
四天了……那臺車跟著自己已經四天了。宗近咬了下齒根。一開始只覺得好像有視線盯著自己,開始仔細留意後,就察覺那視線的來源發自何方。
充滿敵意的視線……雖然因為工作的關係,被人怨恨算是家常便飯,但被跟蹤倒是頭一遭。輕舉妄動的話恐怕薄綠也會被捲入,所以目前也只有提高警覺,等對方先動手再後發制人——
「宗,快跑!不要回頭!」
宗近背後突然遭薄綠用力推了一把,但他又怎麼可能乖乖聽從弟弟的警告,用力扭回頭,只看見那輛車上迅速跳下兩個男人,就往他們衝來。
「綠?怎麼回事!」宗近瞪大眼。
「不要管!那是來抓我的,跟宗沒有任何關係,快走!」薄綠大吼。
「我怎麼可能丟下你!」宗近不知道為什麼薄綠要這麼慌張,即使對方有兩人,但手上並沒有持任何武器,要是真有帶什麼危險物,只要在使用前先打倒就行了,唯一要小心的是別讓薄綠被抓住而已。
「不是那種問題!啊啊……可惡!居然帶土蜘蛛來!」薄綠的雙眼緊盯男人們的身後,又用力往宗近一推,把他推出兩三步外。
砰的一聲巨響,前一秒宗近所在的位置,柏油路面上竟凹陷了一個大洞,土石齊飛。
「什、」麼……
宗近愣住,突如其來的恐懼感在瞬間壓制住全身。
有什麼東西在……有什麼看不見的東西在!如果不是薄綠搶先推開自己的話,自己已經被那個東西砸得血肉模糊了。
「宗什麼都不知道!放過他!」薄綠繼續往那兩人吼叫。
但其中一個男人只是搖了下頭。
薄綠立刻又往宗近衝來,這回宗近被撞倒在地,在頭昏時奮力睜開眼。那是一幅只能以異常來形容的光景,薄綠纖細的雙手撐著地面,離宗近的身體還有一段距離,漂亮的臉孔扭曲著,鮮紅液體從嘴角流了出來。
最駭人的是,薄綠的胸前像被什麼東西給貫穿似的,開了一個透明的大洞——就在心臟的正上方。
「綠……」這樣、薄綠又要……死……
「……咕、不過是……區區土地神……咳……」薄綠噴出大口血,握緊了拳頭,「……月光、斬——」
僅僅一瞬間,幾乎讓人漏聽的風聲擦過宗近耳邊。
砰咚砰咚!不知從哪裡傳出了巨大物品掉落聲,最後甚至發出了像是支撐不住重量的崩毀「喀嚓」聲。
身上壓力頓時減輕,薄綠立刻從宗近身上翻身跳起,只見他一手壓著胸前的洞,滿臉猙獰地瞪著兩個男人。「哈、高野的和尚……也不是我的對手……還不快退下!」
「哼、不過砍了我的車,有什麼好得意的?沒了主人的刀只是廢鐵而已。」男人之一冷笑道。
「你說……什麼……」薄綠氣得全身顫抖。
「念在你還沒吸那個普通人的血,這回就暫時放你一馬。不過……也不會太久,就到今晚夜明前,我們還會再來……到時、帶來的就不是普通蜘蛛,而是蜘蛛女王了。請趁這段期間好好地,跟『哥哥』道別吧。」
***
回想起來,宗近自己都覺得很丟臉,他什麼也沒辦法做,竟被那樣怪異的情景給嚇得雙腿發軟,最後能做的只有把渾身是血的薄綠勉強扛回家而已。
——已經不是醫生能處理的東西了——長期去道場鍛鍊的他很明白人體的弱點,尤其薄綠胸口的洞已經破壞掉部分內臟,然而出血量卻比想像中的少,甚至還能忍著劇痛保住意識。那是連自己都辦不到的事。
望著癱在沙發上的薄綠,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雖然想幫對方倒杯水,但看現在的狀況,即便能喝,水大概也會從胸口那個洞流出來吧。而且、他很怕在自己離去之時,對方會就此雙眼一閉,就這樣,永遠地……
「要怎麼樣才能救你?」宗近握著薄綠被血染成紅色的手。
薄綠像是有點吃驚地望了過來。「宗……對不……起……我、其實……」
「『不是我的弟弟』……這種事情早就知道了,現在重要的是如何讓你復原,一定有方法的吧?」因為、薄綠……這個、跟薄綠長得一模一樣的傢伙,大概,不是人類。
「刃物……」薄綠蠕動唇。
「刃?」銳利的金屬器?
「拿……給我……」
「什麼樣式的?美工刀?菜刀?」宗近追問。
「……家裡、所有的……刃……」
「知道了,等我。」宗近用力握了一下薄綠的手,很快地起身在公寓內四處翻找,一會兒就拿來了兩把美工刀、廚房的水果刀、切肉刀跟菜刀,之後又趕緊拿來了不知道搆不搆得上邊的剪刀。
薄綠顫著手指,觸碰那些宗近拿來的各種刀具,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但急促的呼吸似乎有緩和的趨勢。
「不夠的話我去買!」宗近立刻道。
「……新的、沒有用……上面沒有……灌注使用者的、靈魂……」薄綠把手指抽回,「如果有『刀』或是『劍』的話……最好、但……這個年代……也沒辦法、強求……」薄綠苦笑了下,胸口的洞仍在出血,薄綠的臉色已經白得似死人,能透過肌膚看見下面青藍的血管。
宗近的心臟也緊得難受,三個月前也是這樣,他坐在急診室外頭恍惚地瞪著天花板,腦內盡是不好的想像,護士甚至奔出來大吼著從運送員手中搶過一袋袋血。
——薄綠被人拿刀刺了。
一通在他工作時打來的電話,冷冰冰地說明了經過,情況很不樂觀,要他趕到醫院。
他什麼也沒辦法做,甚至不敢通知雙親。他們把唯一的兒子交給自己照顧,卻讓他出了這麼嚴重的事。
「……不是金屬做的刀,可以嗎?」宗近突然問。
「那是、什麼刀?」
「竹刀!我一直在練的!」
「……嗯。」
宗近連忙起身奔到自己房裡,從黑色套袋內取出每週定期保養擦拭的竹刀。重回客廳,他將竹刀小心翼翼地放到薄綠眼前。
薄綠的表情稍稍變了,下一秒,如餓狼貪求生肉般朝竹刀撲了上去,緊緊抱住不放。
「這個……怎麼樣呢?」宗近問。
「……超、舒服……」薄綠像抱著戀人那樣,露出既溫柔又帶了點情色的微笑,「……想不到宗還藏了這麼棒的女人在房裡……這時真想來杯酒……」
胸前的空洞逐漸被增生出來的肉塊填滿,自然也不再流血。宗近又再次確定「這個」並非人類的事實。
「女、什……」雖然薄綠好像稍微恢復精神了,結果卻開始說奇怪的話……雖然說要拿刃物來療傷什麼的這點就已經夠奇怪了……
「『她』啊。」薄綠對那把竹刀愛不釋手,還把臉頰貼上去摩擦,「小竹。」
「不要擅自幫別人的東西取名字!」
「才不是我取的,她自己說她叫小竹。」薄綠抗議。
「……那、你是誰?」決定放棄爭執竹刀的名字,宗近疲憊地坐到薄綠身邊,聲音顯得相當沉重。
「三日月。三日月……宗近。」
「跟我、同名?」
「不是,宗是打造我的人,就跟父母一樣,當時習慣將工匠的名字放在刀名之後。我是銘刀三日月,地位在九十九神之上、超越土地神,是備受尊崇的偉大神靈!」
「自己說偉大啊……」而且,刀?還有神靈什麼的……
「不只偉大,我還是國家的寶物!在國立博物館內收藏著我的模造品。」三日月驕傲地道。
「也就是說,你是一把刀。」宗近冷淡地重複,既不表示信,也沒說不信。
「沒錯。」
「那我弟弟呢?」
三日月明顯地愣了下,歪著頭,又搔了下臉。
「你把綠弄到哪裡去了!」宗近吼道。
「……『這裡』?」三日月陪著笑臉,指著自己的臉。
「別開玩笑了!」
「才、才沒有開玩笑呢,你弟弟受傷的地方正好是封印我的結界環之一,他的血有鍛造師的氣味,融進結界環之後造成封印鬆動,我是無意識間鑽到他的身體裡去的。」
「聽不懂。」宗近環起胸。「總之,可以把綠還我了吧!」
「現在離開這具身體的話,弟弟君會死喔。」三日月噘了下唇,「……不如說早就死了,現在維持所有器官活動的人是我。」
「你說……什麼?那天晚上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宗近把手指伸進短髮中用力搔著,三個月前的夜裡,事情突然就這麼發生了。薄綠被不明人士從背後襲擊,刺了三刀,雖然都離要害差了點,但失去的血量可不是開玩笑的,如果不是剛上完夜班抄小路回家的便利商店店員湊巧發現,現在早已經……不、剛才「這傢伙」說、「已經」……
「我不知道,雖然我也對擅自使用這個身體感到抱歉,但我是因為嚐到這個人的血氣才甦醒過來,在那之前到底發生什麼,我完全不知道。你兇我也沒用,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三日月露出了像在鬧彆扭的表情,之後就抱著竹刀偏過頭去。
跟薄綠……一樣,不高興的時候,這種表情……
「綠說不定還活著啊!是你搶了他的身體,所以才沒辦法……」宗近還抱著點希望。現在……「弟弟」仍舊好好地在面前活動著不是嗎?
「……這種事情對人類來說的確很難理解,我現在雖然甦醒了,卻是靈體的狀態,人類的話就是靈魂,靈魂裝在以肉體為名的容器內才能活動,每個容器的容量都有其限度,即使能夠強制附身,但在兩魂都保有活力的狀況下,不管是哪一邊都會覺得擁擠,可是啊……這具容器現在非常寬敞,甚至差點有錯覺認為這個就是自己真正的身體那樣舒服,也就是說,這個容器本來的內容已經空了、不存在、消——」
「住口!」宗近用力摀住三日月的嘴,「綠還活著,可能只是睡著了而已!不要亂說!」
三日月望著眼前高大的男人眼中竟泛出淚光,腦海裡鮮明地回想起三個月前,這具軀體能夠自行呼吸並睜開眼時,他所看到的也是類似的情景,只是,當時的宗有著欣喜與放心,這回卻只是在逞強而已。
「……唔唔呼呼(對不起)。」
「總有一天,要讓你把綠還來……」宗近吐出近似於戰敗後的放話,咬著牙,把手抽回。
「雖然我也想這麼做,但是……」
「對了,那兩個人!為什麼要追你?」
「他們是驅魔人……正確來說只有高野的和尚是,另一個是妖魔類的東西,但我不清楚。自開國以來,南蠻的妖物也能隨意進出了,真是的,一堆沒見過的品種。」三日月皺著眉抱怨了下,又繼續說:「驅魔人要抓我沒什麼特別的,身為接受供奉的神物,也同時被強加了許多責任在身上。」
「責任?」
「嗯,守護這個國家的靈脈。」
「……啊?」
「聽不懂也沒關係啦,用現代的話來說,現在的我像是擅自從工作崗位跑走……那樣的感覺?」三日月又苦笑了下。「雖然並不排斥回去守靈脈,反正只是睡覺而已,但要是我這樣走掉的話,這具身體就……」
「那是你這三個月以來一直待在我身邊的理由嗎?」為了,讓薄綠能夠繼續「活著」。
「……哎、這個……怎麼說也是被弟弟君的血氣給喚醒的,像是奉獻了什麼給我一樣,身為偉大的神靈,不、不能光接受獻祭卻什麼都不做嘛。」三日月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地嘀咕。
「那、我也奉獻些什麼給你,能把綠還給我嗎?」宗近立刻問。
「雖然我是偉大的神靈,但也不是什麼都辦得到啊。若要與泰山府君交涉還魂,得去找陰陽師,而且……就我所知能辦得到這種事的陰陽師從過去到現在也只有三人。」
「誰?」
「安倍家的晴明,土御門家的花千代,天龍寺家的鬼綱。」三日月扳著手指。
「呃……」安倍晴明的確是很有名,但那是平安時代的人吧!「後面兩位……現在還活著嗎?」
「當然都已經不在世上了。」三日月理所當然地道。
「那、那總有他們的後人有學習到那個、起死回生什麼的魔法吧?去拜託他們的話……而且,你怎麼知道除了他們三人之外沒有其他人成功過?」
「雖然有點能力的傢伙要到陰間遊玩也不是辦不到,但要把已經到達彼岸的死魂拉回陽世卻非常困難,得配合天時地利,天時就是時辰、地利則是我所守護的東西,也就是這個國家的土地底下所流通的氣息,又叫靈脈。
就算是再高明的陰陽師,本身的力量也有其限度,但加上土地本身的力量就會輕鬆得多。雖然我被封印之後就處於睡著的狀態,但追尋過去的歷史洪流記憶中,誰借了靈脈的力量去用這種重要的事基本上還是會曉得啦……
晴明一次、花千代一次、鬼綱兩次,但第二次他雖然把對方的魂魄送回來,他自己卻留在彼岸了,那是他跟泰山府君交換的條件。」
宗近一時無語。雖然聽到的盡是些無法立刻叫人相信,光怪陸離的玩意兒,但已經親身體驗過被看不見的怪物攻擊,又注意到薄綠的異變,總覺得、那些並不是憑空編造出來的事。
「宗是普通人,所以不要考慮這種普通人辦不到的事,而且生死之術很危險,基本上我不建議任何人……包括陰陽師在內去碰這種術,大幅度干涉他人命運的傢伙不會有好下場的,這可是經驗談。所以,如果、真的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接受弟弟君的事情……我會,待在這裡陪你的。」
像是,在安慰人。三日月摸了下宗近的頭。
宗近心想,真是奇怪的神,因為擔心自己會難過,所以,就這樣假裝成薄綠……雖然很努力,可是一點也不像。有點、只有一點點……可愛啊。
「綠……」不對,「三日月。」
「嗯?」
「你是什麼時候的人?」彷彿閒聊般,宗近問了,
「是銘刀。」三日月強調。
「好好。刀就刀。」
「我換算一下……唔、平安?」三日月歪著頭,「總之,有個叫三条宗近的鑄造師打出了我,至於為什麼取名三日月,是因為刀刃上的波紋呈新月的模樣。雖然並沒有在他身邊待很長的時間,但那時候每天聽著噹噹的錘子聲,真的很快樂啊……怎麼了?」
「不、沒事,只是想……還真久以前啊。」姓「三条」的鑄造師……吶。
「嗯嗯,很久喔。之後我被獻給秀吉大人的正室高台院夫人,夫人過世之後,我又作為她的遺物被……」
「等、等等,那個『秀吉』該不會是……」
「嗯,豐國大明神大人的秀吉,唉呀,可真是變得相當偉大了呢。」三日月感嘆地道,「不過還是身為側室的茶茶夫人比較美就是,以前我有時候會偷偷溜出去看她,還有她的薙刀出雲,那也是跟主人一個樣,品格高尚、性子強悍的美人,跟她搭了半天話,卻一次也沒理……咳、總之……夫人過世之後,我被贈給德川秀忠大人,之後就在德川家傳承了幾代,最後,被挑選為最適當保護國家靈脈的銘刀之一,交由當時的陰陽師封印在靈穴上。以上,就是我三日月宗近的生平。」
「除了你之外,還有其他刀也守護著靈脈嗎?」宗近好奇地問。
「那是當然的,要守護靈脈並不是那麼簡單的工作,為了完成最強的守護陣五芒星,那可是在全國的銘刀中精挑細選,還要配合屬性跟歷任使用者給予的靈力,我是水屬,被封印後又叫冰華三日月,其他還有金屬的大典太光世、木屬的童子切安鋼、火屬的鬼丸國綱、土屬的數珠丸恒次。」
「那……缺了你的話,守護靈脈的工作不就……」以宗近的立場來說,只要有任何一點薄綠的生機他都不想放過,在目前自己無計可施的狀況下,三日月能自願繼續讓這具身體正常運作下去是最好的。
「這個嘛,其實對守護靈脈的任務來說,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雖說封印鬆動,但被釋放出來的只有意識而已,我真正的身體——就是刀本體的部分還是繼續在原處被供奉著。」
「既然如此,為什麼驅魔者還要把你帶回去?」
「因為危險吧,對沒有什麼力量的人類來說,已經從九十九神昇華為神靈的我們,是很具威脅性的存在。」三日月壓了壓下唇,「只有意識被放出來活動,難保哪天不會想取回身體,到時候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為什麼很麻煩?」
「因為是刃物的靈。」三日月看宗近仍然不明白,只好補充:「我們是為了殺人,所以才被做出來的東西喔。」
「啊……」宗近張了張嘴。
「難保不會有這樣的欲望……驅魔人會這樣想的吧。而且實際上也是因為嗅到血氣而甦醒的,要完全擺脫這方面的本能也是難事。」
「……會、想要殺人嗎?」宗近變得有點小心地問道。
「斬殺普通人的話一點意義也沒有。」三日月嚴肅起來,「但是想要跟厲害的人過招,賭上所有的精力與技巧的戰鬥,並不是因為懷著怨恨,甚至沒有殺意,只是想證明自己比較強而已……雖然這麼想,但最終結果讓對方不得不死去的話,也算是從這個時代看來很脫軌的願望吧。」
「像體育選手那樣嘛,只是、你是刀而已。」宗近反射說出了,連自己也沒想到的,彷彿像是幫三日月辯解的話。
像個真正的武士。
宗近因為長期到道場練習,所以在這個部分能夠與對方有所共感,雖然不是拿真刀決勝負,但那追求速度、技巧與體力的結合,渴望與達者過招、並且超越對方的心情——只要手上握著竹刀,赤腳站立在那片木板地上時,就能盡情追求強悍。
「謝謝你,宗。」
三日月微笑。
宗近愣了下,總覺得很難過,在他的記憶中,薄綠似乎……沒有對這自己這樣笑過。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妖刀前線注意報(1)~逢魔三日月~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妖刀前線注意報(1)~逢魔三日月~
那把刀的出現,將習以為常的平靜生活硬生生地——斬成碎片。
這年頭想當個安分守己的刑警有這麼難嗎?神代宗近就是知道眼前的「弟弟」絕非跟他一起長大的手足,果不其然……
我是銘刀三日月,地位在九十九神之上、超越土地神,是備受尊崇的偉大神靈!
日常從眼前崩壞,打從跟這把假扮弟弟的刀扯上關係以來就開始厄運不斷,操縱巨大蜘蛛的危險人物襲來、無故被調動的新單位中可能只有他是人類、而接踵發生的超常事件竟要他負責解決?等等、那他弟弟到底怎麼了?喂!誰來給他解答啊——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紫曜日みな
大阪交流藝術學院畢業。
日美刑事劇熱愛、推理小說中毒、球體關節人偶迷戀、TALES OF電玩系列全番攻略。
討厭甜食。
歡迎諸君到FB粉絲團發表讀後感,或者來攤位上打招呼。
噗浪地址:http://www.plurk.com/f8950023
作品集
「閻王的特別助理」、「牡丹非花」、「冥道」、「妖刀前線注意報」
繪師介紹
CAT姬
愛吃愛玩愛滾床的喵一隻,
以畫圖創作維生!
希望能一直畫到~
世界的盡頭!
家有噗浪歡迎加加我!
Plurk>>cat_g
章節試閱
CHAPTER 1
神代宗近察覺弟弟薄綠的異狀,至今已經兩個月了。
但最大的不可思議之處,就是察覺異狀的只有自己的這個事實。
跟薄綠住在都心這間半新不舊的公寓生活已經邁入第四年,自己會這麼早購房也是意料外的事,四年前全國在不景氣的狀況下,即使連過去號稱寸土寸金的都心房價也跌得亂七八糟,房地產業難過,「要是再作不出業績的話就只能上吊了啊——」高中時期的好友跑來他面前下跪哭訴。
看來不知道是從哪裡打聽到他成為國家公務員,再怎麼說都有份穩定薪水,付貸款到一半突然落跑的機率較小吧。
「拜託你買下這間公寓吧?在都...
神代宗近察覺弟弟薄綠的異狀,至今已經兩個月了。
但最大的不可思議之處,就是察覺異狀的只有自己的這個事實。
跟薄綠住在都心這間半新不舊的公寓生活已經邁入第四年,自己會這麼早購房也是意料外的事,四年前全國在不景氣的狀況下,即使連過去號稱寸土寸金的都心房價也跌得亂七八糟,房地產業難過,「要是再作不出業績的話就只能上吊了啊——」高中時期的好友跑來他面前下跪哭訴。
看來不知道是從哪裡打聽到他成為國家公務員,再怎麼說都有份穩定薪水,付貸款到一半突然落跑的機率較小吧。
「拜託你買下這間公寓吧?在都...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紫曜日
- 出版社: 三日月 出版日期:2014-02-12 ISBN/ISSN:9789861859569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