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批駁韋伯學說的謬誤,倘若我們以韋伯所謂的「理性化」和「除魅化」來界定「現代化」,則在儒家文化的發展史上,一共經過了三次「現代化」:在「軸樞時期」,孔子及其門人解釋《易經》,完成了儒家文化的第一次「理性化」;宋明時期,程朱「理學」一派強調「道問學」和陸王「心學」一派強調「尊德性」,是其第二次現代化。
在「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裡,宋明理學家很難將具有「普遍性」的儒家價值理念建構成形式性的理論,來說清楚「儒家價值是什麼?」因此,儒家文化的第三次現代化,必須充分吸納西方文明菁華的科學哲學,以「多元哲學典範」來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
本書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先建構普世性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羅模型〉,再以之作為參考架構,重新詮釋先秦儒家思想的內容,藉以描繪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態學」。然後再對儒家思想分析其「文化衍生學」,而分別討論:程朱的理學、陸王的心學、明清的經學,以及陽明學對於日本的影響。
在二十一世紀中,華人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任務,是要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黃光國
台北市人,出生於1945年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社會科學的理路》、《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教育部國家講座兩次。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亞洲心理學會會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卓越計畫主持人,目前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及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台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及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黃光國
台北市人,出生於1945年11月6日。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致力於結合東、西文化,以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發展本土社會心理學。著有《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民粹亡台論》、《教改錯在哪裡?》、《社會科學的理路》、《一中兩憲:兩岸和平的起點》、《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倫理療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以及中英文學術論文一百餘篇。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優良研究獎十餘次、教育部國家講座兩次。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亞洲心理學會會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卓越計畫主持人,目前為海峽交流基金會顧問及總統府國策顧問、台灣大學終身特聘教授、台大講座、傑出人才講座及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亞洲本土及文化心理學會會長。
目錄
第一部:以理論挑戰韋伯學說
第一章 韋伯學派與東方主義
第二章 多重哲學典範:由「集體主義」到「關係主義」
第三章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智慧與行動
第二部:傳統中國的理性化
第四章 西歐與中國:解除世界的魔咒
第五章 西方的眼鏡:巫術或科學?
第六章 「天道」與「鬼神」:儒家道德的形上學基礎
第三部: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態學
第七章 儒家的庶人倫理:「仁、義、禮」倫理體系
第八章 儒家的「士之倫理」:濟世之道
第九章 「道」與「君子」:儒家「自我」的追尋
第十章 反思與實踐:儒家的自我修養理論
第十一章 歷練與中庸:儒家的政治行動理論
第四部:儒家的文化衍生學
第十二章 程朱的理學:「正宗」或「別子」?
第十三章 陸王的心學:由「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
第十四章 經學的反思:從「批判」到「揚棄」
第十五章 陽明學在日本:武士刀與算盤
第十六章 本土社會科學:從「復健」到「復興」
第一章 韋伯學派與東方主義
第二章 多重哲學典範:由「集體主義」到「關係主義」
第三章 自我的曼陀羅模型:智慧與行動
第二部:傳統中國的理性化
第四章 西歐與中國:解除世界的魔咒
第五章 西方的眼鏡:巫術或科學?
第六章 「天道」與「鬼神」:儒家道德的形上學基礎
第三部:先秦儒家的文化型態學
第七章 儒家的庶人倫理:「仁、義、禮」倫理體系
第八章 儒家的「士之倫理」:濟世之道
第九章 「道」與「君子」:儒家「自我」的追尋
第十章 反思與實踐:儒家的自我修養理論
第十一章 歷練與中庸:儒家的政治行動理論
第四部:儒家的文化衍生學
第十二章 程朱的理學:「正宗」或「別子」?
第十三章 陸王的心學:由「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
第十四章 經學的反思:從「批判」到「揚棄」
第十五章 陽明學在日本:武士刀與算盤
第十六章 本土社會科學:從「復健」到「復興」
序
自序
中華文化的第三次現代化
本書題為《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其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三章,第一章先談韋伯學說的謬誤及其對國際學術社群的重大影響,接下來的兩章分別說明:我如何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建構普世性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孔門解釋《易經》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其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西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間的600年間,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Axial Age)。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本書第二部分包含三章,第四章強調:倘若我們以韋伯所謂的「理性化」來界定「現代化」,則在儒家文化發展的歷史上,一共經過了三次不同性質的「現代化」。在所謂的「軸樞時期」,老子和孔子門人分別解釋《易經》,儒教和道教已經分別完成了第一次的「理性化」過程。第五、六兩章分別說明:老子解釋《易經》,使道家門人發展出中國的科學;孔子及其門人解釋《易經》,則發展出中國的倫理與道德。
第三部分共有五章,分別以普世性的「關係」與「自我」的理論模型,重新詮釋先秦儒家思想的內容,藉以描繪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態學」(morphostasis)。用韋伯的概念來說,儒家文化在第一次現代化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型態,其特徵為「理性的順應」,和西方世界在基督新教倫理興起後發展出來的「理性的控制」有其根本的不同。
理學家的「道問學」
本書第四部分亦包含五章,分別討論:程朱的理學、陸王的心學、明清的經學,以及陽明學對於日本的影響,這是在對儒家思想作「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的分析。在這個階段,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程朱「理學」一派所強調的「道問學」和陸王「心學」一派所強調的「尊德性」。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思維的特色,來說明儒家第二次「現代化」的意義。
黃俊傑(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一書中指出:傳統中國史家與儒家學者都主張: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淑世、經世,乃至於救世。為了彰顯儒家價值的淑世作用,他們都非常強調:以具體的歷史「事實」來突顯儒家的「價值」,並在歷史「事實」的脈絡中說明儒家「價值」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重變以顯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學城所說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浸潤在儒家文化氛圍中的傳統中國史家認為:價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於歷史與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從「具體性」的史實之中提煉或抽離而出,黃俊傑稱之為「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麼呢?本書第十二章對於程朱理學的論述指出:朱熹主張「理一分殊,月印萬川」,認為源自「天道」的「理」會呈現在「人心」或諸多事物的素樸狀態中。他從各種不同角度,反覆析論: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所謂的「五常」都是「理」的展現;而張載則是努力要刻劃出「儒家的心之模型」。
但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裡,宋明理學家雖然致力於「道問學」,他們卻很難將具有「普遍性」的儒家價值理念建構成形式性的理論,來說清楚「儒家價值是什麼?」這也是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再從中國歷史思維的特色,說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現代化的必要。
形式性的理論模型
傳統中國史學家重新建構具體而特殊之歷史事實的最高目標,是為了要從其中抽煉出普遍性的原理,以作為經世之依據,正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言: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由於太史公著書立說之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以他「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寫成本紀、世家、列傳的對象,泰半是王侯將相,殊少納入一般庶民百姓,而形成中國史家「以史論經」的傳統。朱熹也有類似觀點:
「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古史餘論〉
朱子認為:三代相承之「理」,「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但只有聖人之「心」才能夠「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並將儒家所重視的「人綱人紀」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基於這樣的歷史觀,中國傳統史家傾向於將注意焦點集中在統治者身上。這就是朱子所說的:
「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事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己酉擬上封事〉
這樣的觀點當然不可能再適用於現代華人社會。因此,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必須充分吸納西方文明菁華的科學哲學,以「多元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必須適用於華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不僅止於「帝王將相」。就拿朱子最關注的「人綱人紀」來說,本書第七章提出「儒家的庶人倫理」,可以解釋「五常」中的「仁、義、禮」。本書第三章〈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的「智慧」,則是「五常」中的「智」。至於「信」則是雙方互動的結果,無法以這些形式性的理論模型表現出來。但本書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理論」,卻可以用來說明華人社會中一個人的行動。
用Gergen(2009)的概念來說,「仁、義、禮」是「第一序的道德」(first-order morality),是可以用規範、原則或律則表現出來的道德。「智」則是「第二序的道德」(second-order morality),自我必須隨機應變靈活地將它展現在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之中。這五個概念,並不是同一層次的東西,儒家卻將之並列為「五常」,傳統儒家以及人文學者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加以詮釋,都不容易說清楚。
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
我們可以再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宏觀角度,來說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現代化的意義。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
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無法定下心來,吸納西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以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
「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提出的概念。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長在於「綜合的盡理精神」,是一種「理性的運用表現」。相對地,西方文化則擅長「分解的盡理精神」,以「理性的架構表現」,透過一種「主、客對立」的「對待關係」,而形成一種「對列之局」(co-ordination),從而撐出一個整體的架構。由於中國文化向來注重運用表現,強調「攝所規能」、「攝物歸心」,在主體中以「天人合一」的方式,將對象收攝進來,成為絕對自足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下,要轉換成「架構表現」,便只能「曲通」,而不可能「直通」。
什麼叫做「曲通」呢?針對這個議題,牟宗三提出了良知或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也就是絕對自足的良知,暫時地對其「運用表現」存而不論,轉而讓知識主體以及政治主體,能夠依據各該領域的獨特性發展;在創造科學與民主的活動之後,再用道德理性加以貫穿。
政治主體如何透過良知的「自我坎陷」而開出民主政體,這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範疇,在此暫且不論。然而,從我對於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主張來看,知識主體要想發展社會科學,還得定下心來,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哲學,才有可能運用「分解的盡理精神」,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以「對列之局」實質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生活場域中,運用其「綜合的盡理精神」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後果。
若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心理學本土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建構各種不同的含攝文化之理論,說明中國人在學習源自西方的「知識」之後,如何「轉識成智」,以其「綜合的盡理精神」,在「理性的順應」和「理性的控制」之間找到「中庸之道」,以維持一己的「心理社會均衡」。用孔子強調的行動法則來說:這就是「汝安,則為之!」
更清楚地說,牟宗三以「理性的運用表現」和「理性的架構表現」分別描述中、西文化之特長,但他卻不知道如何整合這兩者,所以才會想出令人費解的良知「自我坎陷」說。我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寫出這一系列的著作,正是要補充牟宗三之不足,以完成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2015年4月15日
參考文獻
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黃俊傑(2014):《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ergen, K. (2009).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pers, K. (1949/1953).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中華文化的第三次現代化
本書題為《盡己與天良:破解韋伯的迷陣》,其內容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三章,第一章先談韋伯學說的謬誤及其對國際學術社群的重大影響,接下來的兩章分別說明:我如何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建構普世性的〈人情與面子〉理論模型,以及〈自我的曼陀羅模型〉。
孔門解釋《易經》
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其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西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間的600年間,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Axial Age)。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本書第二部分包含三章,第四章強調:倘若我們以韋伯所謂的「理性化」來界定「現代化」,則在儒家文化發展的歷史上,一共經過了三次不同性質的「現代化」。在所謂的「軸樞時期」,老子和孔子門人分別解釋《易經》,儒教和道教已經分別完成了第一次的「理性化」過程。第五、六兩章分別說明:老子解釋《易經》,使道家門人發展出中國的科學;孔子及其門人解釋《易經》,則發展出中國的倫理與道德。
第三部分共有五章,分別以普世性的「關係」與「自我」的理論模型,重新詮釋先秦儒家思想的內容,藉以描繪出先秦儒家思想的「文化型態學」(morphostasis)。用韋伯的概念來說,儒家文化在第一次現代化所發展出來的文化型態,其特徵為「理性的順應」,和西方世界在基督新教倫理興起後發展出來的「理性的控制」有其根本的不同。
理學家的「道問學」
本書第四部分亦包含五章,分別討論:程朱的理學、陸王的心學、明清的經學,以及陽明學對於日本的影響,這是在對儒家思想作「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的分析。在這個階段,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程朱「理學」一派所強調的「道問學」和陸王「心學」一派所強調的「尊德性」。我們可以從中國歷史思維的特色,來說明儒家第二次「現代化」的意義。
黃俊傑(2014)在其力作《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一書中指出:傳統中國史家與儒家學者都主張: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淑世、經世,乃至於救世。為了彰顯儒家價值的淑世作用,他們都非常強調:以具體的歷史「事實」來突顯儒家的「價值」,並在歷史「事實」的脈絡中說明儒家「價值」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的「重變以顯常,述事以求理」,也就是章學城所說的「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範焉」。浸潤在儒家文化氛圍中的傳統中國史家認為:價值理念的「普遍性」(universality)深深地根植於歷史與人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之中,而「抽象性」的「天道」或「理」,也可以從「具體性」的史實之中提煉或抽離而出,黃俊傑稱之為「具體的普遍性」(concrete universals)。
然而,這具有「普遍性」的「天道」或「理」究竟是什麼呢?本書第十二章對於程朱理學的論述指出:朱熹主張「理一分殊,月印萬川」,認為源自「天道」的「理」會呈現在「人心」或諸多事物的素樸狀態中。他從各種不同角度,反覆析論:仁、義、禮、智、信等儒家所謂的「五常」都是「理」的展現;而張載則是努力要刻劃出「儒家的心之模型」。
但是,在「天人合一」的文化傳統裡,宋明理學家雖然致力於「道問學」,他們卻很難將具有「普遍性」的儒家價值理念建構成形式性的理論,來說清楚「儒家價值是什麼?」這也是本書所要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再從中國歷史思維的特色,說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現代化的必要。
形式性的理論模型
傳統中國史學家重新建構具體而特殊之歷史事實的最高目標,是為了要從其中抽煉出普遍性的原理,以作為經世之依據,正如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言:
「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由於太史公著書立說之目的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所以他「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寫成本紀、世家、列傳的對象,泰半是王侯將相,殊少納入一般庶民百姓,而形成中國史家「以史論經」的傳統。朱熹也有類似觀點:
「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惟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古史餘論〉
朱子認為:三代相承之「理」,「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但只有聖人之「心」才能夠「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並將儒家所重視的「人綱人紀」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基於這樣的歷史觀,中國傳統史家傾向於將注意焦點集中在統治者身上。這就是朱子所說的:
「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事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己酉擬上封事〉
這樣的觀點當然不可能再適用於現代華人社會。因此,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必須充分吸納西方文明菁華的科學哲學,以「多元哲學典範」(multiple philosophical paradigms),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culture-inclusive theories)。這樣建構出來的理論,必須適用於華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不僅止於「帝王將相」。就拿朱子最關注的「人綱人紀」來說,本書第七章提出「儒家的庶人倫理」,可以解釋「五常」中的「仁、義、禮」。本書第三章〈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中的「智慧」,則是「五常」中的「智」。至於「信」則是雙方互動的結果,無法以這些形式性的理論模型表現出來。但本書所建構的「含攝文化的理論」,卻可以用來說明華人社會中一個人的行動。
用Gergen(2009)的概念來說,「仁、義、禮」是「第一序的道德」(first-order morality),是可以用規範、原則或律則表現出來的道德。「智」則是「第二序的道德」(second-order morality),自我必須隨機應變靈活地將它展現在個人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之中。這五個概念,並不是同一層次的東西,儒家卻將之並列為「五常」,傳統儒家以及人文學者不論從哪一個角度來加以詮釋,都不容易說清楚。
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
我們可以再從人類文明發展的宏觀角度,來說明儒家文化第三次現代化的意義。佛教在漢明帝(西元28-75)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
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1096-1291),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十八世紀發生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殖民主義的策略,往外擴張,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動盪不安的社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無法定下心來,吸納西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以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
「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所提出的概念。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長在於「綜合的盡理精神」,是一種「理性的運用表現」。相對地,西方文化則擅長「分解的盡理精神」,以「理性的架構表現」,透過一種「主、客對立」的「對待關係」,而形成一種「對列之局」(co-ordination),從而撐出一個整體的架構。由於中國文化向來注重運用表現,強調「攝所規能」、「攝物歸心」,在主體中以「天人合一」的方式,將對象收攝進來,成為絕對自足的存在。在這種狀況下,要轉換成「架構表現」,便只能「曲通」,而不可能「直通」。
什麼叫做「曲通」呢?針對這個議題,牟宗三提出了良知或道德理性的「自我坎陷」,也就是絕對自足的良知,暫時地對其「運用表現」存而不論,轉而讓知識主體以及政治主體,能夠依據各該領域的獨特性發展;在創造科學與民主的活動之後,再用道德理性加以貫穿。
政治主體如何透過良知的「自我坎陷」而開出民主政體,這不是本書所要討論的範疇,在此暫且不論。然而,從我對於社會科學本土化的主張來看,知識主體要想發展社會科學,還得定下心來,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哲學,才有可能運用「分解的盡理精神」,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以「對列之局」實質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生活場域中,運用其「綜合的盡理精神」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後果。
若用〈自我的曼陀羅模型〉來看,心理學本土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建構各種不同的含攝文化之理論,說明中國人在學習源自西方的「知識」之後,如何「轉識成智」,以其「綜合的盡理精神」,在「理性的順應」和「理性的控制」之間找到「中庸之道」,以維持一己的「心理社會均衡」。用孔子強調的行動法則來說:這就是「汝安,則為之!」
更清楚地說,牟宗三以「理性的運用表現」和「理性的架構表現」分別描述中、西文化之特長,但他卻不知道如何整合這兩者,所以才會想出令人費解的良知「自我坎陷」說。我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寫出這一系列的著作,正是要補充牟宗三之不足,以完成港台新儒家的未竟之志。希望本書的出版能夠促成儒家文化第三次的現代化。
國家講座教授
黃光國
2015年4月15日
參考文獻
牟宗三(1988):《歷史哲學》。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黃俊傑(2014):《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Gergen, K. (2009). Relational being: beyond self and communit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spers, K. (1949/1953). 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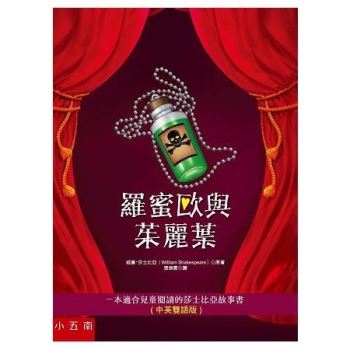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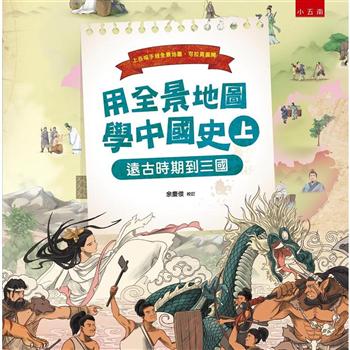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