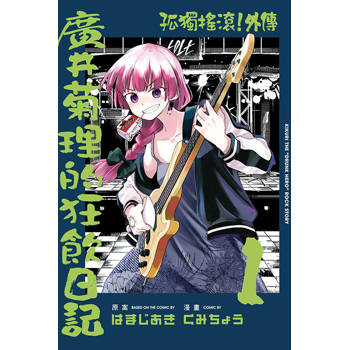翌日,天色才剛微亮,被豢養的公雞們,便此起彼落地扯開嘹亮的歌喉,唱著起床號。
通常都是呂傳第一個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孩子跟自己煮一鍋蕃薯花生湯當早餐,然後再與孩子們一同吃完早餐後,先送呂秀跟呂雄到阿水嬸家寄託,接著帶著呂進一起下田耕作。
可是,今天第一個起床的是呂進,他沒看到平常來回穿梭,催促著大家動作快點的大伯身影,因此,便主動到廚房去替大家準備早餐。
「大伯、阿姆,早餐我已經煮好了,請趕快趁熱來吃。」呂進站在呂傳房間外,隔著一條垂地的花布門簾輕聲喊著。
隔了許久,自己和起床的弟妹都已經吃完早餐了,卻一直未見呂傳走出房間。
「阿秀,妳先帶著阿雄去阿水嬸婆家吧。」呂進緩緩地對著妹妹說道。
「嗯。」呂秀點頭輕允一聲後,便牽著弟弟的小手,一如往常地到隔壁阿水嬸家報到。
同一時間,賭了一夜的阿滿,身疲力盡地踏入家門,先是用眼角餘光瞄了餐桌上的蕃薯花生湯一眼,馬上不屑地抿起嘴角,打了個大呵欠走進房內。
在廚房裡洗碗的呂進,一時不小心手滑,將碗給打破而割傷了手掌,忽然間聽到了阿滿呼天搶地的驚叫聲。
「夭壽喔,你這個死澎肚(腹脹)的,真的死了啊!嗚!你死了以後,叫我要怎麼辦啦?哇啊啊!」阿滿哀淒的聲嘶力竭哭喊聲,幾乎快要將屋瓦給掀起。
「大伯死了?這怎麼可能?昨天晚上大伯還跟我有說有笑,然後說胸口有點悶要先睡覺,怎麼會突然死了?」呂進如被雷劈般地佇立在原地,此刻的他,不管怎樣想破腦袋,也完全不敢接受呂傳的死訊。
左右鄰居在得知呂傳過世的消息後,自動自發地來到呂家幫忙料理後事。由於正值盛夏時節,天氣十分炎熱,又,貧窮的呂家,實在也無法負擔起華麗的喪葬儀式費用,於是在大家的熱心幫忙下,拆掉床板與一塊門板釘成棺木,好將呂傳的遺體安置在內,接著找來平時兼職當師公(法師)的阿全來幫忙唸經超渡,最後,眾人在呂家的田地旁邊,簡易地立了個呂傳的墓碑,好讓他能與呂家祖先葬在一起。
「阿傳啊,你怎麼這麼忍心放下我跟孩子們離去啦。我一個軟弱女人家,以後沒有你的日子,是要叫我如何活下去啊!」按照習俗不能替丈夫送葬的阿滿,穿著一身素衣,跪在家門口哭得肝腸寸斷,可憐的模樣,讓鄰居們無不一陣鼻酸。
呂傳的死,對懵懵懂懂的呂雄跟似懂非懂的呂秀而言,完全無法體會『大伯只是在睡覺而已』,為什麼大家要哭得這麼傷心。
不過,對雖年僅十歲,卻經歷過父親的生離與母親死別的呂進來說,大伯是像母親一樣長眠不起了。他知道自己身為呂家長孫,此時此刻,並沒有哭的權力,儘管內心如何悲傷,也只能咬緊牙根將淚水往肚子裡吞。
「阿姆,您放心,大伯雖然不在了,但是田裡的工作我會一肩扛起的。」被環境無情逼迫而不得不早熟的呂進,意志堅定地對著淚人兒阿滿說。
就在呂傳安葬後的第二天,呂進比平時更早起床替大家準備早餐,但就在他來到廚房準備切蕃薯時,聽到了家裡的大門被人用力踹開的聲音。
「砰!」
平時遊手好閒經營賭場為生的地痞文科,在小弟踹開呂家僅剩的一塊門板後,大剌剌地走進呂家喊著:「裡面有人在嗎?」
「請問你們有什麼事嗎?」呂進從廚房跑出來詢問。
「你阿姆在我的場子裡賭輸很多錢,所以已經把這間破屋讓渡給我抵債了,我希望黃昏前你們要全部搬走。」文科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模樣,囂張地抖著手上由阿滿簽下的借據說。
「我阿姆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你們一定是找錯人了。」呂進不相信大伯剛死,阿滿會做出這種事情。
「阿姆,麻煩您出來一下。」呂進禮貌地站在阿滿的房外喊道。
「不用叫啦,那個女人在昨夜跟我借一千塊後就跑掉啦。」文科無人自請地坐在椅子上,接著點燃了一根煙捲,翹起二郎腿,吞雲吐霧地繼續說:「還有啊,你們家的那塊爛田,那個女人也一塊賣給我啦。」
「不可能。」呂進無法置信自己所聽到的事實,一臉錯愕地連忙搖頭。
「不可能是你在說的,這白紙黑字難不成是我自己編造出來的?」文科按捺不住火爆性子,將整張借據往呂進臉上丟過去。
「閃開!」一名小弟將呂進奮力推開,使得他跌倒在地。
「大仔,他們家的『死人牌』(祖先牌位),要不要現在就拿去燒掉?」小弟走到神龕旁,作勢要拿取呂家的祖先牌位。
「不可以!」呂進忍痛從地上爬起,跑過來張開雙手擋在小弟與神龕中間。
「要是不想被燒掉,到時候就一起帶走,不然的話,我就拿去當柴火烤香腸,哈哈。」文科囂張地大笑後,便準備帶著小弟離去。
「你這個夭壽死囝仔,居然侵門踏戶地來耀武揚威,你祖媽打死你!」阿水嬸不知在門外多久了,一見文科走出來,手持掃帚就是一陣亂打。
「老不死的,妳打夠了沒!」文科一把推開了阿水嬸,怒目咬牙地作勢要揮拳打她。
「大家快來喔,打死人囉!」阿水嬸扯開嗓門大喊,引來了不少人聚集圍觀。
「阿水,妳是怎麼了?」剛要去田裡路過的豬哥叔,從人群中慌張地出來問道。
「這個死無人哭的夭壽仔,阿傳人死都還沒頭七,就要來霸占他們呂家的祖產啦。」阿水嬸一見熟人前來,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哀嚎哭訴。
「什麼我霸占,老子可是有阿滿親手畫押的借據,她一共欠了我五萬塊的賭債,我只是收了這間破房子跟那塊爛地做抵償,算是有良心了。不然,你們誰來幫她還這五萬塊?」文科理直氣壯地在眾人面前秀出借據。
大家都不識字,看了老半天也不知文科手上的借據寫了些什麼,不過,阿滿爛賭成性倒是眾所皆知,若要說她把祖產拿去當抵債,這也符合她的作風。只是,大家想到呂傳死後,留下那三個孤苦無依的孩子,就算再於心不忍,那五萬塊的天文數字,可誰也拿不出來。
「這個阿滿真是失德,呂家出了這個惡媳婦,真是家門不幸。」
「可憐那三個孩子,房子沒了要到哪裡去安身才好?不知道阿傳上輩子是造了什麼孽啦。」眾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宛如麻雀般議論紛紛,倒也沒有一個人願意出來承擔那五萬塊。
「老子又不是開善堂的,總不能叫我吞下這筆帳喝西北風吧?你們大家誰要做大善人,出來把阿滿的帳給還了?」文科看到沒有人願意出來解決,於是再次扯開嗓門喊說。
「我要到田裡去巡水。」
「阿義,你不是要去市場賣菜嗎?」
「對喔,差點給忘記了我還要趕著去街上買棉被。」大家各亦找藉口離開了現場。
「豬哥叔、阿水嬸,我想你們都窮到快被鬼抓去了,應該也拿不出來吧?」文科對現場只留下來的兩位老人家,尖酸刻薄地調侃說。
無能為力的阿水嬸,就算再怎麼忿忿不平,也只能忍氣吞聲地用兇悍的眼神瞪著文科以示抗議。
「一群死窮鬼,浪費老子的美國時間,沒錢就不要在這裡裝善人,閃開!」文科帶著小弟擰眉瞪眼地咒罵,並狠狠地推了豬哥叔一把後離去。
「阿進,你有沒有怎樣?」阿水嬸隨即跑進呂家關切,看見呂進兩腳膝蓋淌著鮮血,張開雙手死命地護在神龕前。
「阿水嬸婆。」呂進見到阿水嬸後,立即委屈萬分地投入她的懷裡嚎啕大哭。
「阿水嬸婆不捨,是阿水嬸婆憨慢(無能),沒有能力保護你們,你要原諒阿水嬸婆。」阿水嬸也緊抱著呂進,老淚縱橫地哭成了淚人兒。
「唉。」豬哥叔看著空蕩蕩的呂家,還有被吵鬧聲驚醒而站在房間外,一臉驚魂未定的呂秀和呂雄,不禁也觸景生情地流下男兒淚。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流浪三兄妹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0 |
二手中文書 |
$ 176 |
少兒文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流浪三兄妹
十歲的呂進決定帶著幼小的弟弟、妹妹,徒步前往台北找他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
不畏一路上的艱辛刻苦,因為他知道,媽媽和阿伯都會在天上保佑著他們,
和爸爸重聚的幸福日子一定很快就會來到……
沒有富裕的物質生活,缺少雙親的呵護照顧,
這樣的我們依然有著最堅定的信心與足夠的樂觀!
因為,爸爸一直是這麼教導著我們的……
某一日,阿伯意外過世,阿姆又因欠下大筆賭債而將祖厝拿去抵債,呂進三兄妹頓時成了無依無靠的孤兒,身邊除了為數不多的錢,只有一張寫著爸爸工作地址的泛黃紙條。
十歲的他勇敢的決定帶著幼小的弟弟、妹妹,前往台北投靠他們如今在世上唯一的親人。然而老天爺彷彿像想考驗三兄妹一般,一路上,他們不僅弄丟了錢與行李,連爸爸的地址也一起被壞人搶走了。茫茫人海中,小小年紀的他們能順利和爸爸重逢嗎……
作者簡介:
張雅義
一枚年屆不惑的外星人,整天穿著地球人外衣,跟著地球人做著一樣的作息,幾乎已經早以被貪婪的地球人給同化了。
你們好,俺是來自「橘子星球」的生物,俺的外星名字叫「橘子醬老爹」,請多多指教。
著有:魔女1/2系列之《魔女訓練營》、《婀娜島》、《聖戰傳說》(心田書房)。
章節試閱
翌日,天色才剛微亮,被豢養的公雞們,便此起彼落地扯開嘹亮的歌喉,唱著起床號。
通常都是呂傳第一個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孩子跟自己煮一鍋蕃薯花生湯當早餐,然後再與孩子們一同吃完早餐後,先送呂秀跟呂雄到阿水嬸家寄託,接著帶著呂進一起下田耕作。
可是,今天第一個起床的是呂進,他沒看到平常來回穿梭,催促著大家動作快點的大伯身影,因此,便主動到廚房去替大家準備早餐。
「大伯、阿姆,早餐我已經煮好了,請趕快趁熱來吃。」呂進站在呂傳房間外,隔著一條垂地的花布門簾輕聲喊著。
隔了許久,自己和起床的弟妹都已經吃完...
通常都是呂傳第一個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為孩子跟自己煮一鍋蕃薯花生湯當早餐,然後再與孩子們一同吃完早餐後,先送呂秀跟呂雄到阿水嬸家寄託,接著帶著呂進一起下田耕作。
可是,今天第一個起床的是呂進,他沒看到平常來回穿梭,催促著大家動作快點的大伯身影,因此,便主動到廚房去替大家準備早餐。
「大伯、阿姆,早餐我已經煮好了,請趕快趁熱來吃。」呂進站在呂傳房間外,隔著一條垂地的花布門簾輕聲喊著。
隔了許久,自己和起床的弟妹都已經吃完...
»看全部
作者序
序-回那個純真的年代
前幾天,看到了一則新聞報導,有名少年因為父親不讓他繼續沈迷線上遊戲,而將他的電腦給斷線,結果,該名少年便將父親反鎖在陽台外,並且在客廳裡,一手持著菜刀,一手持著瓦斯桶,揚言要全家同歸於盡。看著新聞畫面,讓我心裡不勝欷噓,不禁回首想起了那個純真的年代。
記得我小的時候,那個年代可別說電腦,或是線上遊戲了,連電視臺都只有三台而已,而且還不是整天24小時不停的播放節目,那時候小孩的最大樂趣,男生不是一群人掀尪仔標,就是打彈珠,而女生則是玩沙包,不然就是紙娃娃,如果男女生...
前幾天,看到了一則新聞報導,有名少年因為父親不讓他繼續沈迷線上遊戲,而將他的電腦給斷線,結果,該名少年便將父親反鎖在陽台外,並且在客廳裡,一手持著菜刀,一手持著瓦斯桶,揚言要全家同歸於盡。看著新聞畫面,讓我心裡不勝欷噓,不禁回首想起了那個純真的年代。
記得我小的時候,那個年代可別說電腦,或是線上遊戲了,連電視臺都只有三台而已,而且還不是整天24小時不停的播放節目,那時候小孩的最大樂趣,男生不是一群人掀尪仔標,就是打彈珠,而女生則是玩沙包,不然就是紙娃娃,如果男女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張雅義
- 出版社: 心田書房 出版日期:2012-08-04 ISBN/ISSN:978986197512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40頁
- 類別: 中文書> 少兒親子> 少兒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