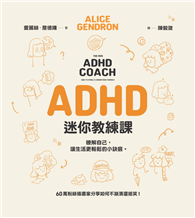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一章
下了幾天的連陰雨,空氣中的濕氣,凝結成薄紗般的霧,將夜色籠罩的分外迷離。
連清籬停好車子,走出小區的地下停車場,已經是凌晨兩點。
每年校友聚會都弄到這麼晚,不過衛空遠和何箏喜歡,他便沒有反對的餘地。
衛空遠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老闆,大學四年,研究生兩年,後來又在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前前後後兩人已認識了十年。何箏是小他三屆的學妹,現在是他的女朋友,相識半年來,感情還算穩定。
他該慶幸自己因為要開車,所以沒被灌太多的酒,不過在那種嘈雜的地方,只是坐著都讓人覺得身心疲憊。身上染滿了煙酒的臭味,他現在只想好好洗個澡,然後上床睡覺。還好明天是週末,否則一定會因為睡眠不足,頭痛一整天。即使他平常奉行的原則是早睡早起,但是偶爾睡個懶覺也是不錯的選擇。
明亮的路燈將據說有健身功能的青石小道,照得纖毫畢現,凹凸不平的路面,吸走了他的腳步聲,呼吸聲便變得格外清晰。
小道的左側種滿了芭蕉樹,雨水順著寬大的葉片滑落在地上,不時發出清脆的響聲。
這片充滿熱帶風情的芭蕉林,是孩子們捉迷藏的最佳場所,在晴朗的天氣裡,這裡總是充滿了歡聲笑語,而此刻,則只有寂寂的雨聲了。
突然掠過一陣微風,葉片在風中搖擺,發出簌簌的聲音,濕冷的空氣中,似乎瀰漫著血的腥味,連清籬不覺停下腳步,遊目四顧。
怎麼會有血腥味?是自己喝多了酒產生了錯覺?他不覺皺起眉頭。
眼角似乎有黑影閃過,他還沒來得及反應,腰後已多了一個堅硬銳利的東西。
「朋友,不介意幫個忙吧?」
突然響起的男性嗓音低沉嘶啞,帶著微微的喘息,同時血腥味也變得更加清晰起來。
小區有著完善的保安系統,他住進這裡整整兩年,從來沒聽過任何有關異常闖入者的傳聞,沒想到第一次出現便被他撞見,他的運氣還真不是一般的「好」!
連清籬沒有試圖掙扎,他知道自己若表現出任何慌亂都會刺激到身後的男人,讓事情變得越發不可收拾。深吸口氣,他強迫自己鎮定下來,然後目視前方,淡淡的道:「如果要錢儘管拿去,都在包裡,請不要傷害我。」
雖然這樣說著,可是連清籬心裡十分清楚,再笨的搶劫犯也不會到這種佈滿監控、且有警衛二十四小時巡邏的小區實施搶劫,何況這男人身手敏捷,實在不像一般的攔路劫匪。
果然,身後的男人先是一愣,立刻便用惱怒的語調低吼出來:「去你媽的!老子不是要錢!該死的!」
「那你想要什麼?」
「我的同伴受傷了,需要幫助。」
男人短促的說著,轉到他的面前。
連清籬一米八的個頭已經不算低,但這男人卻硬是高了他半個頭,方臉厚唇,面貌粗獷,此刻雖刻意做出一臉凶狠,但是眼中依舊流露出濃濃的驚惶。
這麼冷的天氣,男人只穿一件背心,黑色的布料看不出有沒有血跡,可是裸露的肌膚卻處處可見暗褐色的痕跡,他持刀的右手更是染滿了鮮血,連甲縫裡都是暗色的血痂。
如果他身上的血都來自於他的同伴,那麼那個人顯然受了極重的傷。
半夜三更,帶著受傷的同伴,不去醫院反而闖進這裡,這男人絕非善類!
不過那個受傷的人再耽誤下去就來不及了吧?眼神掃過男人染血的衣襟,連清籬猶豫著。
見連清籬遲遲沒有答話,男人惱怒起來:「你他媽聽見沒有?快點按我說的做,否則老子宰了你!」
他狠狠的說著,瞪大的雙眼射出噬人般的凶芒,眼底的惶然卻越發明顯起來。他因焦灼而顫抖的手指幫連清籬做了決定,他抬起頭,看進男人充血的眸,沉聲道:「說吧!你想讓我怎麼做?」
這棟以「絕對私人空間」為賣點的洋房,一層只有兩戶,兩戶共用一部電梯,兩側開門,下了電梯便是住所的大門。
電梯是刷卡進入,而且只能登上自己居住的樓層,安全問題絕對無憂,所以未設大樓管理員。此時恰好給了連清籬方便。
將男人先讓入電梯,他才跟著進入,昏暗的光線下,他只看到伏在男人背上的高大男子有著異常濃密的黑髮。
傷口應該在腰上。那處裹了厚厚一層布條,布條不知是不是被雨水弄濕,顯出黑呼呼的一片,也或者那是滲出的血。
即使真是罪不容赦的兇犯,也有被救助的權利,連清籬知道,自己無法做到袖手旁觀。
電梯鏡面鋼板上,映出男人僵硬的臉。
「謝謝!」
他說。
「是你逼迫我的,沒什麼謝不謝。」
連清籬一臉冷淡的回道。
男人一怔,反而笑了,這一笑,那張染有血跡的臉竟變得憨厚起來。
「我叫石林,大家都叫我石頭。」
他說。
連清籬微微挑起眉頭。
這種情況下隱藏身份是最基本的常識,如果這男人的想法是--反正要殺了自己滅口,即使知道了名字也無所謂,則又另當別論。
石頭感覺到他在看他,又露出一個僵硬的憨笑,連清籬撇過臉,皺著眉頭告訴自己,或許是他多慮了。
「叮」的一聲輕響,電梯已經到了五樓。
「到了。」
連清籬率先走了出去。
從櫥櫃裡取出醫藥箱的功夫,石頭已將背上的傷者放到了沙發上,兩人身上的污泥混著血跡染上乳白色的沙發,看起來格外刺眼。
連清籬在石頭身邊蹲下,順手將醫藥箱放在地板上。
布條纏的很厚很緊,石頭顯然拆得很費力,直到連清籬將藥品、紗布一一取出,擺放整齊,他也只拆到一半。
受傷的男人任石頭折騰,卻沒有半點動靜,這讓連清籬有了不好的預感。
外傷導致的昏迷,大抵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大量失血。
他沉思著轉身看向傷者的臉看去。
那男人只露出半邊臉孔,臉色果然如他所想的那樣灰白黯淡,緊抿的唇乾結裂開,卻已經滲不出一點血來……
但這不是重點!
高鼻闊額,嘴唇很薄卻稜角分明,眼眶深深陷入,可以想見他睜開雙目時眼神會何等的深邃,濃眉緊鎖,低低的壓在眼眶上,讓他的表情看上去凌厲而憤怒--沒有一點病人該有的樣子,乍然一看,會覺得他下一刻便要高高跳起,將面前的敵人撕得粉碎!
這張面孔如此熟悉卻又如此陌生!那眉目輪廓喧囂著逼入他的視線,讓他連硬生生拔離都無法做到!
眼前一陣天旋地轉,他必須伸手扶住沙發,才不至一頭栽倒在地上,胸口像是被重物壓迫,緊得他幾乎無法呼吸,如被夢魘住一般,痛苦萬分卻又無法掙脫!
這張臉,即使化成灰他也能認出--舒慶!
身旁突然傳來尖銳的抽氣聲,他渾身一震,從惡夢中驚醒。努力壓制著急促的呼吸,直到自己鎮定下來,他才轉過頭去。
然後,他看到了令石頭驚駭的原因。
刀口從腰後一直延伸到左胯,因為處理不慎,顯得有些血肉模糊,十幾公分長的口子大大的裂開著,混雜著髒污的水漬,猙獰而又恐怖,此刻依然在出著血。
石頭舉著紗布藥棉,一臉驚惶,顯然不知該如何下手,剛剛那點狠勁兒,到現在已消失的一點不剩,他的臉上是一副快要哭出來般的表情。
如果再耽誤下去,這個人只有死路一條!胸口一陣緊縮般的痛,他咬了咬牙,一把將石頭推開,佔據了他原來的位置:「我來。」
冰冷而強勢的語調讓石頭一怔,就著坐倒在地的姿勢,半天沒反應過來。
幾下撕開周圍礙事的衣物,使傷口充分袒露,連清籬一手取過酒精,一手取過棉球開始清理起來。
「受傷到現在多少時間了?」
他一刻不停的問著,連抬頭的的功夫都沒有。
混合著血的酒精滴滴嗒嗒的滴落在地上,發出的聲音足以讓人牙酸腿軟。
石頭只看了一眼,便錯開視線,嚥了口唾液,才道:「大概半個多小時了吧?」
棉球擦過翻開的肌肉,沾了沙石便再換一塊,看似溫和的男人蹙眉抿唇,一雙眸子沉冷如冰。
「你是醫生?」
只有看慣了這種傷口才會如此從容不迫。
「不是!」
那難道是殺手?
石頭忍不住縮了縮。
他自問自己沒有這般魄力,即使曾經在別人身上製造過比這還恐怖的傷口,但是放在自己人身上,除了驚惶,再無其他。
或許也只是事不關己,才能下得了手吧!
他暗暗的想。
傷口被清理乾淨,暴露的更加清楚。
背部那處起點最深,一路延伸至腰側便越來越淺,可以猜想出舒慶受傷時的情形。他顯然是為了避開來自背後的暗算、迅速轉身時留下刀傷,可是當時沒有直接死掉,也不代表他最終能逃過一劫!
直到現在血還在不停的流著,他卻已經昏迷,如果不妥善處理,他會永遠這麼昏睡下去!
想到這裡,連清籬的臉色變得更加陰鬱起來。
他的表情顯然刺激了石頭。
「他……不會有事吧?」
將止血的藥粉撒進傷口中,然後用紗布緊緊填塞,直到此時,連清籬才有功夫回答石頭的問題:「傷口太大,必須縫合,而且他失血過多,也需要輸血,如果不想他死,你最好送他去醫院。」
石頭眼圈一紅,沒有落下淚來,反而一臉堅定的道:「不能送醫院--他也不會死!」
原本便心煩意亂,額頭還不停的跳痛著,此刻聽石頭這麼一說,連清籬只覺一股悶氣直撲胸臆,想都沒想,他瞪著石頭便罵了出來:「你是白癡嗎?都快一個小時血還沒止住,這麼一直流,你以為他是什麼?怪物?還是九命怪貓?血流乾了不會死?你懂不懂什麼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就算被警察抓住,也比死了強吧?」
等了半天,石頭回他的只有一臉愕然。
他也知道自己的脾氣有些失控。
他一向溫和,這些年來,他甚至連大聲說話都不曾有過,因為沒有什麼事會讓他憤怒到失控的程度!直到今天!
這個混蛋!十年前做了那麼過分的事後,就突然消失!沒想到再次出現竟然是這樣一種情況!而且,他竟真的去混了黑道!他竟依然將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他竟還這般任性!
想到這兒,連清籬壓住傷口的手便忍不住重了幾分!
可惜被凌虐者還是沒有任何反應!如果不是還有點微弱的呼吸,簡直跟死人沒什麼兩樣!
石頭此時終於回神,他握緊雙拳,神情僵硬,毫不退讓的道:「我說不能去醫院就是不能去醫院,而且他不會死!你要是弄不了就讓開!別在這兒說這種嚇唬人的屁話!」
話音一落,連清籬竟然真的站了起來:「壓著。」
石頭忙接手壓上那塊紗布。
他此刻才發現,幾分鐘前還雪白乾爽的紗布,現在已被血完全浸透。
「壓好別鬆手!」
叮囑一句,連清籬便轉身向書房走去。
「喂!你幹嘛!」
「想辦法救人!」
石頭一點也不想讓自己看上去這麼依賴那個陌生的男人,但是不知怎麼,他總覺得此時能救舒慶的人,只有這個男人。
將門關上,連清籬撥響了電話:「小劉,我是連清籬,需要你幫個忙……」
他知道自己完全可以撒手不管,他甚至認為那個傢伙就算是死了,也是他自找的!
反正今天不死明天也會死,黑社會不就是那樣?今天你殺我,明天我殺你……遲早都會死,他幹嘛還那麼費勁的救他?
心中想著,手指卻如有了自己的意志,取過紙筆,寫下了剛剛約定的地點。
「你立刻趕去這個地方,那裡會有一個穿黑色夾克的人等你,你要盡快將他交給你的東西取回來,你的動作越快,他活著的希望越大。開我的車去!車號0259。悄悄的去,悄悄的回來……」
石頭看了看紙條,又看了看他,顯出一臉狐疑,他也不解釋,只是面無表情的道:「當然,你可以不按我說的做,然後你就等著幫他收屍!」
說完,手指一動便要將紙條揉碎,石頭連忙跳起來搶了過去:「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能救慶哥!」
走到門口,他突然回過身深深鞠了一躬,真誠的道:「那慶哥就……拜託你了!」
說完,頭也不回的開門離去。
石頭用了半個小時的時間跑完了一個小時的路程。
連清籬讓他取回的果然是救命的東西--四百CC鮮血,足以從閻王那裡搶回舒慶的命。
他回來的時候,那道可怖的傷口已經用絲線縫上,歪歪扭扭的針腳實在不算漂亮,但已經不出血了。
連清籬當時就遠遠的坐在客廳一角,手中端著杯子,隨著熱氣蒸騰,房間裡充滿了咖啡的香味。
他看起來一副疲憊的樣子,臉色白得發青,只有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眸,看上去依然明亮清澈,卻有種冷冷的意味。
他的五官線條原本十分柔和,膚色白皙,有種說不出的溫柔之意,如春日的湖水,此刻沉冷下來,卻如同湖水結冰,使得整個房間的溫度似乎都降下了幾分。
血順利輸上的時候,舒慶的手背上已經被扎滿了針孔,石頭這時才相信了連清籬的話--他不是醫生,他只是對外傷比較擅長。
「一會兒會有人來接我們,你知道的,天亮以後就不好離開……而且老大很擔心他。我們是青紅幫的人,他是我大哥,名叫……」
「夠了!」連清籬冷冷的打斷他:「我不想知道這些。」
他不需要任何人提醒,他所救的這個人名叫舒慶,也不想知道關於他的任何事!
不知怎麼,石頭突然有種錯覺--這人明顯的冷意,似乎正是針對慶哥!
腦中正自混亂,連清籬已經取了一卷繃帶,向他看來:「過來幫忙。」
他急忙上前。
繃帶繞過腰間,蓋在傷口上,一層又一層,然後繞過肩頭,固定牢靠:「這樣就不怕搬動的時候將傷口撕裂,不過回去最好拆掉,否則會影響傷口癒合。」
昏迷中的舒慶意外的沉重,裹完繃帶,兩人都是一身的大汗。
「最好是等血輸完後再走,最多一個小時,應該還來得及。」
「我知道了。」石頭點點頭:「我會讓他們在外面等著。」
「三天換藥六天拆線,記得按時吃消炎藥,最少吃三天。」
連清籬繼續交代。
「吃藥啊……」石頭皺著眉頭,一幅吞了蒼蠅般的痛苦表情。
連清籬眉頭動了動,似乎被石頭的表情逗笑,但很快他又再度板起面孔,冷冷的道:「我剛才已經餵他吃了一次,將藥壓成粉,捏著鼻子灌下去,也不是很難。」
「啊?」石頭一副震驚莫名的樣子。
「怎麼了?」
「不,不,沒什麼……」摒著家醜不可外揚的理念,石頭急忙搖了搖頭。
原來慶哥只吃藥粉不吃藥片?這下他總算是找到秘訣了!
可是他醒著的時候怎麼灌?
正想著,連清籬已經說出了答案:「也可以將藥粉放在酸辣湯裡,對他我不敢保證,但我有個極討厭吃藥的朋友,用這種方法騙他吃過好多次,從來沒有被識破,你不妨試試。」
「哦!」石頭呆呆的點了點頭。
此時一袋血已經輸了進去,舒慶蒼白的臉上已經有了些微的血色,呼吸也更順暢了。
「你救了慶哥,是我青紅幫的恩人,不管你有什麼要求,只要青紅幫能做到的,必定為你做到。」
連清籬的臉上顯出深思的表情,他看了看石頭,淡淡的道:「要求倒真有一個。」
「你儘管說!」
「今天你所看到的一切,包括我的樣子,我的家,我救了他的事情,不許你向任何人說--這就是我的要求!」
石頭怔住,好一會兒才能發出聲音:「你說真的還是在開玩笑?你要不要再考慮一下?」
「不用!」連清籬堅定的搖頭:「這就是我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做到!」
石頭雖然覺得他放棄這麼好的機會有些可惜,但看連清籬一臉堅持,他還是點了點頭:「我會的。」
此刻他才悟到,連清籬的冰冷不是針對舒慶,而是針對他們這種身份!
正經良民,恐怕都不會想跟自己這種人打交道吧?
第二章
周圍的氣息太過熟悉!
煙味、灰味還有久不見陽光而特有的霉味,重重混雜,縈繞鼻間,不用睜開雙目,舒慶就知道自己現在正躺在他自己的床上。
氣味不算好聞,但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這棟三居室的豪華公寓剛住進來還是新嶄嶄,亮堂堂,可是那種光鮮的面貌也只不過維持了幾天。
他不喜歡旁人進到家中,所以打掃收拾全交給石頭,而那個粗線條的傢伙,沒用垃圾將兩人埋掉,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
睜開雙目,果然就是那片熟悉的蜘蛛網,吊在刻花石膏吊頂的轉角處,黑糊糊一片,如同破舊的漁網。
石頭弄死了蜘蛛,卻沒有將蛛網清掃,就這樣掛在那裡,已經很久了。
正自發呆,石頭的大臉便無聲無息的擋在他與蛛網之間!
想也不想的一拳揮去,石頭哀嚎一聲摀住腦袋,縮了回去。
而他也因為那一下大動,扯痛了傷口,立刻便是一陣的齜牙咧嘴。
「你他媽不聲不響的鑽出來,想嚇唬誰啊?」
他沒好氣的罵道,用手支撐著身體想坐起來。
「唉,慶哥,你小心點,身上還有傷啊!」
石頭忙撲了上來,伸手去扶,嘴裡還一邊念叨著:「慶哥,你還是多躺一下比較好!」
「老子餓了。」
舒慶瞪了石頭一眼,理所當然的說--別想讓他肚子餓的時候躺在床上!
腰間的傷悶悶的痛著。
他向來不怎麼怕痛,所以除了腦袋暈暈,肚子空空,似乎也沒什麼大礙。
還沒挪動身體,石頭卻一下子撲了上來,抱住他的大腿,哀哀的哭出了聲:「慶哥,還好你沒事!你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石頭也不活了!」
被石頭誇張的言行氣得青筋直冒,舒慶屈起手指,一個爆栗便敲到石頭腦袋上:「你他媽哭什麼喪?老子還沒死呢!活的不耐煩了是吧?直接說出來,老子現在就給你個乾淨!」
「可是……嗚嗚嗚嗚……慶哥,你真的……嗚嗚……嚇死我了……」
石頭正哭的欲罷不能,臥室的門突然被輕輕敲響:「慶哥,你醒來了麼?」
是熟悉的聲線,舒慶濃眉一挑,道:「羅成,進來。」
室內垂著厚厚的窗簾,光線陰暗,門一開,客廳的燈光便從羅成身後射了進來,正照在石頭顫動不已的背脊上。
羅成一怔,顯出想笑又拚命忍住的滑稽表情。
「過來,把這個神經病給我扔出去!」
舒慶指著腿上扒著的壁虎,板著臉道。
「是!」羅成彎腰應道,隨即又加上一句:「青爺在外面等你!」
客廳的狀況也不比臥室好多少。
木質地板早已被厚厚的污垢掩去原先的色澤,設計師苦心設計的時尚造型,也被隨處亂扔的雜物和厚厚的灰塵徹底掩蓋。
炎青坐在客廳正中的搖椅上。只有他那張椅子沒有灰塵,也沒有隨處亂扔的內褲背心!
電視上播放著無聊的綜藝逗趣節目,他聚精會神的看著,時不時發出「呵呵」的笑聲。
他看上去大概五十多歲,但是實際年齡已超過了六十。
寬寬的臉龐,厚厚的下巴,笑起來眼睛瞇成兩道小縫,看上去像個和氣的商人,一副溫和無害的樣子。
尤其是此刻。
但是不會有任何人認為他無害!
三十五年前,將七個小幫派聯合起來,創立青紅。短短十年間,青紅便與龍漕幫、天下盟三分天下。
炎青狡詐、練紅狠辣,在兩人合謀之下,天下盟解體,而唯一可與其實力抗衡的龍漕幫這些年也漸漸有了衰退之像,青紅儼然成為關中第一大幫,身為青紅的老大炎青怎會是個簡單人物?
見舒慶出來,守在房間周圍的數個男子恭敬的彎腰,齊聲叫道:「慶哥。」
而站在炎青身後,一臉冷肅的瘦高男人只是微微的點了點頭。
整個房間的人都看著舒慶,包括炎青,可是舒慶的眼睛卻只看著他那張沾滿污垢的純天然大理石餐桌。
或者該說--只看著桌面上擺滿的各式各樣的食物。
稜角分明的俊美面孔,此刻只見一副垂涎不已的誇張表情。
石頭紅著眼圈站在他的身後,向炎青鞠躬道:「青爺。」
炎青沒有看他,只衝著舒慶微笑:「你就餓成這樣了?」
彷彿此時才醒悟過來,舒慶抬起頭,撓了撓糾結的短髮,「嘿嘿」笑道:「大哥,你來了?」
薄薄的嘴唇掀開,露出兩顆尖尖的虎牙。
「我能不來麼?受了那麼重的傷,差點把小命要了!」
炎青冷哼一聲:「吃吧!小心一會兒餓出毛病來。」
舒慶歡呼一聲,直接在桌旁坐下,摟過一個保溫盒,便揭開了蓋子。
魚翅!燕窩!
還真是應有盡有!
「真是知我者大哥也!」
「吃你的吧!」
炎青笑罵。
舒慶不再客氣,將桌上的食物以驚人的速度填進嘴裡。
炎青只是笑瞇瞇的看著,如同慈祥的長者。
突然想起什麼一般,他轉向石頭:「咱們可得好好謝謝那個救了舒慶的人,你去問問他要什麼?只要我炎青能做到的,一定為他做到。」
「是。」
石頭連忙點頭。
舒慶頗不以為然的道:「不就是被砍了一刀!什麼救不救命的?」
他的嘴裡塞滿食物,說起話來含含糊糊。
「你還敢逞強?陸大夫說,如果不是治療及時,你早見閻王老子去了!」
炎青不悅的叱道。
「哎呀!大哥你也太誇張了,我哪是那麼容易死的?」
懶得再理舒慶,炎青只是叮囑石頭,讓他不要忘記這件事。
舒慶也樂得可以放開大吃。
風捲殘雲一般的吃法,沒過一會兒,滿桌的食物已少了一半。
看他肚子填的差不多了,炎青示意將電視關掉。
房間立時靜了下來,只餘舒慶吃東西時發出的呼嚕聲。
他側頭看了看舒慶,沉思片刻,緩緩的道:「吳勁的屍體我已經叫人運回來了,跟他夥同的四人,死兩個,還剩兩個活口,我已經交給老劉去審問,按幫規,背叛是五馬分屍的重罪,這吳勁跟了你五年,竟然一出手便想殺你,更是罪無可赦!讓他就這麼死掉,還真是便宜他了!」
炎青瞇起雙眼,眼神森冷陰沉,讓人不寒而慄,剛剛的和善模樣早已看不到蹤影。
「那大哥你想怎麼辦?」舒慶從飯菜中抬起頭來。
炎青淡淡一笑,悠然道:「他雖死了,可他的家裡人卻沒有!」
石頭露出驚恐之色,舒慶卻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
再看了眼舒慶,炎青欠了欠身子,表情又變得溫和起來:「總之這件事不用你管,你安心養傷,其他的我自會處理!」說著他站起身來:「我帶來的補品記得要吃,還有要按時吃藥!石頭,這些事就交給你了,如果舒慶不按陸大夫說的去做,你儘管告訴我,我會親自來盯著他。」
「知道了,青爺。」
「大哥,你這就走了?」舒慶也站了起來,順便用手背抹掉嘴角的油漬。
「你都沒事了,我還待在這兒幹嘛?吃你的飯吧!不用送了!」炎青笑道。
「那你等一下,讓石頭跟你一起走。你要的帳本我已經拿到了,昨晚情況緊急,被我順手藏了起來,石頭知道地方,讓他帶你去取。」
這本帳冊其實就是昨晚的任務,只是沒想到吳勁會趁機設局,出手暗算他。
炎青一愣,隨即皺起眉頭,似乎不怎麼高興的樣子:「舒慶,你怎麼……」
舒慶笑著打斷他:「大哥交代的事情,我什麼時候耽誤過?」
他一臉狂傲,黝黑的眼眸晶亮銳利,一點也沒有大傷過後的虛弱。
炎青有些無奈的道:「舒慶,你說我是該罵你還是該誇你?」
「隨便。」
舒慶笑嘻嘻的道。
炎青瞪了他一眼,突然伸出手握住舒慶的肩頭,肅然道:「舒慶,我再說一次,你的命是最重要的!下次再敢這麼胡來,我定會給你一頓好打!」
「知道了。」
舒慶隨意的說道。但只看他漫不經心的眼神便知道有幾分誠意。
炎青只得無奈的搖頭。
遇到舒慶之前,他從不知道這世上會有什麼人是他控制不了的,可是這個傢伙卻輕易做到了。你硬他比你還硬,不想兩敗俱傷,他只有妥協。
「帳冊的事不急,讓石頭畫張圖,我另找人去取!免得你受傷沒人照顧!舒慶,我看還是再找幾個人過來……」
「大哥,石頭就可以,人多了我嫌煩!」舒慶連忙反對。
「也好!其他人我也不是很信任……對了,要不要讓炎莉過來?她好歹還能打掃打掃房子……」
炎莉是炎青的乾女兒,也算是舒慶的女人,炎青顯然在給炎莉製造機會。
「不要!絕對不要!」
舒慶一點也不給面子的道。
「你……」似乎還想說什麼,炎青最終還是歎了口氣道:「……隨你吧!」
說完,便轉身走了出去。
炎青剛一離開,舒慶便又撲回桌邊,大吃起來:「石頭你也來吃一點!味道還真不錯!」
石頭愁眉苦臉的搖搖頭,猶豫半響,才小心的問道:「慶哥,青爺真的會把吳勁的老婆孩子抓起來啊?」
「你說呢?」
石頭沉默。
雖然外界都認為練紅毒於炎青,但是事實卻不是那樣,炎青只是更善於偽裝罷了。
毫無疑問,如果吳勁的家人真的落在炎青手上,五馬分屍之刑是絕對少不了的。
雖然石頭極恨吳勁背叛一事,但吳勁已經死了,冤有頭債有主,怎麼也不該遷怒於吳勁的妻子孩子--何況,吳嫂又是那麼溫柔的一個女人。
石頭坐在那裡不住的唉聲歎氣。
「你還讓不讓老子吃飯了?」舒慶一筷子敲到石頭腦袋上。
石頭幽怨的看了眼舒慶,沒有說話。
舒慶皺了皺眉,低下頭,扒了幾口飯,突然道:「吳勁其實是自殺的!他當時刺我那刀雖然被我閃過,但是他如果緊接著再發動攻擊,我未必躲得過去。可是他沒有,反而主動撞在我的刀上……他其實並不想殺我,顯然是有人逼他。
吳勁跟了我五年,一直忠心耿耿,逼他的人必定是控制了他最重視的東西。」
「你是說吳嫂和小勁?」
石頭一臉驚赫。
誰都知道吳勁最愛妻兒!如果用那兩人做人質,讓吳勁自殺都成。
舒慶點了點頭,道:「所以你不必擔心他們會被大哥抓住,吳勁任務失敗,那兩人恐怕早被殺掉滅口了。」
石頭握緊雙拳,一臉激奮:「是誰這麼惡毒?」
「石頭……」舒慶似笑非笑的道:「你該問是誰有這麼大的本事?」
「慶哥指的是--紅爺?」石頭衝口而出。
舒慶臉一沉,一巴掌拍到他的腦袋上:「你他媽不想活了?話是可以亂說的麼?」
「可是……」石頭一臉委屈,看著舒慶欲言又止。
「沒有可是。」舒慶端起保溫盒,將最後一口魚翅倒進口中,抹了抹嘴巴,才道:「你只要記住,沒證據就沒有說話的資格!隨便亂說小心被人滅掉!到時候我也救不了你……牙籤。」
他伸手。
將牙籤放進舒慶手中,石頭不無慶幸的嘟囔道:「多虧我沒有老婆孩子。」
舒慶不置可否的瞪了他一眼,開始專心剔牙。
石頭在桌上找了半天,終於找到那個不起眼的保溫瓶,他打開蓋子,放在舒慶面前。
「慶哥,喝點湯吧?」
酸酸辣辣的味道隨著瓶蓋開啟,慢慢的擴散開來,舒慶吸了吸鼻子,湊了過去,只看了一眼,他便抬起頭瞪向石頭,神色間有種說不出的陰鬱:「這是什麼?」
「酸辣湯啊!」
石頭老實的答道。
他根本沒覺察出舒慶異樣的表情,更沒想到舒慶接下來的舉動會是--大手一揮,將整個保溫瓶掃了出去。
保溫瓶掉在地板上,撞出嘶啞的悶響,鮮紅色的熱湯混雜著銀色的碎片,立刻在烏黑的地板上鋪散開來,那種蜿蜒的豔麗色澤,看上去刺目無比。
石頭不知所措的瞪大雙眼:「慶哥你……」
剛一出聲,肩膀便被舒慶一把抓住,饒是石頭皮糙肉厚,也痛的直裂嘴。
「誰教你弄這個的?」
舒慶的聲音低沉而危險,一雙黑眸幽深冷厲,令人無法逼視。
石頭嚥了口唾液,才戰戰兢兢的道:「……是陸大夫……他說你要喝點發汗的東西……」
舒慶瞇起雙眼,看著他好一會兒,才將手鬆開。
石頭揉著疼痛不已的肩膀,不用懷疑,那裡一定已是瘀青一片。
慶哥這是怎麼了?
正滿心納悶,便見舒慶一把撕開了覆在傷口上的敷料,有著無數條黑色長腳的蜈蚣立時猙獰的袒露出來。
石頭大驚失色的喊道:「慶哥,你幹什麼?」
「果然傷的很重。」舒慶無所謂的笑了笑,放開手。
石頭蹲在他身邊,仔細將敷料再次包好,又急又氣:「慶哥,你想嚇死我啊!」
舒慶不語,垂頭看著石頭,面無表情。
感受到了舒慶的注視,石頭一抬頭,滿身的汗毛立時豎起:「慶,慶哥,你幹嘛這樣看我?」
「石頭,昨晚救我的人是誰?」舒慶沉聲問。
「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過是個內科醫生……運氣真好是不是……隨便一抓就是個醫生……」
石頭竭力讓自己的表情語調自然一些,雖然那很難!
「那人是男的還是女的?長什麼樣?」舒慶不耐的打斷他。
「是男的……長什麼樣子我還真沒記清楚,反正就是一瘦老頭……」
石頭謹慎的答道。
「老頭?」
「是啊!頭髮白了一半,不是老頭是什麼?」
舒慶不再說話,怔然半響,突然站起身子大步走進臥室,「砰」的一聲,將門拍上。
石頭連忙追了過去,卻發現門已經上了鎖。
「慶哥,你還沒吃藥呢!」
他拍著門板大叫。
很快,從門內傳出一聲低沉的怒吼:「滾!」
石頭一縮,退後幾步,不再吱聲。
舒慶顯然心情極差,而一旦舒慶心情不好,躲遠點才是明哲保身的道理。
至於讓他吃藥這回事--還是做白日夢還比較快!
看了看緊閉的門板,再看了看地板上已經開始變涼的紅色湯汁,石頭一臉困惑的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整個腦子都混亂不堪--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關上門,房間便一片黑暗。
左胸下方那塊巴掌大的地方,不斷的抽搐,又悶又痛。
舒慶只得用力蜷緊身子。
腰後的傷口被重重牽拉,立刻就是撕心裂肺般的痛楚,可是這種痛卻可以弱化胸口的煩悶,所以舒慶反而更用力的讓那疼痛再銳利一些。
他很少回想關於那個人的事,如果不是今天石頭拿出的那碗酸辣湯,他原本可以很成功的度過沒有回憶的一天。
他用力的想將那個人驅離腦海,可不知為什麼,平日得心應手的事情今天做起來分外的吃力。
他睜開雙目,沒有足夠的光線,他依然可以清楚的看到那片蛛網。
只要看到那個,他就可以確定,自己是躺在自己的床上,而不是那間簡陋小屋的單人床。那個人極愛乾淨,絕對不會允許自己的房子有一絲一毫的不潔。
他總喜歡煮各種各樣的湯給他喝,最多的,便是酸辣湯。總是在他打架或淋雨後,逼著他喝下一大碗,再怎麼反抗,都沒有用……
胸口又是一痛,他吸氣,吐氣,強迫自己不再回想。
他終究是要找到他,只是時候未到,他的力量還不夠強大!如果不想重蹈吳勁的覆轍,他必須耐心等待。
其實他並不恨吳勁的背叛,如果換做是他,他定會毫不猶豫的去做,而且中途不會有半絲猶豫!吳勁錯在半途而廢,落了個背叛的名聲,還害自己妻兒不得善終,這是吳勁唯一的錯。
果然如舒慶所說的那樣,吳勁的妻兒像在人間蒸發了一般,不見任何蹤跡,顯然是凶多吉少了。
抓到的那兩個最終也沒供出幕後的主使者,這件事就這麼不了了之。
炎青給了石頭一大筆錢,讓他去酬謝那個救了舒慶的「老頭」。石頭是有苦說不出,只得悄悄將錢存起來,打算等這件事完全平息之後,再交給連清籬。
直到第四天,石頭心中的兩塊大石才正式落下。連清籬聽進了他的勸告,沒有做出報警的舉動,派去監視的兄弟終於被叫了回來,而舒慶也再次變得生龍活虎起來。舒慶的恢復能力,連見慣了世面的陸大夫都嘖嘖稱奇,不過石頭心裡清楚,如果沒那兩袋血,舒慶根本不可能好的這麼快。
很久之後,石頭才想起一個重要的問題--相同血型的血才能輸,如果血型不符,鐵定會死人!可是那位先生怎麼知道慶哥的血型?這個疑問在石頭的腦袋裡剛一閃現,便被他拋諸腦後。
事情已經過去,再想這些也只是白費力氣,況且,石頭清楚的知道,那位先生絕不會希望自己因為這個問題去打擾他。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流氓情人(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流氓情人(上冊)
舒慶原本是連清籬想遺忘的一個錯誤。
兩個人都不愛男人,個性及身分也是天差地別,甚至是十年後再相會,他們之間的距離是更加遙遠。
但一個陰雨綿綿的日子,一個意外,他們又再相遇。
原以為只要遠離,那心裡的傷口就會慢慢癒合,淡忘。
可看著那瘋狂又偏執的眼神,緊握得他發疼的手,連清籬迷惑了。
也許,他該讓他知道,真正偏執的人,並不是他……
章節試閱
第一章
下了幾天的連陰雨,空氣中的濕氣,凝結成薄紗般的霧,將夜色籠罩的分外迷離。
連清籬停好車子,走出小區的地下停車場,已經是凌晨兩點。
每年校友聚會都弄到這麼晚,不過衛空遠和何箏喜歡,他便沒有反對的餘地。
衛空遠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老闆,大學四年,研究生兩年,後來又在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前前後後兩人已認識了十年。何箏是小他三屆的學妹,現在是他的女朋友,相識半年來,感情還算穩定。
他該慶幸自己因為要開車,所以沒被灌太多的酒,不過在那種嘈雜的地方,只是坐著都讓人覺得身心疲憊。身上染滿了煙酒的臭味,他現在...
下了幾天的連陰雨,空氣中的濕氣,凝結成薄紗般的霧,將夜色籠罩的分外迷離。
連清籬停好車子,走出小區的地下停車場,已經是凌晨兩點。
每年校友聚會都弄到這麼晚,不過衛空遠和何箏喜歡,他便沒有反對的餘地。
衛空遠是他的好友也是他的老闆,大學四年,研究生兩年,後來又在同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前前後後兩人已認識了十年。何箏是小他三屆的學妹,現在是他的女朋友,相識半年來,感情還算穩定。
他該慶幸自己因為要開車,所以沒被灌太多的酒,不過在那種嘈雜的地方,只是坐著都讓人覺得身心疲憊。身上染滿了煙酒的臭味,他現在...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淳于緋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11-06 ISBN/ISSN:986206050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