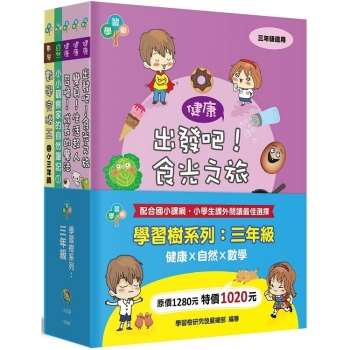第一章
該死的天氣,連買菜都成麻煩事,今天的晚飯怕是要沒著落了。這是祁安看著窗外的瓢潑大雨冒出的第一個念頭,隨之而來第二個念頭,是他沒帶傘。
祁安不喜歡雨,非常的不喜歡,甚至這種不喜歡的感覺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然而老天非常喜歡跟他作對,這個他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城市裡,總是有一半的天氣是在陰雨中度過的。
過多的雨水並不能滋生萬物,倒是非常適合各種黴菌的發酵。就連他本人都覺得骨子裡快生霉了,渾身痠痛,稍稍動一下就能聽見各處關節喀喀作響。
唉,人上了年紀,連身體都不聽使喚了。祁安不知是第幾次為自己孱弱的身體發出感慨,儘管他今年才二十七,算上虛歲也不過二十八,正是大好單身青年的第一個黃金時段。
然而現在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裝成老氣橫秋的模樣,過了二十就說自己是奔三的人了,指著十七、八歲的少年說「看你們這些孩子」,好似虛長了對方幾歲就多吃了幾十年的飯似的,滿口「想當年」。
祁安並不喜好這樣的偽裝,他從不趕流行,更多的時候他會顯得與同齡人格格不入,是真正超出年齡外的老成與淡定。但於他而言,他只會覺得自己是老了,即使是身體還年輕,心也老了。
所以醫學上常說的老年病年輕化就常常會體現在他的身上,譬如在這樣的雨天裡渾身長霉,其實只是關節炎犯了。
「祁安、祁安,你到底有沒有聽到我講話?」主任無可奈何地敲打著桌面,試圖喚回眼前這個不知神遊到天外何處的下屬注意。「這件事我知道你是無辜的,但上面是這個意思,想讓你出面道個歉,把事情了結算了,也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祁安點點頭,沒什麼意見。主任叫他來時他就猜到了會是這樣的結果,也不算意外,記者嘛,總要有勇於承擔報導後果的勇氣。
「你能想得開就好,也不是什麼大事,道個歉也就過去了。」主任拍拍祁安的肩,心裡也吁了口氣,他對這個人還是十分看重的,只是有時候祈安也未免太沒脾氣了點,都摸不清他心裡在想些什麼。
是啊,道個歉就過去了,他就是個十足的冤大頭。這件策劃案本來就是上面拍板定下的,但現在出了事就將責任推給下面的記者,活該是他接的這個任務,最後的責任自然就該由他來擔。
不過還好,任誰遇上這樣的事多了,也該習慣了。祁安在心裡給自己寬解,他確實是老好人,好到沒了脾氣,但並不表示他會沒想法,偶爾也還是會腹誹一下的。
從辦公室出來,祁安受到了同事們表示關切的注目禮。
百年修得同船渡,大家共事幾年,這點感情還是有的。
阿傑最先湊了過來,「怎麼樣,頭兒沒要你停職吧?」這人是部門裡的小靈通,什麼最新消息都是從他的嘴裡最先傳出來的。
「哪有那麼嚴重,就是道個歉而已。」祁安笑著走回自己的座位,他相信只要回答阿傑一個人,等到了下班時整個報社的人都差不多知道他化險為夷的消息了。
報社嘛,講究的就是及時迅速的傳播消息,倘若哪天要評比工作楷模,祁安一定會投阿傑一票。
桌上一團亂,昨天的工作還沒全部了結,今天拿到手的資料又有一堆,下個月省裡就要開兩會,到時候還有得忙了。一想到這,祁安就覺得他沒來得及吃早餐的胃在隱隱作痛。
午休時再去買盒即溶咖啡吧,家裡的已經全部喝完了,要開夜車加班,少了它還真熬不住。
他今天特別的累,也許是這樣的天氣讓人打不起精神,也許是其他的原因,剩下的半天祈安班幾乎是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的。這樣不佳的狀態連主任都看不下去,沒再給他多加工作,全都轉交了別人。
不可否認,他對於主任和同事不動聲色的照顧很是感激,但也忍不住苦笑,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他連面對喜歡的工作都提不起幹勁來,所謂的激情從來都沒有光顧過他。
下午去茶水間倒水時,碰上了廣告部的周娜,一個十分有品味的女人,連點菸的姿勢都是優雅的慢動作重播,一雙狐媚眼無論何時都能生出兩汪清泉來。
「小安,怎麼這麼沒精神,是病了?還是失戀了?」女人噴了口煙,彈了彈菸灰,精緻的臉龐上毫無瑕疵,可以推斷出除了天生麗質,化妝水準也屬一流。
「沒事,就是睡眠不足,欠休息啊。」祁安禮貌地打了聲招呼,快速地倒完水,離開茶水間。
失戀?還算不上,只不過三天前剛剛與那人分手了而已,或者準確地說,連分手都稱不上,只能說是解除了四年的同居關係,重回單身生活罷了。
四年啊,連他都無法想像那人竟然能堅持這麼久,以那人在大學時是出了名的風流,他還以為頂多四個月就了不起了,結果居然是四年。
然而當他完全習慣了那人的存在,甚至偶爾會假想一下這樣的生活或許會持續一輩子時,那人卻十分乾脆地提出了分手,理由是他這個情人實在太無趣了,令人乏味到了極點。
既然如此,那人還能忍受到過了四年後才提出分手,實在是不可思議到了極點,就好比當年那人向他提出做情人的邀請時一樣令他震驚,也同樣在第一時間就默默接受了。
合久必分,天下至理。
今天主任算是大發善心,默許了祁安提早下班的請求,讓他成功地避免了在電梯裡擠沙丁魚般令人窒息的痛苦。
電梯門快要合上時,有人邊跑邊喊:「等等、等等,我也要下樓。」接著就有一隻穿著耐吉球鞋的腳伸了進來,恰好卡住了電梯門。
「你好,我叫陶然,陶瓷的陶,天然的然,攝影部的新人。剛才多謝了。」順利趕上電梯的是個年輕的大男孩,一身休閒裝,頭髮蓬鬆,胸前掛著相機。
祁安先是驚訝,接著就笑了,他對這個富有朝氣的年輕人有良好的第一印象。「你好,我叫祁安,政宣部的舊人。剛才我什麼也沒做,是你趕得及時。」
陶然很健談,搭電梯這短短十三樓的距離都是他一人在說話,祁安只是微笑地聽著,幾乎插不上話。
外面的雨依然很大,天空像捅破了個大窟窿,水像是不要錢地往下潑,完全沒有要停的趨勢。好在陶然帶了傘,他將祁安一路送上車,扭頭下車時忽然勾住祁安的肩膀道:「別這麼沮喪,不就是失戀了嗎?大不了再找一個,這世上誰離了誰還不是得過下去啊。」
祁安茫然,等他回過神想解釋時,車已經開了。他摸摸自己的臉,表現的有這麼明顯嗎,怎麼每個人都說他失戀了?
想了想,還是忍不住微笑,世上誰離了誰還不是得過下去,對那人而言,真是再適用不過了。
***
冰箱裡早就沒有存貨了,祁安很努力地翻找,終於找到了一個雞蛋,一盤剩下的白菜,小半掛麵條,剛好夠解決晚餐問題。
他不是沒有錢出去吃館子,而是節約慣了,從上學起就養成不浪費一分一厘、不亂花冤枉錢的好習慣,一直保持到現在,一塊錢都恨不得能掰成兩半來花,怎麼算都是自己做飯要划算得多。
水很快就煮開了,打雞蛋、下麵條、倒入菜,加鹽、味精、醬油、醋,最後點上幾滴香油,關火,晚飯做好了。一系列的動作熟到不能再熟,要說祁安最為拿手的菜,也就只有下麵了,簡單方便又省事,還能及時填飽肚子。
端著碗走回客廳,那裡忽然就多出了一個人,正不耐煩地踱來踱去,似乎在煩惱著什麼,俊朗的面龐上混合著懊惱與怒氣。
「你怎麼會在這裡?」祁安瞪大了眼,因為太過驚訝,他險些弄撒了今天的晚飯。
「我怎麼就不能在這了,你沒忘記這是誰的房子吧?」男人見到他,顯得更加煩躁,口氣也十分不善,但怎麼聽都帶了幾分彆扭的情緒在其中。
是了,這房子是他的,自己怎麼就給忘了呢?祁安自嘲地一笑,隨即釋然,真正該離開的人是自己才對。
「不好意思,能讓我再住上幾天嗎?我會盡快找到房子搬出去的。」生疏而有禮的請求,祁安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就脫口而出。
想不到四年的同居生活也沒給兩人帶來什麼影響,好聚好散,至少這一點他應該是十分符合男人眼裡的好情人標準了。
「誰叫你搬出去了!?這房子我送給你了!」男人猛地大吼,雙眼能噴出火來。
祁安吃了一驚,心裡忽然就有那麼些不舒坦。這算什麼,分手禮物嗎?送他一間房子,真是好大的手筆,但是對於這人而言,實在是九牛一毛了。
財大氣粗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樣。
「你在想什麼?想罵我就說出來啊,悶在心裡算什麼!」
男人的脾氣越來越壞,已經開始踢桌子踹板凳,領帶袖口也已經扯開,祁安忍不住懷疑再說下去會不會發生一起暴力事件。
「你……今天要住這兒?」
「是啊,你有意見?我這段時間都要住這裡,你沒意見的話就一切照舊吧。」
一切照舊!?怎麼照舊,僅僅是吃住一起,還是連肉體的關係都要維持過去的模式?
「我想,我們已經分手了。」
「是啊,那又如何?」男人忽然繞過桌子,捉住祁安的下頷,凶狠地吻了上去。
這應該不叫吻,應該叫啃咬更為合適,而且是單方面的突襲行為。祁安無力反抗,確切的說是長期的習慣讓他忘記了要反抗,直到嘴上傳來了麻麻的疼痛,他才想起,他已經完全沒有必要再去承受男人如此的對待。
「啪!」清脆的一耳光,打醒了兩個人。
「你……很好、很好!你敢打我,你有脾氣了啊,很好。」男人本是陰翳地盯著他,忽然就放聲大笑起來,好像挨了這一巴掌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
「我餓了。」男人心情愉悅地吻了吻他的面頰,端過桌上的麵條,大口地吃了起來,邊吃還邊不忘評價:「嗯,味道不錯,你也就只有這點還算可取了。」
祁安捂著受傷的嘴唇,實在是跟不上男人變化的速度,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晚餐進了男人的口,而他自己還飢腸轆轆。
「你還站著幹嘛?傻了啊,快坐下吃啊,麵條涼了就不好吃了。」
「只有這一碗。」
他也想吃啊,可是有人一來就搶走了他的飯,還吃得津津有味。
男人抬起頭,看看他,再看看碗裡所剩無幾的麵條,低聲罵了句髒話,又埋頭將剩下的快速解決乾淨,一抹嘴,開始穿外套。
「你這人怎麼這麼懶,一下雨就不想出門了,冰箱裡沒東西了吧,活該餓死你。說吧,想吃什麼,我去給你買。」
男人大概是吃飽了,心情格外的好,連微抿的嘴角都帶了笑意。
「我們分手了。」祁安不得不再度提醒男人,實在沒有必要這麼做。
「我知道,你用不著一再強調,或者你還想讓我堵你的嘴?」男人舔舔唇,邪惡地揚眉,大有祁安只要再多說一句他就把剛才的事進行到底的架式。
飽暖思淫慾,這個只會用下半身思考的動物。祁安忍不住在心裡啐了一口。
「外面雨很大。」
「你是在關心我嗎,很好。不過我有車,淋不著雨。」
誰擔心這人會不會淋雨了,他擔心的是他的晚餐能不能平安地送回來。
「我想吃小河炒麵,順便幫我在超市買盒即溶咖啡吧。」
既然這人這麼主動,又吃了原本屬於他的晚餐,他想讓這人多跑幾趟腿也不足為過吧,反正有車一族做什麼都方便。
「炒麵可以,咖啡不行,我會幫你買牛奶的,看你臉上的黑眼圈,都快成國寶了。」男人甩甩鑰匙,穿鞋出了門。臨走時又一把拽過祁安親了一口,拍拍他的臉頰道:「乖乖在家等著,我馬上就回來。」
門砰地一聲關上,祁安滑坐在地上,把頭埋進膝蓋間,右手還在微微發顫。
他竟然真的打了男人一巴掌,而男人也沒有生氣……哈,這簡直太詭異了,是天要下紅雨了嗎?
上官隸,提出分手的是你,現在突然跑回來的也是你,你究竟想怎樣,糾纏不休可不是你一貫的作風啊。
祁安抱著頭,忽然很想大笑一場。
***
炒麵很快就買了回來,還冒著熱騰騰的蒸氣,香氣四溢。
然而祁安已經睡了,屋裡一片漆黑。
上官隸強忍著要把床上的人揪起來痛打一頓的衝動,鐵青著臉從臥室退了出去。他在即將發怒的邊緣注意到了床頭的鬧鐘,上面訂的時間是凌晨三點,這意味著祁安今晚仍然要開夜車,只是時段與以往不同罷了。
客廳很乾淨,永遠是纖塵不染。這是祁安的習慣,他有輕微的潔癖,很喜歡收拾東西,家裡的一切事物在經過他的手後總是井井有條,擺放有序。
上官隸把身子拋進柔軟的沙發中,點了支菸,猛抽了幾口又捻熄在菸灰缸中,起身去開窗。窗戶開了一半,手又停下了。
他在做什麼?他們已經分手了,他完全沒有必要再去在意祁安的任何喜好,而他竟然像個傻瓜一樣,在這三天裡不僅是對這個人念念不忘,現在更是主動送上門來希望兩人的關係能夠繼續。
他簡直是瘋了!
不,準確來說,當他開口提出要祁安做他的情人時,就已經是瘋了,被一時的情不自禁給沖昏了頭。
如果真要掰著指頭細算一下,他們應當是同居了八年,只不過頭四年是處於同房不同床、相識不相熟的狀態。
那時兩人同校,又是一屆,只不過他讀的是國貿,而祁安讀的是新聞。
新聞系的男生少,安排宿舍時分不齊,多出祁安一個,學校又不肯讓他單獨住一間房,只好調到國貿這邊來。恰好當時上官隸的宿舍中還差了一人,就把祁安給補了進去。
兩個系的課程和作息時間完全一樣,所以除了人在宿舍時,祁安很少和他們有什麼交集,就是在路上遇見了也不過是互相點個頭就過去了,連話都說不上幾句。
上官隸對祁安的第一印象並不是很好,只依稀記得有這麼個多餘的人,沉悶、呆板、無趣,不愛說話也不合群。
男生都喜歡在夜間活動,儘管學校有規定熄燈,但是根本無法起到管束的作用。大多時都是三、五個人聚在一起,點上蠟燭,買上一箱啤酒,鬥上一整夜的牌。要不就是一個寢室的在睡覺前習慣性臥談,談天談地談女人,往往是胡天胡地的亂吹一通,有時聊得太過興奮了,就會從床上跳起來撲到窗前學狼人對著月亮嚎上一嗓子,不久後就能聽到各處兄弟的回應聲。
這些祁安從不參與。他喜歡安靜的環境,白天沒課時在圖書館裡一泡往往就是一整天,晚上十點以後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就躺在床上塞著耳機聽英語。開始時有什麼活動大家還會叫上他,但漸漸地就彼此疏遠了,有事沒事都單獨把他一人撇在外。
祁安也不介意,依舊是獨來獨往,跟誰都不親近。
而上官隸則不同,他一進大學沒多久,就成了出名的蝴蝶公子,換情人比換衣服還快,連新上任才三天的助教他都不放過。
上官隸不是GAY,但也算不上絕對的直男,他對情人的選擇只憑感覺,只要看對了眼,不管是男是女他都OK。他的歷任情人中,各式各樣的類型都有,但有一點是絕對的,那就是要具有足夠漂亮到能吸引他的地方。
他喜歡美的事物,越是美麗的東西,越能夠激發他的佔有慾,想要得到手,想要他們成為自己專屬。然而得到了又不珍惜,厭膩了就會拋棄。
所以站在上官隸身旁的人,總是走馬觀花地變換不停,平均逗留時間最長也不會超過半年。半年已經是他忍耐的最長極限,然後就會開始尋找下一個美麗的目標。
祁安和上官隸是如此迥異的兩個個體,彼此之間的差異甚至可以比作南北兩極。照理說這樣的兩個人是不會也不應該有任何交集的,他們就像是兩條永不交集的平行線,在各自的世界裡穿行。
真正讓上官隸注意到祁安,是在大三時。那時上官隸已經搬出校外去住,連寢室都極少回,根本就忘記了還有祁安這個人的存在。
但忘得還不夠徹底,至少是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印象,所以當寢室的兄弟提出由他去照顧一下發高燒到不能起床的祁安時,他猶豫了一下,還是答應了。
原本有關祁安的任何事都是沒人搭理的,但他這次病得太重,溫度計一測四十一度,打過點滴後燒卻一直不退,始終維持在三十九度,燒到都開始囈語。他們是怕他病死了,這才本著人道主義精神抽籤決定由誰留下來看護病人。
上官隸從沒照顧過人,他身體好,連感冒都不常有,但好在這點基本常識還是有的,知道要用冷毛巾敷額頭降溫。
當時正值夏天,寢室裡有空調又開不得,就連電扇祁安都吹不得。上官隸無奈之下,只好抱著冰水搖扇子,扇子還是用雜誌充當的,即便是如此,仍然熱得他汗流浹背,渾身黏濕不自在。
最後實在是熬不住了,就每隔一陣去沖個涼水澡,然後把電扇架在走廊上,鋪上竹蓆,他就坐在蓆子上,掐算著時間再回來給祁安換毛巾。
祁安燒得很厲害,整張臉都紅得發黑,透出一股子死氣,叫人驚心。上官隸幾度猶豫要不要送他去校外的大醫院,但最終還是放棄了。
這個人不是他的責任,他守在這裡照顧人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沒有必要再去做多餘的事。
傍晚時祁安的燒稍稍退了些,人也平靜了許多,不再頻繁的囈語。雖然上官隸本人沒有偷聽人家隱私的習慣,但他還是聽到了,他聽到祁安在喊媽媽,喊著喊著就會流下淚來。有時說得更多些,就會喊「不要走」、「不要放棄我」、「我會努力的」之類的。
很突兀的,他對這個人的過去生出幾分好奇來。是怎樣的過往,才會讓一個人在最脆弱的時候呼喚自己的母親,並悲傷到流淚。
他沒有過這方面的經歷,所以忽然有種在無意間探知到了對方最隱晦的祕密時的沾沾自喜。他甚至不無惡意地猜想,當祁安在得知自己在他面前哭著喊媽媽時,那張呆板無趣的臉上會出現怎樣的表情。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樂天安命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樂天安命
祁安不敢想像自己居然能和那人堅持這麼久,以那人在大學時出了名的風流程度,他還以為頂多四個月就了不起了。
可當他漸漸習慣了那人的存在,甚至偶爾會假想這樣的生活或許會持續一輩子時,
那人卻十分乾脆的提出分手,理由是他這個情人實在太無趣了,令人乏味到了極點。
他只能默默接受了。畢竟這段和那人在一起的日子,原本就是不可思議之事。
可那人卻在提出分手之後又回來了!
一向溫順的他終是忍不住打了男人一巴掌,而那人竟沒有生氣,更詭異的是,居然還準備要搬回來住?
上官隸,提出分手的是你,現在突然跑回來的也是你,
你究竟想怎樣,糾纏不休可不是你一貫的作風啊!
章節試閱
第一章
該死的天氣,連買菜都成麻煩事,今天的晚飯怕是要沒著落了。這是祁安看著窗外的瓢潑大雨冒出的第一個念頭,隨之而來第二個念頭,是他沒帶傘。
祁安不喜歡雨,非常的不喜歡,甚至這種不喜歡的感覺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然而老天非常喜歡跟他作對,這個他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城市裡,總是有一半的天氣是在陰雨中度過的。
過多的雨水並不能滋生萬物,倒是非常適合各種黴菌的發酵。就連他本人都覺得骨子裡快生霉了,渾身痠痛,稍稍動一下就能聽見各處關節喀喀作響。
唉,人上了年紀,連身體都不聽使喚了。祁安不知是第幾次為自己孱弱的...
該死的天氣,連買菜都成麻煩事,今天的晚飯怕是要沒著落了。這是祁安看著窗外的瓢潑大雨冒出的第一個念頭,隨之而來第二個念頭,是他沒帶傘。
祁安不喜歡雨,非常的不喜歡,甚至這種不喜歡的感覺已經到了深惡痛絕的地步。然而老天非常喜歡跟他作對,這個他生活了快三十年的城市裡,總是有一半的天氣是在陰雨中度過的。
過多的雨水並不能滋生萬物,倒是非常適合各種黴菌的發酵。就連他本人都覺得骨子裡快生霉了,渾身痠痛,稍稍動一下就能聽見各處關節喀喀作響。
唉,人上了年紀,連身體都不聽使喚了。祁安不知是第幾次為自己孱弱的...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佩蘭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8-13 ISBN/ISSN:986206201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