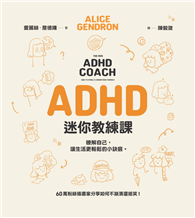第一章
夏末秋初,天清雲舒。
濟安城內遊人如織,南來北往的商客旅人都得了新修成的殤京運河之便,紛紛趕來一睹這花都之城每年十月初十的百花節。
不過此花非彼花,濟安城的百花節賽的是人,而且是各家寶樓繡坊的美人,男女不限,唯美者奪魁。
其實若說直白了,也無非是那些風流之地溫柔之鄉的美人們爭奪花魁罷了,妓院倌館全國遍地都是,哪裡都不缺乏這種招攬客人的噱頭。
只不過這濟安城的百花節,是一年比一年辦的轟轟烈烈,唯恐天下不知。不僅是成了濟安城內最為盛大的節日慶典,甚至還取得了官方認可,由府衙直接出人出力,在百花節期間要確保眾家美人的安全無憂。
甚至連當今的聖上泉帝,也曾在一次遊園中對年輕的太宰大人戲稱道:「百花節上百美人,溫柔鄉裡最溫柔。」
當然,這也不過是皇帝一時興起隨口說說罷了,當不得真。
然而這話傳入民間,倒是比那些絞盡腦汁的招牌標語都還管用,吸引了大批的文人墨客、官宦商賈前來爭睹這能讓當今天子都讚歎不已的百花節。
所以每到十月,在濟安城內隨處可見那些平日裡絕對見不著面的,官階五品以上的官,或是家財萬貫的商。
而城裡的那些寶樓繡坊也正是看好了皇帝金口玉言一字千金,怎麼看都是一塊亮閃閃的金字招牌,於是乾脆找了有名的雕刻大家李一刀,給刻了三塊牌匾,就掛在百花街入口的牌坊上,權當門聯。
這左右兩聯嘛,自然是皇帝的那兩句戲言。而橫批,則是太宰大人當時回敬皇帝的兩個字──風流。
風流本沒錯,只要不下流。多少人以此自命,甚至是趨之若騖,因而牌匾掛出去後,百花街當晚的迎客量立即過萬,再創歷史新高。
但據小道消息稱,太宰大人曾在一次醉酒後,在大理寺內指著一個因嫖妓而犯事的官員罵道:「上樑不正下樑歪,風流不成變下流。」不過既然是小道消息,其真實性還有待考證。
就衝著能在那溫柔鄉裡夢一場,多的是人假借風流之名行快活之事,就算太宰大人真要罵,第一個被罵的也應當是皇帝,離他們這些做臣子當百姓的,還差得遠呢。
***
解憂樓本是濟安城裡一家不算太起眼的酒樓,曾因經營不善而倒閉,一個月前剛換了新主,而七天前才剛剛重新開張。
這酒樓的新老闆倒是一個善於營運的好手,上手先下了大血本將整座樓裡裡外外都給重新裝修了一遍,走的還是時下最為流行的清雅風,桌椅門簾均為竹製。接著又重金從外省聘請了幾位大廚,專做些山野風味素食小炒,每日早中晚還推出不同風味的煲湯,及飲外帶均可。
結果開張不過數日,樓前的門檻都快被踏爛了。人們吃多了那些葷膩味重的菜色,對這種清新雅致並以素菜為招牌的酒樓,自然是別有一種新奇感。又加之菜食本身味美可口,自然是新客不斷,回頭客也不少。
不過解憂樓畢竟還是酒樓,菜色可改,酒卻不可少。
解憂樓裡的酒只賣一種,名為杜康。這樣的命名方式自然是引經據典,借了一句古詩,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杜康酒是甜酒,其本身是依照米酒的做法改釀的,喝不醉人。若為嗜酒之人所飲,必會叫嚷著其與糖水無異,實在是不夠味。然而若是配上了樓裡的素菜,卻是再合適不過了。
酒的清甜加上素菜的爽口,滑而不覺厭膩,淡而不覺無味,互為輔襯,確實是搭配的恰到好處。
有客人願來是好事,但客人過多就不一定是好事了。為了爭位鬥氣不掉面子,時不時總會有些只懂進不知退的人摩擦生事。
不過凡是在解憂樓裡打架鬥氣生事的人,事後不僅要花大筆的銀子來賠償那寫了一長串清單的損失費,而且從今往後都不得再踏進樓裡一步。
也有人不服氣,故意挑釁,結果翌日就鼻青臉腫地乖乖跪在門口又送銀子又賠罪。類似的事發生多了,也就再沒有人敢隨便在解憂樓的地盤裡撒野了。
故而有人猜測,解憂樓裡那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新老闆,說不定是個什麼了不得的大人物,至少也該有個很硬的後臺撐著。
當然,這也不過是那些食客們酒足飯飽後的談笑罷了,他們可是連老闆長什麼樣,是男是女,年齡籍貫為何都不知道呢。
總歸一句話,神祕著呢。
***
「哎,你聽說沒,當今的太宰大人辭官回家了。」
「你可別瞎說啊,我可是聽說那年輕有為的太宰大人可是皇帝眼中的大紅人,皇帝把他寶貝的不得了呢,每年給的那些賞賜啊,件件都是珍奇異寶,別說你我見過了,就是聽都不曾聽說過。」
「這我哪能瞎說啊,是真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老婆二弟的嬸子的侄子的姐夫在宮裡當差,這可是從宮裡傳出來的消息,哪能假的了。」
「這就奇了,太宰是多大的官啊,站在那兒想幹嘛就幹嘛,就連皇帝都要讓他三分,這好端端的辭什麼官?我看是傻了吧。」
「當然不會是平白無故的辭官啊,我聽說啊,是因為皇帝新納了幾位妃子,太宰大人才一氣之下辭官的。」
「這就更奇怪了,皇帝娶老婆,太宰大人生什麼氣,難不成皇帝娶的是他的老婆?」
「這你就不知道了,我可告訴你,其實那太宰大人和皇帝啊……是那種關係。這不皇帝新娶了妃子,吃醋了唄。」
「難怪太宰大人能得皇帝的寵愛,原來是這麼回事。不過能被皇帝看上的人,那容貌那長相,呵呵……想必也不會比皇帝娶的那些美人兒差吧?」
「想也不會差啊,不然哪能迷得倒皇帝啊。我還聽說啊,太宰大人的美貌可是和麒王不相上下。」
「……」
待那兩人結了帳離開後,二樓一間雅廂裡,一個面若桃花的少年對著半敞的窗口啐了一聲,「呸,兩個亂嚼舌根的傢伙,真想把他們的舌頭給割了。」
扭頭又衝著裡間那喝茶的人道:「老爺也真是的,怎麼不叫人把他們給轟出去,就由著他們在這裡胡亂潑墨塗黑。」
那被喚做老爺的青衣人,捧著茶盞微微一笑,倒是不氣也不惱。「話是讓人說的,能堵住他們的嘴,難道就能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堵住一個是一個嘛!老爺您聽著不在意,我們這些做下人的,聽著可就未必舒坦了。」
少年嘟囔了一句,臉上還有未消的忿然之色,臉頰紅撲而粉嫩,像是顆水靈靈的大蘋果。
青衣人放下了手中的茶盞,起身走到少年面前,雙手一伸一捏再一拉,愣是在少年粉嫩的面頰上扯出個鬼臉來。
「你有什麼不舒坦的,我看你是悶太久了想活動下筋骨揍人玩吧。」
「唔……」少年在心裡大叫冤枉,可是苦於臉上受制於人,說不出話只能哼哼兩聲表示抗議。
青衣人捏的差不多了,這才鬆了手,又摸了摸少年青澀冒尖的頭道:「別胡亂滋事。你嫌悶,也不過就忍這幾天罷了,日後有你的事做。」
青衣人一貫溫和的語態裡,隱隱流露出些許命令的威嚴。
少年捂著臉垂下頭,雖心有不甘,卻也不敢再表露出來。他自幼就跟在青衣人的身邊,這點細微的改變自然是察覺的出來。
「行了,別一副不情不願的苦悶相。去給我換壺溫酒來,要有客人上門了。」
青衣人順勢在少年光潔的額頭上彈了一記,看他吃痛的捂著額頭邊抱怨「就知道欺負我」之類的,邊快步向廚房跑去。
待少年離遠了,青衣人這才走到窗邊。
這間包廂正對著樓前喧囂的街道,雖有些吵鬧,卻也視野極佳,此時遠遠就能瞥見一輛馬車正向解憂樓前駛來,車頂上有金屬質地的東西正一閃一閃的發光。
他半垂著眼瞼,長長的眼睫在如玉的面龐上投下兩片扇形的陰影,隨手又闔上了窗。
正巧那桃花似的少年拎著兩壺溫過的杜康酒走了進來。少年聰慧如斯,顯然是知曉杜康酒性太溫,現下又沒菜下酒,一壺是肯定不夠喝的。
***
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那客人腳還沒進門,爽朗的笑聲已遠遠的傳進了包廂。「林小子,你哥哥我看你來了,還不快備上好酒好菜招待我。」
「酒在桌上,菜在鍋裡。既知大哥要來,又怎會怠慢。」青衣人亦是笑道,淡淡的笑意裡帶著幾分真切的歡喜,顯然來者也是他一直想見的人。
來人也不客氣,抓過桌上的玉瓷酒壺舉起便飲,連酒杯都省了,一會兒便灌了半壺進肚。
桃花少年看得直瞠目。他跟在青衣人的身邊也算是見慣了那些達官貴人富家公子飲酒作樂時附庸風雅的作風,今兒個難得見了個特豪爽的,跟看什麼珍稀似的,雙眼瞪得溜圓。
「呵呵,還是你小子上道,知道孝敬哥哥。」那人咂咂嘴,一手還抓著那半壺酒,另一隻手重重地在青衣人的肩上拍了幾下,也不管那力道對方是否承受的起。
忽而又神色哀淒道:「哪像那兩個黑心黑腸的東西,我千里迢迢的跑去,可他們倒好,不但不領情,居然還把我往外攆,你說氣人不氣人。」
青衣人突聞抱怨,頗有些無奈的道:「倘若大哥醉酒後的舉止不至於太荒唐,想必二哥、三哥也不會這般不近人情。」
「你小子怎麼也這麼說我,你哥哥我只是貪杯了點,平日又放蕩不羈了點,又構不成什麼大罪,有必要被你們當過街老鼠般對待麼?真沒兄弟友愛。」
那人說歸說,可畢竟是底氣不足,黝黑的臉龐上泛了幾點紅暈。不過好在他一向皮厚面黑,也不怕被自家小師弟看出。
青衣人也不戳穿,只管應聲說是,好歹也要給大師兄留個面子吧,不然倘若那些事真給誰抖了出去,他們師門可是要一併給抹黑了。
那人也不是個給了臺階不知下的人,立馬轉了話題。「林小子,這回的事我可是聽說了,是那臭小子欺負你了吧,先前娶了一個還不夠,現在又娶了兩個,把你往哪擱呢。要我看啊,你這次既然離了他,就乾脆徹底點別再回去了,斷了這份心思也好。」
青衣人搖頭失笑,還未啟口,只聽那人又道:「現在外面都傳你和那什麼麒王長得挺像的,可我看不像啊。那麒王我也見過一次,長得比女人還漂亮,可你哪,不是做哥哥的我打擊你,要論漂亮,你還真排不上名。」
「大哥這話說的是,若論容貌,麒王可是豔絕天下。我比他,自是比不得的。」
這青衣人不是別人,正是不久前才辭官的前太宰大人──林濤。而來人,則是一同出自天機老人門下的大師兄,梁翼。
梁翼撓撓頭,盯著這有三年未見如今是愈發消瘦的小師弟,囁囁道:「你知的,你哥我就是心直口快了些,說話不經腦,沒別的意思。」
「外人的閒言碎語,大師兄不必跟著放在心上,我聽了這些年,也早就習慣了。」
林濤出身官宦世家,又以幼年之身登朝拜官,在朝多年,什麼樣的大風浪都經歷過了,所謂流言,都是聽過即罷,從不上心。
梁翼看出他不願在此事上繼續糾纏,當下便識趣的住了口,可沉默了沒多久,又忍不住說道:「當初你若不是一心為他,也不至於遭那份罪,還落下了這麼重的病根。看你現在瘦得跟竹竿似的,風吹即倒。」
這話中雖有斥責之意,但更多的是憐惜之情。
林濤何嘗不明瞭師兄多年來的不能諒解是源自對自己的關愛,可做過的事哪有後悔的理,何況當年他早已立下誓言,此生只為一人……
若單論容貌,林濤的確是不漂亮。終年病態的蒼白,身形極瘦,若是解了衣袍,身上的肋骨都能一根一根的數得清,被比作竹竿實不為過。尋常人見了,還當他是久患癆病,命不長久。
髮眉鼻唇都是普通到了再普通,毫無特色可言,更無美感可讚。若是拋開了身分地位不談,他就是在大街上轉上三圈,也未見得有人會多看他一眼。
可若是將他細看去,便會發現那一雙眼眸如同洗盡了凡塵的一汪秋水,凝聚了百煉蒼生的光華,脈脈生輝。
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不重視,乃至漠視,卻無法輕視。他永遠是站在數丈紅塵外,談笑經綸,衣不染塵。
但誰又可知,他是染遍了紅塵,才能這般遺世而立,笑看蒼生。
的確,如果當年他曾有過一絲猶豫,便也不至受盡凌虐酷刑,經脈俱斷,一身武學全廢,身體更是有如破布,多年溫補也不見有絲毫起色。想來這殘損的身子,是注定要帶進墳墓去了。
紅塵漸消,愛恨難了。偏偏遇上了那人,他就從未後悔過。
淡然一笑,林濤也轉了話題。「大哥此次路過,是為別事吧。」
如果沒有馬車頂上那特殊的齊雲山莊的聯絡標誌,他或許會認為梁翼是單純的來找他敘舊的。可扯上了齊雲山莊,事情就沒那麼簡單了。
齊雲山莊本是寧江織造大戶,皇宮裡每年的織衣繡紡,有一半以上都是交由齊家承辦的。而莊主齊淵年逾半百,一向德高望重,聲名不錯。可就在半年前,齊雲山莊發生了一場驚天血案,全莊一百三十八口人盡數被殺,包括齊淵在內,齊家人除了出門遠遊的么子齊笙外,全都死於莊內,而且俱是被一劍穿喉而亡。
當今聖上泉帝對此事也極為重視,派了專人來徹查。不想這一查就是半年,卻連點蛛絲馬跡都沒能挖出來,泉帝無奈之下只得作罷,下旨厚葬齊家,並追封齊淵為寧江候,以表皇恩眷顧。
「沒錯,我此行的確是為齊家的事而來。」梁翼面色一整,眉頭緊蹙,神情肅然。「我和齊家二子齊閩曾有過一段交情,那信物也是他送給我的。齊家慘案一發,我便暗中追查了許久,想著怎麼著也要將那兇手給抓住好祭奠我苦命的友人。可那兇手也狡猾,竟能不留一絲破綻。」
「這麼說來,大哥也沒能找到線索了?」不同於梁翼的沮喪,林濤倒覺得這樣的結果是理所當然。當時不僅是皇帝派出了人,他也派了暗影私下追查,同樣沒能查到任何消息,而單憑梁翼一人,自然是更難以有所收穫。
「那大哥此次來,又是為何?是得了什麼新的消息麼?」
「若是這樣便好了。」梁翼長歎一記,「還不是齊家的那小兔崽子,我聽說他在這一帶有出現過,就想把他找到帶在身邊。如今齊家就剩他這麼一支獨苗了,怎麼的也得保住吧。」
林濤點點頭表示理解,心裡卻令有一番計較。
齊家的么子齊笙,在血案發生後就突然失蹤了。起初他也以為齊笙是在別處遇了害,一查才知是齊笙自己把自己藏了起來。想必是家中突遭大變,也怕對方會斬草除根。
查清了齊笙的所在後,他就派了人暗中保護,隨後就任由那小少爺一路東遊西竄。原本是想放長線釣大魚,可哪知大魚似乎是忘了這條漏網的小魚,再也沒有現身過。
***
梁翼許是太久未見林濤這個小師弟了,這次難得見上一面,便多少是有些想賴著不走了。何況這一路風塵僕僕的,鐵打的人也累得慌。
不過事不待人,加之林濤似乎也沒有留他久住的意思,先是好酒好菜的陪他吃了個飽,接著又選了一間上等的客房供他歇息了幾個時辰,便送人上了路。
臨別時,梁翼瞄了眼那幾乎寸步不離林濤身邊的桃花少年,打趣道:「林小子,你從哪撿了這隻小貓,長得倒挺標緻的,但不是個安分的主啊。」
這話叫人聽了總有些調侃輕視的意味,但實則是一眼就將那少年看了個通透。
「玉不琢不成器,總要磨練個幾回。」林濤朝梁翼拱手一拜,「大師兄日後若有用到人的地方,儘管將他使喚去好了。」
林濤明白,他這個師兄一向廣交豪傑,凡能入其眼者必有過人之處,此番肯點評上幾句,自是看好了少年無限的潛質。
而少年猶不自知,他一貫驕氣,自是容不得被人說上半點不好,此時正嘟著一張小嘴暗恨在心。
梁翼沒將少年的怨氣放在眼裡,撫掌大笑幾聲,又道:「這小貓叫啥?能得你如此看好。」
少年實在是嚥不下這口氣,衝口便道:「我叫林寶,才不是什麼小貓呢,你別亂叫。」說完又臉色發青,皓齒抿唇,似有悔意。待見林濤並無惱意,這才微微放下心來,又一連瞪了梁翼幾眼,方覺解恨。
梁翼瞧著倒覺得這少年著實是可愛,忍不住又逗弄道:「林寶,是林小子取的吧,就不知是寶貝的寶呢,還是元寶的寶。」
林濤「噗哧」一聲笑道:「大哥是想猜後者吧。」
林寶不明其意,困惑地在兩人臉上不住的張望。
梁翼上前一把抱住這個面軟心韌的小師弟,拍了拍他的背,頗為感慨的道:「你小子從小就是生意經滿口,從不做吃虧的買賣,你若覺得值,我們自然也不便多插口。只是好歹都是一家人,別太生分了,有空常回來看看,師父和那兩個臭小子也都挺想你的。」
林濤心底一酸,眼眶也有些潤溼。他不是個輕易就動情的人,但別人待他的好,他卻是分分都記在心裡,時時記得要償還。
他父母過逝的早,師父天機老人待他如父,三位師兄更是如親兄長般處處為他著想。可他當年是鐵了心的要跟著那人,師父師兄雖不贊同,卻也沒可奈何,又加之事後事端頗多,見面的次數也在不覺間越來越少。
現下被提起,說不愧疚是不可能的,畢竟師父師兄之於他,便有如親人,但若言及悔恨,卻無半分。也莫怪師父常歎他才是師兄弟間最為面慈心硬的一個,一旦做過的事就絕不回頭。
待梁翼的馬車遠走了,林寶才壓不住好奇問道:「老爺,這『寶』有何不同麼?字還不都一樣,難不成還能多出一劃來。」
聽這話的意思,倒是在腹誹梁翼的不識字了。
林濤被他這麼出口一問,也覺得好笑,別離的悵然隨即就被沖刷的差不多了。他順手捏了把少年紅潤健康的面頰,這才解釋道:「大哥是暗指我愛財呢。」
林寶卻不以為然。「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試問天下有幾個不愛財的。都說有錢能使鬼推磨,要我說啊,有錢能使磨推鬼才是真理。」
林寶年齡不大,不過才剛滿十七,只因家中曾橫遭變故身心受創,故而說出的話也略顯老氣偏激,但也句句在理。
林濤笑而不語,他雖看出少年是話出有因,仇怨太深,卻也不多加規勸。
人啊,要磨平稜角,疼痛總是再所難免的。
***
天香樓,看名便知是煙花之地。而且在這出名的不是妙齡的女子,而是貌美的男子,俗稱小倌。
林寶被他家老爺給帶到這裡,起先是覺得新奇,左顧右盼一刻也不消停。
可看得久了,便覺得有些膩味。放眼望去遍處都是些甜言軟語、調情打諢的景象,與一般的妓院也沒什麼分別,只是伺候人的由女子換成了少男罷了。
幾番欲問緣由,但話到嘴邊,一瞥見林濤笑中帶冷的神色,就給乖乖的吞了回去。老爺說過要他學會沉穩不流於浮,他可是都字字記在心裡。
林濤選的是靠近角落的一間雅座,位置比較隱蔽,但是視野不錯。他進門時便給了老鴇一顆金珠,只消寥寥數語,對方便知情善意的領他們進了這間雅座,沒派人過來伺候,只送上了幾壺好酒和下酒的小菜。
林寶閒著無聊,也曾打過這酒菜的主意,可剛伸出手,就被林濤一掌給拍下了。
「這裡的酒菜都是經過特製的,若是吃了,你今晚就非得留在這裡不可。」
林寶也不是不知事的人,這樣的事自然是一點就通。他面色微窘,嘴上還發硬道:「這也太陰損了吧,倘若別人無此意,吃了這的東西豈不是不成也得成了。」
林濤看他一眼,「這是花街的潛規矩,沒什麼可意外的。即便是真的發生了,也少有人會抱怨,倘若真有不能消氣的,事後補上幾個銀子說上幾句好話也能不了了之。」
少年終究皮薄,囁嚅了一陣說不出話來,又想著自己當年也曾險些被賣進花樓,心裡更是五味雜陳得難受。
林濤只當沒看見,忽然一指廳堂道:「小寶,我要你今晚冒充這兒的小倌,去陪那人。」
這話說的極硬,連點轉圜商討的餘地都沒有。
林寶一驚,他自從跟在林濤身邊起就知總會有這麼一日,心裡準備也準備了好幾年,但是突然說來就來,仍是免不了有些慌張。抬首順著林濤手指的方向望去,結果又是一驚。
那人年歲不大,與林寶相仿,只是骨骼面相都比這桃花似的少年看得清朗些。穿了一件湖綠色的長衫,手裡還捏著一把扇子搖來搖去,突地一看去還挺老練的,但仔細一看,那人眼中的緊張新奇之色就一覽無遺了。
「老爺,你指的是他?!那個……雛?」林寶實在想不出該用什麼詞,琢磨了半晌才從牙縫裡擠出了這麼一個字。
林濤忍著笑,點了點頭。「沒錯,他就是齊笙,你今晚去陪他,務必要讓他纏上你。明日,我就要見此人。」
他沒有解釋為何梁翼急欲尋找的少年會在這裡出現,更沒有解釋為何要用這種方式讓齊笙主動來找他們。因為沒有必要。
林寶也沒有多加詢問,他此刻已收斂了驚惶之色,帶著一種與年齡不相符的老成與精幹,向林濤施了一禮,便欲下樓。
凡是跟隨在林濤身邊的人,若是沒有隨時為他所用的自覺,也就不必留下了。
林濤突然又叫住了他,為他整了整衣衫,又拍了拍他緊繃的臉頰道:「點到為止就好,可別失了身,不然我這賺錢的買賣可就成了賠錢的事了。」
林寶一愣,臉上浮現出一抹古怪的表情,嘴裡含含糊糊也不知咕噥了句什麼,一個轉身逕自下了樓。但那身影,已經沒了先前時的僵硬。
林濤倚在樓上看了一陣,見那兩個少年相攜著離開了天香樓,他靜坐沉思了一會兒,也隨即出了樓。
此時夜已深,離開了花街的燈火輝煌,方覺大街上早已是冷冷清清空無一人。可他又偏不肯坐馬車,而是獨自一人在這淒清的街道上漫步。
今夜天陰雲厚,月光朦朧不明,偶有陰風忽過,只吹得臨街的那些招牌旗幟呼拉拉作響。又有貓聲隱約傳來,頗有種鬼氣叢生之感。
林濤不怕鬼,他只是覺得這秋夜的風滾了寒氣,吹得他手腳冰涼。有些暗惱自己不知是著了什麼魔,竟心血來潮的選擇用走的回解憂樓。再歎自己這孱弱的身子骨,是熱也怕冷也怕,稍有不適就鬧騰。
也曾有過一了百了的念頭,那時實在是被折磨的太狠了,就剩了一口氣吊著。可他最終還是熬了過來,拖著一身殘敗的身子硬是撐到了那人來救自己。
後來就再沒動過求死的念頭。現在偶爾想起還會覺得不甘,倘若那時他要是真的撐不過了,那豈不是白白便宜了那人。自己為那人付出良多,還沒拿到回報就去了,他就是入了陰曹地府也要爬上來討債。
不過那時自己被那人緊緊地抱在懷裡,看那人一改平日良態哭得淅瀝嘩啦,嘴裡還不住的叫嚷著不要死,任誰勸說拉扯都不肯鬆手,他便覺得自己所受的罪也算是值得了。就算還有欠下的,大不了日後再一分一厘的慢慢討回好了。
想著又覺好笑,諒他是多麼輜銖必較計算清楚的人,遇上那人,這帳就從來都是糊塗的,一次也沒算清過,也沒法算清了。
不知不覺這路已走了大半段,身子活動活動也暖和了許多。想想這次的突發其想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他平日裡的確是太缺乏運動了。應該說,是有那人在身邊,他就是想運動下都要先請旨半天,實在是麻煩的很。
遠遠地,他瞥見解憂樓前似乎站著一個人,還貌似煩躁的來回踱著步子,一見到他來,就立刻站定不動了。
因為對方是站在陰影處,故而他看不清那人的容貌,可單憑那身形和投射過來的視線,心下已隱隱猜出了幾分。嘴邊立時就露出一抹笑容,發自心底、舒心而愜意的微笑,還帶著三分滿足七分得意。
果不其然,對方見他磨磨蹭蹭短短地一段距離愣是半天都走不到頭,便不耐煩的大踏步迎了過來,一把將他揉進懷裡,力道之大他甚至可以聽見自己骨骼的咯吱聲。
「這麼晚了你是去了哪,身子這麼涼也不知道多加件衣服。居然還一個人走回來,你以為現在是大白天麼?要是遇了事可怎麼辦。也不怕著涼,你以為你的身體是鐵打的麼,快點跟朕乖乖地進去待著。朕已經叫人熬好了補湯,你可得給朕一滴不剩的全喝完了。要是敢剩一滴,哼哼,朕就叫你幾天都下不了床,看你還乖不乖。」
林濤安分的任那人摟著,既不掙扎也不出言反駁,耳邊還被轟得直發懵,不過唇邊的笑意倒是變得更深了。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狐狩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8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狐狩
傳聞,與當今的聖上泉帝有染的太宰,
因皇上再納新妃而黯然請辭,歸隱鄉林。
聽得這傳聞的泉帝冷焰泉真是冤啊!
明明是愛人自己一句話都沒說就拋夫棄官離開的,
卻說得好像是他始亂終棄,負心背義!?
看著眼前這讓自己丟下一堆公事而追來的林濤,
他有滿肚子怨氣無處申訴,可也只能認了。
誰叫他的唯一摯愛,也只有眼前這一人呢……
早料到他會追來的。
林濤嘴角噙著那抹一如以往的淡笑,
看著眼前身分尊貴,卻次次為自己折腰的男人。
為了他,自己一身病殘;為了他,自己容忍他的后妃成群。
但忍,偶爾也得耍個小脾氣讓他知道,自己可是在看著呢。
更何況他這一次「辭官」,可不是在耍耍小脾氣而已喔……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夏末秋初,天清雲舒。
濟安城內遊人如織,南來北往的商客旅人都得了新修成的殤京運河之便,紛紛趕來一睹這花都之城每年十月初十的百花節。
不過此花非彼花,濟安城的百花節賽的是人,而且是各家寶樓繡坊的美人,男女不限,唯美者奪魁。
其實若說直白了,也無非是那些風流之地溫柔之鄉的美人們爭奪花魁罷了,妓院倌館全國遍地都是,哪裡都不缺乏這種招攬客人的噱頭。
只不過這濟安城的百花節,是一年比一年辦的轟轟烈烈,唯恐天下不知。不僅是成了濟安城內最為盛大的節日慶典,甚至還取得了官方認可,由府衙直接出人出力,在百花節...
夏末秋初,天清雲舒。
濟安城內遊人如織,南來北往的商客旅人都得了新修成的殤京運河之便,紛紛趕來一睹這花都之城每年十月初十的百花節。
不過此花非彼花,濟安城的百花節賽的是人,而且是各家寶樓繡坊的美人,男女不限,唯美者奪魁。
其實若說直白了,也無非是那些風流之地溫柔之鄉的美人們爭奪花魁罷了,妓院倌館全國遍地都是,哪裡都不缺乏這種招攬客人的噱頭。
只不過這濟安城的百花節,是一年比一年辦的轟轟烈烈,唯恐天下不知。不僅是成了濟安城內最為盛大的節日慶典,甚至還取得了官方認可,由府衙直接出人出力,在百花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佩蘭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3-12 ISBN/ISSN:9789862063286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