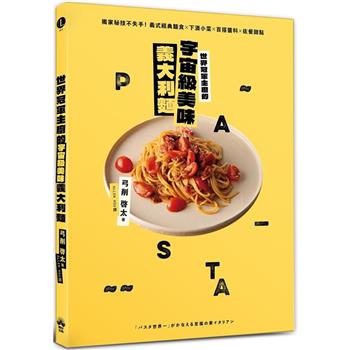第一章
日頭早已高高的升起,金色的陽光遍灑皇城,為泥砌磚疊的高牆打上了一層朦朧而桔黃的光暈,遙遙望去,說不出的巍峨壯麗。
皇帝的寢宮,朝陽殿深處,正是九曲宮室最為中心的部分。
內臣星羅棋布,后妃的屋室遍布在朝陽殿的周圍,擋住了大部分的光線,使得天底下最尊貴之人的居處,反而成了這宮裡頭最不受陽光眷戀的黑暗之地。
早起的僕役們躡手躡腳的在燈火通明的朝陽殿內忙碌著,盡量避免發出過大的聲音。
此刻,本該早朝回來,在御書房批閱奏章的年輕皇帝,仍舊在榻上酣睡。
金線繡製的錦被牢牢的壓在雪白的下巴下,唯恐春光外洩發生什麼差錯似的,連裹在被子裡頭的雙手都死死的攏住被面,看得剛下龍榻、套上戰靴的高大男人又好氣又好笑。
他昨晚,大約是要得太狠了一些。
戰事膠著,他有一年未曾回京,此次回來的目的,不是要兵員,也不是要軍餉,卻是為了請和。
可惜一看到高臺龍座上,皇帝漠然投來的責備目光,慾望就洶湧而上,一心只想把這個高高在上的男人死死的壓在身下,撫遍身體的每一處,然後狠狠的進入他。
高貴的皇帝因激情而略微沙啞的求饒聲,會是這場盛宴中最為動人的樂章。
也許想得太過投入,所以下了朝,直入朝陽殿的他在遍尋皇帝不著的情形之下,心頭的惱火可想而知。
他最終找到要找的人,是在御書房內。
皇帝正握著硃筆,認真的批閱著奏章,不時緊蹙的眉頭,昭示了政事的繁瑣。
他是個相當聰明的人,也懂得知人善任。
儘管如此,整個下午忙碌下來,案頭的奏摺依舊堆積如山。
揉了揉皺太久有些疼痛的眉心,皇帝猶豫著是不是要先休息一下,又覺得御書房的龍椅實在太過堅硬,小憩醒來,恐怕疲憊感只會有增無減。
可也不能回朝陽殿休憩,那個人下了朝,恐怕會直接去寢宮找他。
想到朝堂之上那傢伙赤裸裸的恨不得吞了他的目光,皇帝的心頭就充滿了憤怒。
每次他回朝,下詔免朝三日幾乎成了慣例。
但要做什麼,至少也要等到晚上。
朗朗乾坤,青天白日之下,成何體統?
皇帝暗自握了握拳,決定無視敢於私闖內宮,在整座朝陽殿翻找半天不得,最後等在御書房外的鎮國大將軍--寧不寂。
有什麼好找的?他不屑的撇了撇嘴。該來的早晚跑不掉,君無戲言,十年裡,朕什麼時候偷偷躲起來賴掉承諾過。
頂多就是待在御書房連續七天批閱奏章罷了……
當然後來勞累過度,感染了風寒,那也是國事繁複,不得已而為之,絕不是被某人興致突來,一連幾夜的激烈索求嚇得當了逃兵。
戶部送上來的最新統計顯示,與北夷連年爭戰之下,國內壯年男子人數下降極快,長此以往,主要勞動力持續減少,必定會致使耕地荒蕪,國力下降。
這樣看來,寧不寂一意孤行的回朝,請求朝廷休戰,也有他的道理。
只是就差一步,只要再多一點時日,就可以平定整個北境,徹底遏制住這個多年敵對的鄰國。
可惜國力禁受不起了。
也不宜讓寧不寂的實力消耗過多,寧不寂的戰力弱了,就壓制不住薛家,藩王們也容易蠢蠢欲動。
那一切又會回到十年前的情形。
他這十年所花費的心力,就完全白費了。
「該死的!」
皇帝不甘心的一掌擊在梨花木製的案臺上,沉重而實心的案臺微微震了震,留下一個清晰的掌印。
苦笑著看了看自己的掌心,還是太沉不住氣了,這凹痕清晰的案臺,想欺騙站在門邊瞧個正著的寧大將軍,恐怕是痴人說夢。
知道就知道了吧!
皇帝向來是既來之則安之的個性,那個人即使知道了他身負絕世武功,最多就是高興一下他的體力很好,可以在床上多折騰幾下。
有什麼大不了的!
他若無其事的繼續批閱奏章。
只是握著筆的手,卻帶了一絲絲不易為人察覺的顫抖之意,奏摺上的批注就不似以往般沉穩大氣,稍稍顯得龍飛鳳舞了些。
頭也不抬的批完手邊的摺子,四周始終是一片寂靜。
寧不寂什麼時候變成這麼沉得住氣的人了?
如果寧大將軍是這麼沉穩的人,恐怕十年前也不會率眾造反,還一路打到京城。
皇帝納悶的放下硃筆,暗自揣測。難道他早就知曉了朕身負武功之事?
這可不是好事。
十年來,他們雖然相互扶持,卻也相互防備。
作為皇帝,臥榻之側,有人公然酣睡,是想起來就咬牙切齒的事。
向來被稱為天下第一高手的寧大將軍,若是一早知道枕邊人是絕世高手,怎麼可能還睡得著?
不找他整夜切磋才怪。
……
當然現在也是整夜切磋,但是切磋的方式大大不同啊!
以寧不寂的武痴程度,此刻的默不作聲,必定事有蹊蹺。
皇帝幾乎是謹慎的、非常小心翼翼的轉過頭去,想要從大將軍的臉色中,窺探出一些細節。
「啪啦」一聲,握在手中的硃筆不知不覺間斷成了兩截。
只見御書房門外空無一人。
慢慢的吁出一口氣,皇帝為自己的大驚小怪著實慚愧了一把。
「陛下,請喝茶。」秀美的少年出現在御書房外,一盅清茶輕飄飄的飛到皇帝跟前。
皇帝同樣輕飄飄的接住,未蓋蓋子的茶杯中途沒有灑出一滴水。
「寧不寂回來了,收斂點。」他低聲的斥責。
少年翻了翻白眼,「日頭都偏西了,大將軍這會兒怎麼還會守在御書房前?」
冬日晝短夜長,皇帝遺憾的發現美好純潔的白日已經過去……
「陛下該去寢宮用膳了。」少年竊笑的加重了「寢宮」兩個字。
「彈劍!」皇帝冷冷的瞪著長身玉立的少年。
「是。」少年立正,眼觀鼻,鼻觀心。
到底不敢真的惹怒一國之君。
皇帝負手而去,在御花園繞了好大一圈,才回到寢宮。
「躲得了初一,也躲不過十五。」
跟在後頭餓得前胸貼後背的秀美少年彈劍,默默的在心頭念道。
像是聽到了他的腹誹,快走到寢宮前的皇帝,望著前方,遲疑的停下了腳步,感慨了一番:「今年御花園的桃花想必也會開得繁盛吧!」
算是為自己的拖拖拉拉找了一個完美的藉口。
隨即皇帝抬頭挺胸,迎向走出殿外的寧不寂。
「大將軍來得正好,連年戰事,國庫沒有多餘的錢可以犒勞,就和朕一同吃頓飯吧!」
陛下打招呼的方式還真是萬年不變啊!
旁邊的彈劍望望天,注意到皇帝臉上疲倦之色甚濃,非常體貼的行禮,「微臣告退。」
「等……」皇帝挽留的話還沒出口,少年早已一溜煙的消失在遠方。
跑了就算了。他毫不留戀的收回目光,打起精神,應付宿敵。
「好身法。」一旁的寧不寂倒是望著少年遠去的方向戀戀不捨,「陛下身邊有如此好手,微臣居然不知,實在慚愧。」
皇帝皮笑肉不笑,「輕功不過雕蟲小技耳,不比大將軍征戰沙場,戰功顯赫。」
邊說邊把習慣性攬上腰來的狼爪拍掉,「先去用膳吧!」
在寧不寂不悅的再度伸手過來時,皇帝堅決的握住對方強健的手臂,「吃飯重要,將軍征戰沙場,軍糧粗劣,難得回來,自當好好犒勞。」
說著,不自覺的使出三成內力,一把將對方拖向膳桌。
寧大將軍猝不及防之下,幾乎一個踉蹌。
穩了穩身形,暗自想道,下了朝就沒見人從御書房出來,為了躲他窩在御書房,屏退了所有人,批奏章批到現在,皇帝看來餓得不輕。
他難得體貼的詢問:「怎麼也不叫人送點心去御書房?」
送點心,能叫誰呢?
北有夷族,南有蠻子,薛家在西,朝廷中藩王派系林立。
皇帝無奈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批改奏摺時,他素來心無旁騖,難保端茶倒水伺候的不是誰家的探子。
「關於休兵的事……」皇帝心事重重的開口。
「你我有約,下了朝不談政事。」大將軍自在的喝酒吃菜,像所有認定「一將功成萬骨枯」為必然的將帥一般,絲毫不把日損三千的消耗戰放在眼裡。
可皇帝知道不是這樣,眼前這個男人比王朝所有的人都更加的愛惜士兵。
他是自己見過的,最珍惜人命的人,所以這趟回來,必定早就做好了妥善的安排。
御膳吃得出乎意料的長久,皇帝將之歸咎於自己一天未曾用膳,且寧大將軍需要好好籠絡的緣故。
寧不寂微笑的看著對面的人慢條斯理的細嚼緩嚥,彷彿嫌這樣還不足以拖延更多時間似的,皇帝在自己實在吃不下後,開始頻頻的夾菜給他。
一國之君親自夾菜,這是平常人想都不敢想的驚天大恩寵,卻之不恭。
況且數年來皇帝仰仗他頗多,別說是這些細末小節,大事上,皇帝都讓他不只三分了,所以寧不寂吃得相當的心安理得。
武將常年作戰,體力消耗也大,食量自然和常年處於深宮、四體不勤的帝王不同。
幾日前,還在行軍趕路,風餐露宿,和普通的士兵一起啃窩頭喝涼水。
此刻,至高無上的人侍候著進食,面對的是金箸夾來,玉碗盛放的珍饈。
際遇差別之大,實在是常人聞所未聞。
寧大將軍兵權在握,權勢滔天,連御廚都自認不敢得罪,清晨探聽到大將軍回朝,傍晚就在御膳的菜譜中添加了他喜愛的菜色。
許久沒有好好吃一頓的寧不寂食指大動,風捲殘雲一般,滿滿一桌御膳已經十去七八,他還意猶未盡。
皇帝夾菜夾到手軟……
語氣也由開始興高采烈的勸誘:「一定很久沒好好吃飯了,多吃點,這宮爆雞丁是御廚特製的,知道你愛吃,想必是特地趕製出來的。」
到無力的:「夠了沒有,要不要朕再喚內侍去叫御膳房追加幾個菜?」
心底把寧不寂罵得狗血淋頭。
堂堂皇帝,整整給他夾了近二個時辰的菜啊!
豬都沒有這麼能吃的!
皇帝一邊夾菜,一邊慶幸。好在彈劍溜了,不然再加上一個發育中的少年,這一桌菜絕對不夠他倆吃的。
到時候又會大打出手。
打起來時,彈劍要隱藏身手,寧不寂顧忌著對方年幼,雙方都不使出全力的情況下,按說是沒什麼大事。
可好歹這是在朝陽殿,兩個男人幾次三番在用膳時當著他的面,像市井之徒一般打鬧不休,實在是讓他覺得這個皇帝當得很沒尊嚴。
「也許當初精簡御膳的做法是錯誤的。」他舉著筷子,深深的反省著。
半晌,對面的寧不寂總算祭完了五臟廟,皇帝揉了揉發痠的手腕,起身離席,往浴池的方向走去。
未到中途,高大英挺的身影就大步的追上來,修長有力的手臂攬上身,熱氣曖昧的噴到耳邊,低語著:「一起?」
「你不是已經洗過了?」身旁清晰的傳來一陣皂角的清香味,皇帝用力的甩掉章魚觸手一般令他起寒意的手臂,悻悻道:「一天都等得了,還在乎多等這一刻?」
背後的高大男子贊同的點頭,「有道理,是不在乎多等這一時半會兒。」
言畢,對方如皇帝所願,很合作的鬆手,轉身往回走。
就他所知,這傢伙不是這麼好說話的人吧?
皇帝狐疑的回頭打量著寧不寂的背影。
偏偏確確實實,寧大將軍是頭也不回的往反方向而去。
只不過,他邊走邊嘀咕著:「等一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待會兒多做三刻補回來就好了。」
「……」被留下來的皇帝氣勢頓萎,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臉色開始變得很難看。
猶豫許久,眼看寧大將軍的背影將要消失在迴廊的拐角處,想到明天爬不起床的慘狀,皇帝不甘願的說道:「還是一起洗吧!」
遠處,寧不寂明顯在竊笑的聲音傳來:「微臣已經洗過了。」
這個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傢伙!
皇帝咬牙切齒,臉色鐵青,「朕命令你一同沐浴。」
自己的語氣聽起來真像個強迫民女的昏君……
皇帝憂鬱的想起下午批覆的大半都是「親賢臣,遠奸佞」的勸誡摺子,暗示他們不正常的君臣關係應當及早停止。
他也很想啊!
可這是他能說了算的嗎?
瞧瞧眼前的狀況,那些老古板若是路過,聽到他這聲旨意,多半也不會把媚主的角色套到寧不寂身上去,只會在心底把昏君的帽子扣在他的頭上。
皇帝越想越不甘心,惱怒的抬腳就走,壓根兒不想看見寧不寂小人得志的猖狂笑臉。
沒走幾步,溫熱的氣息欺上前來,寧大將軍攔腰抱起皇帝,微笑道:「臣遵旨。」
來不及臉紅,皇帝就被這聲遵旨再度勾起了惱意,平日裡處處跟他唱反調的人,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會抬出聖旨來調笑他。
「你可以不用遵旨,」他冷冷的開口,「你抗命的時候還少嗎?」
「陛下何出此言?微臣一向對國家忠心耿耿,陛下對此難道會有所不知?」寧不寂的回答一如往日的悠閒。
雖然是實話,可皇帝依舊聽得一陣氣悶。
就是因為太知道這個人有多忠於國家,心底才倍加鬱悶。
近在眼前的眸子,笑意盎然,眼神溫柔得似能滴出水來,沒人知道,若是有誰阻礙了他的信念,這個男人可以殘酷到何種地步。
是的,寧不寂有著深切的執念,他近乎頑固的敵視皇室,痛恨權貴。
在他看來,皇帝也好,高官也罷,都不過是國家的蠹蟲,窮苦百姓身上的血蛭,是一群他迫不及待想要滅掉卻無法得逞的碩鼠。
這個男人草莽出身,魯莽慣了,朝堂之上,根本不屑於跟一般人眼中高不可攀的達官貴族們虛與委蛇。
他直截了當地指出他們的虛偽和貪婪,尖銳的措辭和嘲笑的語氣讓許多顯貴下不來臺。
如果不是軍權在握,皇帝毫不懷疑,挨不到下朝,寧大將軍就會被群臣的唾沫星子淹死。
哪怕他是王朝第一高手,也逃不掉死無全屍的命運。
上朝時,寧不寂會和眾人一起隨著內侍的唱喏聲稽首下拜。
彼時,高昂的額頭低下來,高大的身形匍匐在地上,這是多麼卑微而服從的姿勢。
皇帝卻絲毫沒有因此而得意過。
從這個男人堅定直接的眼神中,他明瞭,這個男人拜的是這個國家,不是皇帝。
坐在龍座上的皇帝,只不過是名義上代表了國家而已。
就像寺廟裡的泥塑真身,明知道神佛高高在上,不在人間,眼前的只不過是一堆泥石雕漆的偶像,信徒們依舊會虔誠的下拜。這是因為,這些偶像代表了神佛的存在。
皇帝,在這個男人眼中,也不過是泥塑偶像般的存在罷了。
什麼真龍天子、奉天承運,這些,在寧不寂眼中,通通都是狗屎。
初時,多年的皇家教育使然,自恃尊貴,皇帝還會不服氣的與之辯論,「朕受命於天,身分不同,不可與常人同日而語。」
「有什麼不同?受命於天的你被人砍一刀不會流血?還是不吃不喝也餓不死?」
那時年少,兩人整日爭論,相當的不對盤,寧不寂的耐性也比現在要差得多,措辭毫不客氣,「真龍天子了不起嗎?還不是被我壓在身下。授命給你的天呢?怎麼沒在你哭喊求饒的時候跑來救你?」
彼時年幼,他尚有熱血,聽得此言,即是一巴掌甩過去,換來的,也不過是對方身體力行的證明,他跟常人沒有任何區別。
一樣耐不住慾望的煎熬,一樣累了會昏厥,一樣痛到極點了會哭。
及長,一日復一日在動盪的朝政和寧不寂不客氣的嘲笑中,他漸漸學會了隱藏真正的情緒。
相處久了,也會漸漸瞭解彼此的個性,所以不冷不熱了一陣後,兩人的關係逐漸升溫,這對君臣目前雖然沒有如同傳聞中那樣,好得蜜裡調油,至少也勉強稱得上相敬如賓。
不過也僅止於此了,少年時的陰影太過深刻,皇帝一直不敢真正把大將軍裝在心上。
儘管他在心底不得不承認,這些年來,若沒有寧不寂守著,他的皇位早就落在別人的手中,下場大約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浴池裡,熱氣氤氳蒸騰。
皇帝雙眼迷濛,沉浸在往事中,一直都顯得心不在焉。
寧不寂當然也不是好相與的角色,他自覺還不至於在意皇帝到無時無刻想知道對方想法的地步。
分別一年,他有更想做的事要做。
皇帝迷迷糊糊的在寧大將軍懷中讓他抱著洗了澡,壓在身下一陣熱切的親吻。
劇烈的運動使得不只是龍榻,彷若整個寢宮都在搖晃,門外的宮女們害羞的紛紛避開。
身為當事人之一的皇帝卻自始至終都在走神。
直到實在超過某個可以忍受的極限,他才在艱難的喘息中抗議:「你騙朕,哪只多做了三刻?」
寧不寂停了一下,笑聲震動胸膛,使得貼著他的皇帝一陣敏感的顫抖,「臣最初有說今夜要做到什麼時候嗎?」
皇帝受制於人,惱恨的無法言語,不得不被迫與禁慾了一年的大將軍在床上翻滾了整個晚上。
恍恍惚惚撐不住要睡去時,他才後知後覺的在心頭泛過一絲疑惑。這傢伙,該不會是在報復早朝時自己對他休戰提議的斷然拒絕吧?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臥榻之側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3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臥榻之側
他前輩子,一定欠這寧不寂很多錢。
因為十年前的承諾,他這本該萬人之上的皇帝,
卻夜夜得在寧不寂一人之下承歡。
是說君無戲言,就算這該死的傢伙總是索求無度,
他也不曾賴過他的約,只是……
「等一刻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待會兒多做三刻補回來就好了。」
唉……他就不能少做一點嗎?
身為皇帝,臥榻之側,有人公然酣睡,
是想起來就令人咬牙切齒的事。
雖然很想一劍砍了被稱為天下第一高手的寧大將軍,
但若是讓這武痴知道自己會武而且還不低的話,
不找他整夜切磋才怪……
當然現在也是整夜切磋,但是切磋的方式大大不同……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日頭早已高高的升起,金色的陽光遍灑皇城,為泥砌磚疊的高牆打上了一層朦朧而桔黃的光暈,遙遙望去,說不出的巍峨壯麗。
皇帝的寢宮,朝陽殿深處,正是九曲宮室最為中心的部分。
內臣星羅棋布,后妃的屋室遍布在朝陽殿的周圍,擋住了大部分的光線,使得天底下最尊貴之人的居處,反而成了這宮裡頭最不受陽光眷戀的黑暗之地。
早起的僕役們躡手躡腳的在燈火通明的朝陽殿內忙碌著,盡量避免發出過大的聲音。
此刻,本該早朝回來,在御書房批閱奏章的年輕皇帝,仍舊在榻上酣睡。
金線繡製的錦被牢牢的壓在雪白的下巴下,唯恐春光...
日頭早已高高的升起,金色的陽光遍灑皇城,為泥砌磚疊的高牆打上了一層朦朧而桔黃的光暈,遙遙望去,說不出的巍峨壯麗。
皇帝的寢宮,朝陽殿深處,正是九曲宮室最為中心的部分。
內臣星羅棋布,后妃的屋室遍布在朝陽殿的周圍,擋住了大部分的光線,使得天底下最尊貴之人的居處,反而成了這宮裡頭最不受陽光眷戀的黑暗之地。
早起的僕役們躡手躡腳的在燈火通明的朝陽殿內忙碌著,盡量避免發出過大的聲音。
此刻,本該早朝回來,在御書房批閱奏章的年輕皇帝,仍舊在榻上酣睡。
金線繡製的錦被牢牢的壓在雪白的下巴下,唯恐春光...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起霧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8-05 ISBN/ISSN:97898620646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