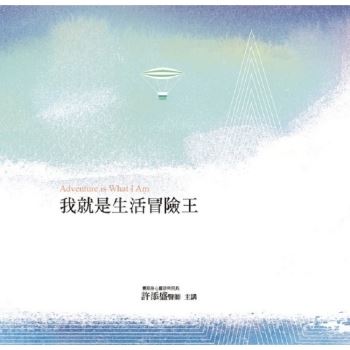序 上天安排你倒楣,你是躲不過的。
盛夏,山崖前集聚著幾個書院的孩子,平日吵吵嚷嚷,一刻不得閒的小傢伙們,如今正噤若寒蟬地看著他們的先生。這是個普通的書院先生。他正低著聲音啞著嗓子講道德問題,關於德行和人生的幸福是怎麼樣的相關。
總的來說,這先生是很厲害的。因為世上敢在最缺乏德行的平心崖下宣導道德的教書先生,恐怕還不多。雖然看這個先生的樣子,也是哆哆嗦嗦的,偏生還要繼續講,也是了不得。先生剛剛完成了引經據典的部分,然後用更低的聲音指著山上對小傢伙們說,萬一你們不好好學習,道德敗壞了,那就會被趕上山了。這上面可是有大堆禍害,人人得而誅之。
一個小孩子突然插嘴,「我聽說,上面的禍害長得可好看了。」
戒尺狠狠落在他的頭上,「說這麼大聲做什麼?被發現了怎麼辦!」
「你剛剛還說人人得而誅之。」小孩子摸著自己的頭,不解。
「那是人人得而誅之,不是你我得而誅之!」先生心驚膽顫地看看四周,沒有動靜,才稍微放心,繼續說,「而且越是好看的禍害,越是危險的禍害。」先生最後總結說,這個世界不是以貌取人的,重要的是道德的完善。
說這話時,這位先生身後那片亂草堆上,有一根狗尾草輕輕抖動了一下。那不是因為剛好有風吹過,或是什麼昆蟲在攀爬,而是它笑了。這根狗尾草不但會笑,還會思考,簡而言之,就是所謂的快要得道成精了。
注意,只是快要,而不是已經。
我就是這根狗尾草。 可惜我眼前這個古板的先生絕對不會知道。他只顧著匆匆結束對孩子們的實地教育,然後帶著他們飛速逃亡了,真真連平心崖下的一片樹葉都沒碰動。
「教書先生真是世界上最虛偽的職業,要教導小孩子們相信自己都不相信的事情。難道這個世界上的成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活得像個聖人嗎?」 我看著那先生帶著孩子們遠去,心裡懶洋洋地想著,順便在陽光下舒展著自己那麼一丁點黃不黃綠不綠的葉子。「要知道,這個世界絕對是以貌取人的。」
就拿成精說吧,當年上天和世間萬物早就說好,只要大家好好修行,誰都有成仙得道的一天。於是大家信心百倍,高喊著「我們要成仙我們要成仙」一齊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啊。幾千年過去了,這世上成仙成精的可多了去了。什麼蘭啊梅啊菊啊,只要跟花沾點邊的,哪年不是成打成打地仙啊妖啊來著?可是咱狗尾草自家,幾千年了,能走到靠近成精這一步的,還就只有我一個。而比狗尾草更難看的,像苔蘚,蕨菜啊什麼的就更沒戲了,你可有在傳說裡聽說過苔蘚仙人或是蕨菜仙人?明明說好了萬物皆有靈,到頭來卻是如此不公,唉。
我族幾百年前就看破了這一點,所以也不浪費時間去修行了,每天就在山裡曬曬太陽打打盹,春天發芽,冬天結根而眠,修行嗎,偶爾意思意思就算了,日子過得也挺滿意。
但是我不一樣,我要得道成精!你說我為什麼這麼奮鬥,哎,人家說環境造就人生,這句話絕對有道理。從平心崖西去三十里,有一條小河,兩岸綿延數里都是桃樹。原本我就生在那片桃林之中,不過那已經是非常非常早之前的事情。
那時是多麼美好啊。每過一些年,我都能親眼目睹桃花林中修煉成精的花妖誕生。我永遠記得那是多麼美麗的場面。花妖誕生的那刻,天上彷彿下了一場花雨,紛飛的花瓣中,飄渺的身影從桃樹中脫身而出,隨風而舞,桃林中有著淡淡的花香。花妖或淡雅,或清新,或溫柔,或嫵媚,帶著修行成功的狂喜在桃林中穿梭飛行。
從花而誕生的妖,不論最終化身為男為女,都是那麼美麗。這種時候,我總是盡量伸展自己的枝葉,幸運的時候,花妖的衣帶邊角會拂過我的身體,帶著清雅的香氣,那是多麼讓人陶醉。單是這樣,我就已經滿足了,這就是我的人生,沉迷在花朵的芬芳和面容的艷麗之中。
守著這片桃林看花妖,我就這麼小小的一個願望。
我想,世上只有我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花痴。
然而命運是如此強大,就算你的人生終極目標只是做個本分的花痴,也不一定能實現。
那是一個冬天的早晨,我盤根沉睡,所以錯過了樹精們借冷風傳遞的「風聲緊,撤乎」。待我醒來意識到情況不對的時候,四周凡是有點道行的都跑光了。
我盤起身子正待要跑,遠處卡的一聲,吸引了我的注意。
影影綽綽的,似乎有人踏雪而來。起先我以為是花妖回來看望同修的兄弟姐妹,因為這樣的好模樣,除了花妖還能是誰?但當他靠近的時候,我嗅到他身上野心的味道,只有人類才有這樣的味道。
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片桃林並不意味著我不諳世事。修行成功的花妖常常還會回來,給大家講這個世界上的事情。順便說一下,大約是做花的時候不能說話,基本上每個花妖都是話簍子,他們的話匣一開,沒十天半個月停不下來。所以我們都很瞭解這個世界,也第一時間明白了,他是個人類。
人類照理說是很可怕的。但是這個人身材挺拔,溫文儒雅,,頗有超凡出塵之勢。對除了花妖外很少看到美人的我有致命殺傷力,一種甜蜜在心頭蔓延開來,是初戀,絕對是初戀!
唯一讓我不安的是,他步履輕快,踏雪無痕,看來是有道行的。
說來也巧,走到我身側時候,他偏偏就停住腳步,我從下而上地仰望他,想來他應該不會留意腳下的這顆種子。
他只喃喃自語,「靈氣四溢,雖然是好地方,太冷了。」
然後他兩根手指輕輕一擦,熊熊火焰就在地上燃起來。不是吧?為什麼人類都喜歡玩火?要知道我可是一粒種子啊,偏偏天公不作美,風向變了,火焰直衝著我的方向而來。不會吧--
恐慌中的我沒注意到別的事情,突然陰影一片籠罩了下來,我便陷入黑暗之中。過了好一陣我才明白,有人對我伸出援手。
不,準確地說是伸出援腳。
來人一腳踩在我頭上,我趕忙把自己的身體撐到最大,死死卡在此人的鞋底下。
然後我聽到的是剛剛點火那人的聲音,「哼,好久不見。」
「道友,何苦在此妙處生火?豈不浪費了這片好景致?」這個聲音,應該是那個後來的人,溫柔極了,我很是喜歡。當然我更喜歡的是,他話音未落,火焰熄滅的哧的一聲。
太好了,我正想從他的鞋底落下來,卻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不知道這人的鞋底是用什麼東西做的,居然把我卡得動彈不得,慘了。
「道友,你叫我來此,究竟意欲何為?」還是這個把我卡在腳下的人的聲音。
「距此東三十里,有一處山崖,」
另一人打斷他,「平心崖。」
「開天闢地以來那裡就是,」
又打斷,「陰陽交匯之處。」
「那裡,」
又打斷,「日間陽氣極盛,夜晚陰氣四溢。」
此人爆,「姓奚的!你幹嘛老是接我的話!」
那人跺跺腳,似乎笑了,「大約,是因為我通人性?」
對方似乎背過氣去了。過了一會兒,也許緩過來了,又說,「我只想問,你為何這樣做?」
「為何?當然是因為我想這麼做。」把我卡在腳下的人似乎奇怪那人為何有此一問。
對方似乎又背過氣去了。
這個人似乎一點也不氣不急,「道友啊。我知你怨我得了這山崖去開山立派。但我都是為你好啊,前些日子我掐指一算,你命中有陰陽二相,若是再留在這陰陽相沖的地方,你的下場定是人妖了。」
哎,你說話就好,不要再跺腳了。
「我倆平輩論交,你何苦欺人太甚。」
「道友,此話怎講?」他的聲音甚是委屈,但說的話就比較狠了,「就算是你的,我搶過來了,也就是我的了。」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說著說著,決定要到那個什麼平心崖上去解決這件事,於是兩人一齊離開。
照理說我應該很高興的,如果我不是還被卡在這隻腳下的話。
不要啊!我不要離開生我(身)養我(眼)的桃林啊!
我在鞋底拚命折騰,不知道過了多久,鞋底什麼地方突然一鬆,我啪地掉在地上。等我從暈頭轉向中恢復過來,已經在一片山崖之下。
這是哪裡啊?
冬天黃不拉幾的草地,稀疏的槐樹,河面薄薄一層冰和冬日刺骨的冷風。花呢?那些美麗的花呢?絕艷的花妖呢?我生活的目的呢?都沒有了?
痛定思痛,當晚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要修煉成精,回到那片桃林。
時間究竟過了多久,我並不十分清楚。我只知道這片河畔林地,再也沒有什麼來過。我非常寂寞,好幾次都想算了,就這麼著了吧。但是我頭腦裡那根叫做花痴的神經卻每每在這個時候跳出來,不!要死,我也要死在花叢中,絕不死在這塊雜草堆上!
或許是我的決心感動了上天,也或許是其他的什麼原因,總之,到了這個秋日的夜晚,我離成妖只有一丁點了!我的妖化,只剩下最後一次吸取月光的精華!一旦幻化人形,就可以離開此地,回到那片桃花林去。
第二天早晨,我精神百倍,迎接自己成妖的第一天。
我給自己鼓勁,這是改變我命運的一天。
事實證明,這確實是改變命運的一天。
順便一說,我估計任何人遇到他,都得多少改變一下命運。
第一章 那一場風花雪月的事,代價就是煎熬。
月亮初升的時候,河畔突然傳來人聲,我異常警惕,趕忙把自己縮回到雜草叢。因為人實在是給我留下太多的心理陰影。白色的人影由遠及近,是一男一女。美人,絕對是美人!實在忍不住,我探出草叢,偷看這兩人。
走在前面的女子美極了,跟花妖相比半點不遜色,美目流盼,暗香浮動。那話是怎麼說的?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這些話簡直就是給這女子的旁白。
一種又甜蜜又羞澀的感覺向我襲來,這才是初戀!
她剛剛走到這片小草地,似乎是累了,停下腳步,「掌門師兄,這些夠了吧?」
她一揚手,羊脂白玉似的手腕,纖細柔嫩的手指,太迷人了。我的葉片在風中搖擺,這是我高興的表示。她手上拎著個小竹籃,裡面全是些了不得的東西,像是七葉一支花、叢紅景、神農籐、紅白芍、九死還陽草,都是極其罕見的同族。
「我們可以回去了吧?」那女子有點發嗔了。
這時,我才看到後面站著的那個來人。就算在花妖中,他這容貌也是罕見的俊美,然而他也不是花妖。他身上有一點絕艷的花妖永遠難以企及,那就是他眼裡閃耀著的光芒。
慾望或野心是人類特有的感情,此種情感燃燒時奪目的光芒,任何妖物也無法做到。我的眼神無法從他身上移開,看到他的感覺不僅甜蜜羞澀,還叫人心裡發抖。初戀,這次才真是我的初戀!
不過我也暗自奇怪,在他眼裡看到的耀眼光芒,既不屬於慾望也不是野心,而是別的什麼東西造成的。當時我並不知道。很久以後我才懂得,他雖然是人類,但不算是典型。他眼裡閃耀的光芒遠比野心或慾望更麻煩,是通常人們所說變態的光芒。
那男子微微搖頭,示意不行。
「反正對於中妖毒者來說,就算煉再多靈丹妙藥又有什麼用?我不明白你想找什麼?」女子似有些不滿。
男子沒有答話,只是四顧,我覺得他的視線投過來,他微微一笑,這是驚世絕艷的笑容,我給活生生看呆了。今天到底是什麼好日子?我在這冷清的山崖下苦待這麼多年,就是為了這一刻嗎?
老天爺,我感謝?,讓我在成妖前,還能有這麼美麗的際遇!
剛巧一陣風過,捲起零落在地上的點點花瓣,碎紅一片,而月光似雪,正好散落在這二人身上,花瓣隨風而舞,恰恰觸碰兩人的衣角髮梢。
我暗自讚歎,風花雪月,與這兩位美人真是絕配。忍不住,又抬高了一點頭,痴痴看著。
那男子的目光掃了過來,然後腳步輕快停在我面前,一直保持著那優雅的笑容,伸出他的手,連動作都這麼美妙,我貪婪地看著他慢慢放大的容顏。
隨著輕微啪的一聲,我突然感覺自己懸空了。怎麼回事?我還沒反應過來,只感覺自己被舉起來了。女子一撇嘴,「就找這麼根狗尾草。」
我我我,我居然被拔了?
那拽著我的手晃動了一下,把泥土從我的鬚根上紛紛抖落,我的鬚根在風中飄動。
太羞恥了,我努力捲起鬚根,希望在附近沒被人看見。對植物來說,根鬚被看到,這可是跟人類裸奔一個等級的行為。
順便一提,我說人類啊,你們也要尊重我們植物的尊嚴啊。
你說為什麼被挖走移植的樹木不容易活下去?那不是什麼生理的問題,完全是我們心理問題。你們把我們拔得光溜溜的,用繩子捆好,然後一溜煙放在車上招搖過市,被那些好好待在土裡的兄弟姐妹們嗤笑。我們的面子能掛得住?就算再栽到土裡,那也是身心俱傷,哪能再好好做樹,天天向上?如果換了你們人類被扒光捆成龜甲縛狀,一打一打拉著從別人面前過,然後又套上衣服要你們好好做人,你們也做不到,是吧?
人所不欲,勿施於妖嘛。
如今我只能靠捲起的丁點泥渣護住最後的尊嚴,就像,就像人類保住底褲一樣。我已經羞得葉片都要翻黃了。偏偏那女子也走上前來,手指一彈我捲起的鬚根,把最後一點護住隱私的泥渣都給我彈掉。
我正左挪右騰想著能不能勾住點渣的時候,他們又說話了。
「我看平心崖上下,也就這根合適。」男子微笑著,「它看似就快成妖,如果此時煉化,它雖失去妖體,元神仍舊可以不滅,會本能吸食附體的東西,不管是妖力還是妖毒。」
女子哼了一聲,「讓我煉化它是可以,條件就是我們上次談好的。」
「當然。」男子微微頷首,同時我被他塞進了那小竹籃裡。
他們、他們要煉化我?
老天爺,我恨?,?就下這樣的狠手?
可憐我只差幾個時辰了啊!
我一路羞且憤及悲地被帶回了一個青石砌牆的房間,那女子小心翼翼把我從竹籃裡挑出來,輕輕洗淨。當一雙柔荑輕撫過葉面的時候,我還是幸福得簡直忘了待會兒等著我的是什麼。
我幸福的幻覺在女子對我說話的時候徹底被打破。
她嬌笑著把我捧在手上,「嗯,確實很接近成妖了。不過也沒關係,只是煉化而已,不痛不痛哦。」
如果可以落淚我一定哭得十分滂沱,特別是看見那巨大煉化爐的時候。
對妳來說當然是煉化,但是對我來說這就是火化啊!
煉化的過程我已經記不清楚,沒多大痛苦,只是麻痺,很快就失去了自我意識。彷彿我一直在漂浮,似乎知道這個世界的所有,存在於這個世界的每個角落;又好像我哪裡也不存在,什麼也不知道。我就這樣模模糊糊,迷迷濛濛地存在於一片混沌裡。
然後某一刻,我似乎被從那片混沌裡拉了出來。再次啟動的記憶是在那片滾燙和冰冷交錯的水裡,有什麼東西源源不斷溶進來。不知何時開始,我突然再次擁有了自我意識,開始感到自己和周遭的東西好像有所不同;接著擁有的是感覺,極度的飢餓感促使我拚命地向所依附的東西吸食。古怪的是,越是吸食,就越是飢餓;但越是飢餓,意識就越發清晰起來。
隱約覺得,自己似乎在吸食著了不得的東西。
然後復生的是觸覺,我可以感覺到自己依附在一個堅韌的軀體上,雖然會一片片慢慢從那上面脫落,然而意識卻沒有消失,反而開始凝聚。我探索著那個軀體的形狀,飢渴地吸食,然後某一夜,我終於再次獲得了最為寶貴的視覺,突然睜開的雙眼,看到面前的一切。
最先看到的是我一直依附的那個東西,當時我只是驚訝,因為人的軀體上是那分不清五官的青紫臉,以及一雙無比明亮的眼睛,看著我,不動聲色。
然後我的視線慢慢移動,這個洞窟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洞口狹窄,視物全靠頂上數顆熠熠明珠。因為正中這個沸騰的水池,洞窟內熱氣騰騰,水霧環繞。在四面,霧氣凝結成水珠滴下,水珠匯作汩汩水流四處流竄。潮濕和悶熱,是這洞窟裡的最大特色。
不過更讓人吃驚的是,居然有人可以在這麼惡劣的環境裡睡得坦然自若。靠近洞口的地方橫著一個鼾聲大作的傢伙。他睡得死死,光溜溜的身上只搭了條毛巾。但他身體裡,同樣蘊藏巨大的法力。奇怪的是,他身上的法力似乎和這個人身上的法力同源而出,有著十分相似的味道。
因為是吸食典墨的妖毒成長,他理所當然地認為我應該服從他,他太兇惡了,我不敢不從。何況自己也還是清楚,畢竟能再次成形,完全是因為此人的關係,而且如果他願意,立刻就能讓我恢復成麵團一個,所以雖然心裡踹他一萬腳, 我可不敢違逆他。
在他的授意下,我繼續偽裝成麵團一塊。這個人原來喚作典墨,那個光溜溜倒在地上睡的,是他的師父李梳。聽他們對話的口氣,李梳好像地位比較高。跟我面對面時那個惡劣的典墨,在他面前低聲下氣,簡直變了一個人似的。然而我覺得怪怪的,明明典墨的法力要強得多啊,為什麼他要對李梳惟命是從呢?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越來越能輕易化為人形,行動也越來越流暢。我滿懷著對新生活的嚮往,白天努力做一塊老老實實的麵團,晚上勤勤奮奮地收集從典墨身上掉下來,飄散在池子裡的麵屑,希望能早一日到外面去。
我心裡時時記掛著距離平心崖不太遠的那片桃林,那是我活著的意義。
典墨讓我吸食妖毒,不過他向後仰躺在溫泉壁上示意我來的時候,我總是暗自嘆氣。
如果是花妖,或是那個跟人吵架結果完敗的道人,或是把我從地裡拔出來的男子,又或是煉化我的美人,隨便哪個也好,若是他們向後一仰示意我上,我肯定流著鼻血歡天喜地撲上去了。
可是面前這個比黑炭還黑、還醜,連五官都看不見,渾身走動詭異金色紋路的鍋底男,我實在沒有向他撲過去的意願。雖然妖毒是很美味的,可附在他身上吸食,總是有點敗胃口。
就算燕窩一碗,放在痰盂裡給你,你總是吃不下去吧。
很久以後,有個人疑惑我當時怎麼那麼客氣,不狠狠吸個夠本,那時候我說了上面的話。
他白了我一眼,說,你懂什麼,吃燕窩就是吃燕子的口水,放痰盂裡正好。
我嘔--
由此可見當時我有多不想伏在他身體上吸食妖毒!不過當時我有多不願,後來我就有多後悔!我怎麼眼光那麼差啊!
後來又想,不,不能怪我眼光不好,要能從那黑不溜丟的東西上看出後來他妖毒褪盡的長相,這需要的不是長遠的眼光,而是突變的眼光!我哪裡知道典墨能出落得那麼驚艷?我要早知道他後來長那個模樣我死活也要貼在他身上不放啊!所以當時的我只能在典墨看不到的地方,捏著鼻子閉著眼睛吸食。
就當他是奶牛,還是頭比較醜的。
當典墨發現我可以粗淺化形之後,他似乎非常高興,而且更加大度地讓我吸取妖毒,甚至法力。
我開始覺得古怪,自己的身體似乎在改變。吸取人體的妖毒是妖物的本能,所有瀕死的妖物都能做到,因為對人體來說,妖毒是外來異物,零散於氣血之外,是身外之物,就像衣服一樣。
但是法力卻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修道之人身體裡所蘊之法力,就如骨中髓肉裡筋,深藏體內,隨著功力越發深厚,甚至融入魂魄,是成仙之基礎。
吸取妖毒和吸取法力,這二者差別巨大。你想啊,要拔一個人的衣服容易,要抽一個人的骨髓那就難了。
當然,這也要看情況的。在清水文中拔衣服,基本比在SM文中抽骨髓還要難。
所以,我居然可以輕鬆吸取他人法力,有古怪。莫不是只能吸他的?
典墨好像能讀懂我的心似的,讓我在李梳身上試試。趁著李梳睡得死仰八叉光溜溜的,我打算像撲典墨一樣撲上去,結果被一腳踹翻在地。
「撲什麼,皮膚接觸不就可以了?」他狠狠瞪我,臉如漆黑鍋底,眼如鍋底上兩個大洞,嚇死個人,不,嚇死個妖。
我雙手伸向李梳法力最集中的胸口,被踹。
我雙手伸向李梳氣樞要道的脖頸處,被踹。
我雙手伸向李梳血脈縱橫的大腿處,被踹。
頭,被踹。
臉,被踹。
腳,被踹。
背,被踹。
膝蓋,被踹。
肚子,被踹。
我可憐巴巴地盯著典墨,你看,要不要乾脆給我懸根絲線?
典墨可能也覺得讓我懸絲診脈一般地吸取法力,這難度委實高了點。最終,我和熟睡的李梳小心翼翼手指尖相對(姿勢詳見米開朗基羅名畫《創造亞當》),稍微用力,法力緩緩而入,證明對方無心或無力反抗的時候,我確實可以吸取法力。
但是典墨也忒小氣。我才吸一點點就被趕回水池裡。難道典墨是如此捨己為人?可以貢獻自己的法力卻不讓我碰李梳的法力?
搖搖頭。不是,絕對不是。但原因究竟為何我就不清楚了。
很快,我已經可以說話了。一能開口,我就大喜過望。要知道對於妖物來說,開口說話基本上就是修煉成功的標誌。人類天生能言,自然不明白其中的意義。而對於動物類的妖物,生為動物起碼能嚎幾聲吧,但是植物類的妖物,成妖前哪有這機會,那可憋得緊啊。
「啊啊啊啊,我能說話了,我真的能說話了。老天爺啊,我居然能說話!咳,哆來咪發嗦啦嘻哆,不錯。我覺得這嗓子還不錯還不錯。聽說世界上有唱戲的那行,我估計我也能做的。你覺得我的嗓子怎麼樣?」這是值得紀念的第一句話。回應我的也很值得紀念,是他的腳丫子和更黑了幾分的臉。
典墨,好像相當後悔讓我進化到可以說話的地步。
又過了一天,夜幕再次降臨之前,李梳就打著呵欠睡了。隨著他的呼吸聲變得悠長平穩,典墨的眼神也經歷著從乖巧到乖戾的變化。我剛從水池邊脫身而起,就看見典墨的嘴唇輕動,對躺在遠處的李梳下了言咒,「睡吧,啟明星升起前,不要醒過來。」
李梳身子微微一震,睡得更熟了。其實我極端懷疑他施展這個法術的必要性。就我觀察,李梳此人一旦睡著,別說啟明星升起,就算太陽升起來,他也還是醒不過來。
我正待目送他離開,典墨卻對我做了個跟上的手勢。呃,雖然你讓我離開山洞很好,不過,那洞口的道符怎麼辦?我苦惱地看著那片威脅十足的道符網。
「你要自己出去,還是我一腳踢你出去?」典墨不耐煩地看著我。
「我就沒有別的選擇了?」
典墨漆黑如鍋底的臉轉過來對著我,「有,你可以選左腳或是右腳。」
「可是、可是小妖我妖力微弱,這道符網太強,恐怕還沒通過我就已經掛了。」我可憐兮兮地看著他,「我死不足惜,但是還沒能幫上你一分一毫就死,實在死不心甘啊!」
當然事實的真相是,桃花林的花妖們,人間的美人們,我連你們的手都沒有摸到過,我死不甘心啊!
他嘖嘖兩聲,「時代變了嗎?連妖物都這麼諂媚了。不會死的,跟上來。」
典墨領著我穿越道符網,他的方式很古怪,每走一步,都雙掌互擊,而每一次擊掌,我都可以看見奇特的空間在他面前展開,無聲無息地扭曲了面前張張道符佈下的法陣。典墨一步一步,自由自在地穿行。趁著空間還未回復,我連忙三步並作兩步擠進去。空間的扭曲能把我拉長壓彎,拗過來扭過去,幸好我現在的身體原形是麵團,柔韌性極佳,倒不至於被弄壞。奇怪的是,典墨似乎完全不受空間扭曲的影響,在我前面走得不慌不忙。
跟了一陣,我忍不住問,「我們現在是在哪兒啊?什麼都看不見,完全沒有東西,會不會迷路會不會走不出去啊?」
典墨頭也不回的說,「是在劃分三界的三方神界的縫隙。」
「原來如此,所以從這裡可以自由穿越空間。」原來這就是鼎鼎大名的三方神界?我權當作是在觀光,東張西望,不過憑良心說,這裡沒什麼好看的。腳下漆黑一片,陰冷的風四處亂竄,完全是個紊亂的空間夾縫,「不過你怎麼找得到這個地方?」
「我曾經花了很長時間尋找三方神界薄弱之處,當時無意中發現這個裂縫。」
「你找三方神界薄弱之處做什麼?你想去仙界還是妖魔道啊?你真有追求啊,我雖然是剛生成的小妖,對這些天地構建還是很有興趣的,你是怎麼無意中發現這個裂縫的啊?」我興致勃勃地問。
典墨斜了我一眼,「左腳還是右腳?」
我不敢再多嘴,眼前景色驟然一變,我們出來了!
四周的景物看著眼熟,這可不是洞口嗎? 回頭一看,身後正是那道符構架的法網,如此薄薄一層,卻讓我跟著典墨足足走了半個時辰才穿越。
我很興奮。這是第一次擁有身體站在大地上,感覺非常新奇,草地的香味,微弱的星光,風穿越樹林的沙沙聲,夜鳥間或啼叫。原來擁有可以感知的身體是這麼美好的事情!
我正要讚美世界激揚文字,耳邊傳來一句冷冰冰的話,「多嘴一句,打成麵粉。」
哆嗦,藝術的衝動就這樣被強權給壓制了。
「不過,」跟著他走了一小截,好奇心又起了,實在耐不住還是冒著被打成麵粉的危險,我問道,「如果剛剛真被道符法網逮到,會怎麼樣啊?」
典墨突然停下腳步,柔聲說,「放心,你有機會體驗的。」他詭異地一笑,漆黑的皮膚襯著雪白的牙齒,再加上暗月陰冷的反光,露出叫人顫慄的笑容。
你們要相信我,能露出這種表情,就算此人自願打掃公共地帶,攙老太太過街,扶跌倒的小弟弟,每天垃圾分類包裝,也決不可能是個好人。
第二章 揭開假象才能看到隱藏的真相,這是真理。
但別信得太早。
因為假象很可能跟地獄一樣,也有十八層。
不知怎麼三拐兩拐,我們就進了一間小院落。門虛掩著,豆大的燈火在紙窗上透出人影,顯然屋裡人還未眠。
典墨沒有停頓走上前去,但他僅是推開門卻不進入。一個大叔級別的人坐在桌前,抬頭看見典墨進入,也沒有露出特別吃驚的樣子。
雖然他是個大叔,不過看上去很有性格,而且沉穩的氣氛讓我喜歡。我的心跳慢慢加快,又是初戀吧?
「典墨,你突破結界深夜至此,有何事?」
典墨站在門口微揖,「潘師伯見弟子來此,自是已經對前些日的事情瞭若指掌。」
那人哼了一聲,目光掃過我,又回到典墨身上,「怎麼,這次我是你的目標了?那你還不進來?」
「師伯說笑了。師伯以房門為限設下靈獸之陣,擅入者立死,我哪能進來?」典墨似乎笑了一下,露出森白牙齒,「師伯過慮,可否解開殺陣,讓我入內一談。」
「也罷,你進入吧。」也不見他如何動作,房內肅殺之氣大消,典墨昂首進入,我猶豫再三,還是跟入了。
「那麼,師侄來此究竟為何?」他挑亮了燈火,緩緩說道。
「也沒什麼,想和師伯做個交易而已。」典墨笑道,「我想一個人死早點。」
「誰?」
「我會來找師伯商量的,還能有誰?」
他注視著桌上跳躍的火焰,過了一會兒,說道,「想殺掌門於鏡?為什麼?」
「師伯可否聽師侄講講他失蹤的那十年,究竟身在何處?」
「願聞其詳。」
「十年前天地異變,妖魔道開。他獨身進入妖魔道深處,得遇一隻凶獸,你們是這麼稱呼的吧?」他臉色已變。典墨似乎很滿意地笑笑,「他與凶獸訂立契約,將牠解放到人間,而凶獸承諾在他有生之年,服從他的命令。凶獸的契約,一旦訂立絕無背棄的可能,不過只要他一死,那麼契約自動失效。」典墨平靜地說,「凶獸地離有一項異能,既能將對方的法力吸走,又能賦予對方法力。他最需要的,就是這項能力。所以他私下邀回老掌門,在他授意之下,我吸取老掌門的功力賦予李梳法力,嫁禍李梳,轉移視線。接下來呢,他已經藉口為老掌門療傷,閉而不出,我則趁此機會吸取你和其餘大弟子的功力,平心崖必然大亂,到時候他出關,重新整頓門戶,而我也要將獲得的法力轉交於他。」
「但我想要自由地體會這個闊別數千年的世界,才不想成為他的法器。」典墨繼續說道,「我想要盡可能縮短與他的契約。我的打算也非常簡單,讓你比他更強就可以了,現在是最容易擊敗他的時候。於鏡天生異能,驅鬼而戰,不過他的血鬼已經在十年前被我吞噬殆盡,如今即便有其他,也不足為懼。如今你只要能夠在法力上強過他就行。而你和他的差距,大約也就是三四百年的功力。」
「怎麼,你要傳功力於我?」
「當然不可能,他和我契約在前,不得到他的同意,我不能傳功力給任何人。不過,可說是機緣巧合吧,」典墨指指我,「他是吸取我身上妖毒而妖化的麵人,居然也分得了我吸取功力的能力。他現在尚不知此物的存在,而李梳身上的正是近千年的功力--」
「我不是物,我是妖。」我小聲地抗議,被無視。
「在他得知之前,我還可以自由差遣他。所以,機會只有現在,你考慮地如何了?」典墨總結道。
他反問了一句,「你將此事告知於我,我已知情,將來他必不會放過我,我還有選擇嗎?」
典墨笑了起來,「你若一定要這樣想,藉此減輕自己犯上作亂的罪名,我是無所謂啊。」
呃,他們到底在說什麼?
我只好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窗外的夜空裡。
偌大的天空,星星寥寥。
典墨叫我走的時候,我就走。不過他沒有立刻回去,讓我在路口等他一下,自己又去了別的什麼地方,不太清楚。最後典墨回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濛濛亮,他的表情相當愉快,不知發生了什麼。但是我覺得他身體內的法力,好像少了很多。
這樣還能這麼愉快,搞不懂。
接下來的幾天,我能從他身上吸取的妖毒已經很少,他基本上已經脫離妖毒之苦,只要再三五天,經過最後一次妖毒發散,他就痊癒了。現在我也可以很輕鬆地形成麵人形,對平心崖的門人已經沒有什麼怨恨了。
我這個小妖一向很想得開,雖然這樣子妖化和我的原計畫有一定出入,不過好歹還是循著我計畫的大方向在前進。等沒我的事的時候,我就可以回到桃花林去見美人了。
總的來說,我幫了一個為妖毒所苦的人,自己也功德圓滿,這就叫雙贏吧。
只是有一點不好,不知道是不是這次的妖化全靠吸收典墨身上妖毒和法力的原因,我跟典墨之間,彷彿出現了類似共生的關係。不,不是共生這麼公平的關係,而是附生之類的關係。
比如說吧,如果典墨集中精力的話,可以把他的思維傳遞到我的頭腦裡面,但是我卻不能將我的思維傳遞過去。
不公平,是吧? 這只方便了他對我發號施令。如果我也可以像他一樣傳音入腦的話,我絕對要逃得遠遠的,然後每天在典墨頭腦裡念一千遍《君子守則》、《道德操守》之類的,對他精神轟炸。
當然我只是想想而已,日子還是貌似和平地前進。雖然我希望,但我也知道這和平的日子過不了幾天。今天一入夜,準確地說是李梳一開始打呼,典墨的情緒就不對勁了。
別問我為什麼知道,總之就是知道。誰叫我是和他最有肌膚之親的妖了呢?他體內法力動盪,我幾乎可以感覺到他心緒不穩。我想大約是妖毒即將散盡,令他有些焦急。
當時我正趴在水底休息,典墨突然踢踢我,問,「你的法術怎麼樣了?」
「呃,還可以啦。不過你也知道我才成妖不久,高深的法術是完全不會的,不太高深的呢,我是說那些中級的我也不會,我能做的就是那些小小的把戲而已,完全不登大雅之堂,你不會看得上眼的,不過--」我正要大加陳述,典墨似乎極不耐煩一腳踩我頭上,「你試試用法術驚醒李梳。」
我心裡嘀咕為什麼,典墨不是一直讓我藏起來不被李梳發現嗎?不過他的話,我不敢不從。
那個午夜,我初次嘗試妖術。要驚醒李梳不難,他雖然能睡,但是人類對溫度很敏感。我念動法咒,召喚來黑霧,石洞裡立刻一片昏沉。灰沉沉的陰氣,伴著一絲絲的冷風貫穿著這個石洞。我需要的就是陰氣四溢,寒氣逼人的感覺,這在平心崖這種地方很容易做到,即便是溫泉洞裡也一樣。
李梳沒動靜。
我回頭看看典墨,他做了一個去查看的姿勢。得到許可,我拖著滑溜溜的身子浮在岸邊,探頭看看李梳,黑霧籠罩下我看不清楚。估計他應該是睡得太死了。我慢吞吞從池邊爬起來,搖搖晃晃站著,靠近一點仔細看看。原來他的法力於體內形成迴圈,排斥著外來的黑霧,所以他不會立刻受到黑霧的侵襲而醒。
那要不要加強法術?
我正打算回轉溫泉徵求典墨的意見,突然洞中陰風咋起,刮得我這個妖都哆嗦一下。
我還沒來得及反應,「典墨!」一個剛睡醒還不夠清醒的聲音響起。
是李李李李梳!他醒了!
李梳試探地喊了一聲,沒反應,他似乎向這邊望過來,不過黑霧繚繞,他應該看得不是很真切。然後李梳呆住了,他看著我;我也呆了,我看著他。
典墨只交代我用法術喚醒他,現在喚醒了怎麼辦?我回頭看了一眼,典墨已經不在剛才那個地方。那,要我怎麼辦?我不自在地移動著步子,想著要不要跟李梳打個招呼?雖然他是不認識我,但是我卻認識他有些日子了。誰知道我剛剛對他走過去兩三步,才清清嗓子,李梳便被蛇咬了一般慘叫起來!然後他跳起來就跑過來。你要知道這山洞不大,他這一跑,自然是圍著池子跑,池子是圓的,他一繞,就會跑到我身後,變成他追我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還沒來得及想雙腳自己就動起來,盡量和身後的聲音拉開距離。我和李梳一前一後,環著水池繞圈子。可是李梳在我身後越追越快,越追越快,迫不得已我也越跑越快,越跑越快,到最後乾脆滑行了。
眼前一花,突然失去了李梳的身影。
但是我很難停下腳步,這洞裡經年累月被蒸汽和水流弄得光溜溜的石頭和我那滑不留手的身體簡直絕配,我完全停不下來,憑著剛才的一股衝勁外加慣性滿山洞轉悠,發出哧溜哧溜的聲音,停也停不下來,那叫一個鬱悶。
我唯一能做的是盡量把握好方向,不去碰那道符滿布的洞口,我剛剛要扭身從洞口上方滑過的時候,不知道哪裡飛來粒石子,我一斜,失去平衡直撲到道符網上面。
你知道這是什麼感覺嗎?
讓一個妖物撲到道符網上,其效果如同濺了一滴水在滾燙的油鍋裡。我聽到嗤嗤的聲響,燙得渾身火花,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典墨應該做了點什麼,下一刻,我突然被高高拋出,重重摔在地上。
再看的時候,我已經在山洞外,一回頭,看到道符網破了。
典墨你這個騙子!說什麼用法術喚醒李梳,其實你原本就是這麼打算的吧!雖然這麵的柔軟度和彈性很好,可是這樣摔一下還是頭昏腦花呀!
典墨的聲音從腦海裡傳來,「躲起來。」
什麼話啊,我又不是你的奴隸,你說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啊?好歹我也是狗尾成妖第一草啊!我想著,哼哧哼哧地一頭鑽進草叢,啪的在石壁上貼得像張麵餅。
「跟著他。」傳過來的思緒有幾分混亂,我可以感覺到典墨似乎正處於散毒的關鍵時刻,暫時不能動彈。
跟就跟嘛,我遠遠尾隨著李梳到了一處大殿,月色很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李梳先是跌跌撞撞跑到門口,猶豫了下,似乎轉身要走,這個時候,一聲慘呼響起。他又轉過身去,跑到門口,他似乎啟動了什麼法術,我看見他在門口走來走去。
反正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我就躺下來休息休息,再怎麼說,連走路都還沒完全習慣的我,卻一來就挑戰最高等級的跑法,裸奔,能不累?
當我開始啪啦啪啦打蚊子的時候,我聽到了門開的聲音。如果李梳將門關上,我怕是進不去的。可巧李梳脫下鞋,把門給卡住。等李梳的身影消失在門裡,我慢慢蹓躂過去,扒在門縫朝裡面看看。黑漆漆的,看不見什麼。
不太想進去,真的。裡面一片寒意,似乎是有什麼不祥的法術在施行。
我剛要縮回身子,有人從後面一腳猛踹,我直接撞開雕花大門撲到地板上。不用想了,我一抬頭,面前那個黑黑的人影,不是典墨是誰?
身後的門無聲無息關閉,有什麼東西硌著我的腰,伸手一抓,一隻鞋,正發愣著,典墨對我做了個噤聲的手勢,我們藏身大廳裡一個角落。 典墨低聲念了幾句,手一揮,光芒過處設下三角結界,讓我們完美隱藏。
很快,走廊深處傳來急促腳步聲,我看到一個年輕人拉著李梳走了出來。年輕人很有靈氣,看上去不錯,算個美人,我盯著他看,朦朦朧朧的,初戀的感覺又襲來了。
不過,有一點很怪。這個年輕人的法力居然和李梳不相上下,也像是和典墨同源而出。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們在說什麼我聽不清楚,只聽到李梳突然問,「我的鞋呢?」然後四顧找鞋。
我低頭看自己的手上,正是一隻鞋。典墨冷冷的眼光刺在我背上,我趕忙偷偷把鞋放地上,用腳尖慢慢將它推出結界。
李梳找了好半天,眼光才掃了過來,嘟囔著「怎麼跑這裡來了?」撿起鞋坐下來套上。
典墨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走。」
他一抓我的胳膊,我便頭發暈,剛剛那該是什麼法術吧,睜開眼時發現我們已經在一扇門裡。床上躺著一個光溜溜的人,已經不動了。 這個人,不就是上次典墨帶我去找的那人嗎?我伸手捅捅他,發覺他還活著,只是不會醒過來。
「算他聰明,龜息之術。」典墨簡單地說,「不過,也不會有所影響。哼,這對師徒。」
師徒?
這個人和外面那個年輕人是師徒關係啊?我疑惑著,又問,「為什麼?你不是和他訂立了契約之類的?他倒下了你不是很不方便嗎?」
典墨露出慘白的牙齒和「你以為你知道的就是全部啊」的表情。然後他偏偏頭,說,「他徒弟劉席很快回來了,上。」
呃,上那個秀氣的年輕人,我倒是願意。
不過,你是不是選錯人了?
難道你不知道我是麵人嗎?
麵人的最大特點,難道不是軟嗎?
所以你要我怎麼上?
我盡量委婉地表達了這層意思,典墨居然笑起來,他溫熱的呼吸落在我耳邊,輕輕說,「對對對,是我錯了,」典墨惡意地笑著,用手指捅捅我的肩膀,「所以,你別『上』了,還是『下』吧。」
不待我反應,他一腳撂翻我,讓我立刻倒下攤開。
我還在抗議,「他功力那麼強,我怎麼吸得到。」
「做得到,我會在房裡控制他的抵抗。」
「可是。」我其實有點抵制吸取別人功力這種事情,修煉很不容易的,我自己深有體會。所以這樣做,好像良心有點負擔。典墨瞪了我一眼。我懦懦地閉嘴了,我的良心永遠趕不上他的狠心。我只好化作原形,貼在地板上等候。
一小會兒工夫,那青年男子慌慌張張地跑過來,他一腳踏上我身體的時候,我立刻彈起將他包裹起來。他似是一驚,但還算鎮定,體內法力即刻匯聚,但還沒來得及抵抗,大約典墨做了點什麼,他一下子摔在我身上。
劉席摔在我身上那一刻,我看到他的表情由震驚變為淒惶,法力飛快地從身體接觸處流入我體內。激烈跳動的熱流,是劉席的,而另一股沉穩的力量,就明顯不是他的。最後還有一股,和典墨身上法力簡直一個味道,我突然好像有點明白了。
大約典墨也跟他說了點什麼,借給他法力對付了他的師父,然後又藉我對付他。
不過,這不是便宜了我嗎?吸收了這麼多法力。
我可以感到體內的熱度,我開始扭動身體,自然而然想要更好地融合法力,我還想要一張臉,我頭腦裡閃過了這對師徒的臉,於是模仿他們的模樣,真的,慢慢脫身而起。這年輕人驚惶失措的表情還在我眼前,我心裡嘆息,「你啊,你下手對付你師父之時,可有想到你也有淪為獵物的一刻,而且這一刻來得如此之快?這正是殺人者人恆殺之的道理,你若能……」
我正陶醉在自己的哲學之中,一個飛來水桶砸得我頭昏腦花。
我被壓得扁扁的,好不容易抬起了頭,看見李梳定定看著我。
李梳是想救他吧,不過這麼一個猛砸,如果不是我墊著,不怕把他直接砸死啊。
我和李梳四目相對,他啊啊了兩聲,拔腿就跑。我體內雖然法力洶湧,不過頭腦還算清醒,知道要先看看老大的想法。我眼光看向房內,典墨只露出半張臉,示意我,「跟上去!」
好吧,那就追著李梳好了。
李梳跑是跑,就是速度稍微有點慢。
其實如果他一條直線地跑,那麼跑得慢點也沒什麼,最多我跟慢點好了。可是李梳不但跑得慢,還要迷路。常常是跑了一截發現路不對,又回頭跑,害我在後面追得戰戰兢兢。
典墨讓我跟著李梳,可又沒說跟著他做什麼。跟太近了,怕他掉頭跑的時候撞個面對面,到時候要怎麼辦?跟太遠了,怕他跑丟了,那時候我又該怎麼辦? 我不得不跑跑停停,確保他有足夠的時間在前面迷路和選路。
更可氣的是,李梳慢跑就慢跑吧,迷路就迷路吧,他還要一路雞飛狗跳地吊嗓子,「啊啊啊!正派難做啊!逃命難為啊啊!」
我邊追邊想,李梳你逃跑困難,我追就不難了嗎?你正派難做,我反派就好當了?
我想著想著,沒注意,一不留神發現自己已經追他追到了山崖上。離他還有幾丈遠的時候,我停下來。不為別的,我又不知道追到了該做什麼。
剛停下來,突然覺得自己不對勁。我跑的時候,還沒什麼感覺,可是一停下來,突然發覺那法力在我身體裡洶湧澎湃,心裡難受得慌,有什麼東西灼燒著我的身體。李梳似在說什麼,現在我已經顧不上他了。
經脈異動,法力流竄,精神開始渙散,已經快要無法壓制身體的異變。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很符合我現在的情況。
不會吧,該不會這突然而來的法力超過我身體能接收的程度,就要引發第二次妖化了?
法力攪動,洶湧澎湃,我的肉體已經撐不住,開始冒出一塊一塊的氣泡,糟糕,當真是二次妖化!而且已經要失控了。失控的後果是什麼,我不太清楚,只知道麻煩大了。頭痛欲裂,渾身麻痺,更可怕的是,思維和記憶開始混亂,我還知道,這是魂魄受到過大的法力擠壓,開始破裂。
慘了!已經無法再維持人形,我慘叫一聲,身體大大張開伸展,形成可怕的網狀,不要啊,我拚命維持自己的理智。二次妖化對我這樣的小妖來說,無疑是極度危險的行為,雖然成功的話,也許立時入列仙界也不是不可能,但是失敗的機率,確實大得嚇人。
說白了吧,如果我這樣還沒真正成形的小妖不歷經一兩千年的修煉,直接二次妖化,基本上的後果就是魂飛魄散,永世湮滅。
正受著煎熬,突然聽到一個聲音在頭腦裡響起,「過來!」
身體一軟,向後倒去,將後面那人裹在身下。是典墨?是典墨!
不行了,我要不行了。我痛苦掙扎著,拚命抵禦二次妖化的到來。
「你能撐這麼久,也是不錯。」我身下的典墨似乎很滿意,「好了,來吧。」
劇痛襲來,體內的法力不受我的約束,開始逆流亂竄,我無法控制自己,發出慘烈的叫聲。和我肌膚接觸的東西,正在發狂吞噬我身上的法力,就像我對劉席做過的那樣。法力的流竄很劇烈,連帶著身邊燃起猛烈的青色鬼火。
劇痛傳來,我唯一所想就是掙扎著脫身而去,但一隻手掌硬生生將我壓了回去。接下來的時候頭暈目眩,只覺得身邊的一切都化成了模糊的影像,不再真實,風聲中交雜有人說話的聲音,男的女的小孩的老人的聲音,一會兒像是身處鬧市熙熙攘攘,一會兒又像有金戈交錯殺伐之聲。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正在做什麼。只知道在我包圍之下的身軀,慢慢伸展開,而二次妖化的衝動,被打消掉,身體內的法力,則吞噬了個乾淨。
身下的人,正在成長。
不必看,我感覺得到。
我慢慢癱軟,從他身上滑了下去,緊貼著他,那麼近,我看到了讓我一生都不能忘記的臉。就連我癱軟在地上,眼睛還是一直看著站在面前的這個人。
我不想再描述他的模樣,不知道的人請參考《倒楣就倒楣》。
不要怪我這樣沒出息的樣子,如果和這樣一張臉近距離面對面而你的心跳還不加速的話,只有兩個可能:第一,其實你沒有心,第二,你的心原本就是觀賞用,不能跳。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輪到誰倒楣(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7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輪到誰倒楣(上冊)
是說我好好當我的狗尾巴草礙著誰了?
每天曬太陽等成妖,心心念念的不過就是桃花林裡的美人,
花痴有罪嗎?
為什麼接下來的「妖生」是一路坎坷不順?
先是在成妖前被人拔了煉化,
後來又被迫日夜面對這個比黑炭還黑、還醜,連五官都看不見,
渾身走動詭異金色紋路的鍋底男。
雖然妖毒是很美味的,
可附在他身上吸食,總是有點敗胃口。
就算燕窩一碗,放在痰盂裡給你,你總是吃不下去吧?
來到人類的花花世界,我學到最重要的真理就是──
沒有最倒楣,只有更倒楣!
章節試閱
序 上天安排你倒楣,你是躲不過的。
盛夏,山崖前集聚著幾個書院的孩子,平日吵吵嚷嚷,一刻不得閒的小傢伙們,如今正噤若寒蟬地看著他們的先生。這是個普通的書院先生。他正低著聲音啞著嗓子講道德問題,關於德行和人生的幸福是怎麼樣的相關。
總的來說,這先生是很厲害的。因為世上敢在最缺乏德行的平心崖下宣導道德的教書先生,恐怕還不多。雖然看這個先生的樣子,也是哆哆嗦嗦的,偏生還要繼續講,也是了不得。先生剛剛完成了引經據典的部分,然後用更低的聲音指著山上對小傢伙們說,萬一你們不好好學習,道德敗壞了,那就會被趕上山...
盛夏,山崖前集聚著幾個書院的孩子,平日吵吵嚷嚷,一刻不得閒的小傢伙們,如今正噤若寒蟬地看著他們的先生。這是個普通的書院先生。他正低著聲音啞著嗓子講道德問題,關於德行和人生的幸福是怎麼樣的相關。
總的來說,這先生是很厲害的。因為世上敢在最缺乏德行的平心崖下宣導道德的教書先生,恐怕還不多。雖然看這個先生的樣子,也是哆哆嗦嗦的,偏生還要繼續講,也是了不得。先生剛剛完成了引經據典的部分,然後用更低的聲音指著山上對小傢伙們說,萬一你們不好好學習,道德敗壞了,那就會被趕上山...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阿七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2-09 ISBN/ISSN:9789862066041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