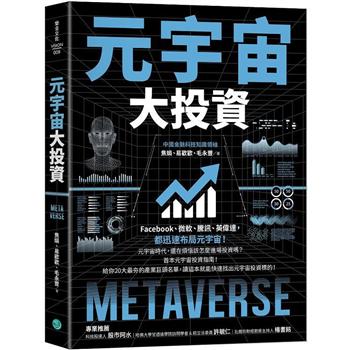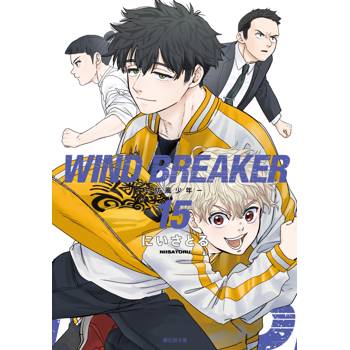楔子
早春的風,在中夜裡,依舊帶著一絲涼意。
京城光華寺的方丈禪房外,一燈大師正孜孜不倦的抬頭凝視著星空,觀測著天象的變化。
只見明月當空,群星耀目,其間最亮的兩顆星子,光芒連閃,忽明忽暗的漸趨黯淡。
至下半夜,這兩顆星竟不約而同的最後閃爍了一下,忽而熄滅。
然其周遭之星辰,光華不減,甚而有一顆星逐漸有增明之兆。
眾多最初環繞著最亮的兩顆星的星辰,緩緩的聚到一處,將突然間亮起的星子圍在中央,在這顆星的輝映下,原本跳動的光芒,皆有穩定的趨勢。
霎時,紫藍色的夜空星光暴盛,竟隱隱有同月競輝之象。
一燈大師收回目光,低頭捋了捋鬍子,沉思道:「帝王星隕,天狼星滅,兩星並存,已是曠古奇事,而今同日隕滅,福兮?禍兮?老衲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兄有何高見?」
旁側的中年人一身青衣道袍,手執拂塵,對於一燈大師所言之事並不驚詫,顯然早已知曉此間情狀,同樣皺眉道:「貧道日間卜得一卦,卦象所言,同大師觀測天象所得,相去不遠。」
一燈大師感興趣道:「道兄精於卜算,老衲素來欽佩,不知卦象如何?」
青衣老道理了理拂塵,而後作揖,「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易位之卦也。變亂將至,我中洲十年安穩,恐已趨盡頭,貧道深恐此兆是禍非福。」
方丈聽到「是禍非福」四字,眉心蹙起,沉默半晌,搖頭道:「非也,非也,帝王星現,而天下大治,天狼星出,則天下大亂。二者共存,其勢相互抵消,是不治,亦不亂也,天下可安。如今同日隕滅,雖盛世不再,須引以為憾,然變亂亦隨之消弭,不可不謂是一大幸事。」
青衣道者聞言,一同看向夜空,但見那新興之星,其光芒雖不如之前的帝王天狼耀目,然其勢甚穩,原本因帝王天狼而彼此對立的眾星辰,在這份不容置疑的穩固下,競相安定下來,似是空前團結之象。
正要開口,突然間,不遠處的林木叢中,一陣「淅唆」聲傳來,青衣老道聞聲暗用內勁,瞬間手中拂塵暴長數尺,向林木中央捲去,其勢雖甚疾,終究晚了一步。
收回來的拂塵尾處,黏著一片褐黃的布塊。
看衣料,正是光華寺中,極為普通的僧袍邊角。
光華寺歷來游離於政局之外,寺中若混有他國探子,本不足為懼,然而每日打坐之時,眾僧鋪位有限,皆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有心人若是已經滲入,必是有一僧人已經遇害。
一燈大師即刻下令鳴鐘召喚寺眾,清點人數,護寺武僧中果然少了一人。
不多時,搜寺的眾僧們在林中找到一處新土,往下挖掘,刨出的屍身,赫然便是那失蹤的武僧。
一燈大師上前探查死因,只見死者面相安詳,除了胸口印有紫色掌痕之外,全身上下,並無其他傷痕。
青衣道者俯身打量這奇特的掌痕,驚詫於這紫色的鮮濃,「看這顏色,恐怕是摧心掌練到了第七層的高手所為,摧心掌出自南齊,唯其皇室之人專有,地位越高,往往所學越精,恐怕這個探子,來頭不小。」
方丈點頭稱是,嚴令全寺戒備後,著手處理遇害僧人的火化事宜,之後誦經超度,自不必說。
卻道那逃走的探子,不是別人,正是南齊王爺──慕容鴻,倉促間躲過青衣老道的拂塵後,雖無皮外傷,但老道內力驚人,既然觸到了衣角,傾吐的暗勁自是不小。
慕容鴻只覺得五臟六腑都在隱隱作痛,將脫下來僧袍捲成一團丟棄在路旁後,堂堂南齊王爺一身單衣,跑去農舍行竊,不慎被屋主發現。
「什麼人不學好,敢來此偷盜?」呼喝聲伴隨著鋤頭迎面劈下。
被農夫們一陣追打後,慕容鴻狼狽的歇在路邊,喃喃咒罵:「媽的,最近過的是什麼日子?本想離間計失敗後,中途暗殺了那中洲皇帝和鎮國將軍,不想那些廢物竟然被幾顆雷火彈嚇得畏縮不前,今夜這老和尚和臭道士囉嗦半天,全無重點,還害得本王行跡敗露受了內傷。」
南齊出名風流瀟灑的閒散王一瘸一拐的穿著破爛的單衣走在路邊,內傷外傷弄得他狼狽不堪,便把帳通通算到了害他失敗的中洲皇帝身上,「李承業,你給我記著,本王不會輕易善罷甘休的。」
第一章
春日裡,桃花盛放,柳枝輕嫋,暖風薰人欲醉。
赤焰軍的副統帥奉天,便在這陽光璀璨的晴日回到了京城。
白衣紅馬,輕騎直入軍中,一路含笑向打招呼的兵士們點頭。
刀戟林立的軍營,從外頭看來,依舊井井有條,操練的兵士們呼喝著號子,長矛盾牌交錯,陽光下,銀芒閃爍,一派輝煌。
至於裡頭就……
「軍師,你終於回來了。」一干副將們幾乎是痛哭流涕的衝上前來,將一月前出外督運糧草方歸的奉天團團圍住。
「出了什麼事?」白衣副統帥費力的從激動的抓著他搖晃的武夫中掙脫出來,「阿寂呢?怎麼我一路走來,都沒見到他的身影,通常這時,他不是都在軍中練兵?」
此話一出,霎時全場安靜。眾人表情各異,推推擠擠,誰也不肯先行開口。
奉天臉一沉,「到底出了什麼事?」
最終,有人因為擔心,率先開口:「軍師,你外出幾日後,大將軍練完兵進宮伴駕,至今月餘,不曾回營。其間只捎了幾封信回來,告知屬下,他有要事,不能離宮……」
話未落,底下便一片竊竊私語聲,「該不是宮中出了什麼變故吧?」
「應該不會,聽說皇帝還是按時上早朝的。」
「會不會是皇帝扣住了咱們大將軍,不讓他回來?」
「有這個可能,可大將軍寫來的信中半點暗示也沒有啊!」
「這信也許是皇帝找人仿照大將軍的筆跡寫的。」
「不可能,大將軍的字我看了十年,怎會認錯?」
「那會不會是咱們將軍在宮中看上了個把美人,樂不思蜀?」
「是啊,宮中啥都不多,就是美人多啊!」
「大將軍真是豔福不淺哪!」
「……」
鎧甲嚴整的副將們圍在一處,發表了各自的「高見」。
奉天沉默的傾聽半天,對於事情的真相,依舊一無所知。
「好了。」白衣人揮了揮手,「該幹什麼幹什麼去,我進宮去探探情況,順帶把你們八卦的內容和阿寂交流一下,相信等他回來,應該會把不在之時,練兵落下的部分通通補回來!」
「不要啊!」剛才還在興高采烈談論的副將們立刻哀號,「軍師你太殘忍了,我等也是憂心大將軍的安危才在此討論的啊!」
奉天驚訝,「是嗎?我以為諸位是過於思念阿寂才圍上來的。」
眾人搖頭又點頭,寧大將軍在時,練兵的狠勁令人髮指,不在之時,又挺讓人想念。
白衣人微笑,「我知道軍中無聊,你們找點樂子而已。這就進宮,看看你們愛戴的大將軍目前處於何種情形!」
「軍師,要記得啊!我等啥也沒說過啊!即使有所揣測,那也是過於關心寧將軍的安危,才會一時失口……」
身後被鎮國大將軍寧不寂的魔鬼練兵法摧殘了若干年的副將們不死心的挽回著,如果他們剛才隨口亂說的話落到寧將軍耳中,未來的日子著實堪憂……
奉天笑著步出軍營,來到郊外山坡的一處山洞。
山石嶙峋,入宮的暗道掩沒在一片荒草之中,多年未曾有人踏足,剛打開入口,一股子霉味就撲鼻而來。
望了望正午明亮的陽光,這時候,要避開侍衛,直闖禁宮,恐怕不易,眼前這條密道,就成為唯一可行的路徑。
奉天撩起衣襬,踏入洞口,一按機括,入口自動閉合,兩邊牆上的火把無風自燃,照亮前方。
這條密道建於先帝在世之時,知道的人沒有幾個。奉天快步向前走著,心頭滿是疑慮。
寧不寂平日裡律己甚嚴,除非作戰之時受了重傷不能下床,否則每日幾乎都是準時出現在練兵場上親自練兵,風雨無阻。
現下他會滯留宮中不歸,除非是生了重病,但重病之人,怎會有精力三日一封信,派人送至軍中,布置軍務事宜?
如若生病的不是寧大將軍,那便只可能是皇帝了,但又聽說,皇帝是每日按時上朝的。
「這兩人到底在搞什麼鬼?」旅途勞累的白衣人加快了前進的步伐,「希望不要出什麼事才好。」
密道的出口,在御花園靠近冷宮的角落,因為鬧鬼的傳聞,向來少有人煙。
奉天一身白衣,在陽光下極為醒目,他也不避諱,熟門熟路的逕自往朝陽殿而去。
因為姿態太過從容,巡視的禁軍反倒沒人敢上前盤問。
直到進入了守衛的核心之地,聞訊而來的禁軍統領才上前阻攔,「奉天軍師,寧將軍無恙,不出月餘,便可回營,尊駕冒然闖宮,恐怕不妥,還是在此止步為好。」
奉天跟這禁軍統領相識已久,看到他凝重的臉色便猜到了事情的大概,低聲詢問道:「可是陛下出了什麼事?」
禁軍統領宇文旋個性耿直,見此事皇帝沒有瞞著大將軍的意思,想來告知奉天也無妨,因此悄悄的把白衣人拉到一旁。
「陛下月前中了一種奇怪的毒,白日可如常行事,與常人無異,然而一到夜裡,便周身無力,內勁全失,若無人攙扶,連行走都成問題。」
奉天皺眉,這種毒聽來極為耳熟,不知道是不是他想的那種,於是沉吟道:「御醫們怎麼說?」
「御醫們多日來束手無策,連藥方都不敢輕易配製,就怕藥性相剋,加重陛下體內的毒素。」
這就怪了,看這光景,雖然症狀相似,但御醫都束手,看來皇帝中的應當不是軟魂散。
白衣人思忖片刻:「阿旋,今番你不要攔著,我略通一點醫道,且讓我探視過陛下後再行回營。」
宇文旋向來爽直,既然該說的,不該說的,都已經告知了這位赤焰軍軍師,再攔著他也沒有意義,答應一聲,便去通報。
沒多久,滿臉憂色的寧大將軍走出殿外,看到好友,目光中露出一絲希望,「奉天,你來得正好,快來看看陛下的情況,宮裡頭那群庸醫,個個都是飯桶,將近一月,還是半點法子也想不出。」
安慰的拍拍對方的肩,奉天道:「先過去看看吧!陛下可是在寢宮?」
寧不寂搖頭:「這會兒正在御書房批閱奏章。」
奉天走到御書房外時,皇帝已經批完了大半的奏摺,趁著寧大將軍不注意,回過身來對白衣人打了個手勢,表示自己無礙。
「陛下,微臣有些軍務方面的事想請教寧將軍,可否暫時借人一用?」宇文旋接到皇帝連續的暗示,終於明白過來,借詞幫忙支走寧大將軍。
皇帝點點頭,「朕白日裡尚可,軍務要緊,你倆可先行離去。」
寧不寂雖然迫切的想知道奉天診治的結果,但他也不是因私廢公之人,皇帝中毒也快一個月了,一直不好不壞,也不必急於一時,所以很合作的跟著宇文統領走出門外。
兩人的腳步聲漸漸遠去後,皇帝方才長長的鬆了一口氣。
雖然對方已經暗示了沒事,奉天還是不放心的搭了搭皇帝的脈搏,片刻後釋然,「軟魂散?」
握著朱筆的皇帝興高采烈的點頭。
奉天無奈的問:「阿寂可是哪裡又惹到了陛下?」
皇帝一怔,反常的搖頭:「這倒不是。」
「那陛下為何在自己身上下軟魂散?要知這毒雖然無害,卻會讓所中之人七七四十九日內,夜間喪失內力,體力比之常人,更差三分。」
「朕要的就是這個效果。」
「這是何故?」
「呃,」皇帝不好意思道,「月前閒來無事,和寧不寂比劍之時,以勝負作賭……」
十餘年來一同征戰沙場,沒有人比奉天更瞭解寧不寂的實力,因此白衣人肯定的問:「陛下賭輸了?」
皇帝沮喪的點頭。
奉天不贊同道:「願賭服輸,陛下怎可失信?」
皇帝無語,他不是不想履行諾言,只是當日裡仗著寧不寂重傷未癒,心想好歹打個平手總綽綽有餘,因此輕率的答應了大將軍的挑戰。
如今想來,實在失策,寧不寂若沒有完全的把握,怎肯下這種「打輸了,一月之內,夜間全憑贏家發落」的賭注。
結果夜裡,勝者在床上花樣百出,在知曉了身下之人懷有上好武功後,寧大將軍全無顧忌,所有曾經以為對方文弱、不敢施加的手段通通施展出來。
皇帝叫苦不迭,偏偏有言在先,不好反悔,故而在看到御花園栽種的金盞花和曼陀羅後,心頭之激動,可想而知。
「朕有失信的理由,你以後就知道了。」他含糊的一句帶過,揪住白衣人的袖子,「總之你千萬要瞞住寧不寂這事,朕與他的賭約今日就到期了。」
「金盞花和曼陀羅合成的軟魂散效力是四十九日,陛下所中之毒還有幾日?」
皇帝歎了口氣,「尚餘二十五日。」這是唯一美中不足之處了。
「請恕微臣無能為力。」奉天遺憾的看著他。
「朕知道你素來跟寧不寂投契,但這次真的有理由……」
「陛下,臣也想幫你瞞住的……」白衣人神情古怪,欲言又止。
皇帝暗自慶幸,忙不迭的打斷,「你肯瞞住就好。」
奉天一臉同情:「恐怕晚了!」
「啊?」
「阿寂此刻就在門外。」
「……」
寧不寂倚門而立,臉上殊無不悅之色,只是仔細的詢問好友,「這四十九日後軟魂散藥力散去,可會留下什麼後遺症?」
奉天思忖片刻道:「按醫書記載,金盞花本身無毒,而曼陀羅有麻醉之效,這兩者所合成的軟魂散並非毒藥,自然不會有什麼後遺症。除非……」
皇帝大奇:「還有除非?」軟魂散的製作方式是幼時奉天閒暇之時教他玩的,原以為無毒無害,不想竟還有其他枝節。
「只要不碰上合和果,基本無大礙。」
白衣人說完,忽然發現不對,對著臉色突變的兩人發問:「合和果生長於北境,陛下去徐州之時,可曾誤食?」
皇帝的臉色很難看:「吃了許多,但是都過了這麼久……」
奉天目光凝重,想起朝陽殿中暗探無數,壓低聲音道:「中軟魂散之人,原本四十九日後藥力自退,並無妨礙,但有一點,若是在此之前曾服食過合和果,則藥性會殘留體內,三載之內,不定時發作,發作日數不定,有人一年一次,也有一年數次,發作之狀況同初中軟魂散的情形相同。」
聽到還有此等關節,皇帝不由得用眼光埋怨白衣人,「當日教我之時,怎未曾告知?」
奉天無奈的看了一眼御書房的案几,又望望外頭的草地,然後抬頭凝視天花板,顯然是在暗示,「我教到一半,你幹什麼去了?」
皇帝這才想起,年幼之時,他玩心過重,聽了大概,自以為配製之法講完已是全部,對方剛告一段落,就被他硬纏著捉蛐蛐去了,頓時無話可說。
另一側的寧大將軍倒是鬆了一口氣:「如此便無礙,平日裡看緊陛下即可。」
皇帝和奉天互望一眼,對於寧不寂被騙二十餘日,現今發現真相,竟未有絲毫氣憤之意,皆感奇怪。
騙人的那個當然不好問這種問題,白衣人可沒有這層顧忌,小心的探問道:「阿寂,你沒生氣?」
寧不寂疑惑,「我應該生什麼氣?」
奉天看了一眼皇帝,想到多問提醒了寧大將軍,明顯陷皇帝於不義,因此並不作答。
正要轉移話題,寧大將軍卻也不笨,自行猜道:「你是覺得我二十餘日被蒙在鼓裡會有所不快?」
他接下去道:「二十幾天來我擔足心事,只怕陛下會有所不測,現今發現他無事,高興都來不及,難道要為了他不會毒發身亡而生氣?」
此話全然真情流露,語中欣喜之意懇切而真摯,聽得皇帝一呆,反倒心中無端生出愧疚之意。
尚未答話,奉天想起一事,先一步開口:「陛下與寧將軍以何作賭?」竟然逼得堂堂一國之君對自己下毒來抵賴。
皇帝咳嗽兩聲:「朕是病人,先去休息了。」起身便要溜走。
白衣人只好把目光轉向大將軍。
沒想到,賭勝的那方同樣沒有回答的意思,顧左右而言他道:「既然陛下無事,我先回軍營看看。」
言畢,同樣預備出門。
奉天作為赤焰軍的軍師,多年來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之外,觀察能力自是一流。
看到兩人耳後同時出現可疑的暗紅,已然明白。
白衣人這樣建議皇帝:「陛下何不把軟魂散下在阿寂身上,不是一樣能達到目的?」
皇帝折回來解釋,臉上紅暈未褪,「若下在他身上,那便是你口中的抵賴了。」
言下之意便是,「朕還是願賭服輸的,只是寧不寂對著『病人』,自己放棄了得到賭注的機會,這須怪不得別人。」
奉天忍不住翻個白眼,心道:「你這種隨時會毒發出事的樣子,阿寂若還下得了手,那當真是禽獸不如了。」
一回頭,正見寧不寂對他怒目而視,顯然這偏幫皇帝的建議讓他很是不滿,白衣人只好解釋道:「我只是覺得奇怪,隨口問問。」
罷了罷了,這是他們的家事,外人攪和在這裡,一點好處也沒有。
奉天揮揮手,道一聲:「告退。」便安心的走出門去。
御書房內,皇帝和寧大將軍面面相覷。
平日裡在榻上什麼荒唐事都做盡的兩人,卻因著白衣人臨去前瞭解的目光,同時一陣赧然。
「陛下,微臣離開軍營多日,請允准臣回營探視。」寧不寂恭恭敬敬的行禮。
「卿但去無妨。」皇帝落落大方應道。
臣子不可背身朝君,寧不寂一直到門外,方才側身離去。
這二人相處十餘年來,從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此時破天荒的依足了禮數,竟然雙方一點都不覺得彆扭。
皇帝坐回案几旁,繼續批閱剩下的奏章。
朱筆在字裡行間圈圈畫畫,分神想起寧不寂方才所言:「現今發現他無事,高興都來不及,難道要為了他不會毒發身亡而生氣?」
心頭湧上一點愧疚和喜悅,「也許,朕這次真的做錯了一回,不該這樣急著對自己下毒,應該跟他商量一下。」
想著想著,一下午都笑容滿面,竟也不覺得政務繁重,比往日更輕鬆的批完了奏摺。
一望窗外,日頭正要偏西。
「不好。」他迅速起身,卻已經來不及,身子一軟,便要跌倒在地。
冷不防背後一雙手臂探出,接住了倒下的身體。
瞥了一眼案頭堆積的奏摺,寧不寂皺眉道:「怎會批得這樣晚?」攔腰抱起軟魂散發作之人,往浴池的方向走去。
皇帝尷尬的倚在大將軍的懷裡,努力的說服自己,「二十多天都這麼過來了,不差這剩下的日子。」
想歸想,心裡頭到底不安,畢竟那時寧不寂尚在擔憂他的「病情」,完全忘記了打賭這回事,現下知道他無恙,會怎麼做,就極難預料。
這人身上有著淡淡的硫磺味道,看來是從軍營練完兵回來,沐浴過後才來到御書房找他。
皇帝努力的掙扎著想下地,半晌後,完全徒勞無功,喘息方定,開口道:「既然已經沐浴過,就不必再去溫池了吧!」
寧大將軍不贊同:「微臣雖然已沐浴完畢,然而陛下尚未,自然是要去的。」
皇帝這才想起,一下午心神恍惚,雖則習慣使然,在奏摺上的批註依舊一板一眼,但到底忘了最重要的一件事——須在日落前趁著軟魂散未發作之時,自行沐浴完,鑽進被中。
不然,便會淪落到眼下這情形,身不由己的讓人抱著走,連掙扎的氣力都無。
他從下藥後自身的處境,到寧不寂會有的反應,原本都一一算計妥當,只挨到四十九日一過,叫御醫裝模作樣獻上解藥,一切便迎刃而解。
只可惜日子才過去一半,奉天就半路殺出,戳破謊言……
皇帝不禁暗暗思考,近日裡可曾不小心得罪過白衣人?
否則好巧不巧,為何不挑別的時辰,偏在寧不寂折返之時,跟他說及最關鍵之處,而且還提醒寧大將軍要記得生氣。
是了,當日奉天有叮嚀他,不可冒然對那些軍中的探子下手,他不聽勸的瞞著對方讓這些人去徐州送死,使得白衣人得到消息後,擔憂之下趕去徐州,從而受了重傷。
想起小時候奉天常教他的一句話:「凡事要學會忍耐,等待最佳的時機,儘量讓別人代勞。」
這是用來對付敵人的,眼下不會拿他開刀吧?
皇帝懷著微弱的希望問抱著他的大將軍:「下午你是獨自去練兵的嗎?」
寧不寂搖頭:「和奉天月餘未見,有許多事要聊,所以一同去的,陛下怎會問起這個?」
「朕擔心你和奉天同時不在,軍中會有變故。」他膽顫心驚的繼續問:「就聊了些軍務?」
「倒也不是,奉天詳細的向臣解釋了一遍軟魂散的配製過程,一再強調所中之人不會有大礙,讓臣千萬不要有所顧慮,以免貽誤軍情。」
「……」回了軍營中都不忘再強調一遍。
冷汗「刷刷」的從額頭滑下,皇帝默默的在心頭飲泣,「奉天,你太會記仇了!」
「真的沒事嗎?」寧大將軍擔憂的望著懷中虛弱的人,「怎會連沐浴都忘了,可是情形惡化,這軟魂散提前發作?」
皇帝搖搖頭:「朕沒事。」
想起自己為了這人的一句話而心頭雀躍了整個下午,一時臉紅過耳。
他本就生得極為俊秀,白皙的臉一紅,更添三分秀色,這也是寧不寂平日裡最愛作弄他的緣由。
寧大將軍問話之時,一直關注著懷裡人的神情,皇帝神色間的所有變化,盡入他眼中。
他惡習不改,調笑道:「陛下政務繁忙,這沐浴之事,微臣代勞,自是義不容辭。陛下只要安坐即可,何必為了此等小事,見臣到來,迫不及待以身相迎?」
皇帝分辯道:「朕根本沒發現你進來。」心底暗罵:「誰迫不及待了?」
寧不寂忍笑:「臣只是覺得陛下倒下的時機巧了點,正趕在微臣進門之時。」
他自己算好日落的時辰跑去找人,卻抵死不承認,非要栽贓對方投懷送抱。
皇帝心頭大慪,憤懣得幾乎吐血,偏生無言以對,臉上紅暈愈甚,更添麗色。
寧大將軍目的達到,欣賞夠懷中皇帝動人的神色後,不欲逼人太甚,替對方沐浴之時,倒沒有不軌的舉動。
只是皇帝天生敏感,一番洗浴下來,讓人挨挨碰碰之下,要不起反應,著實困難,他一動情,寧不寂自也不能倖免。
於是洗完浴,兩人躺在偌大一張龍床上,大眼瞪小眼半天。
皇帝警告道:「一月賭期已過,汝不可再肆意妄為。」
他不提還好,提了,寧不寂反倒想起了身側之人,踐約之日不足六日,又憶及奉天下午曾言:「軟魂散無害,不必有所顧忌。」
於是點頭道:「不錯,一月之期確實已過。」
皇帝狐疑的望著他,對於這人突然這麼好說話保持不信的態度。
果然,寧不寂續道:「因此微臣肆意妄為之時,陛下有權利反抗。」
試著抬了抬手,不出意料的,依舊毫無力氣,皇帝望著眼冒綠光的大將軍,心頭兀自疑惑,「都是騙人的吧?這哪是沒生氣的樣子?」
遠處,赤焰軍的軍營裡,白衣人正對著一下午跟著寧不寂練兵練趴下的副將們微笑,「所謂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早叫你們不要趁著阿寂不在之時偷懶了。」
眾將默然……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衷情:岸谷之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3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衷情:岸谷之變
身為中洲帝王,
自應事事為國事考量,
況且他從來都不是個膽小怕事之人,
為了安定北境,北魏一行他是勢在必得!
但隻身犯險的如意算盤打得好,
卻無法擺脫鐵了心要護送他去北魏的寧不寂。
面對這任職大將軍的正直武人,
再加上兩人關係非同一般,
就算他尊為皇帝,也無法強壓一頭,
最終仍是遂了寧不寂的意。
帝王心術,運籌帷幄,
他的目標……絕對要達成!
《臥榻之側》系列作──皇帝與大將軍的糾纏之愛依舊蔓延!
章節試閱
楔子
早春的風,在中夜裡,依舊帶著一絲涼意。
京城光華寺的方丈禪房外,一燈大師正孜孜不倦的抬頭凝視著星空,觀測著天象的變化。
只見明月當空,群星耀目,其間最亮的兩顆星子,光芒連閃,忽明忽暗的漸趨黯淡。
至下半夜,這兩顆星竟不約而同的最後閃爍了一下,忽而熄滅。
然其周遭之星辰,光華不減,甚而有一顆星逐漸有增明之兆。
眾多最初環繞著最亮的兩顆星的星辰,緩緩的聚到一處,將突然間亮起的星子圍在中央,在這顆星的輝映下,原本跳動的光芒,皆有穩定的趨勢。
霎時,紫藍色的夜空星光暴盛,竟隱隱有同月競輝之象。
一...
早春的風,在中夜裡,依舊帶著一絲涼意。
京城光華寺的方丈禪房外,一燈大師正孜孜不倦的抬頭凝視著星空,觀測著天象的變化。
只見明月當空,群星耀目,其間最亮的兩顆星子,光芒連閃,忽明忽暗的漸趨黯淡。
至下半夜,這兩顆星竟不約而同的最後閃爍了一下,忽而熄滅。
然其周遭之星辰,光華不減,甚而有一顆星逐漸有增明之兆。
眾多最初環繞著最亮的兩顆星的星辰,緩緩的聚到一處,將突然間亮起的星子圍在中央,在這顆星的輝映下,原本跳動的光芒,皆有穩定的趨勢。
霎時,紫藍色的夜空星光暴盛,竟隱隱有同月競輝之象。
一...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起霧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05-05 ISBN/ISSN:9789862066744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B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