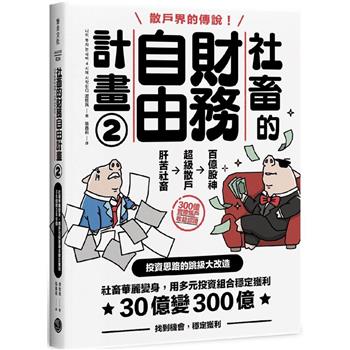一、夜弦
立秋以來的第一場雨,在夜裡簌簌落下,涼意沁人,夜弦從紛亂的夢中驚醒,在五更的秋寒中竟滲了一身細汗,再無心安枕,乾脆披衣坐起,挑亮了燈盞,對著窗外深不見底的夜色發起呆來。
邊關的捷報傳來已有月餘,算算日子,再有三兩天,鎮北將軍沈英持該率大軍凱旋了,夜弦胸口一陣躁動不安,長長地吸了口涼潤的空氣,壓下心頭隱隱的雀躍。
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分別了半年,每天都在想他。
一顆心像水上的浮萍,漂移不定,乍喜乍憂,邊關的戰事時緩時急,京城中總能聽到他的消息,即使是深居簡出的夜弦,貼身丫頭寶珠也會繪聲繪色地描述那人的一舉一動,真切宛如親見。
末了總是抿唇一笑,眨著一雙靈動的大眼睛看他,調侃一句:「公子可是思念將軍了?」
身邊的人怕是都看出來了吧?夜弦望著跳動的燈花,淡淡地笑了,一雙漆黑如墨的眼瞳映上迷離的光彩,胸口那一點帶著甜意的微酸慢慢擴散開來,彷彿連四肢百骸都浸透在濃郁的思念中,那其中還夾雜著一點無措的恐慌--記得聽聞沈英持負傷的時候,那種喘不過氣來的焦慮與憂心如焚的掛念,胸口疼得好似要裂開,恨不得插翅飛到邊關,是生是死,都陪在他身邊。
雙頰泛起脈脈的熱,穿窗而入的冷風喚回神遊天外的思緒,夜弦攏了攏衣衫,身上漸覺寒意逼人,心中卻依舊躁亂得全無睡意,正想起身去走廊裡站一會兒,門外傳來由遠及近的腳步聲,是巡夜的人麼?才這麼想著,房門被推開,夜弦驀然抬頭,又驚又喜地看著門口俊朗偉岸的男子,雙唇翕動了幾下,竟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沈英持回手闔上房門,幾步走到他面前,抬起他的下巴,低聲問:「怎麼,高興得連話都不會說了麼?」
夜弦瞪大了眼,生怕這一切是上天賜他的美夢一場,他屏住呼吸,一手撫上沈英持略帶滄桑的面容,聲音低啞微顫:「你……你怎麼……」
「太想你,快馬加鞭趕回來了。」沈英持滿意地攬過他的腰,低頭吻了下去,霸道的不容拒絕的親吻,品嚐著他朝思暮想的唇瓣,夜弦低喘一聲,雙臂環上他的頸項,柔順而熱情地與他唇舌交纏,身體緊緊貼在一起。
一吻終了,夜弦喘個不停,扶著沈英持的肩膀平復了呼吸,子夜般的眸子漾滿柔情,看著他被雨水打溼的衣袍上風塵盡染,夜弦走到桌前倒了杯茶給他,道:「我叫下人燒洗澡水給你。」
一轉身,又被抱了個滿懷,滿盞的茶水潑了出來,沈英持笑得有幾分頑皮,低頭咬他的耳朵:「我等不及了,夜弦,難道你嫌棄我不成?」
夜弦搖了搖頭,將臉埋在他的頸窩,幾近貪婪地嗅著對方夾雜著青草氣息的男性體味,幾不可聞地低語道:「我怎麼可能會嫌你……」
清晨時分,寶珠帶著兩個丫頭來伺候夜弦起床,在門口看到了沈英持丟下的斗篷,她識趣地停下了腳步,對著跟來的丫頭做出噤聲的手勢,悄聲說:「去告訴管家,將軍回來了,昨晚宿在夜公子房裡。」
床帳不住地抖動,壓抑不住的呻吟聲縈繞其間,混著粗重的喘息,夜弦趴臥在被褥上,細瘦柔韌的腰被一條健臂托起,隨著身後的撞擊而扭動迎合,紅腫的唇吐出碎不成聲的呻吟,體內盈滿的白濁由於身後熱楔的一再侵犯而溢出穴口,沿著大腿滑落下來,沾染床褥。
夜弦繃得泛白的手指抓擰著床單,努力想在洶湧而來的快感中保持一分清醒,卻是徒勞,沈英持一手包裹住他前方顫抖的分身,放緩了律動,然而每一下都撞擊在他最敏感的地方,逼出一聲聲失態的吟叫,夜弦的眼淚迸了出來,眼神渙散,沈英持扳過他的臉蛋與他深吻,將對方情動至極的尖叫聲吞嚥下去,感覺到一股熱液沾溼了手掌,而包裹著自己的柔軟火熱痙攣著收緊,銷魂蝕骨,他滿足地低歎一聲,也隨之釋放。
半年未見,一朝重逢,對他的渴求再也無法壓抑,兩個人纏綿竟夜,到天明時分才雲散雨收,夜弦渾身虛軟地喘息著,沈英持緊摟著他的腰,沉甸甸地壓在他身上。
雖然被壓得氣悶,但是那種熟悉的溫度與重量卻讓他覺得無比心安,只是……夜弦動了動腰,被反覆侵佔到酥麻的後穴,仍能清楚地感覺到異物的存在。
他紅著臉轉過頭來,小聲道:「把你的那個東西……拿……拿出去……」
「嗯?」沈英持低沉的聲音讓人酥了骨頭,而他探到相連之處的大手卻充滿調戲的意味,「你不喜歡?」
夜弦把臉埋在枕頭裡,悶聲悶氣地央求:「英持……」
沈英持親親他的後頸,暫時收起欺負人的念頭,緩緩退出夜弦的身體,將他翻過身來,伸手摟住,調笑道:「跟了我這麼多年,怎麼,還害臊麼?」
夜弦濡溼的黑眸乖順地望著他,順手挑過他一縷長髮在指間把玩,道:「我……還是記不起來,英持,對不住……」
三年前,他從一場大病中醒轉,前塵往事俱已忘懷,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從服侍的丫頭寶珠口中得知,他自小就跟著沈英持,從那人一文不名到位列朝堂身居顯貴,始終不離不棄,相濡以沫,沈英持也對他獨寵珍愛,連侍妾都不曾納過,這三年來更是慇勤備至,縱然是聚少離多,這份深情厚意,也足以讓夜弦心動不已了。
「傻話。」沈英持一指點住他的唇,眼中柔情萬千,「別去想那些了,你只消記住,我會疼你一輩子就好。」
夜弦點了點頭,睏倦感陣陣襲來,他枕著沈英持的手臂,打了個呵欠,漸漸沉入夢鄉,而那個一直擁著他的男人,手指輕輕撫過他的後背,覆上一個清晰的虎紋刺青,寵溺的眼神變得幽深難測,若有所思地盯著他。
夜弦再度醒來時,已近晌午,雨雖然停了,天色卻依然陰沉晦暗,溼冷的空氣帶進幾分桂花的香味,若有若無地縈繞在鼻端,夜弦深吸了一口氣,閉上眼睛靠在床頭。
被褥換了新的,早已散盡餘溫,身上也乾淨清爽,昨夜種種,恍然如夢,然而腰間傳來的陣陣酸軟疼痛告訴夜弦,那是真的,他真的回來了。
撐著快要散架的身體起來穿衣,哆哆嗦嗦地繫好衣結,指端彷彿殘留著堅實而火熱的觸感,讓他回憶起自己是怎麼一遍遍地撫摸著對方結實汗溼的肌肉,夜弦不禁有些恍惚,三年前失去的記憶仍然讓他耿耿於懷,像是丟失了珍貴的東西,總令人忐忑不安。
少年時的沈英持是什麼樣子,他很想記起來,而在陪伴著他的那麼多年,兩人又是如何相處呢?
在他心中,自己究竟是何等身份?
若說寵孌,夜弦已經過了稚嫩纖細的少年時代,而沈英持對他確是一片真心,三年來不娶妻不納妾,亦很少涉足秦樓楚館,像他那樣身份的男人,即使是對結髮妻子,也未必會如此專一,夜弦明白他的好,越是明白,一顆心陷得越快,無法自拔,沉迷中卻免不了患得患失--兩個男人,如何能天長地久?
開門聲喚回他的思緒,寶珠笑盈盈地道:「公子總算醒了,將軍還特意吩咐過讓奴婢們晚些再來伺候。」
夜弦回了她一個淺淺的笑容,披上外袍,起身梳洗。
沈英持清晨進宮面聖,晌午被留在宮中用膳,夜弦一個人對著滿桌菜餚,困乏已極,分外提不起精神,草草動了幾筷子,便叫人撤下了,寶珠見他胃口不佳,叫廚房做了些甜品端上來,硬逼著他吃完,夜弦眼皮都快黏在一起,大口吃完甜羹之後,碗一推,腳步虛浮地晃進內室,和身撲在大床上,連衣服都顧不得脫就倒頭睡下了,寶珠為他解開外袍,脫掉鞋子,順手拉過錦被蓋在夜弦身上,無奈地歎了一聲,自言自語道:「將軍也真是的,怎麼沒個節制,把公子累成這樣。」
半夢半醒的夜弦聽見她的話,臉皮紅了紅,不自在地轉過頭去,整個人縮進被子裡,寶珠忍住笑,輕手輕腳地退了出去。
收拾了碗盞下樓,迎面撞見匆匆趕來的門丁小池,對寶珠揖了一揖,道:「煩勞寶珠姑娘稟報夜公子一聲,黎國的使節來拜謁將軍,拜帖在此。」
寶珠皺眉,道:「將軍還沒回府,找公子做甚?公子不管事的,你去找管家。」
小池一張臉垮了下來,道:「劉伯一大早就出門採買去了,府裡能主事的只剩夜公子一人,誰不知道他也算半個將軍夫人……」
「閉上你的嘴!」寶珠低斥一聲,「這種話少在公子面前說,真不知道你是冒失還是笨得不透氣!」
夜弦在府中的地位很是尷尬,身為男子,注定名不正言不順,縱使將軍把他寵上了天,「將軍夫人」的名份,也斷然落不到他頭上。
小池委屈地扁了扁嘴,看著手上的拜帖,撓頭道:「那,這個怎麼辦?」
「怎麼回事?」低沉的男聲插了進來,兩人驀然抬頭,對上沈英持問詢的目光,寶珠行了一禮,笑道:「黎國使節前來拜謁,將軍沒碰見麼?」
「打發了。」沈英持輕描淡寫地一揮手,問:「夜弦呢?」
「夜公子剛歇下。」寶珠指指樓上,拖著還沒反應過來的小池,飛快地告退。
房內簾幕低垂,幽沉晦暗,沈英持撩開床幃,靜靜地凝視著那半掩在枕間的睡容。
忘記了過去的夜弦,純稚如紙,像初生的嬰兒一般依賴著自己,倘若,他回想起往昔的種種,這番景象,是不是只有在夢中才能重溫?
手指輕輕拂過他的臉龐,眷戀著那溫暖的氣息,沈英持一時忘情,低頭輕吻他的面頰,一手滑到他的頸項,按住一處溫熱的脈動。
只要再用力些,他就完全屬於自己了,沈英持漸漸箍緊手指,神情冷冽猙獰,沉睡中的夜弦皺起眉頭,不安地低喃一聲:「英持……」
窒息的疼痛在胸口漫開,沈英持驀地鬆開手,盯著夜弦頸間隱隱的瘀痕,半晌,緊鎖的眉頭平緩下來,手指輕輕地摩挲著他的頸側,眼眸中滿是憐惜。
夜弦被擾醒了,半睜開眼睛,含糊地輕喚一聲:「英持?」
「嗯。」沈英持脫靴上榻,將夜弦連人帶被擁進懷裡,歪著頭看他,問:「還想睡麼?」
夜弦搖頭,閉上眼睛,愜意地靠在他身上,低聲道:「做了個怪夢,夢見你我對峙沙場、兵刃相見。」
本以為對方又會笑話他胡思亂想,沈英持卻沒做聲,將他擁緊了些,子夜般深邃的眼眸凝視著他,溫柔中閃動著莫名的傷感,夜弦心中一悸,撐起上身,疑惑地看著對方,感覺有什麼東西正在胸中左衝右撞、蠢蠢欲出,只是無論如何也憶不起那如飛沙散霧般的過往。
沈英持回了個溫柔的笑容,放開他起身,道:「宮裡有夜宴,不能陪你了,叫寶珠丫頭過來侍候,我盡量早些回來。」
夜弦點點頭,自然地服侍他更衣,沈英持一雙濃眉微蹙,不悅地按住他的手,道:「這些瑣事,叫下人來做就好。」
夜弦愕然,問:「你……我服侍你不是天經地義麼?」
沈英持執起他的手,笑道:「你歇著吧,等我回來,有你累的呢!」
曖昧的低啞聲音暗示了又一夜的濃情蜜意,夜弦收回手,心頭的疑惑又濃了幾分。
沈英持離開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夜弦立在廊上,望著檻外扶疏的花木,晚風帶著沁膚的涼意,他傾身過去,摘了一片梧桐葉在指間把玩。
修長有力的手指骨節分明,掌心還帶著薄繭,這雙手,以前究竟是怎樣,挽弓持劍還是執斧劈薪,無從知曉。
「公子,晚膳備好了。」寶珠帶著幾個擺飯的丫頭,娉娉裊裊地上樓來,柔聲道:「夜裡風涼,還是進屋裡去吧,凍病了我可沒法向將軍交代。」
聽出她話裡三分調侃,夜弦笑道:「我有那麼嬌弱麼?妳們將軍怕是杞人憂天了吧!」
寶珠頑皮地皺皺鼻頭,一揮手讓那些丫頭先進去擺飯,她倚著欄杆,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看著夜弦,道:「將軍這番出征平亂,又立戰功,你猜皇上會賞他什麼?」
夜弦淡然一笑,漠不關心地道:「不外是黃金美人、寶劍名駒罷了。」
寶珠湊近了些,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道:「我聽劉叔說,皇上似乎有意把榮玉長公主許配給將軍。」
夜弦胸口一緊,眼中仍是波瀾不驚,淡淡地道:「那我倒要恭喜他了。」
長霄殿,香氣繚繞,緩歌慢舞,明眸皓齒的美人們穿梭在席間,慇勤把盞,笑語嫣然,真要讓人生生醉倒在溫柔鄉中。
年輕的天子摟著一名美豔舞姬,眉眼含笑地轉向沈英持,問:「沈愛卿不必拘禮,朕這後宮的傾城美人,比得上你藏在府中的心上人麼?」
鎮北將軍沈英持沉迷於一名男寵、不娶妻不納妾的事已是公開的秘密,無論是朝中大臣的竊竊私語還是民間的街談巷議,都當作一個絕大的笑話,朝中幾位大臣曾動過將女兒許配與他的念頭,卻被一一婉拒,皇帝賞他的美豔女子,都被沈英持的管家安排嫁人,聽說將軍府還貼了不少陪嫁,讓那位小氣的管家抱怨過不止一回。
朱錦恆雖然對朝臣的家務事沒什麼興趣,不過那位深居簡出、甚少露面的男寵倒讓他起了好奇心,召見了一回,倒覺得與他原本的想像出入甚大,那人面容俊美奪人,卻無媚氣,言談舉止流露出尊貴而內斂的氣度,沉穩淡然,寵辱不驚,讓一向苛刻的朱錦恆也挑不出毛病,態度自然溫和了些,結果還沒多說幾句話,沈英持那個小氣的傢伙就用活像要吃人的眼神瞪著自家主子,生怕心頭肉被人剜了去似地,讓九五之尊很不是滋味。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況那麼個丰神如玉的美男子,朱錦恆明白沈英持對夜弦忠貞不二的緣由,不禁又羨又妒,雖然身為皇帝,不好意思眼紅得太過明顯,暗中使幾個絆子倒是無傷大雅,所以他時不時借些名目賞賜美人給將軍府,沒事給他破破財也好--而那個吝嗇管家的抱怨聲只怕已經上達天聽了。
至於榮玉公主的事,雖然碰了個軟釘子,他也不打算鬆口,總之要讓他這位所向披靡的大將軍傷傷腦筋才成。
沈英持似笑非笑地掃了那群舞姬一眼,輕聲道:「芸芸眾生,臣只得一人足矣。」何況這個人還是他千辛萬苦才抓到手中,怎能不盡心珍惜?
「你聽見了麼?」朱錦恆與身邊的舞姬調笑道:「咱們鎮北將軍可是個百裡挑一的有情郎呢!」
「陛下過獎,臣不敢當。」沈英持四兩撥千斤地帶了過去--反正說來說去,這皇帝雖坐擁後宮佳麗三千,卻總覺得少一個,就是看不慣別人雙雙對對、只羨鴛鴦不羨仙罷了。
朱錦恆討了個沒趣,輕輕推開懷中美人,抿了口酒,又冒出一個戲弄人的餿主意,他笑得像隻狐狸,道:「愛卿既有意與你那心上人白頭偕老,不如由朕做主,賜你們結一對佳姻如何?」
沈英持後背的寒毛都立了起來,苦笑道:「皇恩浩蕩,臣感激不盡,卻是愧不敢當,惟恐污損陛下聖名。」
嘴上打著官腔,心裡已有藉機開溜之意,奈何皇帝目光如炬,早看出他的心思,適可而止地收起頑心,歡飲之後,賜了他一名黎國獻上的歌姬:瑞雪。
那名黎國美人確實色藝雙絕,姿容絕世,只是,沈英持已經開始頭痛了。
這個皇帝,就那麼想看他將軍府雞飛狗跳的樣子麼?
用過晚膳,夜弦下了樓,信步朝後園行去,寶珠挑著燈籠,像塊牛皮糖似地黏在他身旁,哄都哄不走。
「若不讓奴婢跟著,公子被鬼捉去了怎麼辦?」寶珠振振有詞,一臉誓死護主的堅決,夜弦差點從台階上栽下去,哭笑不得地看了她一眼,對這小丫頭徹底沒轍。
好在寶珠頗為知情識趣,覺察到他心神不寧,一路上只是默默地跟著,連腳步都輕得像一隻貓。
一場秋雨過後,池塘中的荷花更顯頹敗,沒精打采地收斂了一身芳華,殘落的花瓣浮在水中,映著淒迷的月色,蒼白如紙,一顆顆飽滿的蓮蓬低垂著頭,蘊含著清甜而苦澀的果實。
秋意已濃,連夜晚的鳴蟲都噤了聲響,夜弦負著手立在池塘邊,神情若有所思,寶珠忍了又忍,實在壓不下心中的好奇,小心翼翼地問:「公子可是在煩惱榮玉公主的事?」
夜弦被一針戳中心事,臉上有些掛不住,欲蓋彌彰地清清嗓子,道:「煩惱有何用?庸人自擾罷了,畢竟君命難違,一張聖旨下來,他做他的駙馬,我……」
低淺的聲音戛然而止,夜弦皺起眉頭--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這話說起來容易,只是一個全然忘卻了前塵往事、生命中只剩下沈英持的人,縱然割捨得下那份眷戀,又怎知何去何從?
「若真有那麼一天,便是緣分盡了吧……」他低聲道,眉宇間似有些迷茫,寶珠心疼地看著他,道:「也未必一定要離開,聽說榮玉公主溫柔敦厚,或許……」
「寶珠。」夜弦打斷她,笑吟吟地看著她,道:「何至於如此委屈求全?我不甘心與人分享心愛之物,若不能獨占,讓位便是。」
寶珠咬了咬嘴唇,低下頭,聲如蚊吟地道:「將軍這些年,只有公子一個,連皇帝賜下的美人都沒有碰過……」
「我知道。」夜弦低歎道:「我又何嘗不是只有他一個?」
寶珠欲言又止,眨巴著大眼睛看他,她進將軍府已三年,從夜弦病中開始服侍,原本以為他像所有大戶人家豢養的男寵一般,恭孌柔順,只是主人洩慾的工具,可是時間久了,她發現沈英持對待夜弦像對待結髮的妻子般,忠貞不二,寵愛非常,而夜弦,也不似那些小官相公一樣嬌媚豔麗,他始終淡淡地,從容溫和的表相下帶著自然流露的尊貴與傲氣,甚至時而顯現出迫人的凌厲與冷銳,只有在面對將軍的時候,會有些情生意動的羞澀,使得平素總是優雅淡泊的神態,平添了幾分孩子氣的天真。
寶珠不禁有些心酸,恍惚中覺得夜弦像一隻被關在金絲雀籠中的鷹,在沈英持的愛情中斂去了一身的光華,甘願背著男寵之名,不離不棄地跟著他。
究竟是怎樣的濃情厚意才能如此?寶珠並不曉得他們之間的種種緣由,也沒有懷疑過將軍關於青梅竹馬互許終身的說辭,她只是單純地希望夜弦能恢復記憶,補上那一塊總是讓他迷惘不已的空缺。
也許等到憶起從前,他就能放下胸中芥蒂,與將軍長相廝守。
多愁善感的小丫頭陷入難以自拔的愁緒中,一張俏臉籠上淡淡的哀傷,夜弦綻開一個安撫的笑容,道:「我都不愁,妳愁什麼?回去吧,天色不早了。」
寶珠吸了吸鼻子,點點頭,挑著燈籠照路,夜弦轉過身,突然停下腳步,朗聲道:「什麼人?」
寶珠嚇了一跳,下意識地擋在夜弦身前,循著他的目光望去,發現重重樹影之下,果然立著一個模糊難辨的黑影,她瞪大了眼,叱道:「你是人是鬼?!出來!」
那個人遲疑了片刻,緩步走了過來,靜靜地站到他們身前,此時天上烏雲散盡,朗月當空,雪白的月光加上寶珠手中的燈籠,足以映得人眉目清楚。
寶珠看清了他的長相後,眼睛瞪得更大了,連夜弦都不由自主心生讚歎。
好漂亮的少年!絕美狷麗的面容猶如天上的明月般,奪人心神,每一分每一寸都完美無瑕,而他那雙水晶般漆黑的眸子,冷凝而尖銳地盯著夜弦,其中的敵意,連寶珠都覺察到了,她上前一步,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少年,見對方一身家僕打扮,便問道:「你是劉叔帶回來的?」管家前幾天似乎提過要買婢購僕的事,這個人面生得很,又不甚懂規矩的樣子,大概是新來的。
少年忿忿地瞪了她一眼,勉強點點頭,神情很是不甘,又惡狠狠地朝夜弦瞪過去,倔強驕傲的神態像一隻被侵犯了地盤的貓,夜弦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以前幹過掘人家祖墳的勾當,才惹得這孩子一臉恨意,而且,這神態,似曾相識,不知道為什麼,能感覺到敵意,他卻油然生出寵溺之感,或許是對方太過美麗的容貌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要珍惜吧,他放緩了語氣,柔聲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少年的聲音清冽乾脆,咄咄逼人,胸膛劇烈地起伏著,眼圈泛紅,一副氣惱交加的樣子,夜弦皺了皺眉,不明白自己哪裡惹到他了,寶珠像是看出些苗頭,怒斥道:「放肆!在主子面前也敢撒野?!」
少年的眼神霎時變得殺氣騰騰,深吸了幾口氣,又瞪了夜弦一眼,一言不發地轉身就跑。
「喂!」寶珠氣得冒煙,提起裙擺想要追上去,卻被夜弦制止:「別跟小孩子一般見識。」
「是。」寶珠悻悻地停下腳步,憂心忡忡地看著夜弦,沒敢把心中的猜測說出來。
橫逆而來,必有所恃,他敢對夜弦無禮,除了攀上將軍做靠山,還會有別的緣由麼?
而那人對夜弦的敵意,也讓她想當然地理解為--爭風吃醋。
只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她又陷入悲情洋溢的想像中,夜弦在她額頭上敲了敲,道:「回去了,妳不冷麼?」
夜越深,寒意越是沁骨,寶珠打了個哆嗦,乖乖地陪他回停弦樓。
明月逐人,脈脈無語,一路上,夜露沾履。
管家在門前迎沈英持下馬,聽說這回只賜了一個美人,吊在嗓子眼的一顆心終於落回原位,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以往每回賞賜都是十個八個,打發起來勞心費力又耗財,讓一向節儉的劉管家一想起來就肉痛。
這回賞下的美人也是千嬌百媚,劉全使了個眼色,讓小丫頭帶她去休息,原以為會像往常一樣,安排嫁人拉倒,可是沈英持一句話,讓他笑不出來了--
「她是黎國人。」
劉全在府中年月最深,察言觀色的本事也爐火純青,他略一躬身,問:「那依將軍的意思……做了?」最後兩個字壓得極低,同時做了個刀切的手勢。
「不,留著。」沈英持簡短地命令,「盯緊一些,看看他們想玩什麼把戲。」
「是。」劉全應了一聲,沈英持滿意地點頭,快步穿過中庭,停弦樓燈火未熄,夜弦在等他吧?沈英持心情好了些,連腳步也輕快了許多,帶著小別勝新婚的急切,管家識相地退下,決定明天再向主子報告新購進僕婢的事。
洗去一身的酒氣,沈英持神清氣爽地回了臥房,夜弦落下一枚白玉棋子,抬頭微笑道:「你回來了。」
沈英持在他身邊坐下,看棋盤上才落了三十幾子,若待他分出勝負,只怕會到東方破曉,良宵苦短,豈能虛度?他傾身攬住夜弦的腰,一隻不規矩的手探入衣襟,撫摸著那溫熱緊繃的軀體,夜弦癢得朝裡縮了縮,笑道:「你就不能等我破了這一局?」
「不能。」沈英持袍袖一甩,棋盤上縱橫交錯的棋子叮叮噹噹地落了一地,兩個糾纏不分的身影,順勢倒在矮榻上。
不見那鐵甲將軍夜渡關,不見那朝臣待漏五更寒,都是為功名辜負了鴛鴦枕,為富貴忘卻了豔陽天,沙場上幾番出生入死,終於回到他身邊,怎能不共赴巫山、細敘別情?
衣裳落了一地,喘息聲愈見濃郁低沉,片刻之後,夾雜了壓抑不住的呻吟,情到深處,雨密雲稠,他們狂亂地、毫無保留地分享著彼此的熱情,每一次深刻而徹底的結合,都帶來入骨的歡愉,恨不得就這麼融成一個人,生生世世再不受別離之苦。
翌日,風清雲淡,天晴日暖,直到沈英持早朝歸來,夜弦仍睡得人事不知。
素白的面容帶著顯而易見的憔悴,眼下泛起淡淡的黑暈,連他的手指碰觸都喚不醒對方,可見前一夜累得有多慘。
「真想把你嚼碎了吞下去……」沈英持笑得有幾分無奈,喃喃低語道:「這樣,你就再也不能離開我了。」
走廊上傳來的腳步聲喚回他的神志,寶珠輕敲了幾下房門,道:「將軍,劉管家正帶著昨天買的三男二女候在寧華廳給將軍請安。」
沈英持給床上沉睡的人掖了掖被角,起身開門,吩咐道:「妳守在這裡等他醒來,閒雜人等一概不許靠近。」
「奴婢知道。」寶珠偷看了面無表情的沈英持一眼,目送他離開,立即像一陣風似地掠進內室,急急地喚著夜弦:「公子、公子、醒一醒!」
夜弦好夢正酣,被晃得天搖地動,睜開酸澀的眼皮看了她一眼,有氣無力地靠回枕上,低哼道:「不要吵……」
「夜弦公子!」寶珠仍不死心,急叫道:「大事不好了!」
「怎麼了?」夜弦強撐著神志,呵欠連連地示意她繼續,寶珠咬了咬嘴唇,道:「今兒個早上我見著劉叔新買的僕婢了,沒有昨天晚上碰見的那個!」
五個人她都仔細看過了,只有一個身形相像,面容卻平凡得讓人懶得多加注目,與昨夜那驚鴻一瞥的狷麗容貌簡直是雲泥之別。
夜弦靜候了片刻,才反應過來她已經說完了,當下一頭栽倒在柔軟的錦被中,不耐煩地揮手道:「沒有便沒有,值得大驚小怪麼?」況且也不關他什麼事,何故一大早擾人清夢?
寶珠氣得直跺腳,抓住夜弦的肩膀猛搖,道:「劉叔說府裡沒有這樣的人,那他不是被藏起來了,就是我們撞見了鬼!」
夜弦被搖得瞌睡蟲跑了一大半,無可奈何地坐起身來,道:「妳怕將軍金屋藏嬌麼?不會,他若有了新人,不會瞞著我。」
那個人雖非君子,卻是心懷坦蕩之人,躲躲藏藏的事,他不屑做。
寶珠被他的篤定與信任鎮住了,怔怔地立在床邊,思忖著難不成真的撞見豔鬼?後花園的池塘曾經淹死過人麼?
夜弦被她這一番折騰,睡意全無,無奈地歎了口氣,起身漱洗更衣。
沈英持一心掛念著夜弦,漫不經心地掃了幾眼恭立在堂下的僕婢們,目光停在個頭最矮的一個人身上。
那是個身形瘦削的少年,面容蒼白平凡,眼圈卻通紅一片,腫得像核桃一樣,眼中密佈著血絲,一副可憐兮兮的樣子。
「這是怎麼回事?」他朝那個少年抬抬下巴,冷厲的目光凝在他臉上,少年連頭也不敢抬,哆哆嗦嗦地回答:「……想家……哭了一夜……」
劉全向前躬了躬身,解釋道:「他本是城北杜家少爺,叫杜月,杜老爺犯了案子,家破人散,不得已賣身為奴。」
「哦?」探詢的目光落在那人的手上,果然是細皮嫩肉,不見絲毫做過粗活的痕跡,沈英持端起茶盞,悠然拂去水上的熱氣,劉全小心翼翼地揣測著自家主子的心思,提議道:「我看他知書識禮,也算聰明,不如給夜弦少爺做個小廝也好。」
話音未落,少年愕然抬起頭來,紅腫的兔子眼閃過難以捉摸的神色,偷瞄了沈英持一眼,又怯怯地低下頭。
沈英持饒有興致地盯著他,緩聲道:「全打發到廚房去做粗使,夜弦身邊,我自有安排。」
再一次地,對方聽到夜弦二字時,眼底滑過轉瞬即逝的波動,沒有逃過他識人無數的凌厲目光。
這小鬼渾身上下都透著生嫩,也妄想在將軍府裡興風作浪麼?沈英持冷笑一聲,精緻的青瓷茶杯在他手中發出一聲脆響,化為齏粉。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夜斷弦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05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夜斷弦
三年前,他從一場大病中醒轉,
前塵往事俱已忘懷,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
幸好,有自小一起長大的沈英持伴在身邊。
沈英持對他獨寵珍愛,身為將軍卻從未娶妻納妾,
這份深情厚意令夜弦心動不已。
可那塊失去的記憶卻化為胸中的芥蒂,
夜裡不時出現的怪夢中,鐵馬金戈、縱橫沙場,
他策馬揚鞭闖入敵陣,
卻見那個揮戈相迎的男人那雙深邃的眸子熟悉得讓人心驚……
是誰擂起戰鼓,任遍地凍結的赤雪映紅了天邊的冷月?
又是為何,夢見你我對峙沙場、兵刃相見?
章節試閱
一、夜弦
立秋以來的第一場雨,在夜裡簌簌落下,涼意沁人,夜弦從紛亂的夢中驚醒,在五更的秋寒中竟滲了一身細汗,再無心安枕,乾脆披衣坐起,挑亮了燈盞,對著窗外深不見底的夜色發起呆來。
邊關的捷報傳來已有月餘,算算日子,再有三兩天,鎮北將軍沈英持該率大軍凱旋了,夜弦胸口一陣躁動不安,長長地吸了口涼潤的空氣,壓下心頭隱隱的雀躍。
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分別了半年,每天都在想他。
一顆心像水上的浮萍,漂移不定,乍喜乍憂,邊關的戰事時緩時急,京城中總能聽到他的消息,即使是深居簡出的夜弦,貼身丫頭寶珠也...
立秋以來的第一場雨,在夜裡簌簌落下,涼意沁人,夜弦從紛亂的夢中驚醒,在五更的秋寒中竟滲了一身細汗,再無心安枕,乾脆披衣坐起,挑亮了燈盞,對著窗外深不見底的夜色發起呆來。
邊關的捷報傳來已有月餘,算算日子,再有三兩天,鎮北將軍沈英持該率大軍凱旋了,夜弦胸口一陣躁動不安,長長地吸了口涼潤的空氣,壓下心頭隱隱的雀躍。
雁門迢遞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分別了半年,每天都在想他。
一顆心像水上的浮萍,漂移不定,乍喜乍憂,邊關的戰事時緩時急,京城中總能聽到他的消息,即使是深居簡出的夜弦,貼身丫頭寶珠也...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羅蓮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11-18 ISBN/ISSN:978986206805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羅曼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