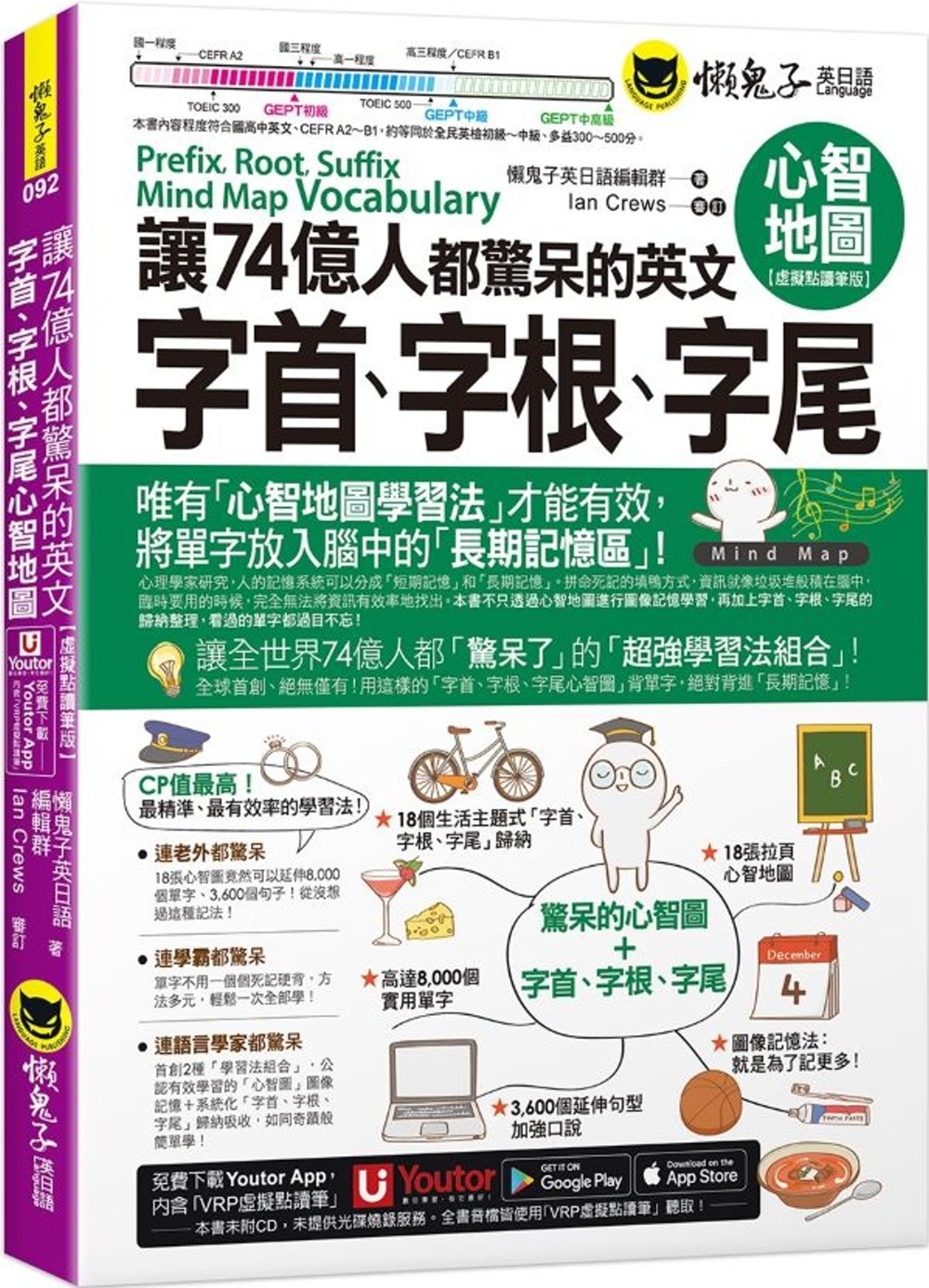序
我在心中放了一個盒子。
盒子中鎖住了一扇窗戶、一個陽台、一隻大白兔娃娃。
那天我轉過身沒有看著盒子只是拿了杯水,掉頭,看見了白兔娃娃站在陽台上對我笑著揮揮白色短短的手。
『掰掰,哥哥。』
白兔娃娃這樣說,然後跳下去。
窗外,只看見白兔娃娃摔在地上,全身扭曲變形,雪白的棉花像是雪般落下,紅紅大大的眼睛被撞飛了散落一旁再也變不回原本可愛的樣子。
於是我將心中的盒子鎖得緊緊,然後盒子外開始下雨。
那雨,從來不曾停止。
第一章
雨聲滴滴答答的落下,一點一滴的落在泥土、在柏油,畫出了好幾好幾大大的圓圈圈,像是那水灘頑皮的睜眨著眼,像是風般跳躍的步伐點過。
「各位同學,請將課本翻到下一頁……」
帶雨的天氣總是很令人煩躁的。
講台上的老師重複著每學期永遠說不完、相同的話,略略滯悶的空氣夾著多日的梅雨氣息讓人更是心煩氣躁。
席顃看著窗外,早就無心聽課。
這堂課的人並不多,嗯、換個方式來說吧,其實大學的課堂很少有滿堂的時候,尤其是如此枯燥乏味的國文課,蹺課的已經過了大半,剩下的另外一半又畫分為三分之一的人正在與周公下殺著不曉得第幾盤的棋局,三分之一正在做著自己的事情,最後的三分之一又有一半是在發呆;而真正聽課的,大概一隻手的手指可以數得出來。
講台上年邁的老師早就習慣對此視而不見,仍然努力的授著那浩瀚千年的中國文學,堅持著他聽者得之的信念。
他轉著手上剛剛買來替用的藍筆,無趣的在一旁的便條紙上畫下一個又一個圈。
圓圈上加了眼睛和耳朵,立即變成軟軟的小兔子。
雨還在下。
席顃,二十歲,今年大二,就讀整體造形設計學系。性別是男,若是看見這名字還要問上是不是女生也就太多餘。他上面還有個兄長叫做席颯,大了他七歲,是做廚師的、目前與朋友合夥開業中;一個姊姊叫做席柔,大了四歲,職業是美容師,同樣與好友併資開了一間小館一半做美容一半從事服裝展示販賣。
席家並非全部住在一起,求學的求學、工作的工作,包括父母在內的一個家五個人,通通住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每到假日的時候,若是恰好所有人都排到休假了、求學的想回家了,才會極度難得的碰在一起,但是並不將席家父親算在內。
他們並不希望那個稱為父親的人回到那裡。
不曉得是多久之前,就開始如此。
當席家還有六個人的時候,他們很少想過各居異地是怎樣的滋味,就算是受盡了痛苦也要兄弟姊妹們同聚在一起。現在,卻好像是呼吸空氣般再正常不過。
席顃還有一個小妹,叫做席堄。
但是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經不在了。
大約是席顃高二要升高三那年,十三歲的小妹與父親發生了一次口角之後,跳樓自殺了。他是第一次如此痛恨父親,也痛恨自己。那天小妹哭得很厲害,抱著自己送給她的生日禮物、一只白色的大兔寶寶,哭了很久很久。
他只是離開一下下,要拿水給小妹,只不過十多秒的時間,他轉過頭,來不及抓住那抱著兔娃娃往窗外一跳的小小身影。
他來不及抓住。
猶記得小妹最怕的就是痛,就連小小的傷痕都會痛得大哭。但是那一天,小妹卻是從十五層樓上跳下。沒有人能揣測她的心情是多麼複雜,那巨響傳來就像喪鍾敲起,接著是模糊難辨的叫聲從樓下遠遠傳來,幾乎是不真實的聲音。
長輩的重男輕女觀念一直很嚴重,就連大姐小時候都被修整得很慘,而兩個男生卻是稍微好了一些,雖然仍是會捱打,但機率比起女孩少了許多許多。小妹出生之後也是相同狀況,而他獨獨就與小妹感情最好。
若不是在收拾小妹遺物看見日記之後,他大概永遠都不曉得為什麼小妹會跳下那高樓,為什麼父親會這樣痛恨小妹。
那個人有外遇,曾經把女人帶回家上過床,而那天小妹剛好生病提早回家,就這樣撞見了原本不應該是她撞見的事物。從那天開始,父親更是視她如眼中釘般狠狠逼迫。
席堄死後,父母幾乎不過問喪事,是由當年已經成年且工作的大姐和大哥兩人一手包辦。
那段期間他只見過午夜中母親偷偷掉淚。
隔年,他就考上了外地大學,離開了那高高的大廈。
不知道是不是存心或者是無意,就在他離開之後大哥大姐也紛紛的移住外地,連母親都有工作為由在外面租了屋,長期不歸。
那個地方已經不是家,只是個建築。
空盪盪冰冷冷的建築物,無人願意踏入。
白色的兔娃娃他帶走,就放在租屋當中,兔娃娃因為衝撞力的關係早就已經變形,紅紅的眼睛原本是漂亮的玻璃珠,後來撞碎了他還買了新的替換縫上,白色軟軟的毛皮還沾了血印,至今已經泛黑。
如同現在煩滯的空氣當中,思緒就會帶著他回到當天跑下樓、親眼看見小妹慘死的那幕。
像是一種詛咒般繚繞不去。
轉著筆,他有點煩躁的咬了下唇。
昨天放假時候才去墓園走過一圈,看看那碑上仍然笑得天真無邪的相片。原來慣用的筆大概就是那個時候掉了,害他今早怎樣都找不到,只好匆匆忙忙的就近書局買了一枝不怎麼慣用的牌子。
天知道那枝筆是很久以前大哥送的,自己也習慣手感了,現在商品流通替換太快的市面上也很難找到這種款式。
想想等會兒下課之後一定要找個時間去大點的書局找看看平常慣用的那個罕見牌子,或是問問能不能替他進貨。
就在下課前幾分鐘,一根手指從旁邊的桌子無聲無息的爬來,在他桌面上輕輕敲響了兩個小小的聲音。
轉過頭去,正好碰上一張擠眉弄眼的臉。
「又作白日夢?」那臉的主人湊過來,很小聲的問著。
席顃伸出手,直接一巴把他的大頭推回原位。
大頭的主人叫做舒蜻,和席顃是完全相反的兩種個性。要說席顃是不多話冷漠的人,舒蜻大概就是傳說中的運動兼陽光少年,這人的活躍度大概在系上是一等一的,就連各系的老師也都很看好他。
舒蜻與他認識很久,久得可以算是孽緣了。
兩人認識的時候很奧妙,也可以說是詭異至極的。
時間可以追溯到三年前。
就在兩人都還是高中的那一年。
那年,兩校不同住的區域也是大大不同的兩人照理來說應該不會有任何交集的。不過,事情就是這樣照著時間安排所進行。
當天席堄跳下去之後,第一個目擊完整事件的的不是別人,就是正好要去找同學問功課而碰巧路過的舒蜻;而且還要是那小女孩正好就在他三步遠的地方摔得支離破碎、像是蛋殼娃娃被拋下一般散亂。
到處都是血,還有肉塊濺在他身上。
當場舒蜻真的是差點被嚇得差點連屎尿都拉出來,而這種狀況下,他竟然還可以安慰隨後跑下來一臉慘白像是要死的席顃要節哀順變。
連自己都有點佩服自己了。
不過猶記當時席顃的反應是不分青紅皂白就給他一拳,打得他這無辜兼路人幼小心靈被巨大創傷的受害者眼冒金星,帥臉被打得像熊貓一樣兩輪黑黑,還整整被班上同學笑了半個月之久。
會知曉席家是後來舒蜻多事的四處亂打聽,甚至還收買了席顃那校的奸細到處詢問,才了解了席顃家中情形,然後就這樣死皮賴臉的巴上那年心情最低落的席顃。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只記得那天眼前的不但有可怕的屍體,還有一張極度慘白、像是隨時會昏厥,可是又勉強自己撐下去的面孔。
舒蜻的家世很好,雖是單親家庭不過家庭和樂溫暖,是人人羨慕的那種好模範。
他是第一次看見那麼可怕的慘白。
可他也不知道該幫那個陌生人做些什麼,就是慢慢的靠近他,試圖認識他多一點。
不知道多久之後,兩人就這樣變成了朋友,最後還考上了同一大學、同一科系,就連租屋都是合租。
舒蜻很了解他,就連他發呆時會不由自主的想起那日的畫面這事都知曉。
然後,他總會在注意到的時候如同現在,毫不客氣的打斷他創造出來的悽涼氣氛。
「我餓了。」那很陽光的面孔委屈的說著,然後席顃才想起來這傢伙因為今天早上睡過頭,第一節課還遲到半小時才匆匆忙忙衝進教室,大概連早餐都沒有吃。
看了手錶,已經十點多。
下堂是空堂,直到下午第三堂兩人才有設計類科的課。
正想轉頭問問等等去餐廳吃東西時候,席顃著實愣了一下,那個把頭縮回去的人竟然無視於老師講課,大方的抽開了一包巧克力還開始招呼左鄰右舍共用。
如果因為一包巧克力讓這傢伙的國文被老師當掉,他可不管。
很明顯注意到如此光明正大的舉動,國文老師警告性的咳了幾聲,然後就是講課到一段落提早十來分鐘下課。
幾乎是同一秒,那個本來還在發送巧克力的傢伙以光速的動作將滿桌子散得亂七八糟的課本和文具收拾乾淨,然後整個人就跳起來,「顃顃,去吃飯!」他咧了嘴笑,也不管席顃意願怎樣,一把將他桌上的東西全抄了丟進自己的背包,然後拖了人就往外衝。
這畫面太常見了,整班的人幾乎見怪不怪,收拾了東西然後也各自散去了。
雨還在下。
梅雨季節都是這樣折騰。
***
十點四十分。
學生餐廳的人潮並不多,但是為了因應等會兒中午的爆滿餓死鬼學生,各食攤早就已經開始準備,四處都傳出熱騰騰的白霧以及香氣,鐵盤上也早已開始堆積滿滿的東西。
懸掛在天花板的電視播放著時下最流行的卡通。
說實在話的,在充滿大學生的食堂裡面播卡通實在是很奇怪,多少應該播些學術性的節目還比較有大學的感覺,要不也要是些風景觀賞、新聞之類的。
卡通……他怎樣都看不習慣。
不過偏偏就是有舒蜻這種心態極度「反璞歸真」的人喜歡得要緊。
席顃看不懂,好幾隻色彩繽紛的外星球青蛙有什麼好看了,可是舒蜻就是喜歡得要死,手機、背包上面也串滿了迷你青蛙,有時候還會和班上的女生交換樣式。
有一次他甚至在洗衣機裡面驚悚的抽出一件印著青蛙的T恤,纏著自己原本應該是雪白、然後被廉價染料弄成蘋果綠的襯衫……那隻退色的青蛙也沒有多好,斑斑駁駁的顏色整個看起來像是某種從地府裡面爬出來的鬼青蛙。
後來那件襯衫又被他漂白回到原來該有的樣子,不過如果可以,他更樂意拿來勒死那個青蛙衣服的主人。
電視上的彩色青蛙正在發出極其詭異的共鳴,而旁邊原來正在咬著焗烤麵條的舒蜻居然無聊到一邊吃面一邊跟著學那個詭異的共鳴聲給他聽。
很吵。
「閉嘴!」這是目前他唯一想得到的兩個字。
席顃完全不排除自己如果再繼續聽青蛙共鳴雙聲道下去不會產生宰了第二隻、也就是眼前這隻的衝動。
如果他不認識舒蜻這人,接下來的舉動絕對是一拳揍得他發不出共鳴。
「這很好玩耶……」將麵條塞進嘴中,舒蜻一點也不受影響的發出最標準不過的聲音然後嚼著口中的麵,「我妹啊……現在也很喜歡綠色的那一隻……可是我比較喜歡紅的,因為紅色的很搞笑……」叉子比畫了半圈,最後插進一片鳳梨當中,然後戳起來。
「我全部不喜歡。」一句話打斷眼前傢伙想要找青蛙同好的妄想,席顃拿起桌上的拿鐵湊進鼻間嗅了嗅香氣。說實話,學生餐廳當中的咖啡實在是可以說差強人意,不是即溶就是隨便亂沖,連評分標準都搆不上邊,要不是沒有他想喝的東西,他也不會浪費這幾十元只嗅那差強人意的味道。
「我也不喜歡。」騰出來的塑膠叉子指指他手上的紙杯,然後正在嗅著暖熱咖啡香氣的人才想起來眼前的朋友有著對咖啡過敏的體質。
舒蜻碰到咖啡會瘋掉,可以想像一零一忠狗裡面那個永遠得不到狗皮大衣的女人發飆,大概就是那樣子。
不過瘋完之後會像洩了氣的球,只剩一層皮攤在角落,還打上層層黑影。
有時候,席顃會有難得的壞心,就拿咖啡整他。
不過不會是現在。
梅雨,讓人什麼勁都提不起來。
「沒人叫你喝。」席顃毫不客氣的拋去這樣一句話,眼睛掃過對面桌上的七百西西大塑膠杯,裡面裝著淡淡金黃色的蜜茶、還塞滿了一大堆冰塊。跟他共租房子的舒蜻很愛甜,尤其是蜂蜜這種東西,所以與他共用一個房子有很大的困擾,就是特別容易有蟻患。
那一大堆一大堆的蜂蜜只要處理不好,隨時都可以看見各種品種的螞蟻群大大方方出現在房子裡面逛大街。接著倒楣的就是席顃,因為他最痛恨的東西就叫螞蟻,每當螞蟻大軍出現的時候就是他的惡夢開始,然後整天房子都籠罩在濃濃的殺蟲劑味道的陰影下;此類相同的場景不斷重演再重演,也不知道幾百次了。
只要嗜蜂蜜狂還存在著,大概永遠沒有終止的一天……不,或許解決掉源頭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舒蜻聳聳肩,將盤子裡最後一個鳳梨片解決掉,終於心滿意足的舔舔唇露出大大笑容;像隻剛被餵飽的大貓慵慵懶懶的掛在椅子上。
「吃飽了?」看著自己桌面上的紙盤子,還兩片鬆餅,上面的楓糖和奶油塊幾乎完整無缺,其中一片只缺了邊邊一口。因為舒蜻說一個人狂吃沒人陪味道會失色,所以強迫他也點個什麼東西來吃,這下可好,剩的算是浪費了。
沒回話,貪心的眼睛正盯著他桌上幾乎沒動過的鬆餅。
正確說,是鬆餅上的楓糖。
席顃在心中歎了口氣,然後將盤子往前移了一點距離,「我吃不下。」他食慾一向不好,尤其是搬出來住之後更加明顯,有時候一天甚至就只吃一餐。
有時候食物也會讓他想到那天,支離破碎的東西和屍體。
所以他食慾一向不好。
「顃顃,你會營養不良喔。」看了看鬆餅,舒蜻一臉哀痛決絕的轉開臉,「我等你吃完。」等等沒課,說好要去體育館打球,呃、顃顃是在旁邊看書,體育館規定是不能帶東西進去吃,而他只要一打球沒兩三小時不會停手,肯定會打過中午,不趁現在先吃飽怎麼可以。
看著盤子裡面的兩片單薄鬆餅,席顃放下手上一口也沒喝過還裝得滿滿的紙杯,「……另一片給你。」他捲起咬過的那一片,送進口中。
很甜,甜得要像是血的味道。
他搞不懂他為什麼很喜歡甜味,太甜的味道會讓人精神失常。
舒蜻看了他好一下,確定他真的不想再吃之後才飛快的掃光盤子中的另外一片餅,「你很瘦了,不用學女生減肥,不然再瘦下去看起來會像健康中心裡面的那個骨頭人。」現在女孩都很流行把自己弄得像骨架人一樣,說真的走在路上還有點恐怖。咧了笑,他將滿桌殘藉收拾了一下,「席老大說有空要請我們吃飯,今天晚上去吧?」
挑起眉,席顃沒有多說什麼。
他口中的席老大就是他大哥、席颯,原本是在北部某個大飯店當中當大廚的。不過大概幾個月前他辭了工作,改在這邊的市中心一帶和幾個朋友共資開了一家略有獨特風味的餐館,聽說挺受一般女性的喜愛,還被很多部落客放在網路上介紹過,所以經營得還算不錯。
不過就他來看好像大半部分是衝著他哥的臉去捧場。
可席颯倒是不覺得有什麼,甚至還說他臉也算是店中的一大特色,沒幾間餐館比得上;能說真的是囂張至極了。
不過餐館的生意越來越好倒也是真的,比幾剛開始的幾隻小貓,現在要去可都得預約的了。
「好嗎?好嗎?」舒蜻把垃圾丟進回收櫃裡面,問著。
如果到餐館吃飯,席顃吃進去的東西就會變很多,因為席老大會強迫他每種菜色都要吃一定分量,不然不放人。
有空就可以去吃飯是席老大說的,不過正確翻譯是,有空要把他弟拎來店裡讓他監督吃飯,要不然席顃什麼時候會餓死都不曉得。
當然,這話絕對沒有讓本人知曉。
另外就是舒蜻也很喜歡餐館的菜色,超喜歡。
「隨便你。」他想,就算自己說不好,這傢伙總有千百理由要抓著他去,所以問句只是參考意見。
「耶!」
接著,收到同意的舒蜻咧了嘴,又發出與電視上面的七彩青蛙相像的詭異共鳴聲。
「你給我閉嘴!」不然今晚吃的絕對不會是什麼名菜,而是非常鄉土的東西,叫做田雞大雜燴,另外像是田雞湯、炒田雞也不錯。
外面的雨仍然在下,綿綿的像是絲綢一般,連景物都變得有些朦朧模糊,像是被潑了水的彩色畫一般。
「對了,顃顃。」抽起門外置放架上的雨傘,舒蜻霍然回過頭,差點讓走在後面的席顃一頭撞上,「你下次要去看妹妹的時候,記得找我一起去。」
那個墓園,其實有點遠。
遠的,一個人走會很孤單。
席顃看了他一眼,然後緩慢的、點點頭。
就在兩人一前一後張開大傘同時,走在前面的舒蜻又停了下來,這次是很明顯的愣著不走。隨後的人有了疑惑,快步的走來,看見了不遠處的影。
是個人。
站在綿綿細雨當中不曉得已經有多久,渾身都溼透,連衣服都已經透明。
是個男孩。
***
「小弟,你站這理會感冒的。」
先回過神的是舒蜻,他幾個大步跑過去然後將傘分給那個男孩。
男孩的年紀看起來應該是十二、三歲上下的樣子,不是該出現大學校園的那種年紀,更別說他們學校不是開放式,怎會闖進來這年紀的訪客?
抬頭看著略高他一些的舒蜻,男孩沒說話,然後又轉頭看著稍後一點的席顃。
他突然笑了。
被笑得很莫名其妙的兩人交換了一下視線。
「小弟,你是來找人嗎?」通常外客進校園大部分都是要找人,舒蜻直接問了最大的可能。果不其然的,男孩立即很用力的點了點頭。
賓果!
「找誰?」
略為思考了一下,男孩往前跑了幾步,然後站在席顃面前舉高了手,一個細長的小管子就躺在他的手心上。
仔細一看,那也根本不是什麼小管子,是一枝筆。席顃立即就認出來,這是昨天探墓之後弄丟的藍筆,因為筆管上面還有舒蜻惡作劇時候刮傷的痕跡。
男孩看著他,又是露出微微的笑容。
「你特別撿回來還我?」雖然覺得好像哪邊怪怪的,不過席顃也只能猜到這個可能性。然後,男孩笑著用力點了點頭。
他記得昨天探墓時候並沒有見過這個男孩,他怎麼知道筆是他的?
男孩看著他,大大的眼睛沒有同年紀孩子該有的單純,一潭如同深黑的水般湛出湖綠的顏色,像是歷經千百年的時間洗鍊般的睿智。
睿智?
席顃突然發現自己有一瞬間是呆愣著,沉浸在男孩那雙詭異的眼睛當中。
他搖搖頭,想甩去那種奇妙的感覺,回過神之後才發現舒蜻已經開始找男孩攀談,可是連續問了好幾個問句,男孩仍是一句話也不說。
雨仍然在飄,就連待在傘下的他都可以感覺到雨絲貼在肩上的冰涼。
舒蜻一把將男孩拉進傘中,然後回頭看著他,「顃顃,我們先回家,他再淋下去會感冒,先帶他回去換衣服。」他皺著眉發現,這小鬼身上根本已經沒一處乾淨了嘛,搞不好把他衣服全部脫下來擰一擰還可以擰出一個水桶的水。
籃球,不玩了。
沒有多說什麼,席顃點點頭,兩人立即改變了原本行進的方向,然後往停車的車篷走去。
就走到一半時候聽見舒蜻喊聲,然後意識到的時候那個男孩已經竄到自己的傘下,抬頭又是衝著他一笑。
很怪。
非常奇怪。
他相當不喜歡這種感覺,男孩的眼睛太利,利得像是可以看穿人心,怎樣都不自在。
打個比方,像是給頭小獸盯上的感覺。
「顃顃,雨變大了。」快速的腳步聲通過他的身邊,舒蜻幾步就跑進暫時可以遮雨的篷,然後拉出扣在衣上的鑰匙低身下去抽開自家摩托車的大鎖。
他們兩個買的都是重型機車,還是同款的,只是自己的是白色,席顃的火紅色,就像他的名字一樣、像一把火。
但是絕對不像車主本人的個性,只是個人對於顏色的喜好罷了。
同樣做了開鎖動作的席顃打開機車置物箱,這才發現雨衣只有一件。畢竟他從來沒用機車載過人,就連安全帽也只有一頂,怎麼載這個男孩?
舒蜻同樣發現了問題,不過很快就幫他解決了,「反正這個小弟長的就一小球,你讓他躲在雨衣裡面一下下,警察不會發現的啦。」而且下雨天耶,哪個警察這麼悠閒抓沒戴安全帽的,泡茶躲雨都來不及了說。
像是同意他話一般,男孩自動自發的坐上機車後座,又是衝著他直笑。
席顃沒轍了,只好甩開折緊的雨衣穿上,然後讓那個男孩躲進後面。
他突然覺得自己還真像那種媽媽載著小孩,後面鼓起一大球。
就在兩部摩托車同時發動的那秒,席顃愣住了。
冰冰涼涼的感覺貼在他的背脊上。
基於舒蜻經常有這類舉動,他可以百分之百的確定,後面的小鬼整個人貼在他身上。
「顃顃?」像平常一樣等他先出車篷的舒蜻發出一個問號。
「沒事。」招呼了一聲,席顃甩去背上詭異的感覺,然後油門一加,瞬間一白一紅的摩托車一前一後、宛若流星般直接衝入雨中。
| FindBook |
有 1 項符合
墓草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24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墓草
妹妹在他升高三那年自殺身亡。
死時還抱著自己送給她的大白兔布偶。
慣用的筆掉在墓園了。
席顃想著下課後要再去買一支,不料還沒去買,
就有人幫他把掉了的筆送回來了。
倪草──他是這麼自稱的,是一個在雨中等著還筆給自己的十二、三歲小男孩。
可就在他暫且先把小草帶回家後,小草卻變成大草──
他成了一個長相俊帥的年輕男子。
他說他是妹妹席堄墓上的草,是來給自己三個願望的,
要自己不再傷心,以還給墓園安寧。
這種事……未免太離奇了……
章節試閱
序
我在心中放了一個盒子。
盒子中鎖住了一扇窗戶、一個陽台、一隻大白兔娃娃。
那天我轉過身沒有看著盒子只是拿了杯水,掉頭,看見了白兔娃娃站在陽台上對我笑著揮揮白色短短的手。
『掰掰,哥哥。』
白兔娃娃這樣說,然後跳下去。
窗外,只看見白兔娃娃摔在地上,全身扭曲變形,雪白的棉花像是雪般落下,紅紅大大的眼睛被撞飛了散落一旁再也變不回原本可愛的樣子。
於是我將心中的盒子鎖得緊緊,然後盒子外開始下雨。
那雨,從來不曾停止。
第一章
雨聲滴滴答答的落下,一點一滴的落在泥土、在柏油,畫出了好幾好幾大大的圓圈圈,像是...
我在心中放了一個盒子。
盒子中鎖住了一扇窗戶、一個陽台、一隻大白兔娃娃。
那天我轉過身沒有看著盒子只是拿了杯水,掉頭,看見了白兔娃娃站在陽台上對我笑著揮揮白色短短的手。
『掰掰,哥哥。』
白兔娃娃這樣說,然後跳下去。
窗外,只看見白兔娃娃摔在地上,全身扭曲變形,雪白的棉花像是雪般落下,紅紅大大的眼睛被撞飛了散落一旁再也變不回原本可愛的樣子。
於是我將心中的盒子鎖得緊緊,然後盒子外開始下雨。
那雨,從來不曾停止。
第一章
雨聲滴滴答答的落下,一點一滴的落在泥土、在柏油,畫出了好幾好幾大大的圓圈圈,像是...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紅麟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2-08 ISBN/ISSN:9789862068960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漫畫/輕小說> 輕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