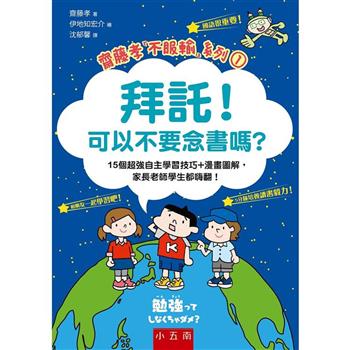宣懷風從小院裡,嗅著晨光中飄來的槐花清香,慢慢踱步出來。
走了一會,忽然醒悟過來的停下。
不由失笑。
真是,這陣子習慣了每天一起床就往白雪嵐房裡去了,可現在白雪嵐在自己房裡睡得正香,自己走這個方向幹什麼?
今天總署那邊文件還沒送過來,也不是處理公務的時間。
他便挑了水邊的間草石板路,一邊欣賞著清新的晨景,一邊往小飯廳去。到了廳前,忽然聽見張戎的聲音,遠遠的在後面打招呼,「宣副官,您起得早啊。」
宣懷風不由停下步,朝他點了點頭。
張戎轉眼就跟上來了,笑著問:「吃早飯呢?」
「嗯。」宣懷風問:「你也還沒吃?」
張戎呵呵一笑,「瞧您說的,我算哪根蔥,敢到這正經飯廳吃飯?就算吃了,那飯菜也要貼著脊梁骨下去。我是過來給那一位端早飯的,好歹過門也是客,總長沒空招呼,我們當下人的總不能沒空吧,您說是不是?」
宣懷風見他朝自己擠擠眼,就知道他在說誰了,有些驚訝地問:「他還沒走嗎?」
張戎說:「沒呢。在總長房裡坐了一個晚上了,我看總長沒發話,他也不敢就這麼不吭聲的走人,要是惹得總長心裡不痛快,他這碗飯以後也不用吃了。」
宣懷風心裡歉疚起來,忙說:「這樣讓人家一宿不睡的等著,實在不應該,我去看看他,請他先回吧。」
轉身踏下一步石階,忽然又覺得不妥。
白雲飛是個身分頗尷尬的人,白雪嵐把人家丟在房裡一晚不聞不問,現在自己一大早過去請人家出門,很有爭寵炫耀的嫌疑。
而且,白雲飛和奇駿也是很熟的,宣懷風想起日後白雲飛再遇見奇駿,不知怎麼說這回事,心裡倒有些微微心虛的忌憚。
宣懷風想了一會,又回頭把張戎叫住了,說:「勞你幫我走一趟。把早飯端給白老闆後,和他遞一聲對不住,就說昨晚總長遇到緊急公務要處理,冷待了他一夜。因為署裡事情還沒完,今天只能請他先回去,等總長把事情都處置好了,再親自過去謝罪。」
他說一句,張戎就應一聲。
宣懷風說完了,見張戎還站在不動,揚揚手說:「去吧,不要讓人家老等了。」
張戎便知道他是不懂這裡面門道的,臉上笑得有點曖昧,低聲說:「宣副官,該給人家多少,您總要說個數目,我才好和帳房領啊。」
宣懷風這才醒悟過來。
但他家從前,父親和手下那班軍官雖然也常叫堂子,卻大多是在外面的,很少叫到大宅子裡來,況且,就算叫到大宅子,宣懷風也不是負責給錢的那個,誰知道該給多少呢?
宣懷風便躊躇了,向張戎打聽,「一般該給多少呢?」
張戎說:「這就不清楚了,平時都是看總長的,總長說給多少,帳房就出多少鈔票。少的二、三十,多的一、兩百,有時候總長高興了,給四、五百也是有的。」
他算了一下,給宣懷風出主意道:「這一位到底是個名角,人家又在這過了夜的,給少了,讓別人說總長小家子氣。依我看,怎麼也要給個三、四百的。」
宣懷風無端端的,忽然有些不自在起來,搖了搖頭,「總長昨晚並不在那房裡,和他清清白白的,好端端給一筆大款子,反倒此地無銀三百兩了。對總長名聲不好,對白老闆名聲也不好。」
張戎用古怪的眼神往他瞅了一眼,壓低聲音,「您這話,嘿,真是,唱戲的還講什麼名聲?他又不是只到咱們這一個公館,其他人家的公館,難道他也是守空房?早就沒清白這回事了。這和逛窯子一個道理,不管床上有沒有成事,姑娘進房過了夜,都要算錢的。」
宣懷風雖然知道他說的是白雲飛,自己卻不知為什麼一陣難受。
忽然又想起「其他人家的公館」,林家公館必然也是其中之一了。
手指尖微微抽搐了一下。
他不想張戎這精得鬼似的聽差從自己臉上看出什麼來,便作出沉著淡定的表情,點頭說:「好,就按你說的辦,從帳房裡領五百塊給他吧。人家畢竟空等了一個晚上,說話要客氣尊敬。對了,叫一輛黃包車送他。」
把事情吩咐清楚,叫張戎去辦了,他才進小客廳。
腰腿都還在隱隱約約的難受,尤其坐在涼涼的木椅上,那個羞人的地方受一點擠壓,就感覺怪怪的,讓人一點胃口也生不出來。
宣懷風勉強喝了半碗粳米粥,就起身走了。
到書房走了一圈,打個電話到總署問了一下,估計今天沒什麼重要公務。
他最近身子空閒,昨晚忽然縱容了白雪嵐一夜,不知道是不是身體無法適應,那個難以啟齒的地方總是梗著什麼似的。
不想坐著,站著卻又更不舒服,竟是坐立不安。
便去到後花園的大花圃,享受著初升的半暖太陽,徐徐踱步,看了好一會花。
琢磨時間差不多了,才慢慢往房裡走。
回了房,走到床前一看,白雪嵐居然還大模大樣地睡著。他睡相真不怎麼好,人伏躺著,手臂裡緊緊把一個枕頭寶貝似的抱住了,被子也差點被踢到一邊,只剩一角虛虛蓋在腰腹處。
兩腿一點也不矜持地岔開,很頎長驕傲。
肩背則十之八九露在外頭。
宣懷風看著他薄薄肌膚下裹著的堅硬結實的肌肉,就不禁想起他昨晚那好像永遠也使不完的力氣,臉上微微一紅。
一樣是留洋回國的,也不知道白雪嵐在哪裡練出這一身勻稱結實的肌肉,難道他到法蘭西去學洋人拳擊了嗎?
也不應該。
洋人的拳擊手渾身肌肉糾結起團,一個個大野熊似的,倒不如白雪嵐這樣恰到好處的陽剛之美。
宣懷風一愕,忽然失笑。
自己怎麼評價起這個來了?
自嘲地搖搖頭,低下頭,伸手抓住被子一角,輕輕往上拉,讓被子把白雪嵐露出來的肩膀都蓋住了。
正要撤手,手腕上忽然一緊。
剛剛還一點聲息都沒有的白雪嵐猛地翻個身,用力一拉。
「啊!」
宣懷風就被站不穩地拉到了床上,跌在白雪嵐懷裡。
白雪嵐兩臂收緊,把他抱住了,意氣風發地笑,「這可逮著啦。一大早,不聲不響的到哪去了?」不等宣懷風說話,唇蹭到臉上嘴上,一氣地亂親亂吻。
第四十八章
白雪嵐兩臂收緊,把他抱住了,意氣風發地笑,「這可逮著啦。一大早,不聲不響的到哪去了?」不等宣懷風說話,唇蹭到臉上嘴上,一氣地亂親亂吻。
宣懷風對白雪嵐這種逾越的舉動,向來是不贊同的,下意識就扭著頭躲,可恨白雪嵐天生一股神力,兩臂雖然沒有勒緊,卻像個恰好的圓箍一樣圈著他,把他圈在懷裡。
越見宣懷風扭脖子轉臉,白雪嵐越新鮮起來,逗小貓似的瞇著眼笑,貼著下巴往頸窩裡親。
宣懷風脖子怕癢,被他一親,猛地縮緊身子,卻剛好牽到最不好受的那隱密地方,不禁「呀」了一聲,蹙起眉來。
索性就不動了。
白雪嵐怕起來,趕緊問:「怎麼?傷到你了嗎?」
一下子,連手帶嘴都老實了,坐起來一個勁打量他上上下下。
宣懷風翻過身,趁機下了床,忙離床走了兩、三步,才回頭去看白雪嵐,說:「大清早的,你就不能規矩點?」
白雪嵐聽他語氣,雖然冷冽,卻還不算太生氣,心裡鬆了一口氣,一邊下床,一邊說:「都這情形了,還立這些陳規矩,要憋死人嗎?」
大大方方把床邊疊好的衣服拿起來,看一眼,心領神會地瞅宣懷風一眼,「辛苦啦,本該我收拾的,倒勞動了你。」
正打算穿起來。
宣懷風始終不慣看他這樣裸著身子在面前晃來晃去,真是驚世駭俗得可以,趕緊別過臉,說:「到屏風後面去換。」
便聽見一聲戲謔的笑,鑽進耳裡。
但白雪嵐還是拿著衣服,到了屏風後面。
不一會,穿好了轉出來,笑言:「沾了你的味道,真好聞。」
舉起衣袖,自己先就嗅了兩三下。
宣懷風被他這些瘋魔舉動弄得臉紅耳赤,只好說:「你該吃早飯了,不然槍傷未好,又添個胃疼的毛病。」
白雪嵐問:「你吃了嗎?」
宣懷風點頭,想起來道:「對了,你的客人,我代你打發了。」
便把請白雲飛先回家,另附送五百塊錢的事大略說了說。
白雪嵐不太在意地聽了,閒閒說:「我昨晚是怠慢他了,虧著有你,比我想得周到,多謝。」
宣懷風也自覺這事做得不失體統,嘴上說:「不敢受你的謝,只要你別說我趕了你的貴客,我就安心了。」
白雪嵐笑起來,「怎麼會?天下只有你才是我的貴客呢。」
待要貼過來,宣懷風已經知機往房外逃了,去到門外,才回過頭來說:「你先吃早點吧,我打電話問過了,今天署裡事情不多,我喜歡早上這股子清清淡淡的風,先到後花園逛一圈,再去練一會槍。」
果然往後花園去了。
其實他不久前已經逛過一大圈,現在跑去後花園,只是因為在白雪嵐面前有些不可言的羞赧。
話既說出了口,只能裝模作樣地在水邊石徑上踱了一個來回,沒多久就膩了,身上原不舒適的地方,大概因為動彈過,漸漸也消了大半的辛楚。
於是就想起白雪嵐來。
自己不在房裡,白雪嵐多半不會在房裡吃早飯的,宣懷風便打算去小飯廳走走,不料半道上遇見一個聽差,一問,聽差說:「總長傳喚,早飯端去書房吃呢。」
宣懷風就折回來,也不經菱花門,另穿一條僻靜的花柳小徑,往書房方向走。
到了窗下,恍惚聽見白雪嵐的聲音。
宣懷風不禁站住了腳,仔細一聽,不是白雪嵐還有誰?正在書房裡不知對著誰吩咐,「……太少,再加兩千送過去。」
接著,又聽見管家的聲音了,說:「是,這就叫個聽差的把錢送白老闆家裡去。」
宣懷風一怔。
白雪嵐在房裡面爽快俐落地說:「不用別人,叫司機開轎車,你代我走一趟,也給白雲飛在家裡人面前長長底氣。」
宣懷風以為這話是對管家說的,不料倒聽見孫副官應了一聲:「好。」
這才知道竟是讓孫副官親去。
不一會,管家從書房裡面出來,看似去帳房取現鈔,宣懷風站在花蔭下,又是在另一側,管家絲毫也沒瞧見他。
宣懷風僵立了好一陣,心像被一股文火微灼著,既委屈,又感羞辱。
他竟不知白雲飛在那人心裡地位如此高的。
五百塊是嚴重委屈白雲飛了,枉自己還傻瓜似的出頭料理,白擔個越俎代庖、吝嗇小氣的罪名。
一時想著,手足都一陣冰涼。
又聽見管家走後,書房裡只剩了白雪嵐和孫副官兩人,白雪嵐輕描淡寫地問:「昨晚聽見了什麼沒有?」
孫副官很坦然地說:「是那槍聲嗎?怎麼會聽不見?幸虧我來得快,見有個護兵端著槍想踹門進去保護總長,趕緊制止了。再一聽裡面的動靜,果然是好好的氣氛。所以我就要他們安靜的都散了。」
白雪嵐笑了,「這好好的氣氛幾個字,真是用得極妙,虧你想得出來。」
宣懷風聽他這一笑,掌心便又更冷一層。
彷彿一把小刀子割著心。
想來在白雪嵐心裡,自己不過也就是優伶一類的角色,身價未必就比得過白雲飛了。
不然這種私密的事,怎麼拿來和別人談笑呢?
真是瞎了眼!
他越想越氣,心裡便想像著昨晚,本該如何斬釘截鐵的拒絕,又如何痛下狠手,一槍把這惡棍殺了,方不至於受這樣的玩弄侮辱。
一邊想,一邊沉著臉轉身,沿著長滿爬山虎的青溜溜的牆根往後走,也不回房,知道要出大門,沒有白雪嵐同意是一定會被攔住的,便索性去了後花園,往假山下面黑黝黝的石洞裡走。
到了盡頭,觸手都是帶著溼氣的石壁。
他也不管地上髒不髒,就背靠著石壁,坐在地上,默默的氣憤難過。
永遠待在這裡好了。
再也不想見白雪嵐。
第四十九章
白雪嵐因為孫副官要出門,順道交代他辦別的幾件事,孫副官答應著就走了。白雪嵐把手頭十來份不得不親自簽字的文件一一看過,批了回復。
歇了筆,想起宣懷風已逛了半日的園子,便到後面來找。不料找了一圈,壓根不見宣懷風的蹤影,問了路上撞見的幾個人,有說沒瞧見的,有說早上恍惚見過一下,後來卻不知道的。
到宣懷風房裡,也不見人影。
白雪嵐聽過宣懷風說今天要練槍,既然練槍,應該找自己拿子彈才對,不然就只有護兵領隊那邊有一些子彈,於是找了從東邊調來,新上任的護兵領隊宋壬過來問。
宋壬卻說:「總長,我和宣副官還沒說得上一個字的話呢。」
管家也過來報告,「飯廳、小書房、側廳都找過了,不見宣副官。也問了門房,都說沒見宣副官出門。」
見白雪嵐臉沉著,管家便試著寬慰,「總長,您放寬心,這麼一個大活人,公館裡總不會平白不見的。我看多半是宣副官好清靜,躲在我們一時想不到的地方清閒去了。等一會吃飯的時候,自然就會見著。人總不能不吃飯吧?」
白雪嵐理智上,何嘗不如此想。
但情感上,卻萬分的焦灼起來。
一時不知道宣懷風在哪,就無比的心慌難受,想得也多,一是自己得罪的人太多,雖然在公館裡,也保不定有仇家派進來的奸細,要是眼睛夠毒,瞧準了懷風是他的心肝,把懷風怎樣了,那真是比往自己身上捅一刀還厲害;二是懷風死心眼,心又太軟,從前和林奇駿那樣好得如膠似漆,如今跟了自己,心裡多少還有疙瘩,對林奇駿必然也有愧疚,如果林奇駿學自己這樣,來上一招苦肉計,或者擺出一張可憐的臉來,恐怕懷風又會動搖起來。
可不管怎樣,這麼多的護兵聽差待在公館裡,總不能懷風就能無聲無息離了公館。
如果在公館裡,怎麼又不見人呢?
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懷風耍性子,故意藏起來了。
可是,他為什麼耍性子?
白雪嵐半瞇著眼,坐在沙發裡,把指節扳得咯咯直響,怎麼也想不到自己又做了什麼惹懷風不滿,昨晚確實激烈了點,可能讓他不舒服了,但要發火早上碰面就該發了,怎麼等到現在鬧一齣失蹤記?
其他人,像他這麼心焦,多半已經在公館裡亂翻亂搜了。
但白雪嵐卻不。
他是善於分析和籌劃的,譬如獵人,要想捕捉極想到手的野豹,光性急不行,先看地形,再分析豹子的習慣脾性,甚至常走的路徑,愛捕食的地點,都齊備了,才能下個百發百中的圈套。
白雪嵐硬是牢牢坐定了,把今天的事情,從早上和宣懷風分開起,到此刻眼前,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腦子裡過了一遍。
心裡猛地動了一下。
趕緊把管家重叫回來,問他:「你剛才去帳房取錢,路上有碰到宣副官嗎?」
管家說:「沒有。」
白雪嵐說:「要不就是帳房先生口風不緊,把這事對誰說了,卻傳到他耳朵裡去了,或者門房看見孫副官備車到白雲飛家去,亂嚼舌頭。」
管家想了想,賠著笑說:「門房不敢擔保,但現在這兩個帳房先生,還是不大亂說話的,再說,宣副官很少到帳房那頭去。總長,依小的糊塗想法,未必就是白老闆的事,或者宣副官正在哪兒看花賞雀呢,公館園子大,房子多,保不定他在哪兒找到一本舊書,看得入迷了。」
白雪嵐心裡便有一絲苦澀的笑意泛起,歎著氣說:「你這樣想是好的,只是太不明白這個人了。真是要我的命。」
不然,就是懷風隔牆偷聽到了。
也不需要什麼證據。
反正他此刻,心裡已篤定宣懷風是知道了給白雲飛送錢的事,故此耍一番脾氣。
不必問,定是躲在一個安安靜靜的地方,想著怎麼和自己一刀兩斷了。
懷風就像他掌心裡一顆摩挲欣賞多年的心愛珠子,大小、形狀、重量,那對應著不同時辰發出的光芒,和貞潔無比,敏感易損的質地,都一清二楚。
原由一想清楚,白雪嵐也犯不著驚天動地的搜公館,自己站起來出了書房,慢慢地往後花園踱去。
他知道宣懷風生起這種感情上的氣憤,是誰也不想見的,待在房子裡總容易被找到,多半會選偌大的後花園藏身。
白雪嵐散步似的,著意挑偏僻的小徑,一邊走,一邊用犀利的眼神查看。
走了小半個時辰,又挑了一條小徑,一直前去,蔭影漸濃,把頭頂上正耀武揚威的太陽遮了大半,真是一條很不引人注意的幽徑;再往裡,才知道是直通到假山後面的,山石下鑿開一個黑陰陰的洞口,只容一個人進的大小。
白雪嵐也不知為何,直覺這就是宣懷風愛挑的地方。
他探身進去,摸著冰冷嶙峋的石壁,一步步往裡走,越走,越覺得潮溼難受,連空氣裡也一股病人似的冷味。
這如宣懷風目下的心境,又讓白雪嵐無端地冒出一股惱火,要耍脾氣,什麼辦法不能用,偏要挑這種傷身子的地方躲著藏著,是故意以此讓自己心疼嗎?
可惱的是,自己確實心疼了。
再一想,初時被關進公館,這人也是不問青紅皂白,首先就自己灌了自己一肚子煙土水,險些連小命也送了。
這樣不愛惜身體髮膚,真是太可恨了。
就只為了天上的宣司令宣夫人,也該好好教訓一番才是。
這樣一來,竟翻起舊恨,白雪嵐眸子裡那股光即刻就嚇人了,無聲無息地摸索進去,到了洞深處,若有所覺地驀然停下。
狹小的半封閉似的洞裡,有細細的呼吸存在。
白雪嵐站了一會,適應裡面的黑暗,慢慢看見一個身影坐在角落裡,背挨著牆,一隻胳膊靠著一個膝蓋般高的石墩,枕著頭,見有人進來,一點也沒動。
嘿,居然睡了。
一剎那,那心似惱似怨,似喜似嗔,彷彿原是繃直的利得能斷喉的弦,在空氣裡那麼淺淺的均勻的呼吸間,就化成了匪夷所思的繞指柔。
白雪嵐不自覺地屏了息,躡手躡腳走到那輪廓前,一點點把手挨過去。
心忖著,昨晚是把他累壞了,今天他又起得早,難怪睡過去。
指尖貼到軟膩肌膚,卻覺得有些燙。
白雪嵐抽了一口氣,輕輕搖他一搖,「快起來,要睡也不看看地方?」
宣懷風在他手底下略略動了動肩,嚶嗚一聲,也不知醒了沒有。白雪嵐急起來,把袖子往上一撩,打橫抱起他。
洞口本來就不大,白雪嵐身高肩寬,還抱著一個人,更不方便。唯恐宣懷風頭臉撞到看不見的凸出的石角,白雪嵐只能側著走,縮肚收腹,自己使勁貼著石壁移了十來步。
出了洞口,後背後肩一陣火辣辣的疼。
走到九曲橋邊,剛好,橋那邊跨上來一個人,正是也在四處找宣懷風的管家。
管家一看,放下心似的,小跑著過來問:「找著了嗎?真是大好事。」
但總長大白天抱著自家副官在花園裡走動,畢竟有些礙眼,當下人的又不太好提,只用眼睛瞅了瞅,沒吭聲。
白雪嵐說:「他在園子裡看風景,大概是累了,坐在冰石頭上睡著了。有點發燒,你快去打電話叫醫生來。」
管家趕緊就去辦了。
白雪嵐把宣懷風徑直抱回自己房裡,放在床上,坐著守了一會,醫生就來了,幫宣懷風略做檢查,抹著薄汗笑道:「貴管家催得我十萬火急來,還以為什麼大病。您放心,病人只是小發熱,打一針就無妨了。畢竟人年輕,底子足。」
給宣懷風打了一針。
白雪嵐對醫生輕描淡寫地說:「還有另一件小事,也勞你看看。」
把上衣褪了,讓醫生看肩背。
醫生嘖道:「恕我多嘴說一句,您真真是太體恤部下了,擦傷得這麼厲害,怎麼卻先人後己起來?雖然是皮外傷,如果感染了,也不是開玩笑的。」
重新把醫藥箱打開,拿酒精給破皮的地方消毒,再行上藥,見白雪嵐眉頭都不皺一下,完全沒事人似的,不禁崇拜讚歎,「總長,您真是硬氣人。」
白雪嵐覺得好笑,「這也叫硬氣?擦傷罷了,比得上槍傷嗎?那我也沒吭過聲呢。」
醫生更是大大拜服。
醫務事了,白雪嵐叫人送了醫生出去,又命聽差端了茶點到房裡,便信手從櫃子裡抽了一本《三言》,坐在椅子上,一邊喝茶,一邊悠閒自在地一頁頁翻。
翻到八十來頁,眼角忽地瞥見床上身影隱約動了動。
白雪嵐只當沒瞅見,仍舊品茶看書,就是坐定了寸步不離。
再翻了三十多頁,就看見宣懷風從床上坐起來了。
白雪嵐把書放下,笑著說:「你什麼時候醒了?好點沒有?」
宣懷風又黑又長的睫毛往下垂著,一個正眼也不看他,默默地下床彎腰穿鞋。
白雪嵐問:「剛才起來,又急著去哪?」
宣懷風本不打算和他說話,但回心一想,覺得這樣打冷戰,反而更顯得他們之間有些什麼似的,更是自討其辱。
最好的方法,莫過於從此以後公事公辦,當他副官時,只把他當上司看待,若日後有機會辭職,那是要頭也不回的走掉的。
聽見白雪嵐問,就臉上一絲表情也沒有地平靜回答:「過晌午了,下屬該去處理今天的公務。」
白雪嵐差點在肚子裡笑出來。
知他其實在吃白雲飛的醋,倒頗有幾分高興。
偏偏這白雪嵐很可惡,臉上裝作一點也不知情,也用一副公事公辦的做派,大剌剌地說:「那個不急。正好,我這裡有件要緊公務和你商量,坐下說話。」
宣懷風覺得他是騙人的,不肯坐,站著問:「什麼要緊公務?」
白雪嵐抬著頭看他,「最近城裡流行起海洛因來了,這東西你聽過嗎?」
宣懷風在英國讀書的時候,海洛因這種毒品是聽說過的,他有一個外國同學,原也是正派青年,竟被這害得極慘,當即肅然道:「什麼?城裡竟然有了這種害人的東西?海洛因比鴉片危害更大,這可不行,必須嚴查。」
一認真起來,戒備的心就疏了,就勢坐下來,問:「是從哪得到的消息?城裡的大煙館有膽子賣這個?」
白雪嵐說:「昨晚從白雲飛那弄來的消息。」
宣懷風怔了一下。
白雲飛和這人在房裡不風花雪月,竟是談公務去了,這是他想也不曾想過的。
聽這「白雲飛」三個字,畢竟有些刺心,宣懷風臉上默了默,說:「難道白雲飛有這方面的毛病?」
白雪嵐說:「他這人,黃連木擺設似的,外頭光鮮,其實裡頭有苦說不出。他家裡敗落後,帶著個妹妹隨著舅舅住,偏他舅舅、舅媽是一對大煙鬼,從前也是大戶人家,大手大腳慣了,又一頓少不了燒煙,日子過得很不成樣子。白雲飛每個月唱戲的包銀,倒是一大半都讓他們買煙土用了,剩下的幾個子,又要供著他妹妹吃飯讀書。所以他為著多點銀錢,或求一件新行頭,總要到別人家裡走動。」
宣懷風還是第一次聽白雲飛家裡的事,微微有些吃驚。
呆了一會,聲音便不像剛才那樣硬邦邦了,歎著說:「我倒從不知道。」
白雪嵐笑道:「你一不看戲,二不捧角,知道這些幹什麼?你道我怎麼和白雲飛談到了海洛因,就是因為他那不爭氣的舅舅,吃大煙還不管用,居然又栽在海洛因上了。這東西藥性要命,那錢也是要命的,為著買它,連白雲飛手上的金錶都剝了送當鋪裡去了。我看著他實在可憐可歎,今早起來想了想,就叫孫副官再送兩千塊錢過去。原打算等見到你就和你說的,不料等半天也不見你來。不過,我想你是不至於反對的。」
這一來,連消帶打,霎時把宣懷風心頭那股酸火吹得乾乾淨淨。
宣懷風便知自己錯疑了白雪嵐,十二分的羞愧,暗幸自己並未把這事當成開戰的藉口,否則一時氣憤衝口而出,那更尷尬了。微紅著臉反問:「我為什麼反對?又不是我的錢,你愛送別人兩千兩萬,儘管送去。」
白雪嵐趁機站起來,繞到他背後,兩手輕按在他肩上,說:「上次玉柳花來,你不是還勸誡我不要亂花錢嗎?怎麼現在我尊重你的意見,你又說這種反話來氣我?」
一邊說,一邊便低下頭,往宣懷風一邊臉上蹭。
宣懷風拿手擋著,那唇就落在手背上,熱熱癢癢的。
又不能縮手,如果縮手,白雪嵐就要親到臉上了,只好讓白雪嵐狼似的吻著自己的手背。
宣懷風忍耐了一會,決定把心裡另一條刺挑出來,正容道:「像我們之間的那些事,你都和什麼人胡說嗎?」
白雪嵐頓時知道,他這一通火氣,原來是在書房外偷聽出來的。
若是聽了外人嚼舌頭,知道給白雲飛錢的事也就算了,怎麼連他和孫副官幾句閒話都入心了呢?
不由暗罵自己粗心。
宣懷風臉皮既薄,心眼又死,以後再不能犯這樣言語上的錯誤。
白雪嵐忙認錯道:「這絕對是我的錯。我向你發誓,以後我們之間的那些事,若是我亂漏一個字給外人,叫我天打雷劈,五馬分屍。」
豎起兩根指頭。
宣懷風被他弄得哭笑不得,回過頭來,拍開他兩根指頭,繃著臉說:「你信洋人的教嗎?不必虛晃這無用的一槍。你既答應了不再和別人提,我就以觀後效吧。」
白雪嵐見他這樣輕輕放過,倒有些出人意料。
高興之餘,抱著宣懷風,在他臉上唇上硬是親了幾口,又要舌吻。
光天白日下,窗戶又開著,宣懷風實在吃不消,氣急敗壞地一把將他推開了,說:「這是什麼時候,你幹這種好事也不看看日頭。」
白雪嵐邪笑,「好罷。我忍到晚上,你可不能壞了我的好事。」
宣懷風哪裡肯接他這句不懷好意的話,顧左右而言他,「我本來說了今天還要練槍的,只不知道上哪去要些子彈?」
白雪嵐到底還是湊上來,啄木鳥似的親了一口,哂道:「子彈不過小意思,你要多少,只管開口。但只一樣,先陪我吃了飯再去。」
宣懷風一看牆上的掛鐘,已偏了午飯時間,腹中也是飢餓。
於是叫廚房準備飯菜上來。
兩人就坐在房裡,和和睦睦吃了一頓午飯。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金玉王朝第二部 礪金(上冊)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金玉王朝第二部 礪金(上冊)
歷經了好些事,海關總長白雪嵐,
總算心滿意足,抱得美人歸。
宣懷風的嘴上雖然不說,
可會為了白雲飛的事吃起飛醋,
會為了他受傷而軟下了心腸,
這世上,還有比這個更令總長大人心花怒放的嗎?
可亂世之中,雖得心意互通,
煩心之事卻接二連三地來。
金玉王朝第二部《礪金》,一場華麗的盛宴即將展開。
章節試閱
宣懷風從小院裡,嗅著晨光中飄來的槐花清香,慢慢踱步出來。
走了一會,忽然醒悟過來的停下。
不由失笑。
真是,這陣子習慣了每天一起床就往白雪嵐房裡去了,可現在白雪嵐在自己房裡睡得正香,自己走這個方向幹什麼?
今天總署那邊文件還沒送過來,也不是處理公務的時間。
他便挑了水邊的間草石板路,一邊欣賞著清新的晨景,一邊往小飯廳去。到了廳前,忽然聽見張戎的聲音,遠遠的在後面打招呼,「宣副官,您起得早啊。」
宣懷風不由停下步,朝他點了點頭。
張戎轉眼就跟上來了,笑著問:「吃早飯呢?」
「嗯。」宣懷風問:「你也還沒吃?...
走了一會,忽然醒悟過來的停下。
不由失笑。
真是,這陣子習慣了每天一起床就往白雪嵐房裡去了,可現在白雪嵐在自己房裡睡得正香,自己走這個方向幹什麼?
今天總署那邊文件還沒送過來,也不是處理公務的時間。
他便挑了水邊的間草石板路,一邊欣賞著清新的晨景,一邊往小飯廳去。到了廳前,忽然聽見張戎的聲音,遠遠的在後面打招呼,「宣副官,您起得早啊。」
宣懷風不由停下步,朝他點了點頭。
張戎轉眼就跟上來了,笑著問:「吃早飯呢?」
「嗯。」宣懷風問:「你也還沒吃?...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風弄
- 出版社: 威向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1-02-15 ISBN/ISSN:9789862069103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