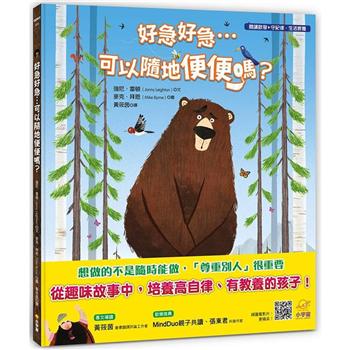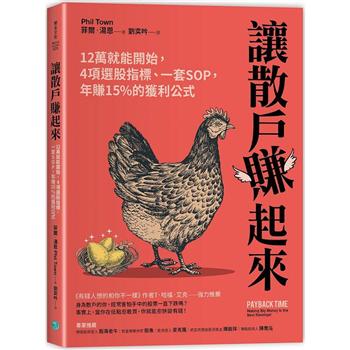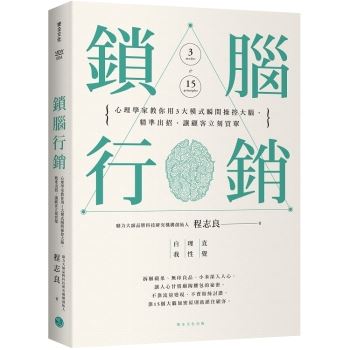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晝夜(上):肅殺心的圖書 |
 |
晝夜(上):肅殺心 作者:C.C.詹金斯 出版社: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08-10 語言:繁體中文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20 |
奇幻\科幻小說 |
電子書 |
$ 220 |
其他科幻/奇幻小說 |
$ 352 |
中文書 |
$ 352 |
科幻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晝夜(上):肅殺心
這是一部嚴肅科幻題材的故事。
在不遠的未來,名為「意念」的特殊力量與它們的使用者
-「主宰」,為人類社會帶來了衝擊與浩劫,徹底毀滅舊社會的戰爭亦因此而起。第四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名受困於殘存人類最後淨土-「樂園城」的主宰士兵伊凡.奧格列斯,在居民(同樣是受困此地的戰爭難民)受到樂園城政府「催眠意念」的大肆洗腦下,一面抵抗入夢後的戰地冤魂,一面與反政府組織-「鐵路局」共同密謀推翻政府,矢志給予戰爭難民自由與解放,並重拾人性尊嚴。
全文採用兩種不同的敘述人稱。在主角伊凡清醒的時刻,選擇以第一人稱的口吻來傳達出主觀且飽含情緒與角色心聲的描述方式,令讀者仿若身歷其境。至於主角在夢境中掙扎、回憶及尋真相時,則希望藉第三人稱的角度來突顯出一個渺小人類在浩大歷史事件中的卑微,以及夢境中那種感官與思緒不甚敏銳的狀態。
故事線會從主角在反政府組織中擔任戰鬥人員的日子開始。這段時間,他飽受惡夢所苦,卻又無能為力。某天,反政府組織中來了一名新人,是名為錫安的戰爭難民。在反政府組織領袖的安排下,伊凡成為了錫安的指導員,教導他成為一名「主宰」所需具備的能力與覺悟,以及反政府組織消滅獨裁政府的遠大目標。
主角個人方面,自密醫處所獲得的實驗型新藥終於讓他擺脫長期揮之不去的夢魘,同時卻也令他在夢境中遇到了死去多年的死黨與戰友。
一天夜裡,主角和錫安於大街上進行例行性巡邏時,卻遭受身為黑幫叛逃者的強大主宰偷襲,間接牽引出黑幫與政府之間的勾心鬥角,以及樂園城中正悄悄醞釀的陰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