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不了解愛,了解其他一切又有何用?
◎法國當代最犀利的小說家韋勒貝克新作震撼登台,渴望快樂卻不可得的你我,在此將找到答案
◎小說家陳雪、駱以軍、顏忠賢 同聲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序)
米榭是個對生命毫無期待的中年公務員,沒家人沒朋友沒戀情沒野心。
瓦蕾西是平凡善良的旅遊業工作者,嘗過同性戀異性戀,社會卻讓她漸漸對愛情冷感。
機運讓他們倆相遇在泰國旅遊途中,回國後譜出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深刻戀情。
在米榭的建議下瓦蕾西發展買春旅遊團行程,眼見事業成功在望,就在他們倆了解愛的那一刻,卻撞上了不可挽回的人生大轉折……世界又回復到偽善的祥和靜謐中……
《情色度假村》對買春旅遊的「提倡」以及對性愛大膽又精細的描繪讓人渾身發燙,但這本小說更令人內心顫動的是,它向我們述說一個美麗憂傷的愛情故事,讓我們跟隨主角去經歷愛情得與失之間的矛盾衝突,在在觸及現代社會最難以啟齒的傷口。
作者簡介:
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
1958年生於法屬留尼旺島,當今法國文壇最炙手可熱的作家,被譽為繼卡繆之後,唯一一個將法國文學重新放到世界地圖上的作家。他只要一出書,法國文壇就要鬧一場大地震;與兩次龔固爾獎擦身而過,引起極大爭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意識形態太不「正確」,不過他的書卻賣得像小麵包一樣好。法國《世界報》頭版頭條新聞除了魯西迪之外就只有他能刊上。
韋勒貝克善於捕捉當今最惹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如西方文明物欲橫流、沉溺於消費的空虛、愛情的失落、性慾的衝動、存在的苦悶、旅遊買春、戀童癖等等,並鉅細靡遺地描繪,筆觸赤裸,爆發力強,極具煽動性,呈現出當今社會的冷酷荒謬,一些評論家認為他比貝克特更為「黑色」。
延續《一座島嶼的可能性》與《無愛繁殖》對現代社會疏離感的深刻筆觸,新作《情色度假村》更直接地以旅遊買春這個活議題引起更多矚目。
作者網站 http://www.houellebecq.info/
譯者簡介:
嚴慧瑩,1967年生,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法國普羅旺斯大學當代法國文學博士,專門研究當代法國女作家瑪麗‧荷朵內的創作。目前定居巴黎,從事文學翻譯,譯有《六個非道德故事》、《緩慢》、《羅絲‧梅莉‧羅絲》、《永遠的山谷》、《沼澤邊的旅店》、《口信》、《終極美味》、《灰色的靈魂》、《落日的召喚》、《無愛繁殖》等書,並著作法國旅遊資訊相關叢書。
章節試閱
1
我父親死了一年了。我不相信唯有雙親過世我們才能真正變成成人這種理論,我們永遠不會真正變成成人。
在老傢伙的棺木前,一些不愉快的想法穿過我腦際:他這輩子過得很好嘛,這個老無賴,混得還挺不錯,活像個首領似的。「你還有了孩子……我的老王八蛋……」我不停地對自己說:「你把那根大雞巴插進我母親的陰道裡。」我當時情緒有點緊繃,那是一定的,又不是每天家裡都死人。我拒絕看屍體,我已經四十歲了,之前也看過屍體,現在寧可避免,這也是我不養寵物的原因。
我也沒結婚,曾經有過機會,好幾次,但每次都還是打消了念頭。我喜歡女人,維持單身有點是生命裡的缺憾。尤其度假時更增加困擾,到了某個年齡,獨自旅行度假的男人多多少少都被另眼相看:大家覺得他一定非常自私,可能還有點怪異,我認為這種想法並沒有錯。
葬禮之後,我回到父親生前最後幾年住的房子,一個星期以前,他的屍體在家裡被發現。家具上和每個房間角落都已經積了一點灰塵,一扇窗戶邊角還結了蜘蛛網,因此,時光啊、回歸啊諸如此類的東西慢慢地占據了這個地方。冰箱冷凍庫是空的,廚櫃裡最多的就是「健美牌」個人料理包、一盒盒加了香料口味的蛋白質替代品、增強體力的活力餅乾棒。我在一樓隨處走來走去,嘴裡嚼著一塊高鐵奶油餅乾,在熱水間裡踩室內腳踏車。我父親超過七十歲了,體力比我還好,每天做一小時的體操,每星期到游泳池游兩次泳,週末打網球,和差不多歲數的人一起騎腳踏車健身;葬禮上,我就遇到幾個他的腳踏車伴,「他永遠騎在我們所有人前面!……」其中一個婦產科醫生說:「他比我們長了十歲,一段持續兩公里的上坡,一分鐘之後就看不見他人影了。」「父親啊,父親,」我默默自語:「你的傲氣何其盛。」
在我視野最左邊,瞥見一個練肌肉的檯子和一些啞鈴,眼前立刻出現一個穿著短褲的笨蛋──若非臉上已皺紋叢生,便和我很相似的一張臉──絕望死命地練著胸肌。「父親啊,父親,」我默默自語:「你也只不過是建在沙上的一座城堡。」我繼續踩著踏板,但已經開始喘起來,大腿也有一點痠了,然而儀表上的段數還只在一而已。回想葬禮的情形,我知道自己給所有人留下一個絕佳的大致印象,我鬍子一向刮得乾乾淨淨,肩膀瘦削;三十多歲頭髮開始稀疏以來,我決定把頭髮剪得非常短;我通常穿著灰色西裝,打著不顯眼的領帶,而且我的神情不怎麼爽朗愉快。我一頭短髮、細邊眼鏡、一張陰鬱的臉,微低著頭傾聽一連串基督教聖歌,覺得怡然自得──譬如說比參加婚禮來得自在多了。說真的,葬禮還真適合我。我停止踩腳踏車,稍微咳嗽起來,夜色降臨在附近的大片草地上。在裝設熱水氣的水泥框架旁邊,可以看見一個沒清洗乾淨的棕色痕跡,我父親的屍體就是在這裡被發現,頭撞破了,穿著短褲和一件印著「I love New York」的T恤。根據法醫研判,發現的時候已經死了三天了,其實,在最極端的情形下,也可以歸結是一個意外,譬如說他剛好踩到一汪油不小心滑倒之類的,可是地上明明是乾的,完全沒油漬,而且頭部裂了好幾個地方,甚至還有一點腦漿濺到地面上,怎麼看都很明顯,應該是樁謀殺。瑟堡警署的修蒙警官晚上會來找我談。
走回客廳,我打開電視,是一台Sony八十二公分的大螢幕,內附環繞音響和DVD影碟機。第一台正在放映我最喜歡的連續影集之一,〈女戰士刄娜〉,兩個肌肉渾厚、穿著金屬胸罩和皮製迷你裙的女人正揮舞著大刀。「妳在位橫行太久了,塔干妲!」金頭髮的那個大聲說:「我是刄娜,西平原的女戰士!」有人敲門,我把電視聲音轉小。
外面已一片漆黑,風輕輕抖落樹枝上的水珠。一個大概二十五歲、北非人模樣的年輕女子站在門外。「我叫艾莎,」她說:「我每個禮拜來兩次,替雷諾先生打掃家裡,現在來拿一些留在這裡的私人物品。」
「喔……」我說:「喔……」做了一個想要表示歡迎的手勢,一個模糊的手勢。她走進來,眼睛很快瞄了一眼電視螢幕:現在兩個女戰士正在打肉搏戰,兩人身旁就是一座火山;我想這一幕對某些女同性戀或許是撩人刺激的吧。「我不想打擾你,」艾莎說:「五分鐘就好了。」
「妳並不會打擾我,」我說:「其實沒有任何事會打擾我。」她搖搖頭,好像懂了我的話,眼光在我臉上停留了一下,她一定是在觀察我和我父親的相似處吧,或許甚至在猜測我們內在性格相近之處。盯了幾秒鐘之後,她轉身走上通往樓上房間的樓梯。「妳慢慢來,」我低聲說:「隨便多久都可以……」她沒回答繼續往樓上走,也或許根本沒聽到我這句話。我坐回沙發上,因為這個會面覺得疲累已極;我應該問她要不要把大衣脫下的,通常人家一進門,都應該禮貌問一下對方,要不要把大衣脫下掛起來,想到這個,我突然意識到房間裡冷得要命──刺骨的溼冷,像墳墓裡的陰冷。我不知道怎樣打開暖氣,也不想嘗試,反正現在我父親死了,我應該速速離開這裡才對。我轉到第三台,剛好趕上〈誰來挑戰問題冠軍〉的最後一回合,這時候,來自瓦浮海城的娜蝶菊小姐正回答主持人朱利安•勒別,說她將繼續下一回合的挑戰,這時候艾莎走下樓梯,肩上背著一個旅行袋。我關掉電視,快速走向她,「我一直很崇拜朱利安•勒別,就算他並不特別熟識挑戰來賓來自的那個城市或小村,總是能對那個省份、那附近地區表示一點觀感,至少知道那一區的氣候、風景;最重要的是他了解生命:他把來參加節目的來賓當作人看,知道他們的悲喜、生活上的困難,來賓的所有人性層面他都知道,都感同身受,無論是從哪裡來的,他都有辦法和他聊從事的職業、家庭、熱愛的事,所有這些在他眼中組成一個人生的要素。我們經常看見某個來賓參加音樂號隊、唱詩班,積極參與當地節慶準備事宜,或是投身某個慈善活動;他們的孩子也經常會來到節目現場。反正通常看完節目,我們會覺得他們很幸福,自己也跟著快樂起來,妳不覺得嗎?」
她看著我,沒有微笑;她的頭髮攏到後面綁了個髻,化著淡妝,衣服樸素,看起來就是個正經女孩。她遲疑了幾秒鐘,才用因為害羞有點聽不清的聲音低聲說:「我相當喜歡你父親。」我找不出話回答,她這句話讓我覺得有點奇怪,不過也大有可能,老傢伙一定有一籮筐故事可說:他去哥倫比亞、肯亞,還有不知哪裡旅行過,曾經拿望遠鏡觀察過犀牛。每次我們見面,他都很克制地嘲笑我公務員的身分,說這個身分可以安定過一輩子,「你找到了個安穩的差事……」語氣中不掩蔑視;每個家庭都多少有些問題。「我念的是護理,」艾莎接著說:「但是離開父母家了,必須幫人打掃,賺錢過日子。」我打破頭想找出一句適當的話回答:或許可以問她瑟堡的房租貴不貴?但最後我只是發出了「噢,這樣啊……」,籠統代表我了解生命的意思。這個回答好像就夠了,她朝門邊走去。我貼著窗戶,看著她那輛福斯Polo在泥濘的小路上掉頭。第三台現在播放一部描述十九世紀鄉村生活的電視劇,薛基•卡攸演一個農場工人;兩堂鋼琴課之間,農場主人──強皮耶•馬西耶扮演──的千金和英俊的農場工人搞上了,他們翻雲覆雨的那幕在馬廄裡上演,正當薛基•卡攸猛力地扯下她薄紗內褲時,我沉沉睡去,朦朧中看到的最後一幕,就是鏡頭跳到一小群豬身上。
我被一陣痛楚,也或許是寒冷弄醒,一定是睡姿太糟糕,頸部的脊椎骨麻痺了,我站起身時猛烈咳嗽,吸進的是房間裡冷冽的空氣。很奇怪,電視螢幕上播放的是〈釣魚天地〉,第一台的常態性節目,想必我中間曾醒來過,或是至少有足夠的意識拿遙控器轉了台,但是完全不記得了。這個晚間節目今天的主題是「六鬚鯰」,一種沒有鱗的大型魚類,在全球暖化效應下逐漸出現在法國境內河川裡,尤其在核能電廠附近的水域。這個報導最主要想釐清一些謎團:沒錯,成熟期的魚身長可達三到四公尺,甚至在中部德龍省地區還發現過超過五公尺的,這一切都是可能的;然而,這種魚從未顯示肉食性的傾向,或是侵襲泳客的紀錄。一般對於六鬚鯰的疑慮其實大都來自釣客,因為在釣客的圈子裡,這一小群專釣六鬚鯰的人經常被當作另類,他們很不喜歡被另眼相看,想藉著節目澄清這個負面形象。當然,他們沒有老饕的理由:六鬚鯰的肉完全沒有食用價值,但是釣這種魚的技術很吸引人,兼具智慧與體能,和釣白斑狗魚的技術堪比,應該會吸引更多的愛好者。我在客廳裡走了幾步,身體卻沒有暖和起來,但是我無法忍受睡在父親床上這個想法,最後上樓找了幾個靠墊和幾床毛毯,勉強安頓在沙發上。〈解開六鬚鯰之謎〉節目一結束,我就關掉電視。夜深沉,寂靜也深沉。
2
什麼都有個盡頭,夜晚也是,我被修蒙警官清晰響亮的聲音從冬眠的蛇一般的昏睡中驚醒。他道歉說前晚抽不出時間過來,我問他要不要來杯咖啡,燒水的當兒,他坐在廚房桌子前,把手提電腦安置好,印表機接上,這樣他就可以在走之前讓我簽好筆錄,我咕噥著說這樣很好。檢警人員被太多行政雜務纏身,根本沒時間做他們真正的調查工作,這是我在好多雜誌上看到的,他聽我這麼說熱切地贊同。這次的調查筆錄順利開始,在彼此信賴的氣氛中進行,Windows發出快樂的一聲開機。
我父親死亡時間是十一月十四日晚間或夜裡,那天我在上班,次日十五號也在上班,當然我也可能開車來殺了父親之後,再連夜開回巴黎。十一月十四號那天晚上,我做了什麼呢?就我所知,什麼都沒做,沒有任何值得記錄下來的,反正我完全沒留下記憶,雖然才不到一個星期。我沒有固定的性伴侶,也沒有什麼貼心好友,在這種情況下,要怎麼記得呢?一天接著一天過去,如此而已。我歉然地看著修蒙警官,真想能幫得上忙,或者至少指出一個值得調查的方向。「我查一下行事曆,」我說,其實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會查到什麼;然而,很詭異,十四號那天那一格記著一個手機號碼,上面還寫著「蔻拉莉」這麼個名字。哪一個蔻拉莉呀?這本行事曆簡直亂七八糟。
「我滿腦袋大便……」我帶著歉意的微笑說:「真的記不清了,或許是去了一個開幕酒會吧。」
「開幕酒會?」他耐心等著,手指在電腦鍵盤上方幾公分。
「是,我在文化部工作,準備補助展覽、表演節目的財務資料。」
「表演節目?」
「表演節目……譬如說現代舞……」我覺得自己全然絕望,被恥辱完全淹沒。
「大體來說,是文化活動範疇的工作。」
「是,就是……可以這樣說。」他半帶親近半帶嚴肅地看著我。他意識到有文化活動這個範疇存在,雖然很模糊但是還是存在。他工作上一定遇到各式各樣的人,任何社會階層他應該都不會完全陌生。警界真是個人文組織。
接下來的對談進行得都還算正常,我曾經參與過電視社會劇的攝影,也知道對話應該就是如此這般:我知道父親有什麼死對頭嗎?沒有,不過也沒有什麼朋友,反正,我父親並沒有重要到會招惹上對頭的程度。他的死會讓誰得到好處呢?哦,就是我。你們上次會面是什麼時候呢?大概是八月吧,八月辦公室裡沒什麼重要的事,但是我的兩個同事為了小孩一定得去度假。我留在巴黎,玩玩電腦遊戲,十五號左右安排了一個週末連續假日,所以就來看看我父親。老實說,我和父親關係良好嗎?好也不好,應該算是比較不好,但是一年來看他一兩次,也算可以了。
他點點頭,我覺得筆錄應該快做完了,其實我希望還能多說點什麼,覺得對修蒙警官產生一種奇怪的、不尋常的好感。他已經準備列印了,「我父親勤作運動!」我突然衝口說出這句話,他抬起頭帶著詢問的眼光看我。「我不知道……」我絕望地攤開手:「我只是想說他生前勤作運動。」他以一個不耐的手勢按下印表機開始列印。
在筆錄上簽好名之後,我送修蒙警官到門口,對他說:「我知道自己是個令人失望的證人。」他回答:「所有的證人都是令人失望的……」我對他這句箴言思考了一段時間。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是一大片無邊際的單調農田。修蒙警官上了他的標緻305,他會告知我調查的進度。直系親人過世,公務員享有三天喪假,我大可慢慢晃,買買當地土產卡蒙貝爾乳酪,但是我立刻駛上高速公路返回巴黎。
最後一天假,我跑了好幾家旅行社,我很喜歡旅行社的型錄,很抽象,把世界各地簡化為一段可能的快樂時光和一個價碼;我最欣賞的是給星星的制度,以此估量可以預期的快樂程度。我不快樂,但是覺得快樂是一個重要的東西,也不停渴望它。根據馬歇爾的模式,消費者是一個有理性的個體,想以付出的金錢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相反的,范伯倫的模式是分析各個購買群對消費者的影響(個體對某個購買群的認同或反對)。科普蘭的模式呈現購買的過程會因產品/服務種類而不同(一般性消費、考慮後的消費、專業購買);至於布希亞-貝克 (1) 的模式則認為消費這個行為,就是在創造特徵。老實說,我個人比較近於馬歇爾的模式。
回去上班那天,我向瑪莉薔宣布我需要假期,瑪莉薔是我同事,我們一起準備展覽的資料、一起為當代文化盡力。她三十五歲,直直的金髮,眼睛淺藍,對她的私生活我一無所知;就層級來說,她的位置比我高一點點,但是她說得很清楚,她最注重的是我們單位的團隊工作。每次有重要人士來訪──藝術指導處的代表,或是文化部官員──她都特別強調團隊這個概念。「這就是我們單位最重要的一員!」她一踏進我的辦公室就這樣介紹:「就是他魔術般處理預算補助這些數字……沒有他,我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邊說她就邊笑,重要人士也跟著笑,或至少露出滿意的微笑,我也盡量勉力配合露出微笑。
我試著把自己想像成魔術師,但實際上我只需要做一些簡單的數字計算。雖然瑪莉薔看起來好像什麼事都不必做,其實她的工作很複雜:清楚知道所有的藝術走向、網絡、流行趨勢,身負推廣文化活動的責任,她一直害怕被批評不積極,甚至無知、狀況外;這是她必須提防的,也必須提防整個工作組織受到這樣的批評。因此她經常和藝術家們、藝廊、藝術雜誌主編們接觸,這些我都不懂;每當她和他們通了電話就雀躍不已,因為她是真的熱愛當代藝術,至於我,我對當代藝術不反感,不覺得這只是種工藝,也不呼籲回歸傳統繪畫,我只老老實實做我籌畫、會計的工作,美學的、決策的範疇都和我無關,我既不用創造,也不用適應新的潮流和世界新的關係;尤其當我背開始駝、臉上的表情逐漸悲傷以來。我參加過很多展覽、開幕酒會、難忘的表演。我的結論自此確定:藝術不能改變人生,至少,我的人生。
我告知瑪莉薔父親過世的消息,她表現出親切的善意,甚至還把一隻手放在我肩膀上,對我請假的要求覺得再自然不過。「你需要整理一下思緒,米榭,」她這麼認為:「好好回歸自己。」我想像一下她的建議,結論是她說的一定有道理。「塞西莉雅會把你開始做的這個預算計畫完成,」她繼續說:「我會交代她。」她在說什麼?哪一個塞西莉雅?我看了一下四周,瞄到一張計畫籌備時序表告示,現在想起來了。塞西莉雅是個紅頭髮的胖女孩,成天不停吃著吉百利巧克力,來單位兩個月了,可能是契約員工或是臨時雇員,一個不起眼的小員工。沒錯,父親死前我正在做一份「小子,投降!」展覽的預算表,這個展覽預定一月在皇后鎮揭幕,內容是警察在巴黎郊區對小流氓幫派的粗暴行為的多媒體影像,但這並不是一項紀錄工作,比較是把時事的場景舞台化,呼應洛杉磯警察的美國電視劇,藝術家採取的是一種玩笑的角度,而不是理所當然的揭發社會面的態度,滿有趣的一個計畫,成本不會太高,程序也不會太複雜,連像塞西莉雅這樣沒進入情況的人,都可以完成預算報告。
通常下了班之後,我會去看一場真人秀,票價五十法郎,有時拖太久射精的話要七十。看著陰穴在眼前舞動,讓我腦袋澄淨;當代藝術多媒體走向的矛盾衝突、維護傳統文化與支持新興創作之間的平衡……在平凡的陰穴舞動魔術下,這些全都迅速消失,我把器官裡積存的液體釋出。同時間裡,塞西莉雅可能正在文化部附近的糕餅店裡狂吞巧克力蛋糕,我們的動機其實差不多。
在特殊情況下,我會花五百法郎開房間,那通常是在我的陽具不太妙時,我覺得它成了一個無用而不聽話的多餘器官,聞起來臭得像乳酪,此時就需要一個女人把它握在手裡,假裝讚嘆它的雄偉、豐盛的儲存精液。不管是什麼情況,我七點半前就回到家,先看我用錄影機預錄的〈誰來挑戰問題冠軍〉,之後看國內新聞。狂牛症引不起我多大興趣,反正我幾乎只吃「慕絲林」牌的乳酪薯泥度日;之後夜晚繼續,我並不悲慘,擁有一百二十八個頻道,清晨兩點,我以一齣土耳其的音樂喜劇作為結束。
好幾天這樣度過,還算平靜,直到我接到修蒙警官的電話。調查進展很順利,他們找到了嫌犯,甚至不能說嫌犯,因為那傢伙已經認罪了,兩天後,他們將要做一次現場還原,我願意參加嗎?「喔,願意,」我說:「願意。」
瑪莉薔稱讚我這個決定很勇敢,談到了結前世、父子相傳的神祕之類的,這些都是應景的場面話,了無新意,不過這不是很重要,我感覺得到她對我存著溫情,雖然我有點吃驚,但很受用。跳上往瑟堡的火車時我在想,不管怎樣,女人們總是懷著溫情,甚至在職場也可能經營出同事感情,她們很難在完全去除情感的環境裡生存,在這種氣氛下,她們就無法發展自我。她們也苦惱自己這個弱點,《美麗佳人》〈心理學專欄〉就不停地告誡讀者們:最好把工作和感情劃分清楚;但是她們做不到,該雜誌〈讀者見證專欄〉也做出相同的結論。火車到盧昂附近時,我重新把事件發現的細節想了一遍。修蒙警官的重大發現,是艾莎和我父親有「親密關係」,多久一次?到什麼程度?他不知道,而且這一點跟他的調查沒有什麼關係,艾莎的一個兄弟很快就承認他來找老傢伙「要求一些解釋」,兩個人談得火氣愈來愈大,之後他留下死在暖氣爐房水泥地上的老傢伙。
(1)譯註:馬歇爾、范伯倫、科普蘭、布希亞-貝克,以上四位皆為社會學家與經濟學家。
1我父親死了一年了。我不相信唯有雙親過世我們才能真正變成成人這種理論,我們永遠不會真正變成成人。在老傢伙的棺木前,一些不愉快的想法穿過我腦際:他這輩子過得很好嘛,這個老無賴,混得還挺不錯,活像個首領似的。「你還有了孩子……我的老王八蛋……」我不停地對自己說:「你把那根大雞巴插進我母親的陰道裡。」我當時情緒有點緊繃,那是一定的,又不是每天家裡都死人。我拒絕看屍體,我已經四十歲了,之前也看過屍體,現在寧可避免,這也是我不養寵物的原因。我也沒結婚,曾經有過機會,好幾次,但每次都還是打消了念頭。我喜歡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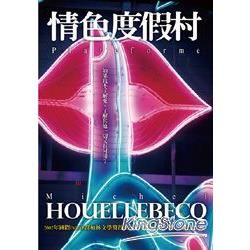
真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文詞來形容我看完這本書的感覺,會看這本書的主因有二:一是作者韋勒貝克,太多讀友同好向我推薦這位法國仁兄,花了兩天的時間後才發現真正受好評的是他另外兩本書:一座島嶼的可能性、無愛繁殖。 二是本書的書名,一般而言,台灣中譯本的書商會慣於竄改歐美書籍的書名,而歐美的版權授權者也不是很在意這種事情,這方面日本書就做的比較嚴格,日本書的中譯本書名,就絕對得按照日本字的字面去翻譯,好啦!講了一堆,就是要說我被本書的書名「情色渡假村」所吸引,而這本書的原文是(plateforme)好像與「情色渡假村」沒有關係。 書的內容果然如中譯本書名「情色渡假村」,描寫一位法國中年公務員,在面臨父親死亡與自己茫然的歲月,在一次跟團到泰國旅行(當然順便買春)的機會認識了一位在旅行社工作的女生,然後就像一般小說的情節,他們就交往了戀愛了,不過本書比較不同的是,他們之間的交往似乎是奠基在性交上,沒有寫錯,是性交不是性愛,所以我在閱\讀上似乎得到了一種看「A片」的過程。 女主角的旅行社正打算要開發海外買春的旅行團業務,於是就與男主角一同展開「色情考察」之旅,看起來似乎本書頗有看頭,只是,這本書的性愛橋段太多且太過於露骨,有點搶了整本書想要表達的東西(如果有的話!),況且閱\讀起來會被性愛撩撥到血氣方剛,反而無法平靜下來仔細咀嚼與思考韋勒貝克在書中的底蘊:虛無主義。 從父親的死亡開始,作者安排主角透過性愛的救贖,然而又用女主角的死亡來結束男主角的自我探索,法國人獨特的一些文思也許\對許\多人是種優雅的呢喃,只是書中的一些形而上的東西讓我覺得有閱\讀負擔,而跳躍式的論述也讓我無法轉換情緒思維,本書可以稱得上是「性交場面+高談闊論」的大雜燴,一下子從精液亂噴跳到法國公務體系的混亂,一下子又從4P雜交跳到歐洲人的自大與狂傲,一下子又從泰國浴跳到回教激進派 持平而論,本書的確有許\多很棒的觀點,譬如對生命的無味與熱情之間的矛盾,譬如藉由旅行去安頓身心靈的東西,如何與面對哀傷與死亡,如男主角Michel父親的死,導出了他對於生命的平淡態度。「為什麼,更廣泛地說,我生命中從沒對任何事情感受到真正的熱情呢?」這個疑惑確實也是多數人的困盾。從文中也可以窺得像法國這種已經高度開發的國家的一般市井小民的困境,主角就說拓過:「有些事情可以做得來,有些事則太過困難。漸漸的,所有事情都變得太過困難,這就是人生簡約的寫照。」這類的想法在日本德國的小說作品當中也經常可以嗅到。如果要以經濟的眼光來看的話,這或許\就是已經面臨成長極限的國家,他們普遍的無力感吧。 這種無力感好像也影響歐洲人的性生活,書中的主角必需到海外買春才能透過性而得到生活唯一的樂趣,主角在面臨人生所愛的兩個人的先後死亡之間,用追求性的愉悅來讓自己的生命與生存有「存在感」,作者想要表達存在主義的中心要素大概就是「性愛」吧,因為性愛而脫離無趣的人生,因為性的刺激短暫忘卻日漸衰老病苦的肉體。 如果說對本書的閱\讀有點失望,好像有點衛道人士的口吻,我只能說,這本書的性愛橋段會不斷干擾思考的冷靜,而失去了咀嚼其中品味的空間,說不定這的確是作者想要故意操弄讀者慾望的把戲吧!總之,這本書讀起來不是很愉悅就是,如果單身男子出國渡假或出差時,千萬別帶這本書,否則長夜漫漫所撩撥的慾火可不是好捱的。 看過以後才發現歐洲男人喜歡找東南亞女人作愛,而歐洲女人喜歡找非洲男人作愛,天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 ....不過我知道老虎喜歡找金髮妹就是....買春似乎有種文化與種族與階級的意識,如果哪天看到成千上萬的大陸男觀光客一車一車地到台中七期的酒店去買春,不知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