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雜誌》選為2009年十大小說之一,稱譽它表現出「本色的威力」。
「飢餓遊戲」系列小說首部曲《飢餓遊戲》美國版於2008年9月問世以來,暢銷年餘,始終無法退燒,迄2009年12月18日為止,已盤據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前五名66週;第二部曲《星火燎原》美國版於2009年9月出版後,與首部曲分佔紐約時報排行榜前二名已15週。
得獎記錄
《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
《美國今日報》排行榜第一名
《華爾街日報》排行榜第一名
《出版人週刊》排行榜第一名
《時代雜誌》2009年度十大小說
《紐約時報》書評編輯選書
《出版人週刊》年度最佳書籍
亞馬遜網路書店年度最佳書籍、編輯選書
《書單書》評年度編輯選書
《科克斯書評》年度最佳書籍
邦諾書店年度最佳書籍
餘燼悶燒,騷亂滋生,都城要報復。
燃燒的女孩飛矢點燃,
星火即將騰空……
在不可能獲勝的情勢中,凱妮絲從飢餓遊戲生還,與比德攜手返回家鄉。依照遊戲規則,往後的日子應該是安全、優裕的。但,他們的勝利是都城的羞辱,而謠傳騷亂已在十二區之間滋生,凱妮絲竟然是叛變的象徵人物。另一方面,狩獵夥伴蓋爾和競技夥伴比德,對凱妮絲的態度,只能是冰冷的深情。
令凱妮絲感到震驚的,是這場因她而起的動亂,她怕是無法熄滅的。當「勝利之旅」的日子來臨,凱妮絲和比德在監控下巡迴十二區,接受全民歡呼,攸關生死的賭注升高了。如果他們無法證明自己真的是在「無可救藥的熱戀」中,讓都城沒有絲毫疑慮,後果將不堪設想。
史諾總統居然親臨凱妮絲位於「勝利者之村」的新家,恐懼因此是具體的,凶兆成為事實。統治技巧展露無遺,恐慌蔓延全國。在殺戮中,凱妮絲必須宣布她和比德的婚約,那是都城多麼歡樂的一刻啊!偽裝的美麗與殘酷、隱藏的現實、施惠國的權力結構、人民的痛與反抗,都將在家鄉、都城和巡迴中的每一站呈現。
然而,最驚人的是第七十五屆飢餓遊戲適逢二十五年一次的「大旬祭」,都城將有令凱妮絲和全國人驚愕的安排。她終於知道,一切已經無可挽回,連妹妹小櫻和母親也無法顧及,她必須離去。至於蓋爾,她逐漸了解,他的意志原來這麼堅定,已經下定決心。這一次,唯有拼得一死,才可能挽救比德。她以為,這是她眼前唯一的目標……
既然僅存的希望已被否決,從此我可以不顧一切
第七十四屆飢餓遊戲已經結束。比德知道了真相,逐漸疏遠,凱妮絲終得放開握緊的手。
看來,只要都城的攝影機離開,一切就可以恢復正常:安全地生活下去,與蓋爾重返森林狩獵。
但什麼是真相?什麼是正常?真的安全嗎?
在至死方休的獵殺競技場上,一切彷如噩夢。友情與愛情,乃至於憐憫,其實也都像夢,虛幻不實。我們不知道什麼是真實的。
但是,回到第十二區的家鄉以後呢?凱妮絲終將明白,第十二區的生活,其實跟競技場中沒有多大區別。他們始終活在威脅之下,恐懼之中。
當抽籤抽到妹妹小櫻,凱妮絲取而代之,進入競技場,以為這就能保護妹妹。但這時,她終將了解,妹妹早已受到傷害。
她在競技場上奮力求生,但回到第十二區,她開始計畫逃亡。她終將了解,她在競技場上獲勝其實一點也不高尚,即便保住自己、家人和朋友的性命,是不夠的。
她終將知道,成為勝利者是不夠的,逃跑也是不夠的。她必須轉身面對。
作者簡介
蘇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暢銷系列小說「地底紀事」(Underland Chronicles)初試啼聲即備受讚譽。「飢餓遊戲」系列更成為突破性的作品,首部曲自2008年9月在美國出版以來,迄今暢銷,佳評如潮,始終無法退燒。目前與家人住在美國康乃迪克州。


 2011/02/20
2011/0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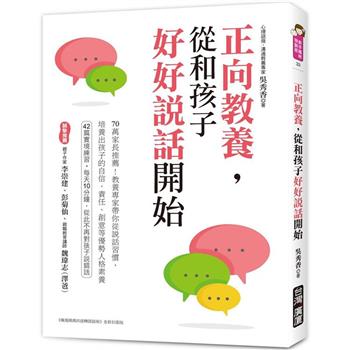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