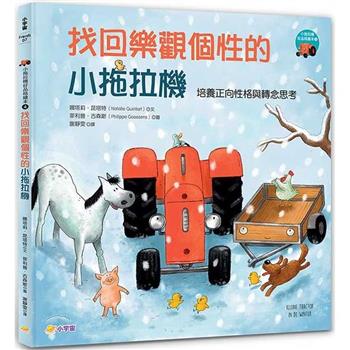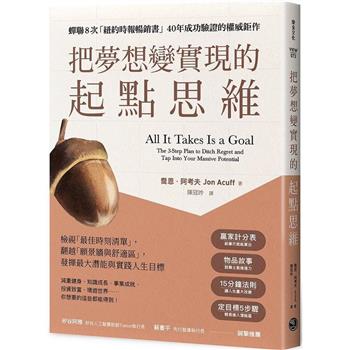即使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也無法改變過去我們跟他們的關係,但是我們可以自主地選擇和決定,要讓他們的哪些特質在我們身上體現出來。
失去父親或母親對所有為人子女者來說,都是一項事關重大的經歷。但父母的死亡對我們的深刻影響,過去幾乎完全被忽略;針對喪親之痛的相關研究,大多侷限於「哀悼」和「失落」,而未能從中發掘正向的力量和改變的契機。
本書作者珍‧賽佛博士(Jeanne Safer, Ph.D.)是資深心理治療師,在高齡母親過世後,發現自己和母親反而更加親近。她客觀地記錄母親的生命故事、深入分析母親的人格特質以及兩人的母女關係對自己造成的影響,並詳細審視母親傳承給她哪些心靈資產。她把這項體認和收穫稱為「死亡的益處」。
作者深入訪談了數十位失去父母的成年人,發現許多子女確實在父母死後得到正向的影響。當他們沒有了必須負責、可以求助或試圖反抗的對象,促使他們深入認識自己、作出改變。
中學教師貝絲.葛蘭特過去完全不須替自己安排時間,因為她得隨時待命、等候母親的召喚。母親病逝後,她卸下「母親隨身女侍」的職務,首度為自己規畫人生。
瑪姬.布朗在父親過世後引以為誡,成功戒菸,並發揮她和父親最相像的正面特質——強韌的個性和責任感——接下打理全家財務的重責。
咖啡店老闆娘潘妮.麥當諾為了和父親唱反調,在不幸福的婚姻中苦撐二十年。父親死後她才想通,過去把全副心思放在反駁父親,反而無法傾聽自己的心聲。
黛安.哥登身為專業主廚,卻從不敢在氣勢凌人、言語刻薄的母親面前做菜。母親過世後,黛安選擇讓母親強烈的保護與愛留在自己的記憶中。美好的記憶不僅可以支撐她,還能驅逐負面的回憶。
失去父母的子女,傷慟是發自內心的,但喪親可以化為主動而富有創造性的心理成長過程,而不只是被動承受的創傷。
不管我們與父母關係如何,失去父母都是重大的損失。然而,死亡帶來觀看全景的寬闊視角,讓我們對過往的思索有了新的深度。子女可以從父母傳承的心靈資產中揀選正面的部分,並釋放負面的部分。
逝去的父母,從現實世界移居到我們的內心世界,餘生仍與我們相隨。我們不但能修正與父母的對話,更可以彌補遺憾、向前邁進。
作者簡介:
珍‧賽佛博士(Jeanne Safer, Ph.D.)
從事心理治療三十五年,出版過三本著作。她常應邀上電視與廣播節目,也常公開演講。作品散見於《歐:歐普拉雜誌》、《模爾雜誌》、《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現居紐約市。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雙親的死亡,可能會成為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成長時機,我自己也有親身經驗。
《死亡的益處》值得我們欣賞和深思。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在生命裡,親情是最深的糾葛。《死亡的益處》讓我們清楚地看見:當父母逝去時,子女能夠找到什麼樣的力量。
——耕莘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 楊聰財
《死亡的益處》探索親子關係之中長久被忽視的層面,讓為人子女在父母過世以後,尋得新的自我。
——亞瑟‧卡力安卓博士(Dr. Arthur Caliandro),資深牧師
《死亡的益處》充滿絕妙的慈悲與直率──以及深度。
——美國詩人莫莉‧皮考克(Molly Peacock)
《死亡的益處》讓讀者在哀悼傷逝之外,也有成長的可能。
——《公報》(AARP Bulletin Today)
父母過世後,我對他們的愛比過去還要深,也更能理解他們曾經面對的挑戰。《死亡的益處》說的其實便是「活著的益處」;我推薦本書給所有成年人,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將經歷父母或親人的死亡。
——網友Michael Richards,美國洛杉磯
《死亡的益處》讓我不必為了在母親死後感到「解放」而愧疚,特別是兩人過去相處並不容易。說來奇怪,母親的死反而讓我們母女更親近,也讓我更了解她。
——網友Bhakti Mathurm,香港
失去父母,可能是子女人生的新起點。這是《死亡的益處》帶給我的收穫。
——網友雪凌,台灣
名人推薦:
雙親的死亡,可能會成為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成長時機,我自己也有親身經驗。
《死亡的益處》值得我們欣賞和深思。
——作家.精神科醫師 王浩威
在生命裡,親情是最深的糾葛。《死亡的益處》讓我們清楚地看見:當父母逝去時,子女能夠找到什麼樣的力量。
——耕莘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 楊聰財
《死亡的益處》探索親子關係之中長久被忽視的層面,讓為人子女在父母過世以後,尋得新的自我。
——亞瑟‧卡力安卓博士(Dr. Arthur Caliandro),資深牧師
《死亡的益處》充滿絕妙的慈悲與直率──以及深度。
——美國詩人莫莉‧皮...
章節試閱
1 母親的死使我成長
母親過世以後,我並不感到孤單。當我領悟到這一點,心裡既震驚又安慰。
她還在世時, 每當我身體不適或感到無助時,就會有某種絕望的恐懼撲襲而來,讓我急速墜入恐慌的深淵。母親過世後,這種容易陷入焦慮低潮的傾向漸漸消退。
要是她知道原因出在她身上,肯定會很傷心。但我很清楚知道,我不再被這種負面情緒所掌控,跟她的離世息息相關。
只有在死亡將我倆永遠分開之後,我才能用客觀與慈悲的眼光來重新看待母親:身為女兒、妻子、母親與女人的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從母親過往生命的片段,尋找母女關係的線索,準備探索自己最幽暗的內心深處。我在母親留下的物品中發現一副超大紅框、鏡片鬆脫的太陽眼鏡,我一把抓走。回到家的頭一件事,就是換上我自己的暗灰鏡片。我知道,這是以不同方式觀看的開端。
與其說我想念她,不如說我想念她存在世間的狀態。對她的欣賞與佩服,並不足以抵銷身為她女兒的難處。
承認這一點,是我探索母親個性的起點。我試著釐清她在我心裡激起的混亂又矛盾的情緒。要確切了解自己的母親,竟是如此艱難。你以為你們應該最了解彼此,以為兩人曾經共用同一軀體,理應擁有某種私密的相知相惜。事實上你們過於親近,充滿過多的需求與投射,反倒無法像陌生人一樣客觀理解她的本質。
下一步就是清點母親的人格,就像我盤點她的遺物一樣,決定要保留什麼、捨棄什麼,以及如何將挑選出來的跟我自己的心理家屋加以整合。
我把自己從母親那裡獲得的心理傳承分為四個類別:
1 我得到而珍視的;
2 我沒得到因而遺憾錯過的;
3 我得到而想捨棄的;
4 我所需要但她無力給予的。
頭兩種相當直接,第三種要下一番功夫才能勇敢面對,但並不難理解。第四種則是未知的領域,母親在世時我完全難以想像。
母親的死亡深具意義,讓我倆找到彼此。我才剛開始耕耘與採收死亡的益處。我打算繼續追求,並鼓勵別人也這麼做。
2 最後的禁忌
幾十年以前,步入中年的成人有父母在世是很不尋常的事。到了二十一世紀,大部分人在三十五到五十四歲之間喪父,而在四十五到六十四歲之間喪母。百分之五十的人到了五十四歲會失去雙親;百分之七十的人到六十二歲時成為孤兒。隨著我們年紀增長,父母也跟著凋零。這樣的時間架構對我們相當有利,不只是因為親子關係持續如此之久(比大多數婚姻長久許多),也因為我們失去父母的時候都已是成人,常常也已為人父母。我們漸漸有了同理的能力。
把喪親的意義淡化,會剝奪這件事的改造力量。很多人未能認識它的影響,也無法把失去父母這件事與生活的重大改變連結起來。有位五十歲的廣告業主管告訴我,她八十九歲的母親剛剛過世,教人感傷。她隨口提及,她近來發現自己平生第一次採買衣服。這位女性向來對時尚沒有太大興趣,也很少在自己身上花錢,卻突然開始往衣櫃裡增添時髦服飾。我問她,這個舉動與喪親有無關係時,她很驚愕地說她不曾這麼聯想過。她母親生前多年沒買過新衣。雖然母親的自我否決總是讓女兒困擾,女兒卻無意識地加以仿效,直到母親死後,才興高采烈地大肆採購。她在不明就裡的狀況下,為了自己人生的下個階段而裝扮自己。
原本讓父母無可取代的種種特質,卻只有在他們離世以後,才會成為讓我們藉以完全茁壯成熟的東西。當我們沒有必須負責、可以求助或試圖反抗的對象時,我們在世上的角色也會有所改變。我們成為最終的權威,也就是「大人」,權責在我們手中。不管我們與父母的關係疏遠或密切(或是混合兩者),他們的死亡讓我們頭一次真正處於單獨(以及真正負起全責)的狀態。
失去父母這件事所得到的關注遠比它應得的少,而失去父母的正面影響幾乎完全被忽略。父母的歿亡讓自己在心理上獲益,似乎否定了親情與忠誠,「那就像是在我母親墳上跳舞、慶祝她的死亡一樣。」有位病人對我說道。
若要與逝去父母維持成熟的牽繫,「抽離」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幫助我們找出去除干擾後的關係本質。我們所切斷的,並非與過世父母的親子關係,而是他們在世時我們嵌入親子關係的方式。這種新的立場讓我們得以重新詮釋過去,擴展我們對父母本身以及身處親子關係裡的自我的了解。抽離本身、抽離提供的視角以及抽離帶來的成長,就是死亡益處裡最棒的一種,而且是享有其他益處的先決條件。
3 翻看遺物,選擇傳承
雖然我們無法挑選父母,但是他們死後,他們哪些特徵可以在我們身上占有最大分量,卻是由我們決定。留心處理遺物,就是第一次可以做出這種選擇的機會。值得慶幸的是,在賣掉房子、檢視紀念物、保留珍貴物品、轉贈不想要的部分後,即使歷經多年,我們仍然能在內心重溫這個過程。
整理父母的遺物,決定保留或捨棄什麼,是我們在他們過世之後的頭幾項任務之一,也是接下來即將進行的心理工作的重要象徵。每個人都害怕這項繁重的任務,也不想去碰那些令人憂慮不安的事──觸動兒時回憶、自己終將一死的傷感、手足之間的競爭、與父母之間的未竟之事。
一個人如何挑選,透露出很多意含。有些人花上幾天精挑細選,試著在手足之間做出理性或至少公平的分配。有些人耗費好幾個月細心篩選每樣居家物品,什麼都捨不得丟,到最後只好將父母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胡亂拼湊在一起,而非融入自己的生活。
有太多人乾脆將物品推進永遠的心靈與實體儲藏室,從來不去面對父母留下的東西,也不肯處理自己的願望或感受。至於如何翻閱東西(起初是實體遺物,之後則是心理傳承),最有智慧、成果最佳的方式,就是好整以暇,但別耗費太多時間。嚴肅認真、有條有理、不時留意這項任務的宗旨,同時很清楚這項任務不大可能、也沒必要做得十全十美。
實物的盤點,是心理盤點的參考點。父母的遺物與童年的物品所喚起的經歷與回憶,可以引導你去了解父母的個性,以及父母個性對你所產生的影響。勸你先做好心理準備,因為心理盤點比實物盤點挑起的情緒更為激烈,也會產生更多衝突矛盾。
當你進行心理盤點時,要問的四個問題:
1 你從父母身上獲得的,想保留的有什麼?
2 你父母擁有,但你並未獲得、因而感到遺憾的是什麼?
3 你從父母身上獲得卻想摒棄的是什麼?
4 你曾經需要、但父母無法提供的是什麼?
貝絲‧葛蘭特作了一個充滿啟示的夢:
夢中我正在尋找放衣櫃的空間,卻在屋裡找到一個新的房間,裡面有好幾個裝滿父母衣物的行李箱。我使用這個房間以前,得先把這些箱子清掉──父母過世到現在都沒處理。這會是個大工程,可是這樣我就有空間放自己的東西。
在貝絲拋開父母的「行李」之前,不會有足夠的空間容納新近擴展的自我。年屆中年的她開始學習演戲,期待在舞台上追尋事業的第二春。現在時候到了,該要捨棄父母拘束又過時的衣物──也就是他們指定給她的角色,然後扮演自選的角色。那場夢說的是,她的工作很適合她、她能擁有屬於自己的房間作為獎賞。
挑選與拋棄舊物的儀式,不是一次就能宣告結束,也不會隨著資源回收車的到來而終止。那是終身計畫的第一部分:在父母死後,徹底了解他們並重新創造他們。死亡的益處就是由翻看東西開始。
4 開始好好過日子
母親過世以後,艾莉絲‧康納的憂鬱症狀跟著消失無蹤,令她喜不自勝。「我在戰戰兢兢中長大。她就像是病毒──她一踏入房間,你就會被感染。」自從母親過世後,艾莉絲的自責消失了。「她真的榨乾了我的精力──現在我有更多精力留給自己和這個世界。」
艾莉絲在母親死後,為何並未陷入低潮、無法原諒自己不曾療癒母親(或是無法原諒母親對她予取予求)?為什麼她不會認為自己非得陪伴母親一起陷在悲慘之中、藉以懲罰自己?她深信,即使母親從未直接說出口,還是希望女兒過得好。
「父母的死亡有益於你的健康」,這項宣告聽起來不僅有違常理,也教人驚駭。守喪者不是都該飽受折磨,傷慟不已,甚而無心進食或照顧自己,以至於形銷骨毀的嗎?旁人也會認定他們此時應該對外在事物失去興趣,並且會有好長一段時間疏於關照自己。那麼,為什麼有那麼多失去父母的人(他們絕大多數都為父母的過世真心感到傷痛)的模樣與感受卻前所未有地好──而且他們這麼說的時候,也並不感到愧疚?
當我訪查死亡的益處時,最常聽到的,就是子女會更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他們提到像是「我減肥成功嘍」、「我戒菸了」、「我加入健身房會員」、「我去看牙醫嘍」。他們感覺自己更有魅力:更亮麗、更優雅或更有男子氣概。而他們也的確表現出來了。我有位同事在性情嚴厲又過度儉省的母親過世六個月後,整個人時髦了起來。有位朋友在老看他不順眼的父親死後,身材很快變得苗條。即使是那些極為尊敬父母的人,在父母過世後,往往也會戒除壞習慣或養成新的好習慣。我在母親過世一年後,重新投入游泳,那時我只知道那是我認同母親的一種方式。
這種改變不只是打點門面而已,它們還反映出自我感覺以及與逝者關係的深沈情感轉變。模樣更好、感覺更佳,代表的是主掌情勢、茁壯成長、抬頭挺胸以及盡情生活。
芭芭拉‧金斯坦一輩子都為了體重而煩惱。有一部分是遺傳問題,另一部分是父母的問題。她二十多歲時曾經一度瘦下來,父母反倒不大自在。現年五十六歲的她回想,「有一次我跟父親出門,遇到他的一位客戶,對方以為我是父親的女友,後來父親就不再和我出門了。女兒和父母的互動關係總是很複雜──我不能太接近父親、不能讓自己在他面前看來太美,因為那會激怒我母親。」就因為她需要討父母歡心,所以對體重的自暴自棄,更勝於對玲瓏曲線的渴望。
父親在芭芭拉五十四歲時過世,在這之前,她的減肥計畫一直虎頭蛇尾。而今父親走了,計畫終於順利執行。芭芭拉的心態也不一樣了,現在她是為了自己而努力。「我再也不用應付那種三角關係了,」她說,「這次我持續不輟,每週運動三次。我再也不覺得自己像個歐巴桑。」
在需索不斷的父母過世後,減重成了女人表達內心泰然自若的典型方式之一。
5 以新的眼光看待父母
我在上紐約州的房子旁邊有片樹林,三年前,樹林裡有棵巨大的白蠟樹轟然倒下,將四周的幼樹甚至大樹壓垮。看到巨人般的大樹無助地橫躺在地,讓人痛心。弔詭的是,這棵樹過去雄偉矗立時,被茂密的枝葉層層遮掩,死後只剩壯健的軀體,反而更顯得威風凜凜。不過,今年春天我注意到讓人出乎意料的東西:巨樹倒下所清出的空地,冒出一叢我最愛的野花:紅色延齡草。碩大飽滿的葉片上脈紋很深,褐紫紅的花朵比周遭其他的花都來得肥美。白蠟樹活著的時候,籠罩在它陰影底下的幼嫩植物難以茁壯,現在卻得到了充分的陽光、空氣與空間。
專橫獨裁、過度膨脹的父母,往往會壓抑子女的發展。整個家以父母為中心,兒女耗費過多的時間在應付父母:渴望父母的祝福、想到可能會惹他們不悅而忐忑不安、拼命努力滿足父母的需索或是達到他們的期望──卻幾乎總是鎩羽而歸。
很多人只能在巨人倒塌後,才有機會伸展自己,就像白蠟樹旁的小花一樣。
我一位友人的父親是頗有造詣的爵士薩克斯風樂手,卻放棄相當看好的音樂生涯,轉行擔任助聽器的業務員。兒子對同一種樂器也很有天分,父親本來也很鼓勵兒子,沒想到等兒子成為專業樂手,麻煩就上門了。每次兒子開始練習樂器,父親不知為何也在另一個房間跟著吹奏,音量大得足以使兒子分心,讓他覺得刺耳又彆扭。儘管兒子自己的音樂生涯相當成功,卻仍然深信父親更為優秀。
身邊若是有喜歡私下或公開和子女較勁的家長,少有子女能毫髮無傷地全身而退,跟這種家長性別相同的孩子(特別是霸道父親的兒子)會嘗到更多苦頭。他們常常得要等到自己的偶像/獄卒過世,才能真正認識自己。
在你抵達那個「死亡空間」以前,無法想像即將在你心眼之前展開的景致。所有人(包括你自己)的輪廓突然變得格外清晰。你看得更深入也更寬廣。拉開一種有療癒效果的距離之後,父母變成了我們的同胞,勢力不再那麼龐大,形象更為深刻,你和他們輩分相當。死亡空間是親子關係的最後邊界,子女在那裡真正長大成人,死亡益處也隨之誕生。
「直到他們的故事結束,你才能體會箇中的含義。那個故事當然會繼續下去,只不過是在你心中發展。」真實生命結束之後,在兒女心中的假想狀態裡,故事裡的人物是固定不動的──這讓子女可以替事情收尾、獲得領悟。在落幕之後,子女可以回過頭來,學會欣賞父母人生的發展歷程,並認出自己在這齣家庭戲劇裡扮演的角色。
6 看清自己——終極的死亡益處
即使我們無法選擇父母,也無法改變過去我們跟他們的關係,但是我們可以自主地選擇和決定,他們過世後,要讓他們的哪些特質在我們身上體現出來。這項事關重大甚而痛徹心扉的人生經歷,可以讓我們獲得深刻的見解。失喪者並非只能被動承受、消極否認或是想辦法撐過去。
不管我們過去與父母關係為何,失去父母都是重大的損失,但只要反覆嘗試本書提供的方法和步驟,喪親之後的時光,很可能成為你人生當中另一段精華歲月。
父母的死亡釋放了我們。它給我們最佳的機會,讓我們碰觸到最真實也最深刻的自己。它創造了獨特的成長機會,幫助我們更有智慧、更成熟、更開放、毫無畏懼。
死亡敞開全新的視角,讓我們把父母當成「普通人」來客觀看待。有些幸運的人在父母在世期間就做到這點,可是有更多人得等到父母離世以後才做得到。死亡使你更容易感受到對父母的同理心、同情、感激與憐憫;當父母不再占據位置時,你更能自在地設身處地看待他們。
內疚、恐懼、認定死亡益處不存在或不該存在,這些都會阻擋喪親子女追求死亡的益處。很多人拘泥於表面,認定除了從失職的母親或父親身邊得到解脫,唯一可能會得到的與財務無關的死亡益處,就是父母的病痛結束或卸下照護重擔。這類心態會將種種可能性排除掉;這麼一來即使可能性浮現,子女也不容易認出來。
兩種互相矛盾的想法──父母的生活對已是成人的我們沒什麼影響、父母的死亡只會帶來沈重的失落──讓我們看不見喪親子女身分隱含的成長潛能。此外還有第三種想法,認為父母死亡對我們產生的影響,或父母的哪種特質會在我們身上延續下去,是我們無法控制的。這種想法讓子女是否能得到死亡的益處成為運氣問題,而不是有意識行動下的成果。這樣態度會阻擋你獲得父母情緒傳承中最好的部分,或是阻擋你克服最差的部分;也會使得你無法把父母當普通人來真正認識他們,進而導致你無法真正認識自己身上體現他們特質的大部分自我。事實上,從父母的殞逝中獲益並非不孝的表現,也不表示與傷慟無法相容。
即使你在父母剛過世時錯失機會,可是要採收死亡益處永遠不嫌遲,因為重新思考你從父母身上傳承了哪些東西的機會不時出現。忌日與生日(包括你自己與父母的)就是行動的好時機。透過能讓你想起父母、喚起強烈情緒的東西,來尋找與逝者溝通的方法。
採收死亡益處的三步驟
1 建構父母的生命故事,盡量保持客觀;把它寫下來。
2 盤點細數父母的人格特質,精密地分析,決定哪些要保留、哪些該捨棄。
3 尋求有助於你發掘死亡益處的人與事,來支持你打算進行的改變。
1 母親的死使我成長
母親過世以後,我並不感到孤單。當我領悟到這一點,心裡既震驚又安慰。
她還在世時, 每當我身體不適或感到無助時,就會有某種絕望的恐懼撲襲而來,讓我急速墜入恐慌的深淵。母親過世後,這種容易陷入焦慮低潮的傾向漸漸消退。
要是她知道原因出在她身上,肯定會很傷心。但我很清楚知道,我不再被這種負面情緒所掌控,跟她的離世息息相關。
只有在死亡將我倆永遠分開之後,我才能用客觀與慈悲的眼光來重新看待母親:身為女兒、妻子、母親與女人的她,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從母親過往生命的片段,尋找母女關係的...
推薦序
導讀
死亡帶來的新視野
王浩威
哀悼(grief)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近幾年在台灣越來越受到重視。
八○年代以後,傅偉勳教授的《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讓國人看見自己生命中的生死,思考和關注隨之而來,而有了生死學的發展。然而,更早以前,在台灣護理界,趙可式女士早已苦行僧般努力數十年。她累積下來的影響,在傅教授等人倡導後,一切就水到渠成般,在醫療界、哲學界和宗教界,都興起了臨終關懷的運動。
死亡在台灣從此不再是禁忌,甚至可以安詳地正視。在那些大家都知道不該觸碰的家庭祕密中,死亡往往是其中之一。但是這些年來,特別是聖嚴法師臨終前安詳採取樹葬,而單國璽樞機主教巡台演說自己罹患癌症和面臨死亡的心情後,死亡不再是台灣民眾絕對禁忌的話題。
當死亡不再是禁忌,當人們也透過生死學和臨終關懷,熟悉了庫柏勒—蘿絲(Kubler-Ross)所提出的面對哀傷的五個心理階段(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和接受),在台灣,我們的哀悼(失去至親的情緒),還有怎樣的議題、現象或溫度可以去追求的呢?
失去至親的五個心理階段只是一種理想狀態,我們藉此從情緒中暫時抽離出來,診斷自己,看看自己走到哪一個階段了。有人則檢視自己的生活是否建立了新秩序,了解自己的生命是否被牽絆而尚未痊癒。也有人開始回顧自己的生命,回顧自己和去世的至親之間過去數十年來的關係。總之,方法越來越多樣了。
我自己習慣引導個案去看過去的生命經驗。
一位多年不見的個案,忽然又打電話來約診,原來是他父親驟逝。當年在博士班時,指導教授對他的呵護和引導,投射在他心中,幾乎化身為一位理想的父親形象。因為如此,不知不覺地也在他的真實生活中,激起父親潛意識的層面嫉妒和進一步的競爭。教授鼓勵個案往專業再進修,甚至出國;父親則堅持個案要開始考慮生活的現實層面。教授不自覺的引導個案走向基督教信仰而接受洗禮,而父親則勃然大怒,甚至在個案面前落淚,表示再也沒人繼承祖先牌位的祭拜。我們的會談,隨著個案自己相當不容易的努力,看到自己和兩位父親的關係,看到這兩位父親甚至在自己心目中終於重疊為一致的形象,而他自己也逐漸走出問題來。
再一次見面以後,我先了解他近年來的發展,包括專業上越來越投入的追求,也包括擁有一位可以支持自己專業的妻子,以及他父親如何死亡。
他父親是急性心肌梗塞而離別的。這樣的告別,忽然之間,讓他充滿了對不起父親的罪疚:特別是在面對母親「反覆不定」的態度時,更覺得自己竟然連母親都照顧不好,而察覺父親的辛苦,卻已經來不及對他表達任何感謝。
對於治療師來說,這是一次不容易的機會。過去心理治療是因為父親議題而激盪澎湃,現在又因為父親去世來會談。雖然喪事的繁重和失落的心理還在急性期,會談的約定往往不容易找到合適的時間,只能隔許久再約一次。
可是,在第一次的引導中,和過去的分析銜接起來了,他自己再一次仔細回想和父親的關係,包括從父親同伴或親戚的描述,似乎有更多的了解,更深的連結。第二次會談時,雖然還受困於母親的心情,但他也開始明白母親反覆的態度是她的哀悼過程,他不必急著要求母親快快走完。
這樣的工作,是傳統的哀悼心理治療所常處理的面向。另外還有處理來不及的告別、來不及的親情等等的,也是常見的面向。只是,果真「死者為大」,一切都是倖存者的功課嗎?在《死亡的益處》一書,心理治療師珍‧賽佛(Jeanne Safer)提出了過去台灣沒談論過的一個主題:失落不一定只帶來自我的負面作用,其實許多人在喪親以後,在身體上,在心理上,甚至在靈性上,反而頗有收穫。
這樣的論點是過去這方面沒有的,甚至是出於壓抑而忽略的。
我所謂被忽略,是指包括我自己在內的許多治療師。現在回想起來,不只一位個案,他們的傷慟之所以徘徊不去,恐怕是他們有一股沒被看到的自責,也就是自責怎麼會都感受到這樣的收穫,也就是在身心靈上更自由的感覺。當個案還處在哀悼過程,這樣忽然冒出的喜悅感,是讓自己更罪疚的。佛洛伊德在《哀悼和抑鬱》裡,早早就提出來,我們一方面會以為自己的一部分消失了,另一方面又會認為是自己本能的某一層面上謀殺了對方。如果是這樣,這時的喜悅不是更教人罪疚嗎?
珍‧賽佛提出的這種收穫,至少在這個層次上是值得重視的。在過去,我自己的臨床之作裡,也許是個案的哀慟情緒太強烈了,也許是自己的反向移情,會談焦點都是放在哀悼和失落本身。現在回想起來,如果當時也可以看到這些被哀傷所掩飾掉的收穫感(甚至是喜悅的),或許處理這些情緒可以更深入。
《死亡的益處》這一本書描述的收穫感受,其實多在哀慟情緒過了許久以後才出現。
哀慟的階段逐漸遠離以後,似乎很多人也不再去談自己這一方面的深處想法了。只是,如果有機會,確實,我們都可以有同樣的觀察。
我自己經常就覺得自己是因為父親的死亡,才真正解決了之前幾年才分析出來的逃家/離家心境。那時已經三十五歲了,我才因為這樣的發覺自己而終於可以回家了。
雙親的死亡,可能會成為你這輩子最重要的成長時機。這是珍‧賽佛說的,至少在我自己身上也清楚出現了。
只是,也許是有些遺憾的,書中的案例描述裡,對個案的同理似乎大於個案的父母。作者對個案的父母雖然沒有太多的直接描述,但透過這許多的間接描述,每一位父母就算沒嚴重到成為子女情感的吸血鬼,至少也都是不成熟的。
如果我們用佛洛姆的理論來思考,就可以了解真正的成熟而不具佔有慾的愛是原本就不容易的,對父母們也就不會有如此完美的期待了。也許作者珍‧賽佛本身還是期待自己父母的完美,也就因為她的反向移情,將個案父母即使十分人性的任性或佔有慾,都描述得有些極端了。
一個人很難沒有佔有慾,即使父母亦如此。只是,唯有父母的死亡,我們才有機會看見原來父母對我們無私付出的愛當中,原來也有這一部分的自私,也許不嚴重,卻糾纏了許久。至少,這是本書帶給我們的學習,而這樣也就夠了。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洞見(innovation),這本書也就值得我們去欣賞和深思。
(本文作者為作家、精神科醫師)
導讀
死亡帶來的新視野
王浩威
哀悼(grief)是一個重要的課題,近幾年在台灣越來越受到重視。
八○年代以後,傅偉勳教授的《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一書,讓國人看見自己生命中的生死,思考和關注隨之而來,而有了生死學的發展。然而,更早以前,在台灣護理界,趙可式女士早已苦行僧般努力數十年。她累積下來的影響,在傅教授等人倡導後,一切就水到渠成般,在醫療界、哲學界和宗教界,都興起了臨終關懷的運動。
死亡在台灣從此不再是禁忌,甚至可以安詳地正視。在那些大家都知道不該觸碰的家庭祕密中,死亡往往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