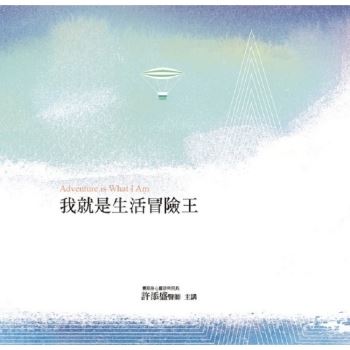推薦序1
全球∕國家∕在地──韓寒與《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多才多藝的韓寒不需要我多做介紹。更多的形容詞只會阻撓我們的視線,讓我們更看不清他的全貌;如果我們在繁多的韓寒傳奇之中抓出軸線,藉此整編加諸在他身上的形容詞,以簡馭繁,提綱挈領,反而可以收到「less is more」之效。
在《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這個書名中,韓寒有意無意總結了他的傲人貢獻︰「和這個世界談談」。他以屢屢嗆聲享譽這個世界,而他的嗆聲真的就是最基本的談談而已。我不是要貶低他的談談,而是要指出,他在甚不友善的大環境下,只是要伸張言論自由(好吧,不要用這個太嚴正的詞,改用「言論的爽」罷),於是他的談談就被擠壓爆炸成嗆聲。而且,餘音不斷︰眾多中國網民的言論之爽,就是要透過韓寒的談談才得以抒發。
當有人(從警察,父母,到地下情人)要找你談談的時候,當然不是只要談談而已。他們是在邀請你踏進一個核爆區。
至於書名中「這個世界」,是指甚麼世界?《在世界的中心呼喊愛情》的世界,是韓寒所指的同一個世界嗎?世界,這個疆界模糊定義曖昧的日常用詞,在韓寒其人其作上頭卻很有意思。韓寒說的世界,可泛指一般民眾,可指中國,也可指國際社會。更準確地說,在地∕國家∕全球就是韓寒對話的三種對象,事實上這三者也是認識韓寒其人其作的三條軸線。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國家夾在全球化資本主義以及在地老百姓之間。韓寒帶來的聳動和鬆動,緊張和緊∕張,就出自「全球」、「國家」、「在地」這三個層面之間的張力。國家在此,自然是指中國。韓寒跟在地的人民談談,但國家不要他發言,於是他就跳到全球的媒體嗆聲。就是因為國家很緊,韓寒才不能放鬆。就是國家無法在全球和在地之間扮好靈活自如的鬆緊帶角色,韓寒才會彈射出來。
認清全球∕中國∕在地三者之間的巧妙張力,才能看清韓寒現象;同時,認識韓寒,也有助於琢磨這個問題︰為甚麼我們談全球化,談在地化,卻不談中國化?(化,在此是指變化。)中國化是不是一個不討好的選項?「中國不化」或「不中國化」,是不是在地人民與全球社群更樂見,更期待的選擇?
說得好緊,其實韓寒也可以好鬆。《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其實並不是一部劍拔弩張的小說;或許韓寒本人也不是一個好戰者。在這本書中,主人翁漫不經心風流倜儻與一個神祕的小妓女結緣,走上流浪之路。這是閒散悖德的新中國浮世繪,其實也是百年前舊中國的復活顯影。中國未必是繃緊的弓弦,弦上其實也大可以拉把琴,快活快活。
文◎紀大偉∕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推薦序2
Behind
凌晨的機場格外冰冷,遠行之前,旅客散在門邊,各自點起自己的煙。
半小時前,往機場的路上我攔了一輛計程車。工作結束得急,在車裡已是無力癱軟,看著車內椅背上掛著的職業登記證,邊緣已經翹起的護貝裡鑲印著司機的名字、車號,以及黏貼得有點歪斜的一張證件照。往司機的背側影對照般地望去,我想或許是每個照相館泰半約好的貼心專業,讓證件裡的那張肖像通常都較本人來得青春許多,看著拍攝沖洗出來的照片成果泰半臉色紅潤、皺紋極少。我想起閃光燈前,我們總是在攝影師的提醒下,保持下巴略縮揚起嘴角面對鏡頭,四張一組先付款後取件,然後謝謝光臨。
開了整天車的司機或許因為走走停停上下客的機械式乏味而顯得面容疲累,或許「昨天沒有睡好」已經是城市裡的文明習慣。或者路上突然煩惱起子女的學費,或宿疾,或女人……或只是煙癮副作用如我?有可能是電台裡的政治評論,或望著前方手握方向盤一成不變……換算成簡單的道理是這就是生活,鬆布的皺紋混濁的眼、懸掛的平安符與茶色的水,也或許我們只是每個人心中各自猜想的或許。
車子靜靜地往前開著,每一公尺我們的生命一起過了下一秒。我們兩個如此地毫無關係。
關係。來自於找不到原因的命定,你的身體來自一個母體、你的靈魂來自「不知道」,當你第一次睜開眼,你處在的土地、經緯度、你的家國歷史、身體種族、教育計劃、神祕主義生命線,已經為你先摺疊好人生的結構。然後我們存在,現實,經驗,上路。天真的那一段叫童年,中間的那一段叫青春,之後的那一段叫社會。
當我已能意識到自己正牽著父母手的時候,他們已經比我先告別過了青春,看著他們的臉,外出工作、回家做飯、機車電視勞動搬家炒菜貸款與卡拉OK,那麼地老成那麼地理所當然。舊照片一疊疊,十七歲即從軍的父親在黑白照片裡帶著墨鏡表示自信,彷彿這個時代正在等他長成未來。母親不忘提醒相本裡某一張茶廠前的留影,身上穿的洋裝都是自己親手裁製,背面寫著當年她十五歲。如今他們的面貌已經衰老,剩下一些記憶仍收在盒子裡沸騰。
他們老了換我們長大。小時候父母牽你的手(可曾想過他們也曾青春)、長大後你已經牽過幾個人的手、又曾被幾個人的手擋開?你因為什麼而跟誰曾經一起走了一段路、停了多長或多短、誰曾經讓你想要進入他的生命史?……當你發現生命得開始自己找道理,社會已經在這裡。
司機禮貌地找了錢、幫我一同把行李拿下了車並祝我一路順風。把行李靠妥皮夾收好後抬起頭,車子已經駛離。拉著行李往前走了五、六公尺,我熟練地加入煙蒂桶小圈圈的圍繞行列。
熟練。
忙碌、疲憊跟寂寞流程熟能生巧,每個人都熟出了一套自己的適應主義,以及一兩句永遠被quote的人生哲學在那裡做最耐用的備胎。每個人的背後都是一座諾亞方舟,人們在路上如此微型如行進般的工蟻,我的心如此大但我卻如此地小。這幾天i-pod裡反覆聽著王菲的「乘客」、機場內翻看著韓寒的《1988》不捨離手,如果有故事可以說出口,那是因為人都需要出口。
此篇也給 ___。
我不是你的世界,儘管生命的路上面對我你沉默,我仍想對你說話。
文◎聶永真∕作家、設計師
作者序
這部小說完成在二○○九年至二○一○年之間,我從二○○九年的夏天就開始落筆,多事之夏,最終停滯。到二○一○年的冬天繼續開始,再停滯。一直到二○一○年的夏天,一樣多事之夏,但完成了《1988》。「1988」是裡面主人公那台旅行車的名字。本來這本書就叫《1988》,副標是〈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不料期間日本的村上先生出了一本《1Q84》,我表示情緒很穩定,但要換書名。又是幾經周折,發現再無合適。就好比在孩子要出生之前,你已經為她想好了名字,並且叫了一年,忽然間隔壁鄰居比你早生了一個和你叫了差不多名字的小孩,你思前想後,發現其實你內心已經無法更改。最後她還是叫《1988──我想和這個世界談談》。
如果有未來,那就是「1988──我也不知道」。
故事在書的末尾告一段落,不知道它是否能有新的開始。我從來沒有用這種方式和文字寫過小說,彷彿之前的一切準備都是為了迎接她。在過往,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好準備,我是否能這樣去敘述。但是在這個凌晨,我準備好了,讓我們上路吧。以此書紀念我每一個倒在路上的朋友,更以此書獻給妳,我生命裡的女孩們,無論妳解不解我的風情,無論我解不解妳的衣扣,在此刻,我是如此的想念妳。


 2011/01/07
2011/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