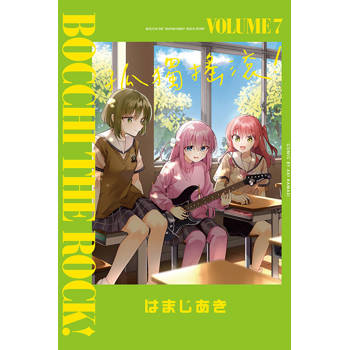摘文作者序:快樂的生活開始了
我五十五歲學電腦,六十五歲學游泳,七十歲玩癌症,七十二歲以後學著養寵物;結果,就碰上了LUCKY,牠是一條黃金獵犬,因為牠太聰明、太善解人意、太會隨著阿公的動作起舞,LUCKY的每個生活片段,都成了我撰寫記錄的主題,同時;也印證了我們不可分割的生命樂章。
這是一段人與狗互動的故事。
在台灣,很多人搶著飼養寵物,很多人又急著丟棄狗狗,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社會。這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現象。不管我們的心態怎樣改變,狗狗永遠是無辜的,牠永遠是受害者;牠永遠是人們的圖利工具。 儘管牠受盡委屈,但牠卻永遠對主人忠心耿耿,我們只聽說主人離棄牠們,卻沒聽過狗狗背叛主人。這是事實。
我有位朋友養了一隻黃金獵犬,有天主人病了,病得很重,住進了醫院,每天和他生活在一起的狗狗,發現主人突然不見了,牠開始焦躁不安,牠整天趴在陽台的窗前,望著街道,等待主人回來,在企盼的三天中,牠不吃不喝,喉間發出哼哼的哀鳴,像是在哭泣,後來,女主人在醫院中拍下主人的照片,狗狗看了照片,興奮莫名,女主人告訴牠,再等幾天,阿爸就回來了,狗狗才恢復進食。有天我去醫院探望這位朋友,發現在床頭的櫃上,擺了各式各樣的狗狗照片,我的朋友每當從昏睡中醒來,一眼看到狗狗照片,他就會開心的露出笑容,有時也會滴下淚水,他想狗狗。
台灣有幾年掀起飼養寵物的風尚,其中又以狗狗最為得寵,各型品種在寵物店中展示,正因為有利可圖,有人不計血統,大量繁殖,近親交配或緊密雜交,構成品種品質下滑,形成市場一團混亂,當寵物的主人發現寵物成長後不符經濟利益時,又任意拋棄,台灣流浪狗成了都市的一大景觀。
我有位在大陸武漢當公務員的朋友,有年來台參訪,他從台北來到高雄,問他有什麼觀感,他說;台灣和大陸最大的差別就是在馬路上看不到公安,但是流浪狗卻比大陸多太多。官方設有流浪狗收容中心,環保人員捕得流浪狗後,在中心關閉一周,在一周之內如果沒人認養,即處安樂死。一條生命就這樣結束,人,製造狗狗的生命,又在發現失去利用價值時,給牠死亡,狗狗又是何等委屈與無奈,人,又是何等殘酷與荒唐?
這本狗的故事書,將從一隻出生四十天的黃金獵犬寫起,在共同生活將近五年中,記述牠的成長過程,牠從嬰兒期、兒童期、少年期、壯年期,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長大,牠的名字叫LUCKY ,現在正是牠的青春年華的時代,當牠的臉上出現白色毛鬚時,牠就進入了中年期,我不等牠到兩鬢斑白,我努力記下牠的每段精華歲月。
狗狗的壽命平均在十五歲左右,等到那時再為牠作記錄,不是牠垂垂老矣,就是我也接近齒牙動搖,眼前茫茫的暮鼓晨鐘之年,那時;我和牠都無法欣賞這本故事的片段了。
在這段精華的日子裡,我們天天廝守打混,冬天;牠陪我晒太陽,看我打電腦,注意我在鍵盤上敲打牠的點點滴滴,夏天;我們出外露營,牠就在大自然中奔跑,夜間牠就睡在箱型車的後段,牠跟著我們在野地架炊煮飯,跟著我們吃火鍋,但是在牠的食物裡沒有鹽,沒有厚油,這都是我那口子為牠調理的野外食物。
一歲半的時候,牠能聽懂我們的談話,牠雖不會說話,但牠也有表達的方式,牠會搖尾巴,嘴唇和前腳作出各種動作,後來又以喉間的吼聲來進一步反應內心的意見……等等。
因為飼養LUCKY,我也去了解流浪狗收容中心,有天,我在市郊的一個中心,見到各種大小狗群,我在角落見到一隻黃金獵犬,牠默默的望著我,眼神是很乞憐的,是等待的,我伸手到欄內,牠很友善的舔著我的巴掌,牠一聲也沒叫,就是搖著尾巴,我明白:牠一定等待我的救援,牠想跟我走,但我是無能為力,因為有了LUCKY,我不可能再收容另一條流浪犬,我對牠抱歉。我走了,我回頭望著牠,牠還望著我,是不是在哭泣?不知道,但我很心酸,我想這不知又是那個主人造的孽。隔了三天,我又去收容中心,我獲得好消息,管理人員說,就在第七天的前一晚,牠被一對夫婦接走了,感謝天,一條生命終於逃過一劫。
我從狗的生活中,獲得很多以前不了解的生命意義,以及人與狗之間的溝通管道,我得到最大的啟示是;人比不上狗,因為狗在一生中,只有一個中心思想,效忠牠的主人;但是人在一生中,有繁雜的思想,不是為財賣命,就是為榮華富貴在效忠,那種搖尾乞憐的表現,比狗還不如。
飼養LUCKY之後,我真的學到很多,也體會到不少。我整天和LUCKY攪和,但我是在學習。
在這本故事中,包含著很多小故事,都很感人,都是很動聽的真實故事。 過年期間,我和我那口子帶著LUCKY到花蓮露營,我們在一戶大宅院內見到一位雙目失明的中年婦人,她歡迎凡是帶狗的家庭到她家中作客,因為她有一條黃金獵犬的導盲犬,這段故事也將是書中的一頁篇章。
我今年七十六歲,LUCKY也貼近六歲,我希望我和牠都能度過垂老的歲月,因為我們覺得一起過日子很快活,何況我現在教LUCKY唱歌,儘管牠鬼喊鬼叫,但牠有興趣,每當牠叫出一聲之後,我就獎牠一粒甘納豆,牠就愛吃甘納豆,每當拿出豆罐子,LUCKY就嘿嘿的笑了,然後一聲嘶吼,LUCKY又開始唱歌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趙老大蹓狗記:黃金獵犬Lucky的生活日誌的圖書 |
 |
趙老大蹓狗記:黃金獵犬Lucky的生活日誌 作者:趙慕嵩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3-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動物 |
$ 221 |
科學科普 |
$ 229 |
中文書 |
$ 229 |
寵物 |
$ 234 |
狗 |
$ 234 |
科學‧科普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趙老大蹓狗記:黃金獵犬Lucky的生活日誌
‧當記者半生的趙老大,曾踏遍大江南北、嘗盡人生甘苦,在這隻黃金獵犬LUCKY的身上,終於感受到難得的真情與緊緊相繫的羈絆。
‧一本全台灣不曾見過的狗狗日記,如果你是愛狗人,會讓你憶起與狗相依偎的幸福;如果你還不是愛狗人,看完後,你也會愛上這調皮搗蛋卻最真誠貼心的好伙伴。
這是趙老大為了感念一隻黃金獵犬陪伴他度過六年的歡樂時光,在罹患癌症末期的不幸中,在病榻旁為LUCKY留下的生活點滴……,字裡行間散發著老人與狗狗的真情流露。雖然結局是狗狗拖斷了老人的一條大腿,但他們之間沒有埋怨和憎恨,相反的,他們更貼心的聚在一起,從他們相對的眼神中,可以明瞭牠對阿公的歉疚和很多的罪過;從老人的表情上,也能看出他對狗狗的付出始終如一,無怨無悔,更加疼愛……
作者簡介:
趙慕嵩
1936年12月15日生。資深新聞記者,退休後走遍中國大江南北,嚐遍各地風味。2003年3月,他決定轉換人生跑道,以銀行貸款方式創業「趙老大北京餃子館」,奮戰七年後,現在轉型為宅配服務。想嚐嚐趙老大餃子的風味,請洽chaomusu100@yahoo.com.tw
早年著作有《醜陋的新聞界》、《老大在現場》、《死刑犯的最後吶喊》之外,近年又出版《遊走中國》、《前進西藏》、《微笑的駱駝》、《悠遊記憶的國度》、《沙漠中的女人》、《趙老大看北京》、《趙老大闖三峽》等等。
目前最大期望:戰勝癌症,常常與Lucky出門遛遛!
作者序
摘文作者序:快樂的生活開始了
我五十五歲學電腦,六十五歲學游泳,七十歲玩癌症,七十二歲以後學著養寵物;結果,就碰上了LUCKY,牠是一條黃金獵犬,因為牠太聰明、太善解人意、太會隨著阿公的動作起舞,LUCKY的每個生活片段,都成了我撰寫記錄的主題,同時;也印證了我們不可分割的生命樂章。
這是一段人與狗互動的故事。
在台灣,很多人搶著飼養寵物,很多人又急著丟棄狗狗,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社會。這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現象。不管我們的心態怎樣改變,狗狗永遠是無辜的,牠永遠是受害者;牠永遠是人們的圖利工具。 儘管牠...
我五十五歲學電腦,六十五歲學游泳,七十歲玩癌症,七十二歲以後學著養寵物;結果,就碰上了LUCKY,牠是一條黃金獵犬,因為牠太聰明、太善解人意、太會隨著阿公的動作起舞,LUCKY的每個生活片段,都成了我撰寫記錄的主題,同時;也印證了我們不可分割的生命樂章。
這是一段人與狗互動的故事。
在台灣,很多人搶著飼養寵物,很多人又急著丟棄狗狗,這是一個很矛盾的社會。這也是一個沒有人性的現象。不管我們的心態怎樣改變,狗狗永遠是無辜的,牠永遠是受害者;牠永遠是人們的圖利工具。 儘管牠...
»看全部
目錄
自序.快樂的生活開始了
Part1 LUCKY來我家
第一天
LUCKY 牠有了名字
LUCKY闖禍了
上學
第一次享受遛狗的樂趣!
LUCKY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
P字鍊和響片
Part2 LUCKY趴趴走
奮起湖之旅。
奮起湖的夜半哭聲
重返奮起湖
阿里山的黑金鋼
走,我們去看海!
喬媽的山莊
LUCKY在太魯閣高歌一曲!
今夜睡汽車旅館!
日月潭到了!
Part3 與狗對話
鄰家的熊哥!
LUCKY的夢中情人!
黃金獵犬的黃金年代!
滿街都是變態狗!
導盲犬的悲情歲月!
LUCKY生日快樂!
LUCKY發飆了!
阿公寫給LUCKY的一封信!
LUCKY...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趙慕嵩
- 出版社: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03-29 ISBN/ISSN:978986213325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224頁
- 類別: 中文書> 生活風格> 寵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