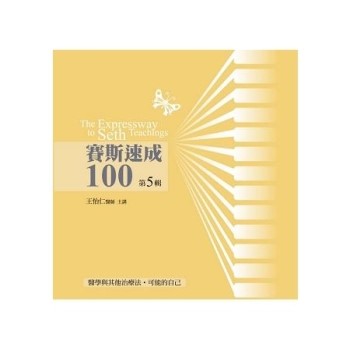[序]
一頭通緝犯,十年犄角:致鯨向海們
「過去怎樣與那頭小鹿對望的下午
明日就長出怎樣的清晨之犄角吧」
通常第一本書,就像是初吻,真的都是一種舊日理想了。
為了紀念《通緝犯》,我的處男詩集,潛逃十年,絕版數年,我選取部分將之化約重組,與這十年來新寫或未發表的詩,新舊口吻交錯,對位纏繞如織物,嫁接繁殖如新品種,出版了這本詩集。因此,嚴格來說,如果按照商禽那本《夢或者黎明及其他》奠定的體例,此詩集全名應該叫做《通緝犯及其犄角》才對(笑)。
犄角,除了是「動物的角」,也有「角落」的意思,是身(心)的邊境。《犄角》簡單來說是《通緝犯》十年來的一種延伸,一種突變。長出《犄角》,既有掩護《通緝犯》繼續偽裝害羞的不老精怪之用意,也可能因此原形畢露,使《通緝犯》的追捕在雪地上留下彈孔,反而更易被辨識分明。
「是啊他仍是一個詩人,堅強而深情
仙鬼的美德與非罹患不可的絕症
那些青春愛戀忽遠忽近
以為這樣的詩亦是犄角
他的深藏不露
卻屢次被當成了豬頭」
我的寫作真的是醫生所寫嗎?有時他們讀起來像是病人的作品。我當然也是有我的困惑與耽溺,害羞與傷心。我其實並不想從事,那種以權威口吻,提供大眾衛生教育一般的寫作。
「病」的概念是相對於「健康」。我以為「健康」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概念,類似「天堂」或「樂園」的概念一般。人怎麼可能真的完全健康呢,恐怕「追求絕對健康」這類想法才是一種疾病。既然病痛是人的自然狀態,我們就不應該逃避,不如以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與缺陷殘疾和談吧。寫詩也是非常講究與內心醜惡坦然面對的;在那種時刻,象徵你的獨特性之犄角總是呼之欲出(既是面向永恆時的極限延伸之物,也是所有往上頂撞昇華的突出物),別因為恐懼某些強權宰制不准裸露,便跟著膽怯了。
在此冒著犄角被側目為「畸角」的風險,舉一個我的癖好來說好了。人們總習慣從「你」或「妳」「他」與「她」去投射自己的性別認同與偏見,我則更傾向於一種沒有明確性別,游移動蕩,可能「雙性」或「中性」或「無性」的詩。我認為任何一個詩人(創作者)在創作中都不該固定自己的性傾向,他應是開放性關係,隨時準備與任何人物談戀愛。因此我所傾訴的對象不是盡量隱藏性別,便是露骨地故佈疑陣,使一切更加曖昧;必要時甚至不惜變造第一人稱的性氣味以擴大詩意瀰漫籠罩的領域,如此,熟悉的自己也能被推向無限遙遠。故而我的寫作通常偏愛把男性與女性一律皆用「你」「他」稱代之,鮮少在作品裡強調「妳」「她」這樣性別限定的代名詞,更別說使用「娥」了。
為了追尋更魔魅,更有輻射效應的歌頌空間,這種堅持值不值得?到底是白目還是遠目?這就是那個難題(that is the question)了--一切還是得回歸我們是否知道自己在發出什麼微波,想接收什麼訊號。
「那是怎樣的龐然
隱隱約約
曾抵達
這個時代
靈魂閃著光
頭頂長出犄角來」
又譬如,我長久以來深切地感受到,眼下應該是小詩的盛世。網路很可能加速了小詩的進展。那些不確鑿鑽研過短詩的人也都不知不覺地寫著短詩。君不見臉書上四處可見塗鴉如詩,BBS上的精彩推文趣味睿智甚至勝於某些詩人寫的短詩。此時代的短詩競爭是激烈的,小詩跟寫詩歷練不一定有關,往往取決於靈光乍現之頓悟。小詩(或其集合)也能寫出雄偉感來,並非長詩就比較偉大。
我也一向偏愛短小的詩(這和我同時欣賞後勁綿長的詩意沒有衝突),總覺得能夠在詩中用略少的字數來傳達更多曖昧是比較聰明的。在這班雅明所謂沒有純粹的聲音、沒有固定的資源、沒有永存氛圍的都市文化?面,小詩宛然是碎鑽與琥珀的存在。如果有辦法把詩寫更短,我是絕對不會故意寫長的。事實上,我所有的詩都懷著把他們寫得更短就好了的期盼。
「所以你整天都在寫詩嗎?」
「喔不,那樣我會詩盡人亡。」
我的現實生活,就是一個普通的醫生,像是所有的醫生一樣,嚴守醫學論文與教科書上的法則與規範,一絲不苟,不能隨便把病人的權益拿來開玩笑。可說在文學上,我雖企圖成為膽大的實驗者,坐在診間的我,卻非常保守老成。況且寫詩也不是想寫就寫的,寫詩的手感也有潮汐般的週期,所以我更珍惜每一次靈感降臨的機會,縱使長出犄角,變成世人眼中的怪物也不惜--畢竟,許多詩一旦錯過,皆是此生無法再寫出來的了。
加上我也不喜歡蓄意規劃主題的寫作,森然呆板地制訂犄角的漸層變化;我其實相信越無所用心無所事事越好,追隨著偶然歧生分岔的直覺,反而越能創造巧奪天工的嚴謹結構。因此只能平日多鍛練詩意的體質,以便隨時通靈(誤)。至少目前是如此啦,我的詩集好像從來都不是在計畫之中的。我並不是那種寫完了一本詩集就開始籌謀下一本詩集的強(迫)者。
「你不時撥開果皮,飲料吸好用力
突然暫停
假裝隨便問問
今天適合做愛嗎
此刻良心
對著整座森林發光
把犄角舉到頭頂」
儘管我難免被歸類為六年級詩人,卻時常懷疑每個世代真會共享同一種詩觀,或者每本詩集會必然遵守某種評論者想像中的整體秩序。我以為秩序是建立於個別寫詩者自我的風格之上,這麼多集體風潮與主義的龐然身軀搞不好都是虛幻的,驀然回首整座森林,真正存在的只有那根令人想入非非的犄角而已。持續地遊戲,持續地對詩充滿熱情,需要保持一些天真和叛逆;與其乖馴地被設定為某世代螢幕的基本布景,我確實更期望能夠不斷搞笑牴觸這種理所當然的衰老論述,冒犯挑釁那些被禁止的不堪意象和形式,成為永遠更新程式的獨角獸。
佛洛伊德曾說:「每個笑話都會募集自己的群眾,而為同一個笑話而笑是心理一致的明顯證據。」我很享受能夠和讀者彷彿心靈相通,為了同一個梗會心一笑那種趣味。那些梗也都是犄角吧,大家都想戳到對的人,「噢!YES!」戳到對方靈魂深處裡去。最唬人的狀態,大概就如同楊佳嫻形容的:「讀鯨向海的詩,有如不小心被變形金剛組合進去」(羞)。最不要臉的時候,於此詩國嚴寒時期的自嗨,應該這樣的:
「你真的帶來各式各樣層出不窮的溫暖耶」
「喔,我想是因為我有比較粗的燃料棒……」
我更且臉紅地癡心妄想自己的詩能夠保持恆溫。文學創作可以幫助創作者抵抗生存焦慮,猶如多數人以結婚生子來確定自己的基因可以延續一樣。每首詩都延續了寫詩者的生命,帶來不朽的幻覺。故而我的詩鮮少註明創作日期,希望他們能夠超越那些被創作出來的片刻,穿梭時空;在長久以後,這些詩若真的可讚,他們的精確時間將不再重要--所謂「羚羊掛角」,他們將變成渾然一體無跡可尋的作品,共同氤氳著,此起彼落噴勃著,某斷代活火山的氣息,而非侷限於某年某月某日單一靈感爆發之後的灰燼。
「獻給
所有升出水面之犄角
我跟你們共用了
同一隻獸」
波特萊爾表示:「要看透一個詩人的靈魂,就必須在他的作品中搜尋那些最常出現的詞。這樣的詞彙會透露出是什麼讓他心馳神往。」那些難以忽略經常反覆突出的詞語就是一種犄角吧,而他們可能都是源自於內心的同一隻獸。這真是所有寫詩者共通的秘密了。挺然翹然的犄角,固然可以是狎邪的,未嘗不能有十字架般的聖潔,端看我們怎麼高舉,怎麼低撫。
照說每個寫詩者都有機會凸顯出自己的犄角,但有時難免因為現實環境太虛胖臃腫了或前輩詩人們的毛髮太濃密了,暫時被壓抑住;須得等到更自得其樂(放棄某些獎項與名氣的汲汲營營),或真的有練過時(終於能判斷自己的優劣而非老是在意別人的看法),才能慢慢把犄角裸露。
從容自在亦是讀詩最好的條件。現代忙碌的生活,每個人都曾經被絕殺過,卻沒有人規定你從此就必須活得好像每天都被絕殺--讀詩就是使人冒出犄角的好方法,大霧之中,如吊橋,如天梯,讓我們的迷惘與偏遠的事物重新聯繫:網路與詩,精神醫學與詩,遊戲與詩……那麼多美好的犄角,詩一直就是我生命中那隻最大的獸。
《通緝犯》固然酷為第一本詩集,是我所有詩集的父執輩,但出詩集這種事情其實無法講究什麼長幼有序。事實上,我的詩集們,彼此間或許都有違背倫常的曖昧,他們皆是偷偷用關愛的眼神微妙的姿態,相互依賴形成犄角之勢的,而沒有什麼傳統的詩歌道德規範可言。總而言之,他們本身自成一種理想與秩序,共用著我,都是鯨向海們。
「所以你出道也十年了喔,偷鯨向海的賊。」
「是的。很高興你還在,我也還在。」


 2016/03/17
2016/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