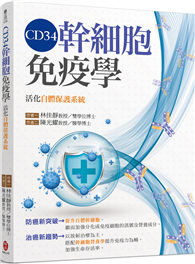這本書,
屬於任何一個曾經糾結的靈魂,
因為那麼貼近現實,
閱讀時也會感覺著痛。
本書是作家歐陽靖於1999年至2005年罹患憂鬱症期間所記錄的文字與攝影。一般人或許很難想像,憂鬱症患者因為長期服藥的副作用,幾乎沒有記憶力。因此痊癒之後的歐陽靖,只能依靠當初所遺留的文字與照片,來摸索關於那段憂鬱而晦澀的期間,自己究竟在想些什麼與做些什麼。很慶幸歐陽靖留下了這些影像與文字,因為藉由這些文字與照片,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一名被囚困於自己心靈的人,曾經多麼的灰暗、絕望,但又慢慢從谷底爬起,好像隱隱地看見了生命的希望與微光。
既便被棄絕在最深最深的黑暗也沒關係,因為,我們終究會活下來。
如我們,大約很難想像,喪失記憶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模樣。
與歐陽靖相談時,她提起罹患重度憂鬱的六年間,完全不記得發生的任何事,去哪裡、做了什麼、甚至是食物的滋味,皆是一片空白。我想那個時候的歐陽靖與我們活在不同的平行時空,她的感官體驗著灰色的滋味,生活充斥晦澀、苦淚、瘋狂、迷亂。
但當走過這段荒涼時刻後,歐陽靖回頭檢視自己的生活,卻發現在完全失落的六年間,她留下大量的文字與攝影。這些從她人生散佚的片段反倒成為最珍貴的寶物,她藉著反覆閱讀這些文字與圖像,記憶曾經的自己。
本書是歐陽靖罹患六年憂鬱症的故事,在書裡,充滿造做、隱瞞、混沌不清的故事,卻全是這六年間歐陽靖忠實記錄下來的一思一想。閱讀的過程宛如一趟旅程,從凝重地令人難以喘息的文字中,穿越一切,看見既虛幻又真實、難以辨認的人生,當我們嘗試在記憶裡尋找關於歐陽靖的報導以驗證的時候,似乎又隨著文字邁向一種近乎於療癒過程的平緩,看見那些回憶與傷痛漸趨平靜,又如歐陽靖回首慢慢地舔舐自己的傷口,最後,隱隱地看見遠處的微光。
這是歐陽靖的告白,同時,藉此撫慰所有同受憂鬱之苦的朋友。
作者簡介
歐陽靖
出生於一九八三年,台灣台北市。曾做過夜店服務生、模特兒、相片沖印師、業餘攝影師,現職是演員與文字創作者。二零零九年出版小說《吃人的街》,主題是存在主義、偽科幻,實際則為作者本身的精神剖析。
成長環境奇特,母親是台灣資深演員譚艾珍,父親左手有隻黑龍紋身。家中曾飼養四百多隻流浪狗、老鷹、貓頭鷹、鼯鼠、松鼠、猴子、野豬、鵝、九官鳥、蛇、馬來熊。
一九九九年,成為重度精神官能症患者,直到二零零五年痊癒之前,只能以大量的文字與攝影創作,做為宣洩與救贖的管道。往後創作的目的,僅是希望能讓多一點人看見:一個人在承受凌遲般痛苦、剖析自我後的染血字句。也想讓讀者了解:攤開自己最醜陋的腦葉皺褶、面對它並唾棄它,你就能得到重生與喜悅。
歐陽靖目前的興趣是長跑、電玩、飲酒、聽台灣獨立樂團。
BLOG:ginoyblog.pixnet.net/blo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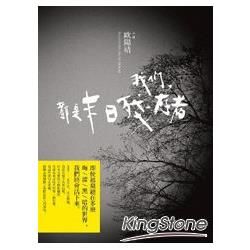
 2012/12/02
2012/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