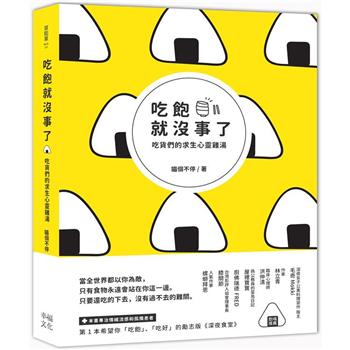滿清格格林佩芬「大清開國三部曲」最知名的《努爾哈赤》全新大幅改寫,重新出版,長達一百四十餘萬字之重量級巨著。
《努爾哈赤》本為作者紀念亡父而作,歷經十餘年始完成,之後更大幅改寫,不但角度更宏觀,更以細膩的現代小說技巧融入龐雜的史料中,帶領讀者深入這些歷史人物的內心世界。
清朝開國當時正值十六、十七世紀,無論歐亞都是奠下現代文明基礎的重要時刻,也都處在風起雲湧、變化頻仍中,她筆下的《努爾哈赤》因此不僅僅是敘述歷史事實的具體表象,而是從「變」的角度出發,看到種種互為因果的大時代變動。
上冊敘述女真人努爾哈赤十九歲即被送給明將李成梁為養子,慣施「以夷制夷」策略的李成梁,終究出兵殺了努爾哈赤父祖,倉促出逃的努爾哈赤矢志復仇,以十三副甲起兵,雖然手下僅有一百多人跟從,但沒想到日後竟成為時代變動的關鍵人物,開創了下一輪太平盛世。
中冊敘述努爾哈赤成為最強大的女真共主,而日本此時也正式進入江戶時代,豐臣秀吉發動對朝鮮發動了一場浩大的跨國戰爭,意圖假道朝鮮、侵略中國。但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為了當個耳根清淨「太平天子」,不但久不上朝,並廣施廷杖,殊不知世界早已天翻地覆⋯⋯
下冊敘述明朝自萬曆皇帝朱翊鈞過世之後,朝政更加混亂,黨爭、宦官爭權,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努爾哈赤勵精圖治,正式稱汗,建國號「後金」,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沒想到明朝雖早已呈敗亡之象,努爾哈赤揮軍南下時卻意外遭逢了前所有有的巨大阻礙⋯⋯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大清開國之君 努爾哈赤(套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275 |
小說/文學 |
$ 1320 |
中文書 |
$ 1320 |
歷史人物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林佩芬
一九五七年生於基隆市,東吳大學中文系,現任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客座研究員。一九七七年開始從事寫作,一九八○年代起開始致力於長篇歷史小說,尤以明清為背景的小說見長。代表作為《努爾哈赤》、《天問》、《遼宮春秋》、《兩朝天子》等書,近作《故夢》更被改編為電視劇。
序
自序
登高壯觀天地間
獨自矗立在宇宙的第一高峯,你會想些什麼?
稚齡讀書,我常從文字中想像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杜甫「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境界;登高望遠,心胸開展、視野遼闊,抗懷千古、俯視天下,人的襟抱與作為於焉受到啟發。稍長,我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看到鎮院之寶—北宋范寬的巨幅山水〈谿山行旅圖〉,從圖畫中領略了巍峨高山宏偉雄壯、頂天立地的大氣,體會到一支筆能具體揮灑出「山川炳煥似開國」的磅礡氣勢,也產生了新的想像:圖畫中的旅人正在層巒疊翠的山間行走,如若前進不輟,一步一階的登上峯頂時,會是何等景象?所見到的又是何等景象?而這正在山間行走的旅人,會是孔子?杜甫?還是我自己?
這份臆測令我神往,時時獨自思索;而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諸多印證—第一次搭乘飛機時,年已雙十,卻像孩童般目不轉睛的看著窗外,遼闊的山川江海、田野平疇如畫卷般展開,蒼莽大地,盡收眼底,實際上體會了得以宏觀全局的開闊視野,心中產生極大的感觸;於是,此後每到一個陌生的城市,我總要登上城中的最高樓,一覽無遺的眺望全景,久了竟成為一種習慣,登高望遠,望盡一城的煙雲。
中年以後,我飛越海峽,足跡遍歷神州大陸,行經萬里長城,我在千年不朽的城上佇立,舉目四望,天地浩渺,氣象萬千,而眸光交錯間,我覺得眼前所見的不是天容海色,平疇沃野,也不是歲月與建築,而是總合了時空的歷史,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是天地之間的人世,是人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探討。
於是,視野成為一個抽象名詞,一種思考意義,也使我對自己產生新的詢問:是什麼樣的眼光能透過這廣闊無邊的視野洞澈歷史?是什麼樣的襟懷能涵蓋這博大宏偉的視野,體悟歷史?
這項詢問不易立刻獲得回答,但時時縈繞心中,反覆思索、探求;偶然間,我行經龍門石窟,登奉先寺,一步一階的拾級而上,站在寺前平臺仰望舉世著名的盧舍那大佛;寶相莊嚴,慈悲圓滿,無論是有形的雕刻還是無形的氣韻,都呈現了完美的境界;時正雨過天晴,天地間充盈著雨水洗滌後的潔淨和陽光重現時的柔煦,也使我的心境祥和寧靜,一塵不染;而不經意間一抬眼,正對著大佛彎垂的長眉下一雙悲天憫人的眼眸,眼眸深處飽含著廣闊無私、對世人充滿了關懷、憐愛與寬和、包容的慈光;霎時間,我得到了感悟,已無須對眼光和襟懷提出詢問。
最終,我又回到自己的書房裏,隨性讀書,一如陶淵明的在書卷中俯仰終宇宙而自得其樂;一面期許自己的寫作是出於沉思,歸乎翰藻,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成一家之言;也希望能具體實踐蓄積多年的理想:
一位偉大的小說家必然同時是史學家、思想家、藝術家與宗教家。
宗教家悲天憫人的胸懷與救世的精神,是一種偉大;藝術家創造完美與詮釋完美,也是一種偉大;思想家探尋真理,剖析人性,提升人性;史學家鑽研古今之變,鑑往知來,啟迪世人,更是一種偉大;而能融此四者於一身,方成偉大的小說家。
寫作原本就是一項偉大的追求與實踐—這雙重的偉大使作品矗立於永恆。
宏觀人類的歷史,是一個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宛如一座永不停息的風車般的輪轉,生死榮枯不停的循環交替,變動的過程與時間一起前進;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國家,哪一種文化,都由出生、成長,進展到強盛、衰老,而後步入死亡,為下一輪的新生者取代。
微觀中國的歷史,也是一個生命,盛世與衰世循環交替,朝代之間如連環般的進行遞嬗,新陳代謝,世代交替,老死的一朝為新生的一朝取代,新朝老化、腐朽後又為下一個新朝取代,周而復始,循環不已。
我選取清朝開國史作為中心點,探討明朝的鼎革遞嬗和時代的完整風貌,書寫《大清開國三部曲》;在時間上的定點為始於一五八三年清太祖努爾哈赤以十三副甲起兵,至一六八三年聖祖康熙帝收服臺灣,明朝的年號完全消失為止哻,共計一百年;百年世事,莽莽蒼蒼,有如大海之波瀾壯闊,有如山泉之幽深曲折,更有如浮雲之瞬息萬變,令人嘆為觀止。
斯時,世界史正寫出一頁驚心動魄的篇章,歐亞美非各洲都處在前所未有的大變動中;歐洲正因地理發現、印刷術傳播、民族國家興起及宗教問題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都發生變化,時代陷入動亂中,國家重組、內部及國際間戰爭頻仍,戰火隨處可見,人們在痛苦中度日,而這情形促使許多人向外拓展,形成頻繁的航海活動,又因為地理大發現,航海者行向亞、美、非三洲,尋找新的發展。
美、非二洲的居民因而蒙受重大浩劫,許多黑人被擄為奴,許多印地安人被殺,許多地方淪為殖民地,惡劣的情況延續了一個世紀以上才得到改善。
對亞洲,歐洲亦以武力入據馬尼拉、臺灣等地,對文明程度已高的中國、日本等國則發展貿易、傳教等項,進而因往來頻繁而關係密切,而相互影響;在經濟上形成全球貨幣體系,彼此休戚相關,榮枯與共哷;宗教、文化的傳播影響了雙方的心靈和精神,科技的交流提升了天文、曆算、製造等學;新式槍砲武器的銷售直接影響戰爭的勝負,成為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亞洲主要國家本身亦處在變動中,中國固為易代之際,朱明政權因庸主在位,朝中黨爭、內鬥,民間經濟崩潰而逐漸腐朽;努爾哈赤起兵後,女真由分裂而統一,進而聯結蒙古,使蒙古的情勢產生變動;最終滿、蒙、明三方合而為一,形成大一統的新朝代。日本則方由「戰國時代」步入「幕府時代」,變動極大,並亟思向外拓展,於是出兵侵略朝鮮,朝鮮以文臣結黨內鬥、武備不修等原因無力抵禦;而朝鮮本為明朝屬國,明朝出兵援朝,形成三國之戰,戰事拖延七年才結束,對各國、各方面都造成重大影響。其後,清朝在入關之前,為免後顧之憂及解決糧食問題,兩次出兵朝鮮,使朝鮮一變為清之屬國,影響至巨。
基於這些,我深刻的體認到,形成歷史變動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每一個枝微末節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彼此息息相關,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心轉意移,牽髮動身;也同時存在著個別性,每一個枝微末節都各自有它形成的原因、過程、特有的現象和影響,也都彼此息息相關,互為因果;這整體性與個別性一如地球的公轉與自轉,同時進行,相互影響,四季運轉,晝夜交替,其原則永恆不變而過程瞬息萬變。
因此,探究這百年世事,既是「通古今之變」,也是「通全球之變」;我的寫作以中國為中心,以「長時間、遠距離、寬視野」的大歷史角度看清朝開國的歷史;而中國既為世界大變局中的一員,與外國的內部變動、外在影響都息息相關—我歸納為八大意義:
第一:滿族建立清朝,由關外入主中原,興起的過程中融合了東北諸多少數民族,又聯結蒙古,並大量吸收漢文化,形成新的、融合式的中華民族與文化;再現中國歷史上進行過多次的胡、漢民族因政權更替而形成民族、文化大融合。
第二:明末衰敗已極,生靈塗炭,經過翻天覆地似的大變動、政權移轉後,注入新朝的新生命力,重新起步,逐漸走向盛世,開創出「康雍乾」的輝煌時代,印證了歷史的盛衰循環論。
第三:明末衰亂,賦稅苛重,民不聊生,不少人為謀生路或投向清朝,壯大了清朝;或聚眾起兵,形成內亂。李自成起兵後,以「不納糧」的口號大得民心,使許多地方自動迎降,印證了「民為貴」、民心的向背決定政權存亡的政治理念。
第四:明、清兩朝的帝王重臣互相對照,印證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聖哲之言。
第五:易代之際,明朝士人面臨三種抉擇,而有四種做法。一為效法伯夷、叔齊隱居;二為效法耶律楚材投效新朝,造福百姓;三為效法文天祥,殺身成仁;三者都可欽可敬。第四種是反覆不定,降後復叛,產生許多特殊行為,堪稱最佳的人性研究案例。
第六:明、清兩朝與日本、朝鮮及南洋、歐洲各國的官方關係固為政治、軍事,而民間活動重點在貿易、科技、宗教與文化傳播,影響亦大。
第七:明末內地陷於戰亂,沿海居民或相繼往海上發展,提升了沿海的經濟;或往他地移居,成為外國的「華裔」人民,開創出新的天地。海盜出身的鄭芝龍等人發展出大型船隊,運貨經商及建立海上武力,往來於日本、南洋各地,並與歐船在海上貿易,如同與歐洲一起進入大航海時代,對全球互動有重大影響。
第八:清兵下江南時,鄭成功起兵對抗;失敗後,在內地無法立足,轉而向海上爭取生存空間,於是收取臺灣—歷史於焉發展出新的篇章。
當時臺灣為荷蘭人所據,欺壓、苛待島上居民,曾引發抗爭事件,怎奈明朝無力救援,任由荷蘭人橫行。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出兵取臺,從鹿耳門登陸,打敗荷蘭軍,迫使荷蘭人離開臺灣,臺灣始為中國所有,歷史於此進入「明鄭時期」,至一六八三年納入清朝的版圖,設官治理—這一連串的演變使臺灣由一座荒島被開發、建設成寶島,日後發展成全球交通、經貿及戰略要地,影響之大無可算計。
而以這八大意義作為骨幹寫作小說,固非易事;但也因為困難,才值得動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