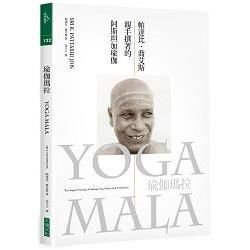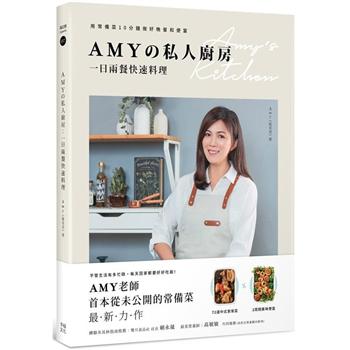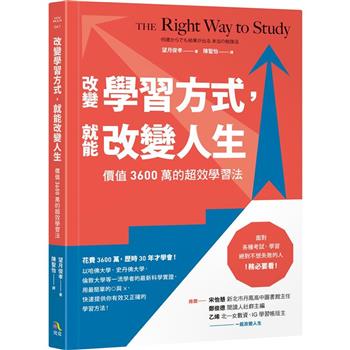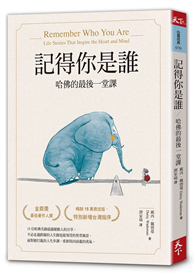帕達比.喬艾斯一百週年冥誕大開本紀念版
阿斯坦加瑜伽最重要的經典文獻
古儒吉親手撰著的著作,首度翻譯成繁體中文
瑜伽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練習,和百分之一的理論。
「瑪拉」(mala)在梵文中是串聯的意思。印度的串聯有許多種含義,其中一種是念珠,它以聖珠穿線製成,可以讓人在念經唱咒的時候計算次數、保持專注。另外也有花環的意義,印度人會把芬芳的鮮花串成花環,放在家裡或寺廟中敬拜神明。古儒吉提出了另一種串聯,它古老傳統,神聖如祈禱,芬芳如花環。他所指的就是瑜伽體位法的串聯,每個呼吸和動作的連結(vinyasa)就像聖珠一般具體可數,讓人專注其中;每個體位法就像鮮花一樣,以呼吸的細線連結成串。我們把念珠戴在脖子上,把花環套在神像上,而瑜伽的串聯也具有相同的意義。當我們認真、專注的練習時,生命就會散發出平和、健康、光彩,最後進而探掘真我。
帕達比.喬艾斯是近代最偉大的瑜伽老師之一。四十多年前,他把這套瑜伽系統帶入西方。這種練習以呼吸搭配流暢的能量律動,激盪出日後各種型態的串連式瑜伽,影響現今廣為流行的多樣瑜伽風格。
《瑜伽瑪拉》是帕達比.喬艾斯撰寫的阿斯坦加權威指南。他在書中精簡的說明瑜伽的道德規範以及哲學理論,解釋了重要的詞彙和概念,循序漸進的教導讀者拜日式以及一級的四十二個體位法,詳細介紹如何練習每一個動作,以及各個動作的益處。這絕對是大師級的瑜伽經典。
作者簡介:
帕達比.喬艾斯(Sri K. Pattabhi Jois, 1915-2009)
帕達比.喬艾斯生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省哈桑的小村莊高席卡,他出生那天正是七月的滿月。他的父親是占星學家、祭司,也是地主,母親負責家務,照顧九個孩子,五女四男,而帕達比.喬艾斯排行第五。他和所有婆羅門的小男孩一樣,從五歲開始,就受到父親耳濡目染,接觸梵文和宗教儀式。他的家人都沒學過瑜伽,也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在那個時代,瑜伽在印度被視為僧侶、苦行僧和棄絕物質生活的隱士所練習的秘傳功夫。一九二七年,帕達比.喬艾斯接受朋友的邀請,去哈桑中學的會議廳觀賞體位法示範。他當下就對體位法震懾住了,由衷的景仰瑜伽行者強健有力、優雅自得的在動作間跳躍穿梭,於是下定決心要學習瑜伽。當時才十二歲的他,開始與偉大的瑜伽行者奎師那馬查利亞長達二十五年的修習。
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間,帕達比.喬艾斯在麥索的梵文學院唸書,鑽研梵文和《吠陀經》,後來又繼續擔任教職,教授吠檀多學派的哲學理論。他一直在學校教書,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全心全意在自己的瑜伽教室裡教瑜伽。
一九四八年,帕達比.喬艾斯在拉施密普蘭的家中創立了阿斯坦加瑜伽研究機構,一心把古老經典和奎師那馬查利亞教給他的瑜伽療癒發揚光大。當時那個房子只有兩間臥室、一個廚房,和一間衛浴。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他才在房子後面蓋了瑜伽練習廳,並在二樓加蓋休息室。
帕達比.喬艾斯第一次來到西方是參加一九七四年在南美所舉行的瑜伽大會,當時他以梵文演說,還被譯為多種語言。一九七五年,他去加州旅行時,常在不同的場合上說:「現在美國只有二、三十個學生練習阿斯坦加,但是漸漸的、漸漸的,二十年之內,一定會廣泛的流傳開來。」後來三十年間,他多次旅遊美國,教學也逐漸開花結果,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現今瑜伽在美國的普及與風行。
帕達比.喬艾斯的瑜伽著作中最重要的就是這本簡短的書籍《瑜伽瑪拉》,清楚明瞭的解釋阿斯坦加瑜伽的練習方式。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以手寫的方式編著,帕達比.喬艾斯總是利用下午家人休息的時候抽空工作,花了兩、三年時間才完成手稿。英文書名中的mala(音譯「瑪拉」),在梵文中是串聯的意思。印度的串聯有許多種含義,其中一種是念珠,它以聖珠穿線製成,可以讓人在念經唱咒的時候計算次數、保持專注;另外也有花環的意義,印度人會把芬芳的鮮花串成花環,放在家裡或寺廟中敬拜神明。帕達比.喬艾斯提出了另一種串聯,它古老傳統,神聖如祈禱,芬芳如花環。他所指的就是瑜伽體位法的串聯,每個呼吸和動作的連結就像聖珠一般具體可數,讓人專注其中;每個體位法就像鮮花一樣,以呼吸的細線連結成串。我們把念珠戴在脖子上,把花環套在神像上,而瑜伽的串聯也具有相同的意義;當我們認真、專注的練習時,我們的生命就會散發出平和、健康、光彩,最後進而探掘真我。
帕達比.喬艾斯不顧當時旁人的眼光,把生命奉獻在瑜伽教學上。他從未停止過教學,不為金錢、不為名利,儘管他最後自然而然的名利雙收,成為聞名全世界的瑜伽大師。帕達比.喬艾斯代表了無私的奉獻,他燃燒自己,照亮了瑜伽的傳統智慧。他於二○○九年去世,享年九十三歲。
譯者簡介:
伍立人 Daniel Wu
台大外文系、台大新聞所畢業,曾擔任六年國際新聞編譯。他因為喜歡瑜伽,二○一一年辭去編譯工作,開始印度朝聖之旅,從此扭轉個人的視野,下定決心專注在阿斯坦加的練習之路上,並於二○一四年獲得阿斯坦加學院掌門人Sharath的祝福,成為KPJAYI的認證老師。現為專職瑜伽老師,同時兼職翻譯,譯有《怪奇孤兒院》、《特別的朋友》、《童年那一場意外》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這是一份瑰寶⋯⋯帕達比.喬艾斯以權威、虔敬的口吻講述瑜伽哲學以及練習的靈性層面⋯⋯對於走上阿斯坦加這條路的練習者來說,這絕對是必讀的經典。——《瑜伽期刊》(Yoga Journal)
古儒吉指導過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學生。這本書中介紹的練習方式和他在麥索的教室裡所教的一模一樣。他希望未來的世代也能持續這樣的練習,保存傳統的瑜伽智慧。——夏勒斯 Sharath
我大力推薦這本精簡的著作,因為它清楚介紹了瑜伽的各方面要素。帕達比.喬艾斯引用正統的梵文經典,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瑜伽哲學以及阿斯坦加的練習規則。——麥索大學副校長 N. A. 尼坎
帕達比.喬艾斯深具靈性智慧,對瑜伽獨具洞見,而且又有切身的練習、教學經驗,這些經驗讓他的著作更顯不凡。我由衷感謝他的貢獻。——麥索大學前哲學院長 M. 亞穆那查利亞
名人推薦:這是一份瑰寶⋯⋯帕達比.喬艾斯以權威、虔敬的口吻講述瑜伽哲學以及練習的靈性層面⋯⋯對於走上阿斯坦加這條路的練習者來說,這絕對是必讀的經典。——《瑜伽期刊》(Yoga Journal)
古儒吉指導過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學生。這本書中介紹的練習方式和他在麥索的教室裡所教的一模一樣。他希望未來的世代也能持續這樣的練習,保存傳統的瑜伽智慧。——夏勒斯 Sharath
我大力推薦這本精簡的著作,因為它清楚介紹了瑜伽的各方面要素。帕達比.喬艾斯引用正統的梵文經典,以淺顯易懂的語言介紹瑜伽哲學以及阿斯坦加的練習規則。——麥索...
章節試閱
[序文]
帕達比.喬艾斯(1915-2009)生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省(Karnataka)哈桑(Hassan)的小村莊高席卡(Kowshika),他出生那天正是七月的滿月。古儒吉在高席卡度過了十三年,那小村莊至今仍然維持著當年的模樣。過去和現在,那裡都住著六七十戶勤奮工作的家庭,圍繞著三座古老的寺廟生活。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席卡才有電;古儒吉年幼的時候,那裡有腳踏車的就算是有錢人了。
古儒吉的父親是占星學家、祭司,也是地主,母親負責家務,照顧九個孩子,五女四男,而帕達比.喬艾斯排行第五。他和所有婆羅門的小男孩一樣,從五歲開始,就受到父親耳濡目染,接觸梵文和宗教儀式。後來,他在哈桑上中學,學校離高席卡大約四、五公里路程。他的家人都沒學過瑜伽,也一點興趣都沒有。在那個時代,瑜伽在印度被視為僧侶、苦行僧(sadhus)和棄絕物質生活的隱士(sannyasins)所練習的秘傳功夫,並不適合有家庭的人修習,因為練習者可能會對俗世失去興趣,甚至捨棄家庭。
瑜伽聖典《博伽梵歌》(Bhagavad Gita)中,奎師那(Krishna)提到,唯有上輩子修行過瑜伽的人,這生才會接觸瑜伽,而且會像磁鐵一般,情不自禁的被深深吸引——古儒吉常常引用這段文字。或許就是受到了這樣的吸引力,古儒吉才會接受朋友的邀請,在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到十一月間,去哈桑中學的會議廳聽演說,並觀賞體位法示範。他當下就對體位法震懾住了,由衷的景仰那瑜伽行者強健有力、優雅自得的在動作間跳躍穿梭。雖然他聽不懂演說,後來也花了很長的時間才了解了瑜伽的哲學理論,但是他知道他喜歡瑜伽,於是下定決心要自己學習。隔天清晨,他很早就起床,前往那瑜伽行者住的地方。當時他才十二歲,無所忌憚的拜託那位瑜伽行者教他瑜伽。瑜伽行者冷冷的問他,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你爸爸是誰?他做什麼的?喬艾斯一五一十的回答後,瑜伽行者叫他隔天再來。從此以後,他就展開了與偉大的瑜伽行者奎師那馬查利亞長達二十五年的修習。
喬艾斯在高席卡追隨奎師那馬查利亞修習兩年,每天不間斷的練習體位法。他當時很年輕,身體的柔軟度也很好,很快就學會了所有的動作。奎師那馬查利亞很高興,常常派他幫忙示範。喬艾斯從來沒有告訴過家人他練習瑜伽,他總是很早起床去練習,練習完才去上學。一九三○年,喬艾斯的父親為他舉行婆羅門的成年禮,大約就在這時候,奎師那馬查利亞離開了高席卡,繼續去各地教授瑜伽;不久之後,古儒吉也離開高席卡,去麥索的梵文學院唸書(maharaja’s Sanskrit College)。他當時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計畫,口袋裡只有兩塊盧比。頭一、兩年,他每天四處乞討,寄住在朋友的宿舍裡。過了三年,他才寫信告訴他父親他在哪裡。一九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間,喬艾斯一直待在學校鑽研梵文和《吠陀經》,後來又繼續擔任教職,教授吠檀多學派(Advaita Vedanta)的哲學理論。他一直在學校教書,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全心全意在自己的瑜伽教室裡教瑜伽。
一九三一年,他和奎師那馬查利亞重逢了,也和麥索的君王搭上線。當時喬艾斯並不知道哪位大師要來梵文學院表演瑜伽,只想著前去觀賞,去了才驚訝的發現那瑜伽行者正是他的老師奎師那馬查利亞。他很開心的拜倒在老師的足下,當時麥索君王派來的大臣也在現場。那位麥索君王叫做奎師那.拉真卓.沃迪亞(Krishna Rajendra Wodeyar),他一心嚮往瑜伽與靈修。他染上重病,聽聞大臣提起有瑜伽行者來訪,立刻派人請他入宮。奎師那馬查利亞博學多聞,又通曉瑜伽療癒,不久就把連醫生都束手無策的病症治好了,於是君王資助奎師那馬查利亞,還在王宮裡為他蓋了一座瑜伽學校,所以奎師那馬查利亞就在麥索待了二十二年。
君王大力推廣瑜伽,派奎師那馬查利亞、古儒吉和其他瑜伽教室的學生去印度各地表演體位法、研讀經典,並研究不同派系的瑜伽。古儒吉曾說,他在印度旅行這麼多年,從來沒見過任何人像奎師那馬查利亞一樣博學,通悉正統的瑜伽練習方式。
君王很喜歡看體位法表演,有時候會召古儒吉和他的同學瑪哈德.巴特(Mahadev Bhatt)入宮。晚上十點的時候,官員會來到他們的房間裡,指示他們隔天四點入宮為君王表演。古儒吉和巴特凌晨三點就會起床,洗個冷水澡,等候王宮的馬車來接他們。君王會告訴他們他想看什麼動作,他尤其喜歡公雞式(Kukkutasana)和烏鴉式B(Bakasana B)。隨後,君王自己也會做一些體位法,最後再派車送他們回去,並塞給他們三十五、四十或五十盧比;以當時而言,這是非常大的金額。他告訴他們:「把錢收好,不要告訴老師。」某一年,君王生日的時候,他還送古儒吉和巴特猴神哈奴曼所穿的絲質短褲表演。古儒吉每次談到君王,還是對他的仁善讚不絕口。
古儒吉偶爾會協助奎師那馬查利亞教學,如果老師遲到了,他就代為上場。君王偶爾也會去瑜伽教室練習,所以發現喬艾斯偶爾會代課;一個星期之後,就派他去梵文學院教瑜伽。古儒吉告訴君王,他來麥索是求學的,但君王提出了優渥的待遇,還願意供給他念完大學,並包辦一切食宿。當時古儒吉以乞討為生,所以也不想放棄這個好機會。他告訴君王,他得先獲得奎師那馬查利亞的祝福,才敢獨自教課。後來,喬艾斯於一九三七年三月開始在梵文學院教瑜伽。每次有人問他是否有教學證書,他總回答有,而且合格考試還很困難:奎師那馬查利亞把一個病人交給他,跟他說:「把他治好!」
古儒吉常常提到一本叫做《瑜伽崑崙塔經》(Yoga Korunta)的典籍。據說那是阿斯坦加瑜伽的古老手稿,奎師那馬查利亞教他的瑜伽練習都以那本著作為依歸。它是由一位叫作梵馬納(Vamana)的聖者所撰寫。奎師那馬查利亞曾追隨他的老師拉瑪.摩漢.班馬查利(Rama Mohan Brahmachari)學習七年半,在這段期間裡,拉瑪.摩漢.班馬查利以口傳的方式把書中的智慧傳承給他。「崑崙塔」(Korunta)字面上的意思是「組合」,據說這本經典探討的就是各種體位法之間的變化組合、最古老的串聯(vinyasa)、凝視點(dristi)、鎖印(bandhas)、手印和身印(mudras),以及哲學理論。奎師那馬查利亞於一九二四年左右開始教課,在他教課之前,有人告訴他加爾各答大學圖書館藏有這本典籍。古儒吉從未懷疑過《瑜伽崑崙塔經》的真實性。據他表示,當時那本書已經斑駁破裂,也缺了很多頁,但奎師那馬查利亞還是在加爾各答鑽研典籍很久。一九二七年,古儒吉開始追隨奎師那馬查利亞學習,學的就是《瑜伽崑崙塔經》中的練習方法。儘管這本書現在已經不可考,但是一般人還是相信帕達比.喬艾斯所教的阿斯坦加瑜伽就是出自《瑜伽崑崙塔經》。
一九四八年,古儒吉在拉施密普蘭(Lakshmipurum)的家中創立了阿斯坦加瑜伽研究機構(Ash¬tanga Yoga Research Institute),一心把古老經典和奎師那馬查利亞教給他的瑜伽療癒發揚光大。當時那個房子只有兩間臥室、一個廚房,和一間衛浴。一直到一九六四年,他才在房子後面蓋了瑜伽練習廳,並在二樓加蓋休息室。
約莫就在這時候,有一個叫作安德烈.范里斯白(André van Lysebeth)的比利時人遇到了喬艾斯。范里斯白懂得梵文,他花了兩個月時間,和古儒吉學一級和二級的體位法。他寫的其中一本書叫做《生命能控制呼吸法》(Pranayama),裡面提到了古儒吉的名字、地址,和一張相片,於是古儒吉的名字透過范里斯白的書傳到了歐洲,後來有一些歐洲人也陸陸續續來印度向古儒吉學習。一九七三年,古儒吉的兒子滿祝(Manju)去斯瓦米吉塔南達(Swami Gitananda)位在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修行所表演之後,美國人也來了。
古儒吉在瑪麗.海蓮娜.巴斯提朵(Marie Helena Bastidos)的邀請下,第一次來到西方,參加一九七四年在南美所舉行的瑜伽大會,當時他以梵文演說,還被譯為多種語言。一九七五年,他和滿祝去加州旅行時,常在不同的場合上說:「現在美國只有二、三十個學生練習阿斯坦加,但是漸漸的、漸漸的,二十年之內,一定會廣泛的流傳開來。」後來三十年間,他多次旅遊美國,教學也逐漸開花結果,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現今瑜伽在美國的普及與風行。
古儒吉把他的部分瑜伽知識,以著作和照片的方式傳承給我們。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這本簡短的書籍《瑜伽瑪拉》,它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清楚明瞭的解釋阿斯坦加瑜伽的練習方式。古儒吉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以手寫的方式編著,他總利用下午家人休息的時候抽空工作,花了兩、三年時間才完成手稿;一九六二年,首次由他在庫格(Coorg)的咖啡農學生幫忙印刷出版。英文書名中的mala,在梵文中是串聯的意思。印度的串聯有許多種含義,其中一種是念珠(japamala),它以聖珠穿線製成,可以讓人在念經唱咒的時候計算次數、保持專注;另外它也有花環(pushpamala)的意義,印度人會把芬芳的鮮花串成花環,放在家裡或寺廟中敬拜神明。古儒吉提出了另一種串聯,它古老傳統,神聖如祈禱,芬芳如花環。他所指的就是瑜伽體位法的串聯,每個呼吸和動作的連結(vinyasa)就像聖珠一般具體可數,讓人專注其中;每個體位法(asana)就像鮮花一樣,以呼吸的細線連結成串。我們把念珠戴在脖子上,把花環套在神像上,而瑜伽的串聯也具有相同的意義;當我們認真、專注的練習時,我們的生命就會散發出平和、健康、光彩,最後進而探掘真我。
英譯者盡可能在寫作風格、文本意義上忠於原著。古儒吉後來也重新寫過部分章節,修改了些許錯誤,並另外加了一些內容。舉例來說,最早的原文中並沒有提到開腿前彎式 D(Prasarita Padottanasana D)和頭碰膝蓋式 B 和 C(Janu Shirshasana B & C),本書中都有介紹。書中部分篇章經過重寫,並加上註腳,以讓讀者更容易明瞭。每個修改、加註的地方,都經過古儒吉的審核、同意,他也以口述的方式提供 許多更多完整的資訊。
古儒吉不顧當時旁人的眼光,把生命奉獻在瑜伽教學上。或許正因為知道家人會反對,所以他沒有告訴他們他當時練習瑜伽,沒有留下隻字片語就獨自去了麥索。也許他知道家人會抗議個沒完沒了,試圖和他說大道理。但是古儒吉沒有絲毫的懷疑。他從未停止過教學,不為金錢、不為名利,儘管他最後自然而然的名利雙收。帕達比.喬艾斯正代表了無私的奉獻,他燃燒自己,照亮了瑜伽的傳統智慧。
艾迪.史登(Eddie Stern)
紐約市
二○一○年三月十日
[前言]
瑜伽練習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如今它不只在我們國家逐漸獲得認同、尊重,還在西方國家發揚光大,我為此深感榮幸。許多經典文獻,例如古典史詩、吠陀經(Vedas),以及神話傳說都顯示瑜伽自古就存在於印度。我們也知道,隨著時代的更迭、變遷,它也歷經低潮。然而,瑜伽的智慧對所有人類來說仍然不可或缺,不管男男女女。
許多人對於瑜伽這一門科學有偏岐的見解,但是這種現象在近代慢慢有了改變。舉例來說,有人說瑜伽只是體能訓練,沒有其他的好處,也有人認為它是修行人或獨身者練的功夫,有家庭的人應該避免練習,甚至有人對瑜伽練習充滿恐懼。這樣的觀點就像不知道糖有多甜,就在糖罐裡挑毛病一樣。一旦人嘗過糖的美味,就會體會到它的甘美。同樣的,一旦學習了瑜伽,我們就會感受到其中的喜樂(ananda)。
然而練習瑜伽的過程中,我們還是會常常被懷疑、誤解所干擾,導致我們的心智、感官疲弱,最後陷入生與死的苦難、折磨中,看不到真理或是內在富裕的靈性。我們應該研讀經典,相信《博伽梵歌》中奎師那所說的:「因此,神聖的教誨可以幫助你決定該做什麼又不該做什麼(Tasmat shastram pramanam te karya akarya vyavasthitau)。」只要練習瑜伽這一門科學,一定會對人類有助益,也會為現在、未來帶來快樂。如果我們持續、正確的練習,我們就會獲得身、心、靈的喜悅,也會更接近真我。我就是懷抱著這樣的盼望,寫了這本書。
滿懷感謝
帕達比.喬艾斯
一九九七年九月於麥索
[摘文]
Sri Gurum Gananatham cha
Vanim shanmathuram tatha
Yogeshwaram Sri Harim cha
Pranat’osmi moohoormuhu.
我向恩典的上師和象神致敬
我向智慧女神和戰神致敬
我向瑜伽的濕婆神和奎師那致敬
我一次次拜首
(來源:傳統禱詞)
Vande Gurunam charanaravinde
Sandarshita svatmasukhavabodhe
Nishreyase jangalikayamane
Samsara halahala mohashantyai.
我拜倒在上師的蓮花足下
上師啟發內在真我的快樂
他宛如叢林醫生,無人能及
讓我解除經驗的毒害
(來源:商羯羅[Shankaracharya]所作的 Yoga Taravalli )
瑜伽練習對印度人來說並非新鮮事。它是一種高貴、無欲的行動,正派剛直,經過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不曾中斷,從亙古以來就一直存在。我們的史詩中有許多故事敘述印度人靠著瑜伽練習獲得神性,古書典籍也強調瑜伽的重要性,還說它是其他科學的根基。然而,現在很多人自稱印度的高貴子民,卻從未聽過瑜伽智慧(vidya),實在令人惋惜。很久以前,在印度的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有人練瑜伽,然而現在大家只追求物質享樂,把瑜伽拋在腦後。每個人的行動不同,獲得的果也就不同;有人修行瑜伽,有人追求愉悅享受,或是體驗病痛。沈溺於愉悅享受,就勢必會染上病痛。有人認為愉悅享受是幸福的,這當然可以理解,但是當你體驗到病痛的時候,你還會說這樣很幸福嗎?
我們來談談瑜伽的真義。我們常常在生活中聽到這個詞,經典文獻、《奧義書》、《瑜伽經》也常常提到它,但是我們似乎還是不能精確的了解它的意思。我們只了解瑜伽的其中一個面向,也就是體位法(asana)和呼吸法(pranayama),這對嚴格的獨身者(brahmacharis)和隱士(sannyasins)很有幫助,但是對一般人卻未必能獲益。但是如果我們更正確的研讀經典,了解其中意義,細細思索,我們就會了解瑜伽真正的意涵。
那麼瑜伽是什麼?這個字有很多意義:關係、方法、結合、知識、物質,和邏輯等。我們姑且說瑜伽是道(upaya),是我們達到目的的途徑或手段。那麼我們該遵循怎樣的道?我們又希望能到達什麼目的?或是找到誰?我們的心智自然會往最好的方向尋找,就好像僕人會想伺候國王,學生會想找最好的老師,妻子會想找理想的先生,我們的心智也會找尋真我(Universal Self)。這也是一種連結。僕人謹守規範,恭敬的伺候主人,最後獲得了主人的認同與祝福,自己也會晉升王室;學生勤奮向上又有慧根,一定會獲得老師的提拔,最後變成一位好老師;妻子賢良淑德,對丈夫忠心不二,也自然會跟丈夫合而為一;同樣的,我們的心智若想要追求真我,最後就會與真我結合。因此,與真我結合的方法就叫做瑜伽。為瑜伽奠定根基的聖者帕坦加里(Patanjali)有一句經典名言:「瑜伽就是終結意識分野的過程(Yoga chitta vritti nirodhaha)。」
我們的感官很自然會想捕捉它們能接收的事物。如果我們的感官與心智合一,或是如果我們把心智放在感官上,我們就會知曉、察覺到外界事物。如果我們的心智和感官之間沒有接軌,我們就不會察覺到外界,所以我們的心智是所有感官的基礎。而瑜伽就是把我們的心智導向真我、同時避免心智追求外界事物的方法,就如《卡達奧義書》(Katha Upanishad)中所說的:「瑜伽就是讓感官穩定的靜止下來(Tham yogam iti manyante sthiram indriya dharanam)。」把感官導向內在真我、避免它往外摸索的方法就是瑜伽。因此,瑜伽這個詞代表的就是把內在本質發揚光大的道。
我們接下來要問自己,單單了解瑜伽字面的意義是否可能讓我們了解它的真實本質。如果我們只研讀瑜伽經典,只了解瑜伽字面的意義,只與別人思辯練習瑜伽的利弊,我們不可能完全了解瑜伽。因為儘管你對於各國料理的知識瞭若指掌,也無法消除饑餓感;同樣的,如果只了解瑜伽練習的道理,絕對無法完全獲曉瑜伽的好處。所以,經典文獻只是為我們指引一條明路,而我必須清楚了解它,然後付諸實踐。我們從練習中獲得力量,並從中學習控制我們的心智和感官,這樣才能到達瑜伽的境界。因為唯有控制我們的心智和感官,我們才能把心智導向自己最真實的內在。知識無法讓我們達到這樣的目標,穿上瑜伽行者的裝束也無濟於事。
因此,有心追求瑜伽的人應該追隨好的老師,持續穩定的練習,或許在脫下這肉身皮囊之前,能夠找到那至高、祥和、永恆、恩惠的內在真我,與創造、保護、毀滅宇宙的能量合一。否則的話,這世界對人來說,不過就是一場磨難而已。
我們要怎樣讓心智專注在一點上,好看到真我呢?這就是阿斯坦加瑜伽要教導我們的。阿斯坦加在梵文裡的意思是「八支」,又作八步功法,其中包括:持戒(yama)、精進(niyama)、體位法(asana)、生命能控制呼吸法(pranayama)、感官收攝(pratyahara)、心靈集中(dharana)、冥想(dhyana)和三摩地(samadhi)。
[序文]
帕達比.喬艾斯(1915-2009)生於印度南部卡納塔克省(Karnataka)哈桑(Hassan)的小村莊高席卡(Kowshika),他出生那天正是七月的滿月。古儒吉在高席卡度過了十三年,那小村莊至今仍然維持著當年的模樣。過去和現在,那裡都住著六七十戶勤奮工作的家庭,圍繞著三座古老的寺廟生活。一九八○年代開始,高席卡才有電;古儒吉年幼的時候,那裡有腳踏車的就算是有錢人了。
古儒吉的父親是占星學家、祭司,也是地主,母親負責家務,照顧九個孩子,五女四男,而帕達比.喬艾斯排行第五。他和所有婆羅門的小男孩一樣,從五歲開始,就...
目錄
台灣版翻譯說明
夏勒斯作序
艾迪.史登作序
前言
持戒
精進
生命能控制呼吸法
拜日式與瑜伽體位法
手抓腳趾前彎式(Padangushtasana)
腳踩手掌前彎式(Padahastasana)
三角式(Utthita Trikonasana)
側角式(Utthita Parshvakonasana)
開腿前彎式(Prasarita Padottanasana)
(A)
(B)
(C)
(D)
側身延展前彎式(Parshvottanasana)
手抓腳趾延展式(Utthita Hasta Padangushtasana)
半蓮花抓腳前彎式(Ardha Baddha Padmottanasana)
坐椅式(Utkatasana)
英雄式(Virabhadrasana)
西方延展式(Paschimattanasana)
東方延展式(Purvatanasana)
半蓮花抓腳西方延展式(Ardha Baddha Padma Paschimattanasana)
單跪腿西方延展式(Tiriangmukhaikapada Paschimattanasana)
頭碰膝蓋式(Janu Shirshasana)
(A)
(B)
(C)
聖者馬里奇式(Marichyasana)
(A)
(B)
(C)
(D)
船式(Navasana)
夾上臂式(Bhujapidasana)
龜式(Kurmasana)
子宮胎兒式(Garbha Pindasana)
公雞式(Kukkutasana)
束角式(Baddha Konasana)
坐姿開腿前彎式(Upavishta Konasana)
睡姿開腿前彎式(Supta Konasana)
睡姿手抓腳趾前彎式(Supta Padangushtasana)
併腿手抓腳趾前彎式(Ubhaya Padangushtasana)
向上西方延展式(Urdhva Mukha Paschimattanasana)
橋式(Setu Bandhasana)
肩立式(Sarvangasana)
鋤式(Halasana)
膝蓋夾耳式(Karnapidasana)
向上蓮花式(Urdhva Padmasana)
胎兒式(Pindasana)
魚式(Matsyasana)
併腿延展式(Uttana Padasana)
頭倒立式(Shirshasana)
束腳蓮花式(Baddha Padmasana)
蓮花式(Padmasana)
上提(Uth Pluthi)
英譯者致謝
台灣版翻譯說明
夏勒斯作序
艾迪.史登作序
前言
持戒
精進
生命能控制呼吸法
拜日式與瑜伽體位法
手抓腳趾前彎式(Padangushtasana)
腳踩手掌前彎式(Padahastasana)
三角式(Utthita Trikonasana)
側角式(Utthita Parshvakonasana)
開腿前彎式(Prasarita Padottanasana)
(A)
(B)
(C)
(D)
側身延展前彎式(Parshvottanasana)
手抓腳趾延展式(Utthita Hasta Padangushtasana)
半蓮花抓腳前彎式(Ardha Baddha Padmottanasana)
坐椅式(Utkatasana)
英雄式(Virabhadrasana)
西方延展式(Pas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