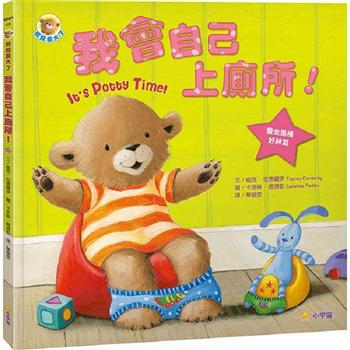年輕女孩古明心在母親驟然去世後,面對人生的轉折點:她應繼續原來的生活,或者追尋文學的夢想?在母親的遺物中,她發現了一枚戒指、幾封母親與作家三毛往返的信件,與一本母親留下的小說手稿——撒哈拉之心。她決定前往北非,為母親走一趟傳奇作家居住的撒哈拉沙漠。
小說以愛情為主題,運用蒙太奇雙線交插敘述手法,重現了作家三毛當年在西屬撒哈拉的生活,而沙漠的革命戰爭及驚世的愛恨情仇,都在狂風飛沙的場景中逐漸登場;作家三毛與荷西的愛情、古明心母親的黯然之戀、明心本人即將在旅途面對的情感抉擇,也在廣袤與絢麗的沙漠中冉冉展開。
故事以北非、西班牙和加納利群島為主要背景,時間在一九七○與現代之間穿梭,以書中書的形式,訴說三毛的愛情與寫作,呼應荷西沉迷於潛水的自由,拉近了古明心與母親最遙遠的距離,「所有的旅途最終都是為了明瞭自身」,《撒哈拉之心》是探索自我成長的心靈之書,媲美麥可.翁達傑的《英倫情人》,也是作者繼暢銷書《徵婚啟事》及文學獎小說《海神家族》之後,又一部重量級作品。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撒哈拉之心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4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撒哈拉之心 出版社:大塊文化 出版日期:2016-05-26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60頁 / 14 x 20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62 |
小說/文學 |
二手書 |
$ 170 |
二手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圖書名稱:撒哈拉之心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陳玉慧(Jade Y. Chen)
早年在法國學習戲劇, 後旅居德國,寫作領域包含小說、散文、劇本和評論。文學創作之外,曾為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等新聞媒體擔任特約撰述,亦從事戲劇和影視策劃工作。
小說作品《徵婚啟事》曾多次改編為電影及舞臺劇和電視影集,是長年暢銷書。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海神家族》曾獲得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第一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以及臺灣文學館金典獎,該小說亦曾由作者本人改編暨導演,在臺北國家劇院演出。該書德文譯本(Die Insel der Göttin)於2008年出版,日文譯本(女神の島)於2011年出版。該書並獲選兩岸三地合辦的 「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票選第三名。
以姿器與愛情為題的長篇小說《china》(又名瓷淚),書寫中西瓷藝史上一段祕辛,德譯本(Die Tränen des Porzellans)已出版,同名音樂劇則於2014年於臺灣巡迴演出。
陳玉慧(Jade Y. Chen)
早年在法國學習戲劇, 後旅居德國,寫作領域包含小說、散文、劇本和評論。文學創作之外,曾為德國《法蘭克福廣訊報》等新聞媒體擔任特約撰述,亦從事戲劇和影視策劃工作。
小說作品《徵婚啟事》曾多次改編為電影及舞臺劇和電視影集,是長年暢銷書。帶有自傳色彩的長篇《海神家族》曾獲得香港浸會大學主辦的第一屆紅樓夢獎決審團獎,以及臺灣文學館金典獎,該小說亦曾由作者本人改編暨導演,在臺北國家劇院演出。該書德文譯本(Die Insel der Göttin)於2008年出版,日文譯本(女神の島)於2011年出版。該書並獲選兩岸三地合辦的 「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票選第三名。
以姿器與愛情為題的長篇小說《china》(又名瓷淚),書寫中西瓷藝史上一段祕辛,德譯本(Die Tränen des Porzellans)已出版,同名音樂劇則於2014年於臺灣巡迴演出。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
| |||
|
|

 2016/07/11
2016/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