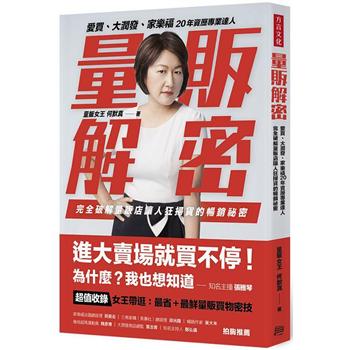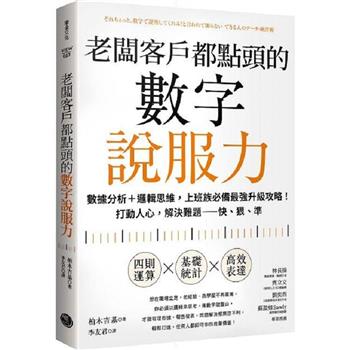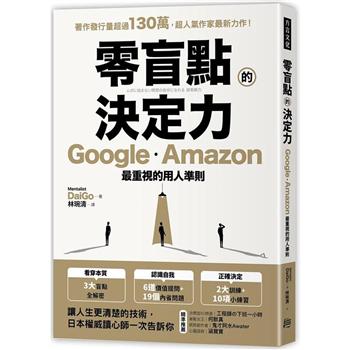他看著筆電螢幕上模糊的倒影,朦朧不清的臉龐困在濃密的文字後方。他調整光線的角度,頭部前後傾斜幾度,讓影像出現層次和立體感。他喜歡這樣調整影像,讓自己的頭像如月亮盈虧一般,先來到新月的尖角,再送回地下世界的邊緣。
他邊讀著今天所撰寫的內容,邊用右手食指指尖輕拍著人中。
我們這一行不同於其他專業領域,無法在低潮時到打擊場練習揮棒,也不能藉由閱讀法律期刊吸收新知。你會失去對某些東西的感覺,最重要的是,失去掌握他人恐懼的能力。
他背後傳來一陣黏液阻塞的聲音。他一直認為恐懼使人發出動物般的聲音──極度恐懼而無助的人類所發出的嘶啞叫喊聲、受傷的狗兒與被困在鐵製陷阱裡的熊所發出的哭號全都大同小異。他沒有轉身,決定再等一會兒。
他有一種詭異的感覺。在這一刻,所有能測量、量化的一切看似沒有不同,包括這個事件、他所扮演的角色、所需要的技巧與工具──彷彿只經過了一天,而不是十個月的手術與復健。然而,如今他卻身處時間的軸心,一切重新來過。如果可以為自己照一張X光片顯示情緒的樣貌,拿來和去年七月四日發生事件前拍下的影像比較,他很確定不會有類似之處:丘陵會變成高山,滴水會累積成河,縫隙會成為峽谷。地球,X星球。
他起身走到一張老舊而斑駁的橡木桌前。為了這趟重新開始的人生,他希望使用來自大自然,但經過人工雕琢的物品。他低頭凝視排列在桌面上那些恐怖的工具。那三點鐘的陽光就早春而言過於強烈,透過天窗灑落在桌面上,使這些工具彷彿熔解中的金屬般染上一層黃銅亮光。
他接受了兩次重建手術,但醫生認為受傷範圍實在太大,就算進一步的手術也無法改善他的傷勢;可是,當他們提出另一個選項時,他感受到這一刻的黑色諷刺裡透露著完美的承諾。他不只將被重新打造,也會重塑自己的內在──拓展極限、提升容忍度。金錢不是問題,他已存下足夠一輩子花用的數目。當他完成此事之後,所有無法忍受的痛苦都將消失。
他用兩架攝影機完整紀錄過程,復原後,他花了數百個小時看這些影片,研究每一次下刀和每一刀所切斷的連結。手術後的幾個月裡,他每天只允許自己貼兩張五十微克的強效止痛貼片,體驗到痛徹心扉的感官知覺。他對生理痛苦的理解大幅改變,足以媲美醫生的成就。
他從桌上拿起那把賀瑞修.肯恩公司於一八六七年出產的一體成型手術刀。他試過拋棄式刀片與塑膠刀柄的大量生產手術刀,可是那些刀子重量太輕,造成問題,因此他要人找來更有分量的手術刀。肯恩的黑檀把手較有分量,比較好拿。剛開始他拿兔子練習,等基本技巧純熟之後才從附近農場運來豬隻。他的醫生說,動物的皮下脂肪和真皮層厚度與人體相近,這是他能找到最接近實物的東西。
一陣熟悉、沙啞的嗡嗡聲使他抬起頭。一隻五公分長的超大黃蜂鑽過紗窗上的洞,飛進屋裡,降落在窗臺上的一片白桃上,那正是他刻意放在那裡引誘它的。
他放下手術刀走到窗前,看到灰色、粗糙、比健身球還大的巨型蜂窩固定在室外的屋簷下,一旁的棚子裡停著布滿灰塵的汽車。這些昆蟲的來訪對他生活裡的例行公事很有幫助。大黃蜂探索著桃子時,他以大拇指和食指指尖朝下輕輕抓住那輕薄的翅膀,提起掙扎、瘋狂發出嗡嗡聲的昆蟲。長時間下來,這個動作有助於磨練雙手細部的行動力與手眼協調功能。他照例用兩指指尖握住黃蜂肥大條紋的腹部,慢慢按到它爆開,此舉有助練習施力感,這種能力很難重新掌握。第一隻大黃蜂飛進來時他正用葡萄練習,後來他發現這生氣勃勃的生物對他的觸摸既敏感又有反應,比水果好用多了,因此開始在窗臺上放一片桃子。這幾個月來,打掃的女傭進門後總發現地上躺著一堆乾癟的蟲屍。
他看著這生物抽搐,生命力卻毫不減弱。渾濁的咕噥聲又出現,時候到了,重新開始的時候到了。他轉身穿過房間,他的偵訊對象坐在一張高背椅上,身上披著寬鬆的藍色手術罩衫,遮蓋了身體曲線;頭上蓋著同樣布料做的臨時頭罩,嘴巴和眼睛處各挖了洞,但嘴巴用黑色膠帶貼住;脖子、手腕、腰部和腳踝分別用塑膠束線帶固定在椅子上。
他彎身湊近對方的臉,皺起眉頭:對方眼神中的恐懼還不夠。他舉起發出嗡嗡聲、掙扎著的大黃蜂說,「很大隻對不對?」
頭罩裡的眼睛瞪大,瞳孔發亮。
「根據我在谷歌上搜尋來的研究資料顯示,這可能是大虎頭蜂,一種亞洲的巨大黃蜂,最毒的那種。據說,受到這種蜂群攻擊只要幾分鐘就足以喪命……過敏反應導致休克──可是,我猜不透這裡怎麼會有。」
他舉起另一隻手的食指說,「你看,」接著用食指戳了一下大黃蜂扭動的腹部,它的腹部尾端立刻向內彎曲,零點六公分長的螫針滑出來戳進他的指頭裡。他毫無反應,也沒有退縮。
他的觀眾疑惑地揚起右眉。
「黃蜂家族和蜜蜂家族之間最有意思的差異在於……蜜蜂刺一次之後螫針就會倒勾進體內斷掉,接著蜜蜂就沒命了。可是大黃蜂的螫針沒有倒勾,可以不斷重複地刺。」他用手指戳戳大黃蜂的腹部,大黃蜂又刺了他一次。「看到了嗎?」他把頭罩的下緣往上拉一些,「這只是讓你放鬆一點,減少腎上線素分泌。」他看著對方用力吞嚥,喉結上下移動,鬆手把大黃蜂放進頭罩裡,「除非遭到挑釁,否則它們並不特別具有攻擊性,不過你最好不要亂動。」
惡毒的嗡嗡聲突然停止,由於大黃蜂體型龐大,他可以清楚看到它在布料底下移動,從臉頰往上爬。頭罩裡的眼睛瞪著前方,沒有眨眼,也沒有對焦,彷彿在回想某人的名字或即將來臨的約會日期。接下來,黃蜂越過左眼繼續往上爬,囚徒緩緩閉上顫抖的眼皮。
在一扇窗外,盛開的野生薰衣草彷彿一片紫色波浪海洋,突如其來的動靜使站在囚徒前的男子抬起頭,他看到十幾條顏色鮮明、閃閃發亮的毒蛇從花叢裡往上跳,以懸空而優雅的拱型姿勢互相攻擊,乳白色的尖牙閃爍著紅光。他看著僅存的那一隻,那血跡斑斑、勝利的生物轉身好奇地瞪著他。
「很好,」他說,「過來這邊。」
那窮兇惡極的毒蛇朝他滑行過來,他閉上眼睛,已經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幻覺。他無法控制這些幻覺的發生,但發現只要緊閉雙眼就能使其消失。他知道這些幻覺是某種精神失常轉化而成的視覺效果。在他的思維裡,這種心理違常是異常催化反應的結果,逐漸將疼痛與苦難合成為新的化學成分,已經如其他的心理元素(愉快、恐懼、憤怒)一般成為他大腦的一部分,這些元素催化了腎上腺素或血清素或一種名為紐初芬的荷爾蒙,當這個新的成分出現時便會引發幻覺。
這種幻覺已經出現很多次了:他看過診所的貓身上長出鐵製長釘;林恩醫師在討論合成—有機聚合體時面孔爆炸;撥開洋蔥湯表面那層融化的葛瑞爾乳酪之後,七彩熱帶魚在湯裡活繃亂跳;他也看過天使從天而降,燃燒的翅膀在背後留下一陣煙霧。這個預兆顯示他的直覺並非妄想,而且正好相反,他那難以對付的對手還活著,當他們再度見面時,他這極端的選擇會得到回報。
他會這麼相信是因為那降臨的天使有著蓋格的面孔。
蓋格。
他睜開雙眼,用平滑而全無毛髮的雙手撫摸臉龐,七月四日事件在腦海裡重演,眼底閃過一幕幕敏銳的細節。那並不是記憶,而是已經成為一種永恆存在的意識:
一通來自地獄的電話告知任務的對象,居然是傳奇人物蓋格,他們這一行的大師,人們稱為偵訊師……他知道後脈搏變強。
在蓋格自己的地頭執行……把他綁在理髮椅上,逼問霍爾唯一提出的問題──那個男孩在哪裡?……用燒得白熱的錐子刺穿蓋格的臉頰……用球棒打他……割開他的四頭肌──但蓋格頑強抵抗,不願背叛他幾乎不認識的男孩,也不願意苦苦哀求或發出哀號,彷彿對凡人的痛楚免疫……
接著蓋格出手攻擊,主導局面,將他們兩人的逼供生涯宣告結束,把他的手指和掌骨都敲碎,指頭碎裂時發出清脆響亮的聲音,痛徹心扉,無法想像的痛……
從此以後,蓋格成了他宇宙的重心,如太陽般控制他所有的想法及所有的決定。蓋格在他身上灌輸了一種他從未感受過的知覺,剛開始只是一顆小小的種子,接著發芽,如今在他體內如信號般發亮著。起先是復仇,但如今已經超越復仇。
頭罩底下的突起物在耳朵旁的部位微微移動。他輕輕一拍,那東西嗡嗡作響、抽搐,被捆綁的被害人突然身體僵硬,喉嚨發出被悶住的低吼聲,眼角流出眼淚。
「我有問題要問你。」
頭罩裡的雙眼緊閉,臉頰不由自主緊繃──大黃蜂又螫了一次。他的身體用力拉扯著綑綁之處,貼著膠帶的嘴巴發出更低沉的怒吼聲,彷彿是第一次怒吼的回聲。
「我叫你盡量不要動。」
他突然一掌打向被害人的太陽穴,對方的頭骨因重擊而顫抖,頭顱內部受到擠壓,頭罩裡頓時黑暗一片。他揮舞著古董手術刀,彎腰與對方面對面。
「這是我主要使用的工具,」他把工具放在被害人的掌心,「試試看,拿拿看,感覺很好,完美的平衡。」
頭罩裡那雙眼睛研究著男人,努力猜測他瘋狂的程度。
「命運的介入真是令人讚嘆不已,你知道──你和我……我們之間有共同的連結。」他抓住頭罩頂端拉掉,「你很可能已經知道我是誰了,不過還是讓我自我介紹。我是達爾頓。」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無名偵訊師(2):雙重告解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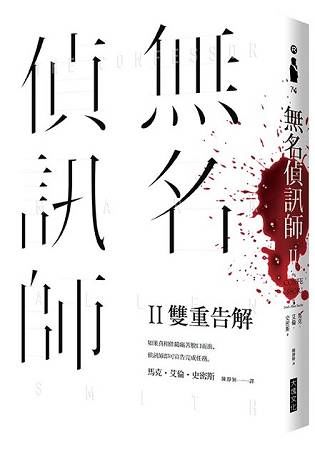 |
無名偵訊師(2):雙重告解 作者:馬克.艾倫.史密斯 / 譯者:陳靜妍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50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小說/文學 |
$ 253 |
小說 |
$ 282 |
中文書 |
$ 282 |
推理小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無名偵訊師(2):雙重告解
在情報擷取這一行,痛楚永遠會帶出真相!
判官、逼供之王,是CIA給他的代號,
無名偵訊師蓋格,是製造身心痛苦的專家,
沒有問不出的答案,找不到的真相。
兩位頂尖偵訊師的較量與復仇!
九個月前的七月四日,艾斯拉的父親大衛.馬瑟斯經營揭密網站,因為公布美國中情局在開羅刑求取供的光碟,中情局派達爾頓逼供艾斯拉,以抓到大衛,拯救中情局的名聲。偵訊師蓋格不忍年幼的艾斯拉承受酷刑甚至喪命,出手相救,將達爾頓打成重殘;自己也受了重傷,下落不明。人稱「獨立日大屠殺」。
復仇心切的達爾頓,外號「刑求者」;如果向來不出重手、傷人性命的蓋格是情報擷取界的陽,達爾頓就是陰。達爾頓布下重重密網,只為引誘蓋格上勾;並熟練從關節精準切下手指的刀法,準備讓蓋格親嚐情報擷取的正統流程:製造疼痛,構築痛苦,擷取真相……
作者簡介:
馬克.艾倫.史密斯 Mark Allen Smith
史密斯是一名成功的電視節目及紀錄片製作人兼編劇,他的首部系列小說《無名偵訊師》描繪稱為「蓋格」的爭議性主人翁,這首部小說的靈感來自他為知名的ABC電視台新聞雜誌節目「20/20」擔任調查工作的經驗,當時他參與調查的節目內容涉及巴拉圭這西半球最後一個真正的獨裁政權,發生於一九七〇年代,一名十七歲青年遭到殘暴刑求及謀殺的案件。另一個推動他實際行動的靈感來源是麗莎.史坦柏格遭養父凌虐致死的震驚案件,這起事件引發對兒童及無辜受害者生理及心理壓力嚴重影響持續性的關注。他的研究過程使他相信,為了讓他的故事能觸及最多的群眾,寫部小說是最好的方式。
譯者簡介:
陳靜妍
畢業於淡江大學英文系,現為專職譯者。
TOP
章節試閱
他看著筆電螢幕上模糊的倒影,朦朧不清的臉龐困在濃密的文字後方。他調整光線的角度,頭部前後傾斜幾度,讓影像出現層次和立體感。他喜歡這樣調整影像,讓自己的頭像如月亮盈虧一般,先來到新月的尖角,再送回地下世界的邊緣。
他邊讀著今天所撰寫的內容,邊用右手食指指尖輕拍著人中。
我們這一行不同於其他專業領域,無法在低潮時到打擊場練習揮棒,也不能藉由閱讀法律期刊吸收新知。你會失去對某些東西的感覺,最重要的是,失去掌握他人恐懼的能力。
他背後傳來一陣黏液阻塞的聲音。他一直認為恐懼使人發出動物般的聲音──極度恐懼...
他邊讀著今天所撰寫的內容,邊用右手食指指尖輕拍著人中。
我們這一行不同於其他專業領域,無法在低潮時到打擊場練習揮棒,也不能藉由閱讀法律期刊吸收新知。你會失去對某些東西的感覺,最重要的是,失去掌握他人恐懼的能力。
他背後傳來一陣黏液阻塞的聲音。他一直認為恐懼使人發出動物般的聲音──極度恐懼...
»看全部
TOP
作者序
[作者給讀者的話]
寫《無名偵訊師》時,我主要的目標是以新鮮、話題性的角度,描寫一個有重要性、曲折、吸引人的驚悚故事。我有超過二十五年的編劇經驗,也曾擔任紀錄片製作人及導演,我知道該如何說一個好故事。我一直崇尚形式,身為作家的我最喜歡的是投入經典的結構,看看我能如何改變,延伸,讓故事所傳達出的比讀者或觀眾所期待的還要多。對我而言,使《無名偵訊師》成為一本強而有力、充滿驚喜的小說是來自未經加工的情緒、角色的深度與驚悚小說的經典本質所交織的方式。
書中許多部分都會使讀者震驚及意外,莫過於此的就是主人翁...
寫《無名偵訊師》時,我主要的目標是以新鮮、話題性的角度,描寫一個有重要性、曲折、吸引人的驚悚故事。我有超過二十五年的編劇經驗,也曾擔任紀錄片製作人及導演,我知道該如何說一個好故事。我一直崇尚形式,身為作家的我最喜歡的是投入經典的結構,看看我能如何改變,延伸,讓故事所傳達出的比讀者或觀眾所期待的還要多。對我而言,使《無名偵訊師》成為一本強而有力、充滿驚喜的小說是來自未經加工的情緒、角色的深度與驚悚小說的經典本質所交織的方式。
書中許多部分都會使讀者震驚及意外,莫過於此的就是主人翁...
»看全部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馬克.艾倫.史密斯 譯者: 陳靜妍
- 出版社: 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27 ISBN/ISSN:9789862137352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416頁 開數:25開
- 類別: 中文書> 類型文學> 推理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