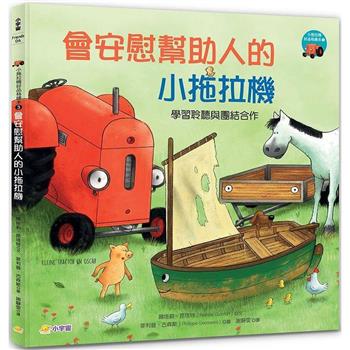★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赫拉巴爾:「我的作品實際上是我生活的注釋。」
★與《過於喧囂的孤獨》同時期完成的回憶錄小說
★赫拉巴爾逝世二十週年紀念版
我不曾料到年華逝去得如此之快。
真是還沒來得及回頭看一看,卻已經要拔去白髮了。
二次大戰結束後,捷克成為共產國家,赫拉巴爾的雙親弗蘭欽與瑪麗因此離開啤酒廠,最後還賣掉所有財產,搬進養老院,與佩平大伯一起在此度過餘生。這座由前伯爵莊園改建的養老院充滿各種驚奇:永遠停留在七點二十五分的大時鐘、戲劇性十足的壁畫、形形色色的老先生與老太太們,還有縈繞在院內、重複播放的優美樂曲〈哈勒根的數百萬〉。
瑪麗在養老院裡結交了三位朋友。他們猶如舊時代的見證人,總是圍在瑪麗身邊,告訴她小城的古老歷史。她喜歡在花園裡的十二月令神祇雕像之間流連,這十二座代表人的一生與春夏秋冬各季節的雕像,如同一部小說,讓瑪麗埋首其中,仔細觀察,體會什麼是人生、什麼是大自然的週期。
聖誕節的趕集消失了,人們在下午和傍晚散步的時代消失了,冬天的酒神遊行不再有了,裝飾小城最美窗戶的競賽沒有了。縱使美好的人與事都留不住了,但時光靜止的小城,仍被彎彎的河水和紅色的城牆環抱,米色啤酒廠的高聳煙囪、鐵皮屋頂依舊閃閃發亮。瑪麗的晚年生活就在這感傷又溫馨的氣氛下展開。
《時光靜止的小城》為【河畔小城三部曲】的第三本,由赫拉巴爾的母親瑪麗道出在養老院的生活。雖然已經年老,瑪麗自由不羈的性格依舊,旁人的眼光與批評無法動搖她,反而讓她對自己的生活態度更有信心。
作者簡介:
博胡米爾‧赫拉巴爾(Bohumil Hrabal)
捷克作家,生於一九一四年,卒於一九九七年。被米蘭.昆德拉譽為我們這個時代最了不起的作家,四十九歲才出第一本小說,擁有法學博士的學位,先後從事過倉庫管理員、鐵路工人、列車調度員、廢紙收購站打包工等十多種不同的工作。多種工作經驗為他的小說創作累積了豐富的素材,也由於長期生活在一般勞動人民中,他的小說充滿了濃厚的土味,被認為是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
赫拉巴爾的作品大多描寫普通、平凡、默默無聞、被拋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人」。他對這些人寄予同情與愛憐,並且融入他們的生活,以文字發掘他們心靈深處的美,刻畫出一群平凡又奇特的人物形象。赫拉巴爾一生創作無數,作品經常被改編為電影,與小說《沒能準時離站的列車》同名的電影於一九六六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另一部由小說《售屋廣告:我已不願居住的房子》改編的電影《失翼靈雀》,於一九六九年拍攝完成,卻在捷克冰封了二十年,解禁後,隨即獲得一九九○年柏林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二○○六年,改編自他作品的最新電影《我曾侍候過英國國王》上映。
捷克《星期》週刊於二十世紀末選出「二十世紀捷克小說五十大」,《過於喧囂的孤獨》名列第二,僅次於哈薩克(Jaroslav Hasek)的《好兵帥克歷險記》,其命運亦與《失翼靈雀》相仿,這部小說於一九七六年完稿,但遲至一九八九年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有人用利刃、沙子和石頭,分別來形容捷克文學三劍客昆德拉、克里瑪和赫拉巴爾,他們說:
昆德拉像是一把利刃,利刃刺向形而上。
克里瑪像一把沙子,將一捧碎沙灑到了詩人筆下甜膩膩的生活蛋糕上,讓人不知如何是好。
赫拉巴爾則像是一塊石頭,用石頭砸穿卑微粗糙的人性。
譯者簡介:
楊樂雲(1919~2009),一九四四年畢業於上海私立滬江大學英語系。曾先後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華大使館文化處,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長期工作,對捷克文學及其歷史文化背景深有了解,數十年來在這一園地辛勤耕耘,翻譯介紹過捷克許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包括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等。
章節試閱
在小城郊外,我的時間停止了的小城郊外,有一座大莊園,這莊園現在是領養老金者的養老院。通往這莊園只有一條爬上山岡的林蔭道,一條由成行老栗樹的樹冠從兩側架起的隧道,走在這條路上,就彷彿走在長長的哥德式拱頂底下。老栗樹的繁枝不僅搭在一起,而且相互纏繞,大風吹來,它們便結成一個整體。樹冠的枝葉為爭奪些許陽光,累得精疲力竭,枯萎了,因此道路上總是落滿因長期摩擦而斷裂的碳化了的枯樹枝。有時候,無風也會突然掉下一整截樹枝,打在沙地上。遇到這種情況,就像見到屋頂掉下一塊瓦,你把它拾起來扔到一旁,心情卻不免沉重:它有可能把你打傷啊。無論什麼時候,我踏上這條林蔭道,就對自己的生命不太有把握了。我舉目往前看,這條路約有五百公尺長,插進樹冠的黑色支撐木棍,看上去很像騎士比武得勝後舉起的梭鏢和長矛。我可以不走這條林蔭道,而走旁邊的一條小路,那裡樹枝幾乎垂到地面。從春天到秋天走這條小路是很愉快的,可以觀賞青翠的嫩葉和繽紛的繁花,夏末秋初可以目睹果殼裂開,棕色的栗子從殼裡蹦出來。可我還是喜歡走那條由黑嘛嘛的樹木構成拱頂的林蔭路,它的盡頭便是莊園的兩扇烏黑大鐵門,這兩扇門是藝術工匠用錘子和鉗子鍛造出來的,形狀有如被打下塵世的黑天使的兩個翅膀,大門只在探視日才打開。當你從林蔭道朝大門走來時,即使在陽光明媚的日子,這條路也光線昏暗。儘管四周遍地陽光,青枝翠葉,色彩斑斕,然而在這裡,你緩緩往上走,卻走進了地下墓穴的陰暗,隨時都會有黑樹枝突然掉下來。可是在莊園裡,鋪了細沙的幽徑和庭院,在陽光中卻顯得格外潔白,鑄在大門翅膀上的史博爾克伯爵的姓名首字母和族徽也映襯得黑亮醒目。這些字母就像弗朗茨寫在啤酒廠帳本上的飯店老闆的姓名首字母,總是寫成花體美術字,用紅色和藍色的墨水筆勾勒,猶如小書本封面上的首字母。大門旁邊,在最後那棵大栗樹下,有一座小屋,裡面坐著看守大門的人。即使在太陽當空的大白天,這小屋也亮著燈。林蔭道的陰影如此濃重,從春天到秋天,樹冠的枝葉把陽光完全遮蔽了。在這座小屋,我們這些安養的老人們輪流值班看守大門。在昔日的伯爵府看守大門,這可是令人肅然起敬的差事。每天十點鐘,每個在這裡看守華麗大門的人,一到十點鐘就完全變了。檢查每一個走進大門的人是莫大榮幸。因此,儘管有些人在這養老院裡床挨著床,就餐時並肩而坐,可在這大門口卻成了陌路人。看守大門的人會盤問來人為何來此,即使是朋友,一到十點,看守大門的人便會忘記所有同院人的面容,因此無論是誰想進門,都不僅要通報姓名,而且得出示證件以證明自己確實住在這裡。因而沿著林蔭道走上山岡的感覺是美好的,哪怕是一個普普通通領養老金的人,一個普通人,哪怕處境悲慘,疲憊不堪,但是在濃蔭中走上山岡,看到那巨大的鍛造精美的黑鐵門,那長矛似的桿子和矛尖,那能工巧匠打造的圓圈和翻騰的波浪。跨進大門的感覺是美好的,穿過花園,順著一條細沙鋪地、兩旁種著矮紫杉的道路走進庭院,看到那些跟我一樣也是領養老金的人,老頭老太太,散著步,一瘸一拐走著,相互觀察健康狀況,就這樣直至聽到呼喚吃早點、吃午飯,又是吃點心,直至最後吃晚飯。對我來說,每次突然來到莊園的門前,心頭總是美滋滋的,當陽光和燈光照耀時,這莊園就成了米黃色,牆上閃著光芒,顯得溫暖,令人眼花。直到過了一會兒,當你適應這種米黃色的光亮之後,你就會注視那碩大的時鐘,黑鐵板鍛造的鐘面滿滿地遮住了大樓三層和四層之間的那塊牆面。黑色的長短針是鍛工高手製作的,大得像魁梧壯漢。我第一次看到這鐘時,心裡不禁一驚,雖然當時是在午前,時針卻指在七點二十五分。從那時起,這裡時間就一直是七點二十五分,大鐘停了,已經沒有人會修理或者有理由修理它。說來可悲,它指著的永遠不動的時間在這莊園恰似Memento mori標誌,因為在這裡以及在這一帶,眾所周知,老人大多死於晚上七點半左右。當我第一次站在這裡,當我看到那些巨大的鑽天楊、橡樹和黑沉沉的雲杉高於這莊園的屋頂,馬蹄形的花園懷抱著端端正正建在朝南方向的屋宇,當我的目光回到正面牆上時,我看到這牆灰泥剝落。這裡那裡露出原來的牆面,那上頭好像裝飾著很大的文字,鐫刻在變硬的水泥上。由於莊園地處時間停止了的小城郊外的山岡上,我聽到風,不停呼嘯的風,刮得樹葉繞著房宇呼呼飛舞,百年老楊樹無風也瑟瑟顫抖,百萬張小葉子不停地掙扎著,想從百萬根樹枝上掙脫出來。我第一次來這裡,就注意到各個大廳都有陽臺,這些陽臺也像大門一樣,都出自藝術工匠之手,形狀有如透明的大浴盆,透明的、伯爵使用的雪橇,透明的帶篷馬車,豪華墳墓的小墓園,我看到安養的老人們坐在這裡曬太陽,他們沉默不語,一動不動,頭靠在裝飾著種花木槽的陽臺欄杆上;枯萎了的矮牽牛、曬黑了的金魚草和百日草從木槽裡掛下來。時鐘下面只見一雙耷拉著的手,癱軟疲憊的胳膊,耷拉著的手有如枯萎的花朵,白得耀眼的襯衫遮住了手腕。透過鐵欄杆,我可以看到一把椅子和坐在上面的某人的一雙分開的腿,身體則被綠色的木槽擋住看不見了。就在這時,大樓一側的一根排水管脫了鉤,它像十字路口的攔道木那樣緩緩落下,像大時鐘上的分針迅速落在一個點子上,然而這生鏽了的管子卻沒有落到地上,它掛在那裡搖搖欲墜,令人望而生畏,從管子裡撒下一地的鐵銹、鳥窩和枯樹枝。有時我想,莊園灰泥剝落的牆,實際上與這些年邁的安養老人們的臉很相似,而時鐘停在七點二十五分,這也像放在膝蓋上的手。我從灰泥剝落的地方,看到原來這牆是大塊砂岩和黏板岩用粗灰泥砌成的。每一個年邁養安養老人的臉!養老院裡也有年輕的領撫恤金的人,臉上甚至一道皺紋也沒有。但這些人的目光總是游離在別處,總是若有所思,彷彿竭力回憶什麼事情,卻又死也想不起來了。也許他們並沒在回憶什麼,他們臉上甚至流露驚喜之色,彷彿一瞬間想起了什麼美好的事情,什麼恢復健康的事情,給人帶來利益的事情。他們的臉讓人看著覺得他們氣質高貴,覺得他們曾經學識不凡,實際上他們現在學識不凡,正處於人人渴望的某種認識的巔峰。不過,也只是我這麼認為。就這些人來說,他們現在的偉大成就,乃是準確無誤地走進這個莊園,找到自己的房間和自己的床位。後來,一扇鑲著玻璃的門霍地推開,玻璃反射的光芒在庭院裡晃了半個圓圈,耀得我眼花。我扭頭一看,只見二樓的陽臺上走出一個大鬍子男人,他兩手扶著欄杆,身體轉向右邊,接著又轉向左邊。這老頭想必就是史博爾克伯爵本人了。他抬起的下巴頦上絡腮白鬍子閃光。此時,他裝出看天氣看景色的模樣,擺出一副名門望族的姿態僵立不動,沉思著,彷彿在品味自己的處境,表明他在這養老院裡是個錯誤。後來,通往前廳的柱子那裡有張臉動了一下,我吃驚地發現,原來那是一個老婦人的臉。老婦人坐在輪椅上,兩手緊抓扶手,聳著胳膊和肩膀,於是,她的後背就像椅背一樣直,我老以為那是斯芬克斯像。她的對面,在另一根柱子旁邊坐著的那個婦人,神態同樣莊嚴,猶如人面獅身像,輪椅扶手也靠在柱子上。因此,兩個不能行走的領養老金的婦人,坐在黑色輪椅上在那裡曬太陽,她們的裙子塞在坐墊底下,活動板子下面有白搪瓷尿盆閃光。後來,彷彿微風從北面歌唱著輕輕吹來,吹得樹葉簌簌拂動,我聽到了遠處傳來的樂曲聲,一首弦樂,很像我聽過的卓別林電影「馬戲團的燈光」中持續不斷的伴奏曲,或者以土魯斯.勞特累克生平為題材的那部電影的伴奏曲,呼喚出一張苦笑的臉。這樂曲在我心裡浮現的感覺,就跟莊園那扇精美的大門一樣。然而,儘管如此,我發現那些領養老金的人並不注意這音樂,他們散步,坐在小長凳上,用手杖在沙地上胡亂劃拉,或者只是那麼坐著,默默地嘬塊糖或薄荷糖。莊園管理處旁邊,有一條寬敞的空氣清新的走廊,露天走廊,不像前面的陽臺那麼華麗;這條走廊有十扇棕色房門,門上都有某種安全裝置。安養的老人們中唯有男性才到這裡來,靠在欄杆上看著下面發呆,一動不動僵立著。他們看著我,可是我知道他們沒有看見我,只是透過一扇無形的窗子在看過去,看過去的年代,那時候他們還年輕。他們執拗地為某件如今已無法挽回的事情氣憤不已、痛心疾首。這件事現在已無足輕重,可是偏偏現在才成熟,而事情發生的原因,為什麼會發生,已經消失不見了……在這長長的走廊裡,我看到這支弦樂曲怎樣飄落,輕煙似的縈繞著每個人,它甚至這裡那裡從開著的棕色房門裡流淌出來。我仔細察看,還走到前廳去看,那兩個坐在輪椅上、雙手緊抓皮扶手的婦人,依然像兩尊斯芬克斯塑像,弦樂隊的樂曲卻在她們周圍迴旋。我發現這音樂原來是有線擴音器裡播放的,它像玫瑰花叢圍著雕像似的圍著這兩位老婦。我舉目四顧,看到在陽臺的每兩道門之間,在過道托架上,都有同樣的小匣子,像餵瞎鳥的那種小匣子,弦樂曲就是從這些小匣子、小箱子裡播放出來的,動人的充滿感情的合奏,或者一把提琴以無比焦急的琴音獨奏了樂章的主題……沒錯!這是〈哈樂根的數百萬〉,數百萬,舊時代一部無聲電影的伴奏曲,戀愛場面、傾訴愛情、接吻,動人心弦的伴奏,讓觀眾掏出手帕抹眼淚……現在,我站在這養老院的庭院裡,昔日史博爾克伯爵府的庭院裡,弗朗茨在這裡為我們倆租了個小房間。佩平大伯在這養老院的病房已經躺了三個月,在舊時代,人們管養老院叫救濟院。當我來此看望佩平大伯時,我曾誠心穿過前廳,誠心走平緩的坡道,瞧一眼旁邊的走廊,那裡有老年婦女在活動,她們撩開窗簾朝庭院裡張望……我還用眼角看一下躺在病房裡的老婦們,聞到兒童尿布的臭氣。我還偷偷看了看食堂,從前這裡可是史博爾克伯爵宴請上百位高貴賓客的地方。最後我走進病房區,大伯躺在幽暗裡的病床上,那邊還有九個病人在看著我,我又聽到了〈哈樂根的數百萬〉。我坐下來注視佩平大伯,見他只是兩眼一眨不眨地瞪著天花板,不說話,什麼意見也沒有,什麼情緒也沒有,只是躺著。我聽到遠處傳來〈哈樂根的數百萬〉,我感到這樂聲只是一種幻覺,藉以抵擋我在這裡看到的一切。我頭一次來這昔日伯爵府探望大伯時看到的一切,令我感到難以接受,我曾多麼地痛苦!可是,發生了一些事情,讓我深為震撼,我決定賣掉一切,弗朗茨也同意,於是我現在站在這裡,站在這庭院裡。弗朗茨租了一個小房間,用他每月的全部養老金再貼補一些,我們將在這裡住下去,像史博爾克伯爵家一樣,只有一個小房間。我們將在食堂大廳吃午飯,吃早飯和晚飯,像史博爾克家一樣,他們也在食堂大廳吃晚飯和午飯。我將在花園裡,在那些砂岩塑像間散步,我將有一天能頭頭是道地說出哪個雕像意味著什麼,我將觀賞天花板上以希臘歷史故事為題材的繪畫,我可以摸摸樓道壁龕裡潔白的希臘器皿,弗朗茨將不斷地看手錶,生怕錯過收聽所有捷克語廣播的時間……這莊園我來過不下十次了,但身為外人,一切都讓我吃驚、害怕。今天,我頭一次身為住宿成員站在這裡,我將在此住下去,直到在我身上發生什麼事,有人突然來找我,對我甜蜜耳語,許下諾言,然後帶我出去,去到一個既沒有邊境,也沒有界線的地方。這莊園我來過不下十次了,可是今天我看到的事情、聽到的聲音和關係更為準確,也就是說,跟以前不同了。
在小城郊外,我的時間停止了的小城郊外,有一座大莊園,這莊園現在是領養老金者的養老院。通往這莊園只有一條爬上山岡的林蔭道,一條由成行老栗樹的樹冠從兩側架起的隧道,走在這條路上,就彷彿走在長長的哥德式拱頂底下。老栗樹的繁枝不僅搭在一起,而且相互纏繞,大風吹來,它們便結成一個整體。樹冠的枝葉為爭奪些許陽光,累得精疲力竭,枯萎了,因此道路上總是落滿因長期摩擦而斷裂的碳化了的枯樹枝。有時候,無風也會突然掉下一整截樹枝,打在沙地上。遇到這種情況,就像見到屋頂掉下一塊瓦,你把它拾起來扔到一旁,心情卻不免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