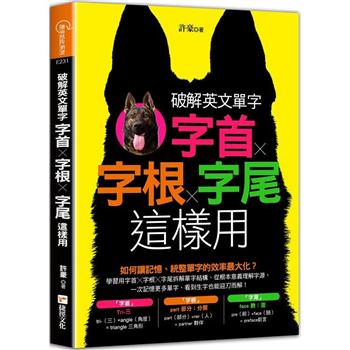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那不勒斯故事3:逃離與留下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6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一篇名為〈野心勃勃女孩的情色回憶錄〉的負面書評,使艾琳娜的第一本小說開始受到注目,報刊出現更多書評,小說再版暢銷,那不勒斯的街坊還向她打探小說情節真偽。但無論如何,艾琳娜開始享受順遂的人生:取得大學學歷、成為作家、即將嫁入名門……艾琳娜終於完成自幼立下的心願:離開那不勒斯。
艾琳娜婚禮的幾個月前,病奄奄的莉拉告訴她:「萬一我被送到精神病院,或是住院,或是更糟。你必須把我的兒子帶走。」久未見面的兩人,以莉拉這番近乎託孤的話語展開徹夜長談。1960年代的義大利社會,工會組織興起、學運不斷、法西斯份子與共產黨員互鬥,這些動盪不安也波及香腸工廠。莉拉被迫捲入其中,寫下工廠苛待勞工的事蹟,並被同事推派為與資方談判的代表。就在這內外交逼的情勢下,莉拉終於病倒……
在【那不勒斯故事】第三集《逃離與留下》中,情節發展進入義大利在20世紀時最動盪不安的年代,學運、工運、法西斯主義復甦、共產黨崛起、民主政治、社會主義……衝擊著每一個角色。作者更加強了批判的筆觸,使小說人物在面對各種事物時,有更深刻的自省。讓原本主要是莉拉與艾琳娜友誼故事的本系列,有更多關於歷史、社會寫實與哲學層面的閱讀收穫。【那不勒斯故事】系列在全球持續熱銷,已翻譯為40多種語文,改編影集拍攝中,將在HBO播出。更有狂熱的讀者聲援苦戀尼諾、得不到回應的艾琳娜,在Tumblr.網站上成立專頁。
作者簡介
艾琳娜.斐蘭德(Elena Ferrante)
出生於義大利的那不勒斯,行事低調,真實姓名保密到家,也從不在媒體露面,但作品依舊廣受世界各地讀者歡迎。
斐蘭德以女性成長故事著稱。第一部小說作品《不安的愛》(L'amore molesto, 1992)描寫女插畫家返鄉調查母親之死,後來被改編為電影。讓裴蘭德的好文筆更廣為人知的第二本小說作品《放任時期》(I giorni dell'abbandono,2002),費時十年才發表,敘述單親媽媽如何面對空虛的人生。
在2011年陸續出版的小說【那不勒斯故事】四部曲,描寫女作家與童年好友的故事,內容廣及十個家族與六十年的生命歷程。這系列在2012年推出英譯本後,讓斐蘭德成為國際市場上的熱門作家,並獲選為《金融時報》2015年度女性、《時代雜誌》2016年百大影響人物;該系列的第四本入圍2016年布克國際獎決選名單。
譯者簡介
李靜宜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系博士,美國史丹福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職出版社與外交部。
譯有《追風箏的孩子》、《燦爛千陽》、《遠山的回音》、《奇想之年》、《史邁利的人馬》、《完美的間諜》、《末日之旅》等。
臉書交流頁:靜靜讀一本書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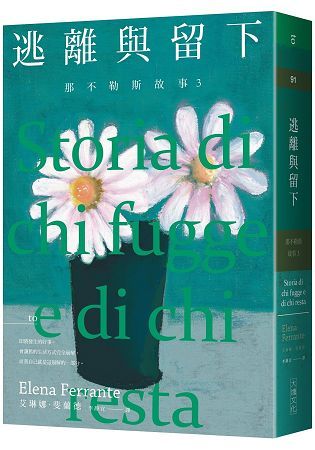
 2017/09/29
2017/0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