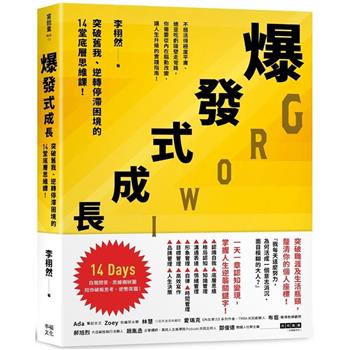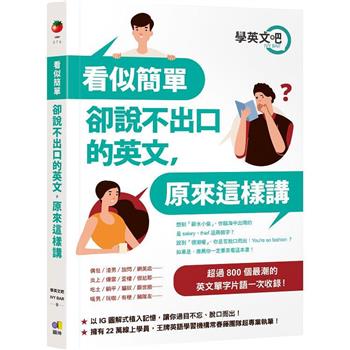圖書名稱:阮是漫畫家
從敖幼祥、鄭問、林政德、賴有賢……80到90年代,台灣漫畫產業曾經歷過一段黃金時期,之後日本漫畫主宰台灣市場,阮光民1997年進入漫畫圈時,台灣的實體漫畫產業已漸漸邁向寒冬期,而在之前,為了家計,他甚至留營「領士班」賺錢養家,也在看板店做過學徒,一直到進入賴有賢漫畫工作室,當起補網點、畫背景、送稿的助手,才沾上漫畫家一點邊。
有朝一日成為漫畫家的夢想,在助手的日子裡不斷提醒著阮光民,他細心觀察體會老師的作品,一邊利用原稿裁下的紙邊,構想自己的故事,終於開始嘗試了創作,並投稿「漫畫新人獎」,然後得獎、出道!而得獎,也只是「燈下一秒鐘」,創作的路既漫長又辛苦,因為熱血,因為那些人、那些事,夢想的路,跪著也要走下去,相比誰走得久、走得遠!
「也許沿途上會有一起走的伙伴,但畫圖時終究還是得面對孤單;想故事是豐富精采的,一旦落到工作就滿單調的。工作大多時間都是低著頭,默默的做,前方很難有明顯的燈塔導引⋯⋯不過,總會有風景在等著我們。」
名人推薦
吳念真(作家、導演):宛如修行⋯⋯
蔡南昇(名設計師):時光的縫補師⋯⋯
賴有賢(漫畫家):師仔的榮耀⋯⋯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阮光民
台灣當前最活躍的漫畫家,作品深具人文色彩,擅長捕捉台灣庶民的生活,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溫情義理,藉著樸實無華的畫風試圖尋找台灣值得代代相傳的生存價值。歷年多次榮獲大獎肯定,《東華春理髮廳》更曾改編成偶像劇。
作品有︰《刺客列傳》《東華春理髮廳》《幸福調味料》《天國餐廳1.2.3》《警賊:光與闇1.2.》及《用九柑仔店》系列等,並跨界合作漫畫舞台劇「人間條件」以及小說《天橋上的魔術師》,備受矚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