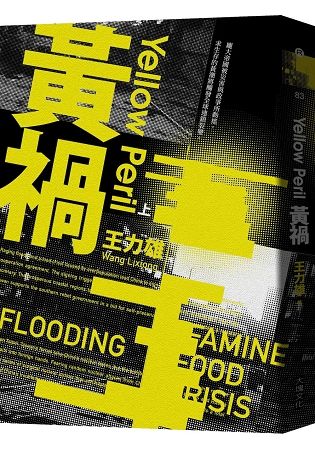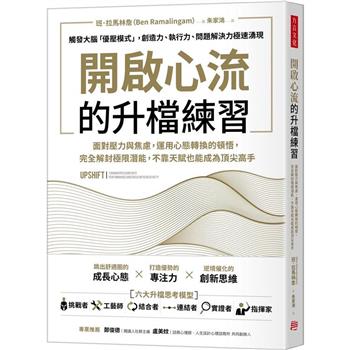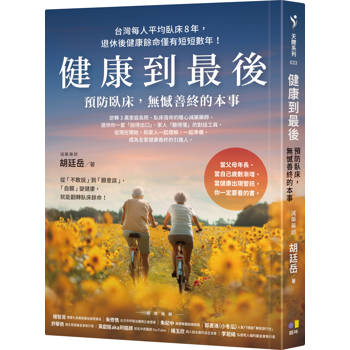◎經典小說《黃禍》名列《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睽違多年,新修完整版全新上市。
◎人類不得不面對的未來:震撼世紀的政治寓言小說,中國的變局必將影響全世界。
◎中國一旦發生災難危機,距離最近的台灣每個人都無法迴避,都得思索應對。
◎「恢宏而又章法井然的政治小說。作者想像力之大膽奇詭,知識結構之寬闊豐厚,文筆之雄健渾熟,都是令人驚詫的。」── 蘇曉康(《河殤》作者)
龐大帝國被災害與政爭所動搖,
求生存的黃潮將觸發全球連鎖裂變。
黃禍不再只是預言,而是近在眉睫的全人類生存議題
洪水肆虐、人口過剩引發的糧食危機等經濟問題,導致中國簽下引發爭議的國際經濟合作協議,立即引發政治鬥爭。總書記遭暗殺,沿海富庶地區乘機搞獨立,中國分裂引發南北戰爭,台灣為自保援助南方自治政府,北京則以核打擊摧毀台北。台灣軍隊奪取大陸核武基地,本要報復北京的核彈卻意外落到了國境之外。為了制止中國的核子濫炸,由聯合國主持美、俄聯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消滅了中國的核武能力,卻引發本已危機重重的中國社會整體崩潰,進而影響全世界的局勢⋯⋯
「黃禍」是百年來,西方世界對東亞恐懼的濃縮。從歷史來看,西元五世紀匈奴王阿提拉攻陷西羅馬帝國,使歐洲進入黑暗時代。西元十三世紀成吉思汗西征,再度威脅歐洲,東歐淪陷桎梏,阿拉伯帝國滅亡。時到今日,亞洲地區的龐大人口和各方面的發展,有任何的變化,都足以影響世界局勢。
被《亞洲週刊》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列的《黃禍》,在全球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影響力巨大。這次的「新修完整版」是作者王力雄新修訂的完整版本,也是睽違許久之後重新面世的最新、最完整的典藏版本。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黃禍【新修完整版】(全套三冊)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黃禍【新修完整版】(全套三冊)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預言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亞洲週刊》),至今仍在台港以及海外暢銷,大量盜版更流傳於中國大陸。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
王力雄
一九五三年生,籍貫山東,漢族。他曾以「保密」為名,出版了震驚海內外的長篇政治預言小說《黃禍》,引起全球媒體的追蹤報導。該書曾入選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亞洲週刊》),至今仍在台港以及海外暢銷,大量盜版更流傳於中國大陸。這位曾被國際媒體譽為「中國最敢言的作家」的其他著作還包括:《大典》(以今日中國現實狀況為背景的政治驚悚小說)、《天葬:西藏的命運》(漢人所寫關於西藏的著作中最客觀公平也是最好的一本書)、《溶解權力──逐層遞選制》(作者自認本書分量超過《黃禍》、《天葬》二書的加總)、《遞進民主》(作者針對中國未來的政治前途,所勾勒的理想藍圖)、《我的西域,你的東土》(作者在新疆歷經牢獄之災,實際走入維吾爾人之中寫成的著作)。
目錄
【上】
地球
Ⅰ
北京
東京銀座區
黃河
北京西山
山東半島二〇一海軍基地
北京中南海紫光閣一號會議室
黃泛區
北京
Ⅱ
台北
閩粵沿海交界
北京中南海
加拿大馬尼托巴湖畔
北京十六號機關
長江三峽
Ⅲ
北京天安門廣場
北京人民大會堂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三峽
山西省仙人村
Ⅳ
福州
美聯社中國福州十月二十五日電
北京亞太展覽中心
福建武夷山
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一總醫院
福州
福建人民代表大會致全國人民電
【中】
Ⅴ
北京中南海
山東半島二〇一基地
福州
浙江仙霞嶺
南京
鄭州
Ⅵ
福建武夷山
陝西太白山自然保護區
福建福州
台北總統府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
巴士海峽一艘甲板無燈的豪華遊艇
福建沿海
Ⅶ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北京天壇公園
南京
英國《泰晤士報》二十二日中國時局綜述
北京
中國大陸〇一四二核導彈基地
Ⅷ
台北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告
北京軍委「親王府」招待所
廣西九萬大山一三五八核導彈基地
北京高等軍事法庭
Ⅸ
南中國又一座被佔領的核導彈基地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湖北神農架自然保護區
聯合國秘書長日記
華盛頓五角大樓
南中國海四百六十米深海底
【下】
Ⅹ
中國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南中國海四百六十米深海底
法國《解放報》文章
北京
中俄東方邊境黑龍江
中國國家安全部文件
北京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收到的報告
北京遠郊燕山一座尼姑庵
XI
西安——太白山
金山嶺長城
東太平洋海盆
西方
北方滿洲里中俄邊境
東南方
河北張家口
XII
歐洲阿爾卑斯山
北京
美國洛杉磯
遠東
北京
XIII
太平洋西經一百一十六度十五分三十一秒北緯二十九度一分七秒
月球普希金月面站
太行山一個流浪漢講的故事
神農架
北京
人類世界
神農架狗圈
荒原
XIV
大地
地球
Ⅰ
北京
東京銀座區
黃河
北京西山
山東半島二〇一海軍基地
北京中南海紫光閣一號會議室
黃泛區
北京
Ⅱ
台北
閩粵沿海交界
北京中南海
加拿大馬尼托巴湖畔
北京十六號機關
長江三峽
Ⅲ
北京天安門廣場
北京人民大會堂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三峽
山西省仙人村
Ⅳ
福州
美聯社中國福州十月二十五日電
北京亞太展覽中心
福建武夷山
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一總醫院
福州
福建人民代表大會致全國人民電
【中】
Ⅴ
北京中南海
山東半島二〇一基地
福州
浙江仙霞嶺
南京
鄭州
Ⅵ
福建武夷山
陝西太白山自然保護區
福建福州
台北總統府
烏拉圭蒙得維的亞
巴士海峽一艘甲板無燈的豪華遊艇
福建沿海
Ⅶ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北京天壇公園
南京
英國《泰晤士報》二十二日中國時局綜述
北京
中國大陸〇一四二核導彈基地
Ⅷ
台北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告
北京軍委「親王府」招待所
廣西九萬大山一三五八核導彈基地
北京高等軍事法庭
Ⅸ
南中國又一座被佔領的核導彈基地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湖北神農架自然保護區
聯合國秘書長日記
華盛頓五角大樓
南中國海四百六十米深海底
【下】
Ⅹ
中國
北京中央軍委總部
南中國海四百六十米深海底
法國《解放報》文章
北京
中俄東方邊境黑龍江
中國國家安全部文件
北京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收到的報告
北京遠郊燕山一座尼姑庵
XI
西安——太白山
金山嶺長城
東太平洋海盆
西方
北方滿洲里中俄邊境
東南方
河北張家口
XII
歐洲阿爾卑斯山
北京
美國洛杉磯
遠東
北京
XIII
太平洋西經一百一十六度十五分三十一秒北緯二十九度一分七秒
月球普希金月面站
太行山一個流浪漢講的故事
神農架
北京
人類世界
神農架狗圈
荒原
XIV
大地
序
序
十年過後談《黃禍》
王力雄
◎《黃禍》的「預言錯誤」
《黃禍》已經出版十年了,十年變化是非常多的。《黃禍》剛出版時,人們認為它是對中國前途的預言,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黃禍》描寫的災難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然而不久,鄧小平的南巡把中國重新推上經濟自由化之路,「六四」後的沉悶和沮喪被勃興的商業大潮一掃而空,政治上的敵對也被紙醉金迷消融,中國的走向似乎就與《黃禍》的描寫分道揚鑣了。
今天,中國的現實似乎離《黃禍》差得更遠。《黃禍》的故事在現實中幾乎都沒有發生。《黃禍》寫到中共內部會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爭取民意,現實卻是中共要員對「六四」保持一致的強硬態度。《黃禍》寫到軍隊奪取了國家權力,把中共領導人當作傀儡,目前情況卻是軍隊完全被江澤民控制,原來人們預料江是過渡人物已被證明是個錯誤。他不但在鄧後繼續留位,而且穩定地控制局面。
《黃禍》寫到軍事政權引發沿海省份的地方勢力與北京決裂,事實是各地諸侯在重大問題上唯北京命令是從,除了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小動作,完全沒有膽量與中央政權對抗。
《黃禍》另一個脈絡是台灣對大陸的介入,實際情況卻是台灣朝野對大陸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捲入大陸事務的動力。《黃禍》還寫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現在來看那種冷戰時期的思路十分過時。蘇聯從原來的第二號強國變成了一堆三等國家。危機四伏,國力虛弱,完全沒有能力再與美國對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來論《黃禍》,打分應該是「0」。
◎我不想當算命先生
一九九四年我對《黃禍》做了一些修訂,改動了很少細節,主要是把蘇聯改為俄羅斯,做了相應地名和情節的改動,其他方面都與原來完全一樣。
照我的本意,把蘇聯改成俄羅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黃禍》當成「預言小說」,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預言家。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我成了一個什麼?當年蘇曉康作的序言把《黃禍》稱為「寓言小說」,我覺得更為合適。我要講的是故事之下的東西,不是故事本身。我與蘇曉康至今未曾謀面,也未有過聯繫,但僅從「寓言小說」之稱,我已經感到他是一個知音。
◎《黃禍》的主線是什麼
《黃禍》故事裡那些黨派鬥爭、諸侯分裂或美蘇大戰等都是筆上生花,在稿紙上過主宰世界命運的癮而已,真正推動著我寫下去的動力--也是貫穿小說的脈絡--是我對中國社會深層危機的憂慮,中國的現實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資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這四項中的每一項單獨論都算得上夠嚴重的危機,四項湊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是我眼裡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所在!即使《黃禍》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機全都沒有發生、都是錯的,這一深層危機卻一直是嚴峻而現實的存在。
《黃禍》出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欲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只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表現為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別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出水面。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面目的出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一九九八年長江不是發了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千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一九九八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一九九一年是十六天,一九九五年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七年二百二十六天,斷流長度也從一百三十一公里增加到七百零四公里。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洩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一九九八年花園口一號洪峰的流量僅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一,水位卻超過一九五八年零點五六米。下游黃河有幾百里高懸空中(高出河南新鄉二十米,高出開封十三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為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了就是爭奪權力,只要權力結構是專制的,得到權力就只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才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向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表面,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
台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台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只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台灣頭上就時刻懸著利刃。面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台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台灣自己,現在只是還沒出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國發生動亂,導致生產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慾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出國界,走向世界。現在只是為了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面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動了全球,如果百萬、千萬、上億中國人走向世界,將導致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們認為《黃禍》中與今天最不貼邊的是美蘇核戰。不錯,俄羅斯現在淪落了,但它仍然掌握著一個足夠把世界摧毀幾次的核武庫。一個掌握著致命武器並且充滿挫折感的巨大窮國,有可能比原來還可怕。說它窮,已經不得不賣家底,但你看它賣的都是些什麼--蘇凱戰機、宇航設備、航空母艦……這樣一個國家,誰能斷言它將來會毫無作為?
一九九九年四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周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類比多次出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面一出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面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了。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千年的歷史航船都走下來了,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著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鏟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了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擴大,出現了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接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侷限在很小範圍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權控制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著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著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裡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著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裡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了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產黨自己尊奉的「歷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出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只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系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繫,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了政權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合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了,那就危險了。人們只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台,控制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合的可能,因此那種整合會從局部逐步向整體擴展,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了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一年
十年過後談《黃禍》
王力雄
◎《黃禍》的「預言錯誤」
《黃禍》已經出版十年了,十年變化是非常多的。《黃禍》剛出版時,人們認為它是對中國前途的預言,當時很多人認為中國社會正在走向一個不確定的未來,《黃禍》描寫的災難不是沒有可能發生。然而不久,鄧小平的南巡把中國重新推上經濟自由化之路,「六四」後的沉悶和沮喪被勃興的商業大潮一掃而空,政治上的敵對也被紙醉金迷消融,中國的走向似乎就與《黃禍》的描寫分道揚鑣了。
今天,中國的現實似乎離《黃禍》差得更遠。《黃禍》的故事在現實中幾乎都沒有發生。《黃禍》寫到中共內部會有人打「六四」牌,以翻案爭取民意,現實卻是中共要員對「六四」保持一致的強硬態度。《黃禍》寫到軍隊奪取了國家權力,把中共領導人當作傀儡,目前情況卻是軍隊完全被江澤民控制,原來人們預料江是過渡人物已被證明是個錯誤。他不但在鄧後繼續留位,而且穩定地控制局面。
《黃禍》寫到軍事政權引發沿海省份的地方勢力與北京決裂,事實是各地諸侯在重大問題上唯北京命令是從,除了搞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小動作,完全沒有膽量與中央政權對抗。
《黃禍》另一個脈絡是台灣對大陸的介入,實際情況卻是台灣朝野對大陸唯恐避之不及,沒有任何捲入大陸事務的動力。《黃禍》還寫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戰爭。那時蘇聯尚未解體,現在來看那種冷戰時期的思路十分過時。蘇聯從原來的第二號強國變成了一堆三等國家。危機四伏,國力虛弱,完全沒有能力再與美國對抗。
因此,以占卜的命中率來論《黃禍》,打分應該是「0」。
◎我不想當算命先生
一九九四年我對《黃禍》做了一些修訂,改動了很少細節,主要是把蘇聯改為俄羅斯,做了相應地名和情節的改動,其他方面都與原來完全一樣。
照我的本意,把蘇聯改成俄羅斯都不是很有必要,因為我從來沒有把《黃禍》當成「預言小說」,我也不想成為一個預言家。如果現實真按照我的描寫兌現,倒會使我毛骨悚然--我成了一個什麼?當年蘇曉康作的序言把《黃禍》稱為「寓言小說」,我覺得更為合適。我要講的是故事之下的東西,不是故事本身。我與蘇曉康至今未曾謀面,也未有過聯繫,但僅從「寓言小說」之稱,我已經感到他是一個知音。
◎《黃禍》的主線是什麼
《黃禍》故事裡那些黨派鬥爭、諸侯分裂或美蘇大戰等都是筆上生花,在稿紙上過主宰世界命運的癮而已,真正推動著我寫下去的動力--也是貫穿小說的脈絡--是我對中國社會深層危機的憂慮,中國的現實一是人口最多,二是人均資源最少,三是欲望最高,四是道德水平最低,這四項中的每一項單獨論都算得上夠嚴重的危機,四項湊在一起,又是「四最」,可想而知會造成多麼巨大的失衡。正是這種失衡,是我眼裡中國最嚴重的危機所在!即使《黃禍》表面描述的那些危機全都沒有發生、都是錯的,這一深層危機卻一直是嚴峻而現實的存在。
《黃禍》出版至今的十年,四個「最」的走向如何?首先中國人口又增加了上億,人均資源因此更少,生態也遭受更多的破壞,中國人的欲望有增無減,社會道德卻繼續江河日下,因此四個「最」更加「最」,它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更加失衡。這說明《黃禍》描寫的深層危機沒有消失,而且仍然在發展,那麼《黃禍》描寫的災難就仍然有可能發生,不同的只是災難由什麼引發和表現為什麼形式而已。沒有《黃禍》那些故事,也會有別的事使那深層危機浮出水面。
◎故事還可能繼續
其實《黃禍》故事中使用的元素這幾年已經有不同面目的出現。《黃禍》開篇寫的是大水,一九九八年長江不是發了大水嗎?波及兩億人口,造成兩千多億的損失。那災難的背後原因就是人口過多,砍伐森林、圍墾湖泊、堵塞河道等,造成了生態的失衡。
《黃禍》中發水的是黃河,一九九八年的黃河卻是一大半時間無水入海,那當然也是一種生態災難。黃河斷流的天數一九九一年是十六天,一九九五年一百二十二天,一九九七年二百二十六天,斷流長度也從一百三十一公里增加到七百零四公里。危機加深的速度是驚人的。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搖籃,斷流的意象比發水還令人沮喪。黃河近年沒發水跟北方持續乾旱有關。其實黃河自身的洩洪能力早已驚人下降。一九九八年花園口一號洪峰的流量僅為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一,水位卻超過一九五八年零點五六米。下游黃河有幾百里高懸空中(高出河南新鄉二十米,高出開封十三米),一旦遇到洪水決堤,破壞將難以估量,成為推動危機爆發的引信完全可能。
目前中共黨內雖然看似偃旗息鼓,然而黨內鬥爭說穿了就是爭奪權力,只要權力結構是專制的,得到權力就只能通過鬥爭,平衡必定就是暫時,發生鬥爭才是必然。而社會的基本矛盾從底層向上傳遞,最終也會引發高層鬥爭,不同的利益集團都會在高層尋找自己的代表,由此形成向上的凝聚和富集。只要有一天社會的深層危機浮上表面,眼前平靜就會立刻打破。
台灣現在採取對大陸不介入的對策,但是台灣的當權者和百姓不會不明白,近在咫尺的大陸是躲不過去的。只要大陸仍然由中共統治,台灣頭上就時刻懸著利刃。面對這樣的威脅,我不太相信一旦有一天只需要台灣助一把力就能在大陸推翻中共,台灣仍然會不介入,那不是幫助大陸,是在救台灣自己,現在只是還沒出現那個時機而已。
設想未來,如果中國發生動亂,導致生產萎縮,這塊土地無法再養活如此多的人,被求生慾驅使的中國人就一定會走出國界,走向世界。現在只是為了掙多一點錢,他們都不惜冒死偷渡,將來面對的是生死之交,難道能指望他們坐以待斃?當年幾十萬越南人漂洋出海震動了全球,如果百萬、千萬、上億中國人走向世界,將導致怎樣的反應鏈條?最終造成什麼結局?現在雖然無法預料,但可以確信那必定是致命的。
人們認為《黃禍》中與今天最不貼邊的是美蘇核戰。不錯,俄羅斯現在淪落了,但它仍然掌握著一個足夠把世界摧毀幾次的核武庫。一個掌握著致命武器並且充滿挫折感的巨大窮國,有可能比原來還可怕。說它窮,已經不得不賣家底,但你看它賣的都是些什麼--蘇凱戰機、宇航設備、航空母艦……這樣一個國家,誰能斷言它將來會毫無作為?
一九九九年四月上萬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震動了中共,也震動了世界。隨後的《亞洲周刊》說《黃禍》預見了氣功團體的強大能量,並稱「文學的洞見往往出奇的準確」。事實上,這種類比多次出現,流民、生態、人蛇等方面一出現問題,就會有人提到《黃禍》。甚至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中國掀起反美運動,也被聯想到《黃禍》中的一些情節。
我則在祈禱,《黃禍》中那些元素的再現到此為止,後面那些可怕的故事千萬不要再繼續成為現實。
◎穩定之下的危機
十年來,我的內心沒有隨時間的過去而放鬆,反而越來越強烈地感到劫難正在逼近。無疑會有人認為我把問題極端化了。我說中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但類似的說法歷史上從未斷過,中國國歌的歌詞也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刻」。哪個年代的憂國之士不曾擔心中國要亡?鴉片戰爭面臨的列強、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日本佔領大半個中國、還有文革和六四,不都好像馬上就要沒有明天?可是中國都一樣過來了。今天談論的中國危機,是不是還會像過去一樣,不過是一種當事者迷的過度解釋,中國還是會安然過去。畢竟幾千年的歷史航船都走下來了,怎麼會偏偏就在今天觸礁沉沒?
對此,首先應該談的不是危機,而是中國目前為什麼會這樣穩定?如果真存在那麼嚴重的危機,為什麼現在看到的現象是相反?而我恰恰在這種穩定之下,感到著最大的危機。
今日中國除了政權以外,沒有任何因素可以在整體上對社會進行整合。政治反對派、意識形態、國家化軍隊、宗教、公民社會那些任何完善社會所不可缺少的整體性整合機制,不是已經死亡就是被鏟除,或是在壓制下無法生長。唯一的整體整合力量只剩下政權。中國社會在這種情況下前所未有的穩定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在這個社會當中,除了政權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凝聚社會,引導人民,對政權形成挑戰,一切都只能在政權的指揮棒下運行。
所以,當今中國的基本狀態是這樣的:一方面是社會自由度擴大,出現了很多新的空間,原來那種社會分子之間被強加的剛性連接逐漸解除,但是並沒有新的組織化形式取而代之,隨之而來的是社會越來越散漫,雖然人人都在鑽營,但都是一盤散沙的個體行為,或侷限在很小範圍的整合。另一方面,政權控制和管理整個社會。形象地形容這種狀態,就是一隻政權的桶裝著十三億人的散沙。散沙內部進行著活躍而無序的分子運動,而桶因為失去信仰的凝聚也已經「脆化」,從毛澤東時代的鐵桶變成了今天的玻璃桶。然而散沙無論如何不會挑戰桶,哪怕桶是玻璃桶,這就是今日中國在外人眼裡顯得穩定和繁榮的原因所在。
但是,這穩定並不是吉兆,卻應該說蘊含著極大的危險。危險在於,萬一一次意外的震動使那玻璃桶破碎了呢?--唯一的整合就會喪失,社會就會失控,那時的中國將會怎樣,能夠怎樣呢?所有的危機將一同爆發,桶裡的散沙也就會漫天飛揚,無法收拾。
不願意看到這種前景,問題就成了中共政權到底會不會垮?如果它能夠永遠屹立,也就沒有什麼可愁。即使過得不太好,至少不會有大災難。然而回答顯然應該是否定的。不談具體,僅從共產黨自己尊奉的「歷史唯物主義」,世上就沒有永恆的事物,中共自身當然也不例外。何況它的高度腐敗、意識形態缺失、喪失民心等,都已經構成它可能垮台的因素。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它以自覺的死亡挽救中國,然而現實沒有讓我們看到那種前景的絲毫希望。
◎我們能否逃出劫難
有人也許會說,中共政權垮了難道天就會塌?車到山前自有路。歷史有過多次大起大落,政權崩潰也層出不窮,不都過來了。不錯,歷史有多種可能,但今天中國與過去的不同是,以往即使其他整合因素都失去作用,至少還有一個「框架」在支撐,一個「底座」在承托--那「框架」就是文化,「底座」就是生態。
一個社會發生政權崩潰,只要文化結構保持完整,傳統的倫理、道德、調整人際關係原則和價值系統還在,人們就可以在沒有法律和警察的情況下自行維繫,社會就仍然是凝聚而不是發散的,即使社會失去了政權的整合,也仍然可以維持基本穩定,獲得一個緩衝時間以重建政權、法律等上層建築,繼而重新整合社會。
如果這種文化結構沒有了,那就危險了。人們只要沒有警察看管就相互損害,那麼政權垮台,控制消失,人與人的關係就將以爭鬥為主,社會因此會進入發散狀態,動亂將迅速放大,社會重新建立統一政權和有效法律的過程,將需要漫長時間。
如果那時人口不多,有一個好的生態,事情也不會到最糟程度。人們雖然不能同舟共濟,共渡難關,至少可以分散到自然中去,各自找一塊地耕種,找一片水捕魚,或是找一片樹林狩獵,總之能活下去,直到社會重新穩定,建立新的整合。而且在好的生態環境下有重新建立整合的物質基礎,人們也有為更大利益而聯合的可能,因此那種整合會從局部逐步向整體擴展,最終實現新的統一。在那種過程中,即使社會政治發生大變化,卻不妨礙民族和文明的延續。歷史上很多民族都有過這樣的經歷。
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今天面臨的狀況可能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絕望,今天的中國既失去了能夠支撐社會的文化結構,又沒有了能在最後關頭承托社會的生態底座,一旦唯一能夠進行整體整合的政權垮掉,就可能落入一個碎片化乃至粉末化的墜落過程。最終災難非常可能是毀滅性的。人類歷史曾數度發生過大文明的毀滅,我們沒有理由盲目相信中華民族一定不會滅亡。
嘲笑這種擔憂是容易的,但遠不如正視這種擔憂對中國更有益。「杞人憂天」頂多是白費了憂慮,而「不見棺材不落淚」卻會在看見棺材時悔之莫及。前者的代價微不足道,後者的代價卻是承受不起。生活常識經常告誡「以防萬一」,那麼哪怕未來發生危機的可能只有萬分之一(何止),我們也只用萬分之一的力量應對,十三億中國人中就至少應該有十三萬人投入為危機做準備。而事實上有幾個人?且都被視為「有病」。
悲觀論者不一定全是在扮演糟糕角色。古人教導「臨事而懼,三思而行,好謀而成」的慎行原則,就是要多考慮不好的可能。從這種意義上,悲觀有其獨特的價值。然而悲觀論者面臨一種悖論,人們如果聽信他們的預言,做出了努力去防止,他們的預言就會落空,也就會因此被譏笑為杞人憂天。
所以萬能的上帝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做預言時總要附加一個條件--就是人們全都不信。
二○○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