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兩河文明的塵眾,徒手捏塑出女人土偶,
肥沃的雙乳、寬闊的臀、堅實的腿,
相信著女神護守土地、看顧農作、庇佑生靈。
我的發酵世界,是女人陪同我掌握了留種、育種的技藝;
是女人引領我採集用作接菌的植物;
也是女人為我揭開發酵的奧義,在那肉眼不見的領域,
以女人的身體和感官領略稻米的生、稻米的亡,
經歷發酵,重生米麴。
與第一任女朋友交往,成為女同志後,已經過了十八年。十七歲時徬徨,內心卻也充滿無畏旁人眼光的愛情至上。十九到二十二歲整個大學時期的探索,上大學的第一個週末,朝聖般地前往「女書店」,當時也把性別研究研討會當做補品,補足自己在性別認同上的勇氣。在那之後的十年,走入一個關心結了婚、有了孩子的女同志議題的組織,辦電子報、倡議遊行,關心同志成家權益,心底收納過許多成家故事的哀愁,卻也不曾失去希望。後來,與共同務農的夥伴,組成多人家庭,實地練習同志成家的功課。經過四年,離「家」,一直迴圈式地探尋遺落在那舊地的自己,想把她帶出舊地,途徑是面對自己的黑暗,在暗裡鑿光,指向來時路,看見洞窟裡一個一個的自己。
就像漬物,懷抱著陽光的初衷,為了熟成,猶必須經過漫漫的黑暗。以發酵、醃漬食物的料理穿針引線,織就女同志的情感、家庭、關係等細細密密的心事。每一個篇章,也各別對應了一種面對自我的黑暗、啓蒙自己的功課。
| FindBook |
有 14 項符合
女同志X務農X成家:泥地漬虹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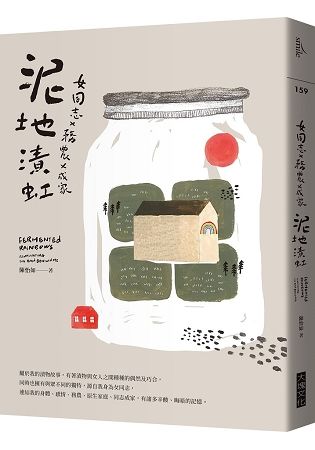 |
女同志X務農X成家 泥地漬虹 作者:陳怡如 出版社: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8-12-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女同志X務農X成家:泥地漬虹
內容簡介
目錄
序
*大地
我多愁善感的身體
我的種種不合時宜
*花與果
流浪的孩子
離家種田,回家做漬物
*引菌發酵
田帶我們找到房子
生而死而生的傳說
收藏
女同志怕老、怕死,想要一個家
一塊田,安置女同志的魂舒
*大地
我多愁善感的身體
我的種種不合時宜
*花與果
流浪的孩子
離家種田,回家做漬物
*引菌發酵
田帶我們找到房子
生而死而生的傳說
收藏
女同志怕老、怕死,想要一個家
一塊田,安置女同志的魂舒
序
序
入甕發酵的心事
兩年前的著作《漬物語》中,我採訪了身邊的女農、漬女,描寫她們做漬物的心情故事,也在〈漬物與女人〉序裡,談及女人擁有孕育的天賦,一如作物的種子,種子是味道的源頭,決定了漬物的滋味。女人在遠古時代擔負採集的職責,如今的女人仍握有植物的秘密,藉植物引菌、發酵。女人的生活周旋於他人、家庭、社會,心思細細密密,一甕甕漬物正收藏著女人的心事。
屬於我的漬物故事,有著漬物與女人之間種種的偶然及巧合,同時也擁有與眾不同的獨特,源自我身為女同志,連結我的身體、感情、務農、原生家庭、同志成家,有諸多辛酸、晦暗的記憶。
人們總是書寫食物的美好、農民的辛勞。採訪、撰稿期間,我從善如流,不敢透露自己與食物之間的那些黑暗面。但是,每當依循節氣做著漬物,嗅到的氣息、瞥見的色水、皮膚的撫觸、味蕾上的滋味,總喚起那些黑暗的記憶,排山倒海而來,像整個夏季除也除不盡的稗草。
我讀著那些深刻書寫耕作心事的文本,尋求一絲慰藉。文本的主角以婚姻建立出的家庭為核心,描寫在農田、在家庭,乃至大家族裡的田事、家事與心事,總牽動著我。可是,以異性戀家庭為藍本,始終無法引起我心中最私密的認同。如今,我們有太多機會在網路平台看見多元的家庭風貌,不再僅侷限在出版書籍上。然而,單身女同志務農就是現代女性自立自強;女同志伴侶務農,就是兩人胼手胝足,其樂融融的畫面,也無法令我獲得安慰。
十幾年前,閱讀到的第一本同志家庭繪本《 Heather has Two Mothers》。作者成長於北美的猶太家庭,有感於童年接觸到的繪本,千篇一律描繪白人家庭,遍尋不著屬於她的猶太家庭認同,於是創作了這個多元家庭故事。
我心中有股熱情,想書寫自己的漬物故事。從來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我,眾人面前經常默默無語,相對的,文字讓我感覺安全又放心。可是書寫過程中,文字卻成了沈重的石頭,在回憶的海裡激起水花,潑了我一身濕。
憶起幼稚園時,班上那個害羞的男孩不敢溜下滑梯,我想方設法要他滑下來,但一等我爬上滑梯,發現什麼時候他已經不在原地了。我跑來跑去遍尋不著,悻悻然回到教室,卻看見他就坐在位置上。那個不敢滑下來,後來又找到方法、自己下來的人,或許就是被困在內心幽暗之處的我吧?
喜歡上相同性別而惶惶不安的初戀;月事來潮的疲憊、掙扎,無法被馴服的野性身體;離開城市來到農村務農,卻同樣面對人生競賽的格格不入。生命不同階段接踵而來的黑暗,逐一被自己隱藏起來,視而不見。在做著漬物時,回憶揉上鹽巴,淌出疼痛的髒水,軟化了堅信不疑的承諾,等待時間醃漬入味、發酵完熟,最後嘗入口中的美味。我終於明白,是黑暗與美好的力量深化了漬物的意義,如同光與影並存的必然性。我練習著面對自己的黑暗,不為自己辯解,真實也好,誤會也罷,都是我行走於世上,映照在大地的光與影。我期待以光亮照耀他人,給出蔭下供人納涼憩息,於是有了這本書的模樣。
蘭陽平原的節氣韻律,交錯著心靈故鄉蒙古的漫漫行旅,與山林草地的野菌撒落在文字;從素日製作漬物時的感官體察作引,以筆爬梳我作為一個女同志,對身體、感情、同運、務農、家庭——原生家庭與同志成家等省思,入甕發酵,漬出人間味道。
謝謝我漬物人生裡相遇的那些人。
這本書,獻給過去的、現在的我們,歲月愈陳愈香。
入甕發酵的心事
兩年前的著作《漬物語》中,我採訪了身邊的女農、漬女,描寫她們做漬物的心情故事,也在〈漬物與女人〉序裡,談及女人擁有孕育的天賦,一如作物的種子,種子是味道的源頭,決定了漬物的滋味。女人在遠古時代擔負採集的職責,如今的女人仍握有植物的秘密,藉植物引菌、發酵。女人的生活周旋於他人、家庭、社會,心思細細密密,一甕甕漬物正收藏著女人的心事。
屬於我的漬物故事,有著漬物與女人之間種種的偶然及巧合,同時也擁有與眾不同的獨特,源自我身為女同志,連結我的身體、感情、務農、原生家庭、同志成家,有諸多辛酸、晦暗的記憶。
人們總是書寫食物的美好、農民的辛勞。採訪、撰稿期間,我從善如流,不敢透露自己與食物之間的那些黑暗面。但是,每當依循節氣做著漬物,嗅到的氣息、瞥見的色水、皮膚的撫觸、味蕾上的滋味,總喚起那些黑暗的記憶,排山倒海而來,像整個夏季除也除不盡的稗草。
我讀著那些深刻書寫耕作心事的文本,尋求一絲慰藉。文本的主角以婚姻建立出的家庭為核心,描寫在農田、在家庭,乃至大家族裡的田事、家事與心事,總牽動著我。可是,以異性戀家庭為藍本,始終無法引起我心中最私密的認同。如今,我們有太多機會在網路平台看見多元的家庭風貌,不再僅侷限在出版書籍上。然而,單身女同志務農就是現代女性自立自強;女同志伴侶務農,就是兩人胼手胝足,其樂融融的畫面,也無法令我獲得安慰。
十幾年前,閱讀到的第一本同志家庭繪本《 Heather has Two Mothers》。作者成長於北美的猶太家庭,有感於童年接觸到的繪本,千篇一律描繪白人家庭,遍尋不著屬於她的猶太家庭認同,於是創作了這個多元家庭故事。
我心中有股熱情,想書寫自己的漬物故事。從來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我,眾人面前經常默默無語,相對的,文字讓我感覺安全又放心。可是書寫過程中,文字卻成了沈重的石頭,在回憶的海裡激起水花,潑了我一身濕。
憶起幼稚園時,班上那個害羞的男孩不敢溜下滑梯,我想方設法要他滑下來,但一等我爬上滑梯,發現什麼時候他已經不在原地了。我跑來跑去遍尋不著,悻悻然回到教室,卻看見他就坐在位置上。那個不敢滑下來,後來又找到方法、自己下來的人,或許就是被困在內心幽暗之處的我吧?
喜歡上相同性別而惶惶不安的初戀;月事來潮的疲憊、掙扎,無法被馴服的野性身體;離開城市來到農村務農,卻同樣面對人生競賽的格格不入。生命不同階段接踵而來的黑暗,逐一被自己隱藏起來,視而不見。在做著漬物時,回憶揉上鹽巴,淌出疼痛的髒水,軟化了堅信不疑的承諾,等待時間醃漬入味、發酵完熟,最後嘗入口中的美味。我終於明白,是黑暗與美好的力量深化了漬物的意義,如同光與影並存的必然性。我練習著面對自己的黑暗,不為自己辯解,真實也好,誤會也罷,都是我行走於世上,映照在大地的光與影。我期待以光亮照耀他人,給出蔭下供人納涼憩息,於是有了這本書的模樣。
蘭陽平原的節氣韻律,交錯著心靈故鄉蒙古的漫漫行旅,與山林草地的野菌撒落在文字;從素日製作漬物時的感官體察作引,以筆爬梳我作為一個女同志,對身體、感情、同運、務農、家庭——原生家庭與同志成家等省思,入甕發酵,漬出人間味道。
謝謝我漬物人生裡相遇的那些人。
這本書,獻給過去的、現在的我們,歲月愈陳愈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