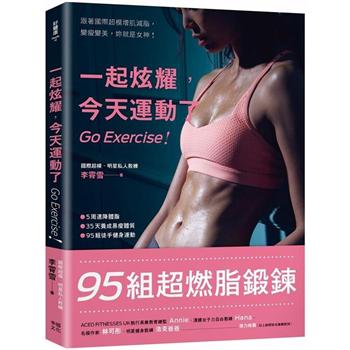安穩國度裡,我們曾無須思考。
瞬間,幸福快樂就從手裡溜了出去。
瞬間,幸福快樂就從手裡溜了出去。
基納尼拉的死巷,是他們的地盤。偷摘芒果,釣魚踢球,抽菸胡鬧,加比與死黨在自己的小天地歡暢度日。夜裡他回到家,在滿開緬梔花的外國人社區,與妹妹和父母過著有僕從伺候的安穩生活,偶爾陪媽媽探訪娘家親戚。
然而,政治鬥爭捲起漩渦,吞噬他們居住的中非小國蒲隆地,沖碎了表面的平靜。法國爸爸與盧安達媽媽爲一家去留爭執不已,舅舅回祖國從軍;加比的小小五人幫也開始分崩離析,真摯友誼有了嫌隙。硝煙與血腥慢慢鑽進了生活的裂縫裡。
多年後,身在巴黎的加比接到一通遠方的來電。街上的香茅芬芳,九重葛畔的夜間漫步,破蚊帳內的午後酣眠,細瑣的對話,啤酒筐上的閒坐小憩,暴雨時節的白蟻——深鎖的心門應聲開啟,他回到一切美好甜蜜消逝的起點……
創作歌手蓋爾.法伊,融合了自身經歷與感悟,以詩意的語言將歌曲中未盡的故事轉化為第一本小說,記下童年盤踞不去的無盡溫柔與萬般酸楚。
我們熟悉巷子的每個角落,
我想要我們一起在這裡過一輩子。
我寫這本小說,是想再現一個被遺忘的世界,聊聊生命裡的快樂片段……我寫這本小說,是想向全世界高聲宣告我們曾經存在,過著簡單的生活、按部就班的日常,伴隨著無聊煩悶;我想大聲宣揚,在四散分離、流亡異鄉,成為難民、移民前,我們也曾幸福過。——蓋爾.法伊,本書作者
*2016 年法國年度暢銷書,銷售逾 50 萬冊,再刷不斷。法雅客小說獎、小說新人獎、龔固爾高中生評選獎等大獎肯定。
*已售出中、英、日、韓、德、西、義等35 語種爭相翻譯,改編電影拍攝中!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台灣非洲研究論壇執行長嚴震生專文導讀。
獲獎紀錄
Prix Goncourt des lycéens 龔固爾高中生評選獎
Prix du Roman Fnac法雅客小說獎
Prix Goncourt, choix de l’Orient, choix de la Pologne et choix de la Tunisie龔固爾海外法語主修學生評選獎:中東、波蘭、突尼西亞
Prix du roman des étudiants France Culture-Télérama法蘭西文化台—電視全覽週刊大學生評選獎
Prix du Premier roman小說新人獎
Prix Transfuge 《Transfuge》雜誌文學獎
Prix Fetkann! Maryse Condé 甘蔗紀念日—瑪麗絲.孔戴文學獎
Globes de Cristal, meilleur roman 水晶球獎最佳小說
以及費米娜獎(Prix Fémina)、梅迪奇獎(Prix Médicis)等多項文學大獎入圍。
各界好評
《小小國》巧妙融合了溫柔與暴力、詼諧與悲劇。震撼人心的作品。——Jeanne de Ménibus,《Elle》
加比不是非洲小孩,他是世界的孩子,被瘋狂的命運所挾持。他代表了我們共同的憂慮。——Maria Malagardis,《Libération 解放報》
極優異的小說初作,令人心碎、情緒激昂,欽佩不已。—— Perreau,《Les Inrockuptibles》
蓋爾.法伊敘事技巧高超。他帶我們進入了前所未見、無人曾訪的世界。——Jean Hatzfeld,《France Inter》
蓋爾.法伊描繪出在千瘡百孔的國家裡度過的童年,文字如此精準,糅合了溫柔與沉重;讀完他的第一部小說,宛如體驗了一個撼動人心的擁抱。——Valérie Marin La Meslée,《Le Point 法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