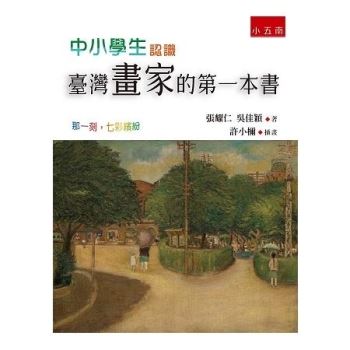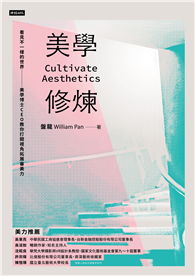1 冰封的十二歲
父親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除夕,忙亂歡樂的氣氛開始溫馨起來。
辦年貨的人買夠了,工作的人離開辦公室了,趕車的人也回到家了。四十多年前,台灣過年的氣氛還非常濃厚,除夕團圓是家家戶戶的大事。
住在我們寧波東街這個巷子的人,都不是什麼富裕人家。街頭巷尾,平時盡是孩子的天下,騎車、追逐、玩球,長年吵吵鬧鬧。這一刻,卻出奇地安靜,好像什麼聲音都沒有。
路上變得異常冷清。我獨自站在門前,一直看著巷口—爸爸會不會突然從那裡出現,回家吃年夜飯?
這一年,我十二歲;那一刻,全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個人。巷子那一端,我的父親始終沒有出現,以後再也沒有出現。
黑夜迅速籠罩大地,和我的人生。
這世界多麼美好,而又無常
我是那種被稱為品學兼優的孩子。考試總在前三名,擔任班長、模範生,又常常代表參加各種比賽,演講、作文、繪畫…,每次都能拿回獎項。
而且,我彷彿自然就樂在其中,不覺吃力。
那時候小學只上半天課,中午回家後,我總是直奔書桌,開始做老師交代的功課。沒做完,幾乎連飯都不想吃。
暑假在家裡閒著沒事,看到牆上掛著一幅油畫,我隨手拿個凳子坐在它前面,拿起畫筆一遍又一遍畫著,幾乎忘記了時間。
偶爾我也會調皮,卻無傷大雅。有一年我當選模範生,到中山堂領獎。回到學校,一個同學想看領來的獎章,我不肯給,兩個人竟然在操場上追打起來,把一身釦子都扯掉了。這個同學叫做方力行,以後做了海洋生物博物館的館長。
這世界多麼美好!我只要付出就一定有所得。我從不懷疑,有一天世界將為我展開。
我不知道的是,這世界同時也多麼險惡無常,變化來臨的時候毫無預警。
那是敏感而緊張的年代。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守來台,接著又發生二二八不幸事件,白色恐怖像一張無形的網,籠罩著那一段黯淡歲月。
一開始,一切好像離我們很遙遠,只是走在路上,斗大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匪諜自首,既往不究」標語,不時就會迎面撲來。
民國50年代初期,雷震事件發生之後,知識藝文圈開始牽扯其中。耳語不斷流傳著,哪個主編被抓走、哪個演員入獄、哪個人被供出來……。
那年秋天,我的父親「白克」赫然列名其中。陌生人的不幸故事,成為我們家的悲慘命運。
我是名導演「白克」的孩子
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父親來台負責接收日本人留下的攝影器材。他隨後成立台灣第一個電影製片廠,並擔任第一任廠長。
父親多年的夢想實現了。
父親年輕的時候,戲劇就是他的最愛。廈門大學畢業後,他回到家鄉桂林從事藝文教育與推廣工作,並因導戲而結識出任女主角的母親。
那時電影產業剛剛興起,父親隨後去到上海涉獵電影製作。旋即,又考取廣西省政府的公費奨學金,準備到當時首屈一指的莫斯科電影學院深造。
那是一個年輕藝術家何等的夢想啊!
父親在上海等候蘇聯簽證,日本人卻在那年八月十三日發動松滬戰役,進攻上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父親像當時所有愛國青年一樣,滿腔熱血,毅然決定放棄留學,投入抗戰行列。
身為廣西人,他加入了由李宗仁將軍率領的五路軍團,在華中第五戰區迎戰日軍。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父親身背相機投入會戰之中,做出第一手戰地報導。父親幾十晝夜沒有消息,母親卻在湖北老河口的戰地醫院待產,準備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漫長的八年抗戰,父親仍醉心戲劇文化宣傳。他曾回到桂林創辦國防藝術社,也曾在重慶推行戲劇運動。在戰爭後期,他做到白崇禧將軍的少將職新聞官。
台灣發生二二八事變,白崇禧將軍奉蔣介石命來台處理善後。父親因而擔任電影製片廠廠長,著手拍攝台灣第一部記錄片「美麗的寶島」。他走遍全台,用鏡頭為台灣說話,讓當時的人對台灣的面貌,重新有了認識。
父親有自己的電影理念,他雖來自外省,卻認為電影在台灣要有發展,就必需走入民間。因此,他主張拍台語片,並導演了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台語片「黃帝子孫」。之後,又導出了叫好又叫座的「瘋女十八年 」、「唐三藏救母」、「南海風雲」、「台南霧夜大血案」、「龍山寺之戀」等戲。海內外片商搶著找他拍片,他被稱為「台灣電影的開拓者」。
除了在片場執導演筒,父親同時也是位學者。他研究「蒙太奇」手法,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電影技巧,並著有《電影導演》一書。他還創辦了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現台灣藝術學院前身)影劇系,親自教授「電影導演」這門課。
他不導戲的時候,也以白克為名,經常在各大報發表影評,廣受歡迎。資深影評人黃仁,在著作中稱他為「台灣影評的創始人」。
因此,我們家客廳除了常有親戚、朋友、學生來訪之外,也少不了明星、導演、製片人,和想找父親提拔的俊男美女。
身為導演的孩子,我跟著享有許多「特權」---到片場看試映會,看到的電影總比同學早一步。看電影不必買票,打個招呼就可入場。甚至父親每個月在美而廉和影劇人士的雅聚,也會帶我去聆聽大人們的高談闊論。
還有維也納合唱團、白雪溜冰團、寶塚歌舞團、馬戲特技團等,都有招待券讓我們一飽眼福。這些事,讓我在兒時同伴面前總是無比驕傲。
不過,父親經常外出拍片,在家裡的時候並不多。即使在,也很少說話。通常吃過晚飯,他就埋進客廳裡的單人沙發,拿起用舊報紙層層包裹的洗衣板,架在把手上當桌面。然後打開收音機,一面聽廣播,一面投入寫作的天地。只見他或者閉目沉思,或者振筆疾書,一篇篇影評、論述,傾瀉而出。
我尊敬他的世界。而我最快樂的時間,是有時候父親會讓我踩在他腳上,抱著他半個身驅,帶著我在客廳裡一面聽廣播,一面緩緩打轉。我喜歡這種靠近他的感覺,我覺得安全極了。
而且,父親寫完評論之後,不時會要我負責謄寫一遍,再給我一塊錢做工資。我緊盯著他的手稿,一字一字謹慎抄寫。有時報社派來家裡拿稿的人,為趕截稿就在門口等待,我抄完稿父親看過就立即送報社。這一刻,我心中得意極了。
可是,這一切突然都凍結了。
那一夜之後,我再沒見過父親
九月,六年級剛開學沒多久,中秋節的前一天,我下課回家。意外的,家裡竟然空無一人。
念初中的姊姊放學回來,我才知道,爸媽白天被帶去一個叫「警備總部」的地方。他們隨身沒帶什麼東西,那麼,晚上應該就會回來了吧,我心裡想。
那個晚上,我們的希望落空了。一天又一天過去,我和姊姊持續等著,每一天都以為,那一天他們應該會回來了。我們不安地祈禱,焦急地等待,不時開門出去看爸媽回來了沒,心裡愈來愈害怕—他們會不會出事了?
那時哥哥正在軍中服兵役,姊姊打電話向親友求助。唯一的阿姨來了一個多禮拜,也不得不放下我們,因為她自己也有六個孩子要照顧。
父母親毫無音訊,我本能地意識到,這不是一件尋常的事,但在老師和同學面前,還得故作鎮定。一向名列前矛的我,成績因此大幅滑落,老師來做家庭訪視,姊姊和我只能異口同聲:「爸媽到香港去,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
三個多月後,過舊曆年之前,突然有一個晚上,好幾輛車在家門口停了下來。
車門打開,「是媽媽!」我在心裡歡呼。她身前身後跟著許多人,不過,我找不到父親。只見這群陌生人進門翻箱倒櫃,把家裡上上下下全搜過一遍,帶走了父親的日記,只留下一屋子的凌亂和驚恐。
突如其來的事件,頓時冰封了我們的人生。我們不會知道,那一天之後,這個家裡將像一座死城,沒有歡笑,沒有哭泣,沒有人問為什麼。
在家裡被搜的同時,姊姊和我獲准去看父親。坐在黑頭車裡,沒有人敢出聲,我甚至沒有意識到那晚姊姊在我身旁。我們被帶進一個很大的房子裡,屋裡很暗,我看見父親坐在那裡,旁邊還圍了許多人。我只能遠遠看著,竟然不敢上前。
父親是一個知名導演,在我的印象中,他總是那樣英氣勃發又沉穩自信。但那晚的他,卻逕自沉默著,不發一語。然後,他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在那巨大的恐懼裡,我只直覺的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父親,最後一次聽他說話了。
我真的再也沒見過父親。隔年,他被處以極刑,三顆子彈穿胸而過。
而我,也從此展開我的生之追尋。
|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勇於真實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2 則評論,查看更多評論 |
|
 |
勇於真實 作者:白崇亮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9-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05 |
行銷企管 |
$ 221 |
財經/企管/經濟 |
$ 228 |
中文書 |
$ 229 |
經營管理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圖書名稱:勇於真實
奧美集團董事長白崇亮,掌握台灣第一大公關、廣告集團,協助許多個人與企業,建立起與他人、與公眾,最真誠適當的「關係」。
白崇亮有這樣的成績,比一般人更不容易。身為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他曾經飽受心靈的隔絕之苦;在一個理工至上的環境,他曾經無視自己內心的渴望,只求符合別人期待。直到他終於領悟:只有勇於真實,向著陽光面對自己,才能在人生旅途中,找到內心的力量,也找到自己的道路。
這是一段深刻的自我追尋,也是一個動人的生命故事。
作者簡介:
白崇亮 著
現任台灣奧美集團董事長,領導奧美廣告、奧美公關等近五百名精英專業團隊。有「公關教父」之稱,也是國內外知名企業的品牌行銷顧問。 他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系,並獲得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及博士學位。現在政大企研所EMBA授課,是少數兼顧理論與實務的經營者。 白崇亮來自白色恐怖的憂鬱受難家庭,卻成就於充滿卓越創意熱情的奧美集團。對於人的內在世界,他有特別的敏銳與關懷。 這是一位跨越工、商、人文,具有真實內涵與情感的領導者。
章節試閱
1 冰封的十二歲
父親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除夕,忙亂歡樂的氣氛開始溫馨起來。
辦年貨的人買夠了,工作的人離開辦公室了,趕車的人也回到家了。四十多年前,台灣過年的氣氛還非常濃厚,除夕團圓是家家戶戶的大事。
住在我們寧波東街這個巷子的人,都不是什麼富裕人家。街頭巷尾,平時盡是孩子的天下,騎車、追逐、玩球,長年吵吵鬧鬧。這一刻,卻出奇地安靜,好像什麼聲音都沒有。
路上變得異常冷清。我獨自站在門前,一直看著巷口—爸爸會不會突然從那裡出現...
父親指著我,用我能夠聽得見的聲音,告訴旁邊那些看守他的人:「這是我的小兒子,他將來會有出息的。」
除夕,忙亂歡樂的氣氛開始溫馨起來。
辦年貨的人買夠了,工作的人離開辦公室了,趕車的人也回到家了。四十多年前,台灣過年的氣氛還非常濃厚,除夕團圓是家家戶戶的大事。
住在我們寧波東街這個巷子的人,都不是什麼富裕人家。街頭巷尾,平時盡是孩子的天下,騎車、追逐、玩球,長年吵吵鬧鬧。這一刻,卻出奇地安靜,好像什麼聲音都沒有。
路上變得異常冷清。我獨自站在門前,一直看著巷口—爸爸會不會突然從那裡出現...
»看全部
目錄
序一:最大的力量是愛,不是恨-高希均序二:面對逆境勇於真實、復原力強的最佳典範-吳靜吉自序:打開內心的視界-白崇亮第一篇跌落谷底1.冰封的十二歲2.最大的恐怖是隔絕3.我逃避了選擇的自由4.成為不想成為的人5.年少時受苦,原是好的第二篇尋找自己6.學習做自己7.經驗是最好的老師8.在黑暗中描繪人生願景9.認識總經理的世界第三篇展開的世界10.世界展開在我眼前11.信任,是最大的資產12.愛情的美麗與哀愁(上)13.愛情的美麗與哀愁(下)14.手中拼圖,該在哪裡落下?15.最神奇的禮物16.「我的志願」實現了第四篇內在的力量17.ActingOu...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白崇亮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7-09-27 ISBN/ISSN:9789862160060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30頁
- 類別: 中文書> 商業> 經營管理
圖書評論 - 評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