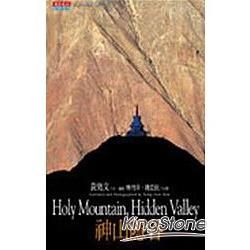「作為一個經常要面對新道路的探險家,我的座右銘是:『願效犬馬作先鋒。』也許假以時日,許多支持者會看到支持探險的必要,明白探險是保護無數珍貴自然及文化的先驅,沒有它,這些東西很可能在我們有機會看一眼或記錄下來之前已經消失了。」 ──黃效文
本書是黃效文先生2003-2005年在中國邊陲荒野探險及保育的第一手報告。持續二十年的觀察與紀錄,作者眼見驚天動地的變化從城市心臟延伸到末梢神經,作者帶領的「中國探險學會」在原民生計、自然保育和文化遺跡的拯救之間,尋找最圓滿的平衡點。
三年的報告大致在「探險家現場」的主題下以Nature Field Diary和Culture Field Diary分成兩本書結集,但兩者之間互有相關,亦不可截然畫分。
《神山隱谷》包括了〈美猴王對傈僳族獵手〉、〈亞洲河狸的最後防線〉、〈金毛盤羊〉、〈尋獲消失中的獒〉、〈犛牛乳酪盛宴〉、〈走後門入西藏〉、〈香格里拉的山卡喇〉……二十多篇珍貴精彩的紀錄。全書中英對照,圖文並茂。
作者簡介:
黃效文 著
二○○二年,黃效文被《時代雜誌》選為「二十五位亞洲英雄」之一,並被譽為「中國成就最高的在世探險家」。 黃效文一向致力於探險活動及自然與文化保育研究,曾被《時代雜誌》選爲「二十五位亞洲英雄」之一,並譽爲「中國成就最高的在世探險家」。他於一九八六年在香港創辦了著名非營利機構「中國探險學會」並成為會長,曾先後多次率領大型探險旅程,其中包括六次爲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之探險活動。他更於二○○五年六月的野外探險中,利用美國NASA最新太空科技發現了中國長江的新源頭,而被廣泛報導。 在環境保育工作方面,黃效文獲獎無數。他提倡採用多層面的模式和策略,在既能保存大自然及文化的同時,又未忘提升當地人民生活素質及經濟發展。「中國探險學會」在保護中國多種野生動物工作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包括:藏羚羊、野犛牛、藏野驢、亞洲盤羊、亞洲河狸、水獺、金絲猴及黑頸鶴等。此外,黃氏於保存西藏古建築、寺廟及壁畫復修研究上,不遺餘力,獲得「勞力士事業獎」(Rolex Awards for Enterprise)的榮耀。他對中國「懸棺」的研究更被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拍攝成一小時的紀錄片,後奪得亞洲最佳紀錄片之殊榮。 黃效文的工作及研究廣爲國際傳媒所關注,包括:探索頻道 (Discovery Channel)、國家地理頻道(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美國有線新聞網路 (CNN)、 英國廣播公司 ( BBC)、 商業電視新聞網路 (CNBC)等做過多次報導。黃氏亦著書無數,於英、美、亞洲等地發行。他所創辦的「中國探險學會」在中國大陸建立了數個中心及主題博物館,現在仍就中國偏遠地區進行著二十多項研究。他亦曾多次應邀對企業主管並在國際會議上(如:YPO及WPO)發表演說。 黃效文持有多間研究學院的學術頭銜,他的工作廣為國際傳媒報導,包括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美國廣播公司(ABC)、商業電視新聞網絡(CNBC)、探索頻道(Discovery Channel)等等,亦得到多間主要公司及知名人士的支持,包括殼牌、可口可樂、萬國商業機器、柯達、匯豐銀行、瑞士銀行 、松下、 路華汽車等。 黃效文的格言為——「值得做,做得好,仍不夠。還要有創新。」前兩句不外聊以慰藉,,最後一句才是挑戰所在。
章節試閱
探險─—科學或藝術?必需或奢侈?
多年來,屢次有初識者或朋友在得悉我曾任職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為探險家後這樣說:「這雜誌真令人艷羨,我們都訂閱多年了。」另一些人則奇怪何以幹這種探險工作的中國人不多。
但絕少人會同時問一問這種「令人艷羨」的工作的支援從何而來。事實上,當我創辦的中國探險學會最初四處尋求支援時,許多人都一口拒絕,好像這份工作既然好玩又刺激,就理應自給自足一樣。或許鐘斯博士(Indiana Jones)所演釋的上世紀探險家應該負上一份責任,畢竟那齣電影賺過數以千萬呢!
回頭說說《國家地理雜誌》吧,其學會及雜誌都創立於一八八八年。電話發明者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是創會成員之一,應該也是最能左右雜誌初期方向的人。確實必須具有遠見才能創出一些價值悠久的事物。時至今日,這本封面有黃框的雜誌在世界各地已成為一個鮮明的標誌。
我面前有一本一八八八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一冊的《國家地理雜誌》,內有六張彩色海洋地圖,但一張照片也沒有。赤土色的封面,封底列有創會時共二百零五個會員的姓名及地址。一個世紀之後,當我在國家地理雜誌工作時,它的會員已超過千萬,全部列出的話將比任何一本電話簿都要厚。
在雜誌社工作時,我有幸能身兼數職──記者、攝影師、探險家,這多重身分令我在學會內路路暢通,得心應手。主編比爾.加勒特(Bill Garrett)習慣把我喚作效文孛羅。每當我遠行考察歸來,雜誌社都會在十樓特設一頓向我致敬的午宴,桌子上並排放著中、美小國旗。這多重身分亦帶來的其他優待,諸如坐頭等艙機位、在香港轉機時住文華酒店等,可能是作為艱辛旅程的一種彌補吧。這艱辛並非肉體上的,而是當年要應付的各種夢魘般的官樣手續及極度刁難的制度。
在西方,早期的探險事業被視為科學,主要由皇室、政府、軍方及學術機構支持,後來一些富有的有識之士也加入支援行列。國家地理學會就是這麼一個以「增進推廣地理知識」為使命的機構,歷經百年而絲毫未變。然而,隨時日遠去,我們這些經年累月探險考察的人卻將原來的科學昇華成藝術。儘管探險事業中存在一些不明因素,但它的某些節奏卻不亞於創作經典名曲或傳世繪畫。一些探險或遊歷鉅著如馬可孛羅(Marco Polo)、李文斯敦(Livingstone)、吉卜林 (Kipling) 及海明威(Hemingway)的作品俱可為證。事實上,吉卜林及海明威二人均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現代,探險事業的定義擴大了。穿著高級衣履,從事高危險活動的旅行家或運動家多已被當成探險家。在大探險時代,許多著名探險家體格平凡,有的更身體殘障,但是腦袋並不平凡。現代的所謂探險家,看見一座山 便耐不住地要爬上山頂征服它。但真正傳統探險家看見一座山, 很可能只去最低的山口。他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尋找山背後所隱藏的,以擴大他對周遭世界的知識。
撇除定義,當代探險家還有另一種共同束縛,就是他們發現了某些東西,但很快的,這些自然或文化的奇蹟就在他們有生之年消失了。世界變化之快速令不少探險家無可避免地加入保育大合奏中,齊聲保護我們身邊的自然及文化遺產。這些呼聲大大推動了世界各地的保育工作。
而我自己在過去三十年的考察旅程中也略有發現,我也學會識別保育方面的緊急需要,設計具創意的專案,籌集資金,並付諸實行,獲得一些認同,也取得一定的成果。
大概這是因為「保育」在世人眼中跟「探險」是不一樣的,不論自然或文化,人們現在什麼都喜歡去保護。很多人甚至轉行從事保育或經營保育生意,因為有錢可募,有錢可花,有錢可圖。當大家都一味地談「持續發展」時,我覺得該是說一說「經濟效益的保育」的時候了,不是嗎?
中國探險學會一直將探險精神銘記於心,擁有種種排難解困的創新方式,隨時從容領先。作為一個經常要面對新道路的探險家,我的座右銘是:「願效犬馬作先鋒」。也許假以時日,許多支持者會看到支持探險的必要,明白「探險是保護無數珍貴自然及文化的先驅」,沒有它,這些東西很可能在我們有機會看一眼或記錄下來之前已經消失了。也許假以時日,那個我常被問的問題—─「為什麼中國探險家這麼少?」—─可以由年輕一代的探險家作出回答。
金毛盤羊
馬兒訓練得很不錯,我的屁股也差不多如此。從今天早上九點十五分起,我騎著牠走了足足十一個小時,共二十三公里。不論我想轉左、轉右、慢跑、煞停,只需輕觸一下韁繩,這頭黑馬便會有反應。同樣的,只需輕輕碰一下我可憐的屁股,我也會有反應。
為了大角盤羊,這一切還是值得的。我們一隊人這次與新疆動物學專家初紅軍及兩名嚮導,進入科克森山尋找盤羊。這種動物的雙角長達六十多吋,是世界各地狩獵錦標競賽者的最愛,而科克森山是少數仍然開放給此類活動的獵場。初紅軍信心滿滿地告訴我這兒盤羊為數極多,似乎想為狩獵說好話。我對此卻不無懷疑,因為在我三十年探險生涯中,只有一九九六年冬天在祈連山見過盤羊一次。
初紅軍是個大個子,腦筋靈活,說話又快,像機關槍。他是新疆北部阿爾泰林業局副局長,正攻讀野生動物學博士學位,更有志將盤羊變成中國狩獵運動中的旗艦品種。以一個頭顱值二萬四千美元來說,他的積極及動機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科克森山面積三百平方公里,高度幾達海拔一千六百公尺,山上滿是草場,但只有低地才有哈薩克牧民在冬天放牧,其餘都是未開發的山野,也是無數群盤羊的家園。 初紅軍說總數有六百多頭,即每平方公里兩隻。
接下來的幾小時,我不得不承認他說的也算可信。我們騎馬走上一個可俯瞰四野的高處山脊時,下面三百米外便有一群為數二十多隻的盤羊列隊走過。這些都是成年及老年的公羊,都頂著碩大的雙角。據說公羊奔走時必須昂首,否則那對超重大角會令牠失去平衡。亦有說老年公羊多數在冬天裏餓死,因為那時草太短,而牠們突出來的長角令其無法觸及地面進食。
一天下來,我們一共遇上了差不多一百二十頭盤羊,三五成群地分布在各個山丘和溪谷,其中更達十多頭一群。我在300毫米/2.8光圈鏡頭上加上1.4X增培鏡,遂能遙距捕捉牠們的威武風姿。還因此發現了一個帶著相機騎馬的小秘訣。如果一個人揹著中距鏡頭照相機,所有的重量都落在他的肩膀上,脖子很快便會酸痛。但如果他是像我一樣拿著長鏡頭,就可以把鏡頭垂直靠在馬鞍上,把重量卸給馬匹,而自己只需要輕輕地兜著相機和鏡頭。這樣省下的力氣便夠我扮演西部牛仔,每次一遇到盤羊群,就拔起相機,好像拔槍一樣,靠穩在左臂,瞄準盤羊在十字棱鏡中心,卡喇卡喇,「射」光好幾筒「子彈」。當然這只是軟片,但當中的滿足感不下於一個獵人,也不用付出二萬四千元美金代價。
我們一邊策馬馳騁,一邊討論。大家都同意在某些地方實行管制式狩獵活動是促進更完善保護的一種平衡方法。初紅軍立論的前提是:當一種動物對狩獵運動者而言 價值這麼高昂時,政府也會非常看重,務必維持其龐大數量,於是便會為之分配資源,令這類動物得以保存。而當地牧民明白了這種動物對外來獵人的價值之後,也不會把牠們白白浪費在偷獵之上,因為他們也可以在政府的收益中分一杯羹。
另一方面,我則提出我的理論:現今的野生動物種群普查在釋譯數字方面存在重大差異,很可能有誤導成分。我認為總數應撇除無繁殖能力的老年雌、雄動物,因為牠們不影響一個生物種的延續,對於這個物種的將來無法有貢獻。然而這些動物卻可以作其他用途,狩獵運動只是其中之一。一個會支付二萬四千美元的運動員也會盡其所能找一個最大的頭來射殺,而這較大頭顱者很可能是一隻沒有繁殖能力的公羊。這些衰老的動物通常都捱不過嚴冬,很容易成為天敵,如豺狼、雪豹的獵物。 在盤羊這問題上,依我推想,由於狩獵者都有其規範指引,自然也總會有一套自我檢查準則吧。絕對愛護動物人士可能覺得我的推論非常殘忍,但我認為它合乎科學邏輯。
再者,有些成年的雄性動物在交配戰中敗了陣,離群獨居,也可以算作是沒有繁殖力的,例如高原上便有不少四處流浪的獨身野犛牛。捕捉這些動物,可以為日漸衰落及退化的家養犛牛注入新血,甚至捕捉雌性野犛牛另建家庭,也可以為這些單身公牛帶來傳宗接代的新生命。
又或者像猴子這類靈長類動物群中,只有最優秀的公猴才有交配機會,其他的公猴也可以不計算在繁殖因子內。在這種情形下,沒有繁殖力的動物可以作其他用途,在動物園或博物館供人觀賞,或作科學試驗品,甚至為市場作出一分貢獻。但是,如果我們從中調適,把牠們從家族中帶出來,也許這些較弱勢的一群便可以在低競爭的控制環境下重獲交配的機會。雖說有礙大自然的適者生存定律,但在瀕危物種保護前提下,也算是另一辦法。否則,牠們便不屬於生存後代方程式的一部分。
我們繼續討論,並計畫明年的活動,打算支援所有盤羊之母──帕米爾馬可孛羊的跨境研究。這種羊的角向外伸展成複圈狀,幾達八十吋長,是狩獵運動中的王者。這個計畫不僅可把中國探險學會的旗幟插到中國最西端,也可使我們的專案影響遠遠延伸到比鄰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及塔吉克斯坦,成為國際專案計畫。
考量中國這種發展中國家的實情,將經濟價值,甚至政治價值引入構想中,一定會吸引新的資源及政府的關注,使我們的計畫國際化是正確的方向。大熊貓計畫便是一個典範,大熊貓在熊貓玩具所獲得的經濟效益、在政治饋贈及強化中國的國際形象方面的重要性,都已遠遠大於牠作為一種需要保護的野生動物。我認為大熊貓優先隸屬於外交部,這話也許太直接,卻千真萬確。
黃昏時分,騎馬下山時,我已然忘記屁股的疼痛,而忽然想起今年初與好友奧地利皇太子卡爾哈普斯堡(Karl von Habsburg)的薩爾斯堡行。卡爾是獲頒金羊毛勛銜的君主,他曾向我解釋這個最古老的勛銜的歷史及意義,並展示他掛在頸項的細小金毛羊。雖然中國並沒有類似的勛銜,但二萬四千元一發子彈,簡稱24K的盤羊也真可算是世界這處最偏僻小角落的金毛羊了。
探險─—科學或藝術?必需或奢侈?
多年來,屢次有初識者或朋友在得悉我曾任職於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為探險家後這樣說:「這雜誌真令人艷羨,我們都訂閱多年了。」另一些人則奇怪何以幹這種探險工作的中國人不多。
但絕少人會同時問一問這種「令人艷羨」的工作的支援從何而來。事實上,當我創辦的中國探險學會最初四處尋求支援時,許多人都一口拒絕,好像這份工作既然好玩又刺激,就理應自給自足一樣。或許鐘斯博士(Indiana Jones)所演釋的上世紀探險家應該負上一份責任,畢竟那齣電影賺過數以千萬呢!
回頭說說《國家地...
目錄
序──高希均前言──黃效文多元生態之間自然昌盛文化衰猴子算盤香格里拉的山卡喇亞洲河狸的最後防線金毛盤羊西藏隱谷探險──科學或藝術?必需或奢侈?美猴王對傈僳獵手緬甸國寶──因萊湖西藏的時光囊犛牛乳酪盛宴尋獲消失中的獒?藏獒之爭議後門入西藏一窩太早,一隻太少北緯五十三點四度,零下三十度人和狗的庇護所大聖伯納教堂走向長江源長江,長江入藏之路的今昔二十世紀絕大地震藏獒大家庭後記黃效文
序──高希均前言──黃效文多元生態之間自然昌盛文化衰猴子算盤香格里拉的山卡喇亞洲河狸的最後防線金毛盤羊西藏隱谷探險──科學或藝術?必需或奢侈?美猴王對傈僳獵手緬甸國寶──因萊湖西藏的時光囊犛牛乳酪盛宴尋獲消失中的獒?藏獒之爭議後門入西藏一窩太早,一隻太少北緯五十三點四度,零下三十度人和狗的庇護所大聖伯納教堂走向長江源長江,長江入藏之路的今昔二十世紀絕大地震藏獒大家庭後記黃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