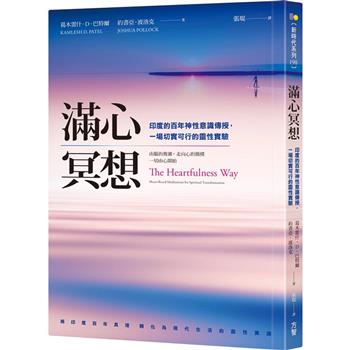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5 項符合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的圖書 |
| 最新圖書評論 - | 目前有 1 則評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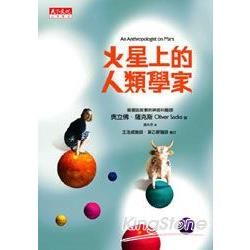 |
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作者:奧立佛.薩克斯 / 譯者:趙永芬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8-08-29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98 |
健康醫療 |
$ 308 |
西醫 |
$ 308 |
西醫 |
$ 315 |
西法醫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圖書名稱:火星上的人類學家
作者簡介
奧立佛‧薩克斯
1933年生於倫敦,出身科學家與醫生世家。在牛津大學接受醫學教育,然後在加州大學洛衫磯分校以及舊金山錫安山醫院,接受醫師養成訓練。從1965年起,他便定居紐約市,擔任紐約大學醫學院神經科學教授,以及安貧姐妹會(the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的神經科學諮商顧問。
薩克斯醫生的文章經常刊載於《紐約書評》和《紐約客》雜誌,以及各種醫學期刊。他也是十一本書的作者,包括《看得見的盲人》、《腦袋裝了二○○○齣歌劇的人》、《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以及《睡人》(獲得奧斯卡獎提名的同名影片「睡人」,就是根據本書改編)。
薩克斯醫師於2015年8月30日不幸因癌症辭世,享年八十二歲。
想要更深入了解薩克斯醫生,歡迎蒞臨www.oliversacks.com網站。
譯者簡介
趙永芬
東海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碩士,曾任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媒體委員、教學設計委員,目前擔任中國工商專校專任講師。譯有《天才老爹爸爸經》、《大逃亡》、《頑石也點頭》等書。
圖書評論 - 評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