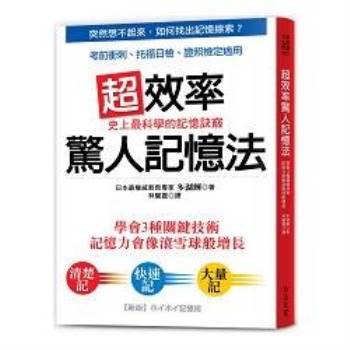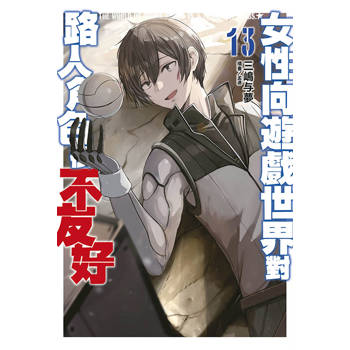一個人
Alone
從小,我就很憧憬一個人的感覺。
我的母親,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夾在中間的我,從前面數,從後面數,都是最常被漏數的那個。五歲那年,我們兄弟姊妹被帶著去參加大拜拜,我竟突發奇想,一個人跑開,沿溪谷往山裡走了好幾公里吧。當然那時還不懂,現在知道,我何其憧憬「落單」的美好時光。
學生時代,我也喜歡一個人坐在樹下幻想。下雨天,我盯著雨滴從簷上滴下來,可以盯個把鐘頭不動。大概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心境才能「對」到那種詩意。
我也想過,等我老了,一個人圈塊地,在裡面放羊,好不快活!曾幾何時,閒雲野鶴的鄉野生活,還真的變成全球最時尚的奢侈!天馬行空的想像,像心靈的旅行,讓我自由自在,徜徉在幻想的草原。
如果孩子們以後都能好好照顧自己,也許內人會准我自己蓋間小茅屋,一個人撿柴種菜,淡泊地過活。週末假日,收一收回家報到,含飴弄孫也很好。
一個人,卻又找得到回家的路,真的是種幸福。你可以擁有美好的關係,又有一座秘密通道,可以通往獨處時最純粹的真實。
旁人常會左右我們的情緒,有時也迫使我們放不下面子。一個人,可以讓你真正回過神來,清晰看見自己的好處或錯誤。
泥濘
The Mud
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面臨人生與事業罕有的低潮。放大的誤解,失焦的溝通,人情的冷暖,讓我帶著無奈的心,遠離這片泥濘,遠至大陸貴州,和當地居民種了一陣子田。
在貴州,沒有人知道我原來是做什麼的。那裡的農民個性爽朗乾脆,有話直說,勞動的汗水就是生活的價值。剛開始我也覺得新鮮,耙土施肥的挺帶勁。有那麼一天,眾人吆喝著齊來抓豬,好大一頭山豬,七八個人使勁要抓,我用力過頭,當場摔了個遍體鱗傷。
沒人笑我。他們笑的是這生活插曲帶的餘興。裡面一個姓什麼的我不記得了,伸出他佈滿厚繭的手把我拉起來,然後往我肩頭一拍:「我看你還行!改天為你引見引見,幫你談個六十塊日餉,上頭可能考慮用你!」大家笑開了,我也笑了。這裡,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他們用沒有偏見的眼睛看我,用一種爽朗的公平,對待他們自己那樣地對待我。
剛抓豬的田,被我們踩成整片泥濘,其上佈滿貴州漢子們和我的腳印。隔著幾千里,我從某片泥濘跋涉來另一片泥濘,卻在這片泥濘中,找到人生前所未有的平靜。
始與終
A Circular Route
每天與農民一起耕作的日子,在最末一次秋收工作後劃下了句點。我已經有勇氣,回台灣重新開始,以我曾有的樂觀和單純,再度面對我在乎的親友和事業夥伴們。
離開貴州的那天,我和一起幹農活的夥伴一一握手道別。在農場一同埋鍋造飯的革命情感,就要暫時譜下休止符。除了身上的衣服和回台所需的證件、費用之外,我把所有東西都留了下來。「黃先生,東西怎沒帶走哪?」一位夥伴不解地問。
我沒有答腔。他可能不知道,丟掉那些衣服,我多年來如影隨形的自卑心,也痛痛快快丟掉了。
帶著一身輕盈。我上路了。在一個是終點也是起點的地方。
合十
Together in Prayer
我曾經寄宿禪寺,在暮鼓晨鐘的洗禮中,悟到許多事。
通常凌晨四點多,打板聲會喚醒睡夢。我總隨著師父們一同早課。
這裡的師父,不論比丘或比丘尼,都是相貌相當莊嚴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大學或研究所一畢業就出家,二十出頭的年紀,已然透出同齡孩子身上難以得見的寧靜與安定,一股力量,源自他們對世事的洞悉,以及對眾生的悲憫同心。
他們闔上眼睛誦經,雙手合十。從這些年輕法師的口中,經文匯集為巨大的合唱,我也身在其中,感受到經句的力量。在那瞬間,所有牽掛、疑惑、委屈,都像被風帶走的灰塵,顯得如此微不足道。
我有時也會凝視著法師的手。這些其實還相當年輕的手,靜靜地合十,連結在一起,就像一個接通所有力量的回路。
不論我們稱之為神,或造物者,那個更高的意志為我們預留了太多太多的珍藏,只是絕大多數比例都是封藏起來的。就像封印一樣。我們的官能感覺得到的東西,其實只佔這世間很小的一部分。
但祂給了我們一雙鑰匙——手。
所有封印起來的一切,必須親自用我們的手,去連結、去開啟、去創造、去感受…我們才有機會知道,原來藏在我們身體與心識裡的,還有這麼多能量。
合十的手,就像一個啟示,讓我感受到悲憫的誦經聲召喚著某處的神秘力量。如何讓手成為介面,成為導體,喚醒封印在身體裡的內在能量?如何與天地間無所不在的能量連結,才能達到療癒的效果,以及我們渴望的幸福與平靜?我如此思索著。
勳章
Medals
三十八歲前,我很喜歡蒐集勳章。我的收藏,多到可以開好幾家勳章店。
勳章是很特別的東西。精雕細琢的造型,華美緞綬或別裔在衣襟上的各種設計,勳章讓我覺得是種充滿故事的物件。它原來的主人是誰?他有過什麼豐功偉蹟?又因為什麼原因,這枚勳章會流入市面,甚至飄洋過海,來到我的手中?
擁有滿坑滿谷的勳章,曾經帶給我一種自己很偉大的感覺。好像我比任何人都要功勳彪炳,勞苦功高。
年過五十的我,現在不再做如是想了。世間功名利祿的虛幻,徒留一枚枚告別了主人的勳章,安靜地見證人世的無常。
看見
Seeing
我總愛到其他國家,一方面體驗不同文化給自己的衝擊,一方面也希望瞭解當地的按摩服務,感受一下與台灣的微妙差異。
在阿姆斯特丹,我預約了三個小時療程,按摩師就像機器一樣,推拿揉捏,絲毫不帶感情。我請她停止,並告訴她,沒有感情,三分鐘和三個小時並沒有差別,然後離開。
路過印度,我也趁空檔接受一位鬍子斑白、個子很瘦的盲眼按摩師服務。全程他安安靜靜,只剩眼白的雙眼,並不望向任何地方。我感受到他的手似乎和我的身體共鳴著,這是充滿情感與故事的一雙手,透過每個動作,我都連結到自己的回憶、甚至老師傅這一生傳奇的經歷。
離開前,我向老師傅誠心道謝。老師傅在我離開的時候,忽然以英文說:I can see you, mister.
我相信他真的看見了。
祖孫
Grandfather and Grandson
我對手的感覺非常強烈。有時候,我甚至可以透過一雙手的質感,或者兩隻手交握的方式,讀出埋藏在裡面的故事。
有一年秋天,我在巴黎,看到一個老人牽著一個孩子,走在我前面的人行道上。
這孩子,應該就是老人的孫子吧。看著孩子白淨的小手,被阿公輕輕握在滿是皺紋的大手掌裡,也許怕把孫子的手握痛,老人的手指像會跳舞的小人一樣,噠噠噠噠地輕點著孫子的手,像跟隨著某個聽不見的旋律。
我幻想也許很久很久以後,小男孩長大了,對小時候很多事情都會沒了印象。但是,他可能會記得阿公在他的手上點踏的感覺。也很有可能,有一天他牽著自己孩子的時候,也會把這個秘密的、手指的小舞曲自然地傳下去。
高度
The Perspective
從前有兩個樵夫,都會到住處附近的森林砍柴。
其中一位樵夫習慣看到樹就砍,然後把整棵樹劈開,很省事地把一天的量在轉眼間劈好,揹回去。
另一位樵夫,則不忍攔腰把整棵樹砍斷。他總是先爬到樹上,悉心砍下每棵樹上可用的樹枝。砍完,再前往下一棵樹,用同樣的方式繼續。往往他得花上半天的工夫,一棵一棵爬上去,但他不以為意。
前面這位樵夫,沒多久發現附近的樹幾乎全被他砍光了,只留下被無情的斧頭砍得光禿禿的林子。後面這位樵夫,則繼續擁有整座茂密的森林,生生不息。
一個人的品格,就像這兩個樵夫對待樹的方式。品格高尚的人,表面上也許沒有那些投機者吃得開,然而品格的高尚,就像一個人天生的高度,讓他在關鍵時刻,做出對的決定。
一個人的成就再怎麼高,絕不會高過他的品格。我始終這麼深信。
浮雲
Drifting Clouds
我成了一個祝福者與肯定者。我曾經歷一番漫長的奮鬥,先成為奮鬥者,為的是使我有朝一日,終能以自己的手,自由地去祝福一切。
…萬物都受過永恆之泉的洗禮,因此超出了善與惡的分野。善惡本身,不過是變動無常的影子、消沉的痛苦、與漂浮不定的雲朵。
——尼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手之書的圖書 |
 |
手之書 作者:黃河南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27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45 |
二手中文書 |
$ 255 |
文學小說 |
$ 255 |
文學小說 |
$ 255 |
小說/文學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現代散文 |
$ 270 |
現代散文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手之書
這是黃河南第一本個人散文集,也是他經歷人生大挫折省思後的感悟。《手之書》真情紀錄了黃河南創建龐大事業的心路,以及隨著社會變遷、生涯起伏、挫折考驗,歷經長時間旅行與簡單生活的沉澱,凝聚勇氣重新再起的序曲。透過如詩如畫的攝影及六十六篇短文,黃河南細膩刻劃回憶與情境,字裡行間流露令人低迴的生命故事。全書以「手」為主題意象,譜寫家庭、事業、人際、感情,以及專注、務實、創造、連結……等體悟。這是一本易讀的,在當下深深感動的書。
作者簡介:
黃河南 著
一個曾經在台灣塑身界締造多項紀錄的傳奇人物,也是行事作風與創業歷程令許多人好奇的一個名字,他在放下一切,親自接觸土地、親自嘗試種植之後,雙手勞動的喜悅,使他的生命得到了沉潛與釋放,寫出第一本個人散文集《手之書》。重新回到他貫注一生心血的事業體,他又以《經典女人》這本書做為邀請,邀請大家一同學會深愛自己,兼愛他人,在情意日趨枯竭的這片荒蕪土地,以真心灌溉情意的花朵。他說:「生命裡,很可貴的是「善」。善,就像心中的容器,要能裝水,又能研磨。初心也可貴。走進眼前幽暗的樹林,初心如炬,照見林外的無盡展延。」
章節試閱
一個人
Alone
從小,我就很憧憬一個人的感覺。
我的母親,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夾在中間的我,從前面數,從後面數,都是最常被漏數的那個。五歲那年,我們兄弟姊妹被帶著去參加大拜拜,我竟突發奇想,一個人跑開,沿溪谷往山裡走了好幾公里吧。當然那時還不懂,現在知道,我何其憧憬「落單」的美好時光。
學生時代,我也喜歡一個人坐在樹下幻想。下雨天,我盯著雨滴從簷上滴下來,可以盯個把鐘頭不動。大概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心境才能「對」到那種詩意。
我也想過,等我老了,一個人圈塊地,在裡面放羊,好不快活!曾幾何時,閒雲野鶴的...
Alone
從小,我就很憧憬一個人的感覺。
我的母親,一共生了七個孩子。夾在中間的我,從前面數,從後面數,都是最常被漏數的那個。五歲那年,我們兄弟姊妹被帶著去參加大拜拜,我竟突發奇想,一個人跑開,沿溪谷往山裡走了好幾公里吧。當然那時還不懂,現在知道,我何其憧憬「落單」的美好時光。
學生時代,我也喜歡一個人坐在樹下幻想。下雨天,我盯著雨滴從簷上滴下來,可以盯個把鐘頭不動。大概只有一個人的時候,心境才能「對」到那種詩意。
我也想過,等我老了,一個人圈塊地,在裡面放羊,好不快活!曾幾何時,閒雲野鶴的...
»看全部
目錄
第一卷訴說悲歡的十個簡易手勢第二卷浮光掠影第三卷生命的交響樂第四卷旅程中第五卷浮世之島第六卷手的迴圈
商品資料
- 作者: 黃河南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2-27 ISBN/ISSN:9789862162859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07頁
- 類別: 中文書> 華文文學> 現代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