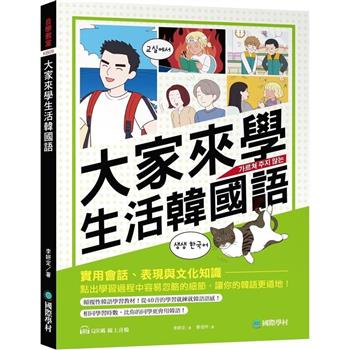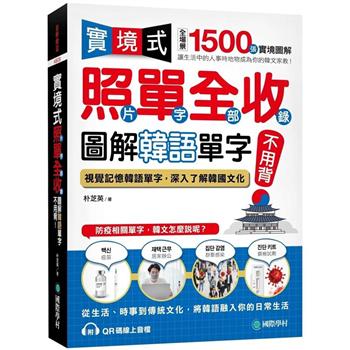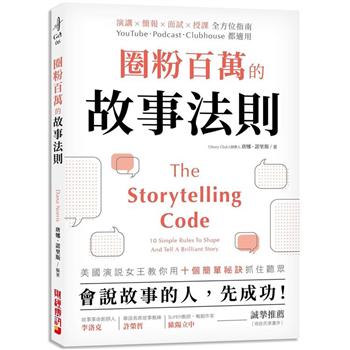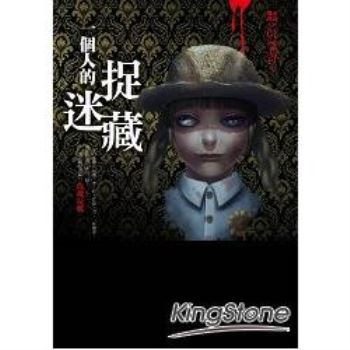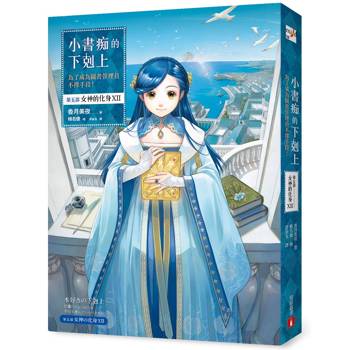海上行不由徑
緯度比較好決定,經度較難。地理大發現初期,航海者在大海中就常常沿著固定的緯度東西向航行,或沿著某經線南北向航行。沿著經線走,緯度較沒問題;沿著緯線走,可利用船速估計所行的距離,再換算成經度的差。
哥倫布第一次西航,從加納利群島出發,想維持加納利群島的緯度(28.5°)西行,只是因為海流的影響,走向稍為偏南。哥倫布會到達西印度群島,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其實是沿緯線航行的必然結果。
海 難
梭貝爾(Dava Sobel)的書《尋找地球刻度的人》(Longitude),談的就是人類測量經度的歷史。她提到一次海難事件,強調經度的難以捉摸。
這是英國海軍元帥夏威爾(Shovell)的故事。1707年夏威爾在地中海打敗法國的艦隊,出了地中海後沿經線北行。經過十二天的大霧,結果迷失了位置。他以為艦隊在法國西北角不列塔尼半島外的威珊島(Ile d'ouessant)的西邊安全海域上,於是勇敢繼續北行,卻一下子發現英格蘭西南角的夕利群島(Scilly)就出現在眼前,四艘軍艦撞沉海底,二千士兵陪葬著元帥的一世英名。
威珊與夕利兩群島經度相差1度,東西相距約80公里;估計船速決定經度,估計居然差了80公里!
國王的贖金
海難不只這一件,相繼的海難迫使英國國會於1714年通過「經度法案」,要賞獎給發明實際測定經度方法的人。標準及獎金如下:能準到二分之一度者,獎金2萬英鎊;三分之二者1萬5千英鎊;一度者1萬英鎊。2萬英鎊在當時是個大數目,所以又稱為(相當於)「國王的贖金」(King's ransom)。
木衛法
當時的競爭者都從天文入手。一種是木衛法,起源於伽利略。伽利略發現木星的四顆衛星,測得這些衛星被木星遮蔽到出現再到遮蔽的週期。不過被遮蔽的時刻和觀測者所在的經度有關;反過來,觀測這些衛星被遮蔽的時刻,就可推得所在地的經度。
可惜,在顛簸的船隻上用望遠鏡觀測木衛被遮蔽的時刻,談何容易,何況天氣不好時什麼都看不到了,只有在陸地上慢慢觀測慢慢算,才能把經度算得準。被請到法國的義大利天文學家卡西尼就用木衛法,確定了法國海岸線的正確位置。可惜經度法案要的是海上也通用的方法。
月距法
另一種天文想法是月距法,亦即月亮在天空運行時,和太陽或某些參考星星間在觀測者所張的角度,它和觀測者所在的地點及觀測的年月日時間都有關。英國皇家天文台長,從第一任開始就對月距法有興趣,每位天文台長都為此法之精進而努力。可惜月亮的運行軌道太複雜,雖歷經數任天文台長,但月距法的進展緩慢。
鐘錶法
經度法案之後,加入競爭的是鐘錶法。想法很簡單:帶一只標示倫敦時間的鐘錶上船,到某地正午時(可觀測太陽的仰角變化來決定),看這只鐘錶是幾點幾分,就知道該地與倫敦的時間差。以1小時等於經度差15度換算,就知道該地的經度。
不暈船的鐘錶
這種方法天文學家很瞧不起,因為它沒有深奧的天文理論與觀測,純粹是機械的研製。偏偏就有一位技藝高超的鐘錶匠哈里遜(John Harrison, 1693-1776),傾全力要製造一只超準又「不會暈船」的鐘錶。
當時的鐘用的是鐘擺,稍微一晃就停擺了。換用彈簧,又有熱漲冷縮及潮濕乾燥的問題,海上氣候變化多端,普通鐘錶一下子就暈船失常。
經度法案要求要有多準呢?15度相當於1小時,所以1度(赤道上距離111公里)相當於4分鐘,半度相當於2分鐘。當時從英國到美洲大概要6個星期,所以一天之快慢不能超過3秒鐘,否則累積起來就會超過2分鐘──其實這是赤道上的要求,若在緯度30度,則要打7折(cos 30°≒0.7),成為2秒鐘;緯度愈高,要求愈嚴。
哈里遜花了一輩子的時間,於1759年完成他自認滿意且經過測試的傑作。但在那些天文學家的挑剔阻撓之下,直到接近生命的尾聲,才於1773年得到應有的承認。
有了不暈船的鐘錶,海上定位的問題就解決了。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從天文地理學數學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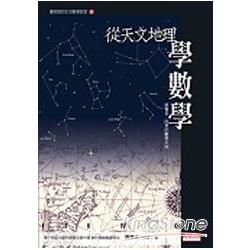 |
從天文地理學數學 作者:曹亮吉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3-1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60 |
二手中文書 |
$ 190 |
自然科學 |
$ 204 |
科學自然 |
$ 204 |
科學自然 |
$ 204 |
科學科普 |
$ 211 |
中文書 |
$ 211 |
數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從天文地理學數學
學數學的目的,
除了學會數學的基本內容,
更重要的是要訓練邏輯思考,
體會到在日常生活中、在各學門中,
有許多需要數學的地方。
在「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第4集裡,
「阿草」透過簡單的數學觀點,
以及歷史上的小故事,
帶領我們從天文地理學數學,
看看數學在天文、地理上的應用。
數學為什麼無所不在?
數學為什麼有用?
來到曹老師的生活數學教室,
你就會豁然開朗!
作者簡介:
曹亮吉 著
1943年生於東京,三歲返台。台大數學系學士,1972年獲得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自1976年任教於台大數學系,曾任系主任,於2001年退休。曾任《中國數學雜誌》(現改名為《台灣數學期刊》)總編輯、《科學月刊》總編輯,目前擔任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顧問。
多年來以「阿草」為筆名,致力於數學與科普寫作,著作包括《阿草的葫蘆》、《微積分基本要義》、《從月曆學數學》(原書名:阿草的曆史故事)、《從生活學數學》(原書名:阿草的數學聖杯)、《從天文地理學數學》(原書名:阿草的數學天地)、《從旅遊學數學》等書。《阿草的葫蘆》更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創作類銀籤獎。譯有《阿基米德寶典》。
章節試閱
海上行不由徑
緯度比較好決定,經度較難。地理大發現初期,航海者在大海中就常常沿著固定的緯度東西向航行,或沿著某經線南北向航行。沿著經線走,緯度較沒問題;沿著緯線走,可利用船速估計所行的距離,再換算成經度的差。
哥倫布第一次西航,從加納利群島出發,想維持加納利群島的緯度(28.5°)西行,只是因為海流的影響,走向稍為偏南。哥倫布會到達西印度群島,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其實是沿緯線航行的必然結果。
海 難
梭貝爾(Dava Sobel)的書《尋找地球刻度的人》(Longitude),談的就是人類測量經度的歷史。她提到一次海難事件,...
緯度比較好決定,經度較難。地理大發現初期,航海者在大海中就常常沿著固定的緯度東西向航行,或沿著某經線南北向航行。沿著經線走,緯度較沒問題;沿著緯線走,可利用船速估計所行的距離,再換算成經度的差。
哥倫布第一次西航,從加納利群島出發,想維持加納利群島的緯度(28.5°)西行,只是因為海流的影響,走向稍為偏南。哥倫布會到達西印度群島,而不是其他的地方,其實是沿緯線航行的必然結果。
海 難
梭貝爾(Dava Sobel)的書《尋找地球刻度的人》(Longitude),談的就是人類測量經度的歷史。她提到一次海難事件,...
»看全部
目錄
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第0篇 緒篇0.1古代的宇宙圖像0.2托勒密的天地第1篇 地球的大小1.1地是球形的1.2地球有多大?1.3哥倫布西航1.4橘子還是檸檬?第2篇 星球的位置2.1太陽的起居活動2.2月亮的起居活動2.3相對遠近2.4太陽系的尺度2.5天文的三把標尺2.6視差法量距離2.7看星等定距離2.8哈伯定律第3篇 行星的運動3.1圓形的世界3.2橢圓形的世界3.3引力的世界3.4模型的世界第4篇 旅者的方位4.1地球的經緯4.2大圓4.3半球4.4球面三角4.5船長的抉擇第5篇 地圖的繪製5.1圖窮匕現5.2東西南北5.3三角化測量5.4頂天立地的巨人5.5為船長...
»看全部
商品資料
- 作者: 曹亮吉
- 出版社: 天下遠見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09-03-12 ISBN/ISSN:9789862162873
- 語言:繁體中文 頁數:235頁
- 類別: 中文書> 科學> 數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