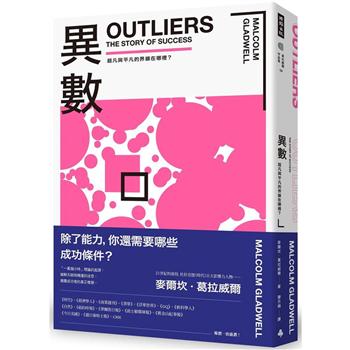前言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普魯希納(Stanley Prusiner)教授來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從瑞典國王手中接過他口中所謂的「大獎」。普魯希納研究普利子(prion)已有二十五年,他最大的成就,是發現造成牛海綿狀腦病(俗稱「狂牛病」)、庫賈氏症以及羊搔癢病的傳染病原普利子,並不是什麼病毒或是細菌,而是不具生命的蛋白質。蛋白質的英文protein,指的是「主要」(prime)以及「原始」(proto)的物質。有位研究普利子的科學家在一部紀錄片裡對採訪者說:「這個東西幾乎可永存不朽。」
瑞典國立卡洛琳絲卡學院指出:時年五十五歲的普魯希納給科學界帶來了一種「全新的傳染方式」。
多年來,野心勃勃的普魯希納養成了對好酒以及美食的喜好,如今瑞典的菁英份子在他們最好的餐館款宴他,一旁不斷有新聞記者拍照並徵詢普魯希納的意見。這一刻正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
當有記者問及,在拿下了科學界最高獎項之後,接下來他要做什麼;普魯希納回答說,他的新目標是尋求「普利子疾病的有效治療」。一九九八年,普魯希納告訴以色列一家報紙,他認為在五年內應該可以找出根治之道。
過了三年,也就是二○○一年,位於義大利威尼斯外圍由許多小鎮及農場組成的維內托(Veneto)區,有個家族舉行了頭一次的團聚,其中成員腦子裡想的就是普魯希納的話。特別舉行家族團聚在義大利並不常見,因為無此必要;義大利人本來就是做什麼事都全家族一起來,對於從來沒有失散的東西,是不必重新聚合起來的。然而這個家族卻有特殊的理由舉辦這個聚會,因為其成員當中有許多人攜帶了某個可怕疾病的基因。
這個家族具有貴族血統,成員當中有醫生、工程師、實業經理,以及一位廣受尊敬的學術界人士。然而這個家族也遭受了詛咒。至少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其成員遭受了某種名為「致死性家族性失眠」(fatal familial insomnia, FFI)的普利子疾病所苦。他們多是在五十幾歲時發病,最後會因失眠而致死。FFI是種體染色體的顯性突變,代表FFI患者的子女有五○%的機率會遺傳此疾。在整個人類族群裡,FFI的發病率是每千萬人當中才有一人;然而對這個受到影響的義大利家族分支來說,可是每兩個人就有一人會發病。
FFI的症狀既顯著且嚴峻,通常是患者進入中年後,會突然發現自己開始冒汗。對著鏡子,患者可以看見自己的瞳孔縮成針孔大小,同時會把頭擺成一種奇怪、僵硬的姿勢。便祕是常見症狀。女性會突然停經,男性則會不舉。患者開始難以入睡,他會想在下午補個午覺,但也不成功。他的血壓及心跳上升,整個身體進入高速運轉狀態。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他會想盡辦法入睡;他閉上眼睛,但就是沒法熟睡,最多淺睡一會兒。有時FFI患者可能進入一種半睡半醒的狀態,類似有些人在醒轉前所經驗到的惡夢。除此以外,他們就是不能夠進入深睡狀態,以取得真正的休息。這些人筋疲力竭的情況,可是超乎旁人的想像。
一旦患者完全不能入睡,情況就急轉直下,他將失去行走能力或平衡感。至於最悲慘的,或許是患者還能思考,曉得發生了什麼事。一開始,他們還能談論自己的病情,甚至寫下想法。再過上幾個月,有些人就失去了這個能力。一旦他們的身體停擺,就只剩下絕望的眼神,顯示他們心裡有數。但也有人一直到最後都還能講話及思考。到了疾病末期,通常是發病後的十五個月左右,患者會陷入油盡燈枯的昏迷狀態,然後死去。美國國家普利子監測中心位於克里夫蘭市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該中心主任甘貝帝(Pierluigi Gambetti)是這個疾病的發現人之一。他告訴我:「以前我認為阿茲海默症是我們能夠罹患的病症裡最糟糕的,但FFI這個病不但要你看著心愛的人在你面前瓦解,同時病人還曉得發生了什麼事,那可是更讓人難過。再來,對我而言,這種病是如此希罕,讓人感覺更糟。我認為就算死於車禍,也不比患上這種病那麼殘酷。」
上面提到的那個義大利家族,是全世界少數幾個受到FFI侵襲的家族之一。他們追蹤這個疾病,可以一路上溯至十八世紀中葉,一位住在威尼斯猶太區附近的醫生。從這位醫生,再傳給了維內托的一位貴族裘塞培,再到一八八○年代的汶森若、一九一○年代的喬凡尼、一九四○年代的皮耶佐,然後是二十世紀後期三○年間的阿頌妲、皮耶麗娜、席凡諾,再來則是……再來是誰呢?這也是每年家族聚會時,縈繞在大家心頭的問題。
從某方面而言,問題的答案是已知的。一九九○年代初,專精睡眠研究的波隆納大學神經研究所針對引起FFI的基因突變,給這個家族的許多成員進行了檢測,測定的結果則存檔備查。因此,誰將死於這個疾病是已知的,只是不知道發病的順序;可確定的是不久以後就會有人因此而死。過去一世紀來,至少有三十多位家族成員死於FFI,自一九七三年以來就有十四位,最近十年則有七位。按或然率而言,在活著的家族成員當中,至少還有十來位攜帶了造成這個疾病的突變基因。
許多致命的遺傳疾病會自行消失,理由是那些攜帶突變基因的患者常在生育下一代之前,就因病發而身亡;但FFI不同(至少對這個家族而言如此),因為患者在發病時都已經過了生育年齡。同時,這個家族的多數成員仍然決定要生孩子;因此,FFI也隨著他們的小孩而存活下來。曉得自己的小孩到了中年可能死於可怕的疾病,仍決定要生小孩,不是件容易的事。波隆納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給這個家族成員進行基因檢測後,有過仔細的衡量,最後決定不告訴他們誰攜帶了這種突變。因此該家族成員不能以此來決定自己要不要小孩,他們也同意寧可對此保持無知。據我所知,這個家族還沒有哪位成員因為害怕把惡疾傳給下一代而墮胎。
波隆納大學雖然曉得問題所在,但卻沒有解決之道。這個家族的成員還是必須等待這個惡疾最早的症狀出現:繃緊的脖子以及針孔般的瞳孔,然後是發汗及顫抖。手邊一直要有塊手帕來擦額頭上的汗,身上的汗衫每半天就得更換。還有就是婦女的停經,以及可怕的下一階段:開始失眠。
譯者後記
知識的饗宴
讀書的方式,因人因書而異。我是那種喜歡一字一句從頭讀到尾、不習慣速讀略讀的人,因此書架上擺了一堆只讀了開頭幾頁就無限期停擺的書。其中不值得繼續讀下去的書是有,但更多的情況,是有其他新書佔去了讀書時間,而放了下來。我的願望之一,就是哪天可以毫無外務、專心一本一本地把藏書給讀完;只不過這樣的想望,近期大概難以實現。因此,翻譯成了強迫自己精讀好書的另一選擇。
自一九九六年著手第一本科普書的翻譯起,至今已出版了十二本書;這是我譯的第十三本書,平均一年一本。每回開始一本新書的翻譯,我的感覺就像當初接下線蟲基因組定序的英國科學家薩爾斯頓(John Sulston)所言:「彷彿聽到牢房的門在背後關上的聲音。」因為那代表我又要開始一段與原文書長期抗戰的日子,也就是說一有時間,都得坐在電腦前從第一頁一直到最後一頁、一字一句對照著原文打出中文來。
翻譯是苦差事,做過的人都知道,但其中也有一些不為人道的樂趣,否則早就讓我難以為繼。我不能說自己譯的每本書都是經典,幸運的是,我從每本書都學到了許多之前聽過但不熟悉、甚至從未聽聞的知識。再者,兩種文字的推敲與轉換,好似拔河般來回角力,不時給人帶來短暫勝利的喜悅。
這是一本談「普利子」的書。普利子是種天然蛋白質,普遍存在於生物體內;但變性的普利子卻具有致命性及傳染性,給動物及人帶來災難。由普利子造成的疾病,以狂牛病及庫魯症最出名,之前不乏報章雜誌及科普書的報導,聽過的人也最多。本書則以「致死性家族失眠症」這個較少人聽聞的普利子症為切入點(原文書名《無眠之家》就是強調這種病),輔以動物的羊搔癢病、狂牛病與慢性消耗病,以及人的庫魯症、庫賈氏症與葛史宣氏症,說了一則則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故事,讓我「譯」不釋手。
科學研究是向未知領域挑戰的工作,逐步拓展我們對自然界的認識;但知識的圈子擴得越大,外圍的未知疆界也變得越廣。過去一世紀來,科學家對普利子疾病的成因已有長足了解,但對發病機制或有效治療之道,卻還沒有多少掌握。本書可讓我們認清,除了發生率極低的偶發及遺傳性普利子症外,大規模的傳染性普利子症都是人自己造成的。如何在「人定勝天」與「回歸自然」間取得平衡,大概是人類永續生存的恆久課題吧。
在此,我要對書中幾個譯名說明一二。Prion這個詞在國內有好些不同譯名,除了「普利(粒)子」外,還有「普利(里)昂」、「普恩蛋白」、「朊毒體」、「病原素」等。當初發現prion並予以命名的普魯希納,是取「proteinaceous infectious」的縮寫當字頭,電子、中子的「-on」當字尾,同時念起來與「普魯希納」自己的姓氏Prusiner還有點相近,故此譯名選「普利」不選「普恩」、選「子」不選「昂」。至於普利子本身即蛋白質,不需再加「蛋白」二字強調。「朊毒體」是大陸用語,「病原素」則由黃崑巖教授獨創,國內使用都有限。
還有,本書對動物及人的普利子疾病名稱有些區分:動物疾病稱「病」,好比羊搔癢病、狂牛病與慢性消耗病,人類的則稱「症」,譬如庫魯症、庫賈氏症與葛史宣氏症等。
最後,要感謝鄭惟和前主編的厚愛,找我譯這本書,並願意等我半年,把上本書譯畢後才開始;同時,還要謝謝她在退休後,擔任這本書的編輯,以她豐富的經驗,挑出許多譯文的毛病。我也要謝謝從未謀面的動物系學弟楊宗宏,在我的部落格留言表達從事翻譯的意願,也接受了試譯的考驗;結果幫我譯了大半本書(本書第一至三、十至十四章由宗宏完成初譯),使得進度不致拖延更久。由於這是宗宏頭一回譯書,所以我在文字上做了較多的更動;定稿的譯文如有任何舛錯,責任都在我身上。
2009/07/21於美國密西根州特洛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