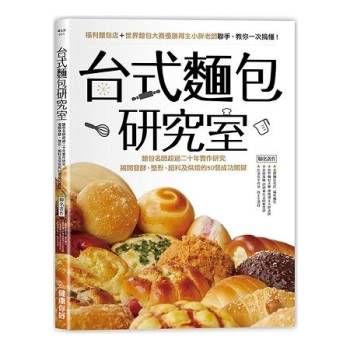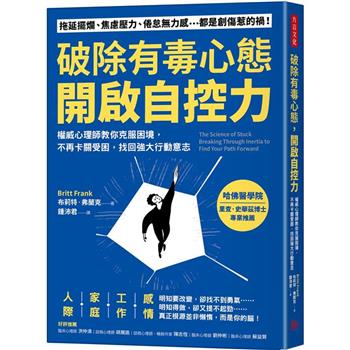紐伯瑞文學獎銀獎作品
一個擁有超能力的女孩,
一趟奇異的人生旅程!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
最起碼白密席的家人是如此!
兩天後的十三歲生日宴會上,
白密席就會知道自己擁有怎樣的超能力!
但天有不測風雲,爸爸出車禍,
她的超能力能拯救爸爸嗎?
她想見爸爸的心願,又將自己帶往怎樣的奇異旅程?
十三歲的生日,對白密席家族的人來說,是很特別的一天。大哥在這天發現自己會放電,二哥則是能招來暴風雨。過兩天就是白密席的十三歲生日,她不禁好奇,自己的超能力是什麼?
可惜的是,在她生日的前兩天,爸爸出了車禍,媽媽和大哥趕去醫院。在家的白密席以為自己已經有了超能力,很想利用它來幫助爸爸。於是,她和二哥、弟弟、教會牧師的兩個孩子,偷渡上了一部送聖經的粉紅色校車。
沒想到這部車卻開上了相反方向,這五個個性迥異的孩子,加上懦弱的司機,以及一個在路上因車子故障被司機撿起來的女士,一起踏上了奇異的旅程。一整天處在同一個空間裡,打架、叫罵、互相看不順眼,同時也慢慢認識對方、甚至發現對方的祕密。究竟,白密席的超能力是什麼?爸爸是否安然無恙?這趟旅程又將如何結束?
作者簡介
英格麗.羅 Ingrid Law
為了找尋自己的超能力,英格麗涉獵過服裝設計、花藝設計,和纖維藝術。她也賣過鞋子,在書店工作,幫其他人找工作,以及組裝漢堡紙盒。如今,她寫作,並和13歲的女兒一起住在可愛的老拖車屋上,她們相信那是太空船和鞋盒的組合體。她們喜歡在牆上寫字,在屋頂畫畫。家裡充滿美妙的事物,像是好書、鬆軟的枕頭,還有烘培蛋糕的香味。
個人網站為:
繪者簡介
王書曼
台中技術學院商業設計系畢。作品曾入選2006年義大利波隆那國際兒童書插畫展。繪有《天涼好個秋》、《紅豆生南國》、《台灣生態》。喜歡太陽天、喜歡大自然、喜歡看電影、喜歡聽音樂,更喜歡做夢。畫畫是興趣,畫出一個個令人感動的夢想,為「夢想」努力中......
譯者簡介
趙映雪
住在南加陽光普照的聖地牙哥,離藍藍大海很近,當然離每年都要到加州騷擾的焚風野火也不算太遠。最愛的生活:打網球、家庭音樂會、和老公女兒打打鬧鬧、寫作、和朋友喝咖啡、和一大群人去旅行;最不愛的:買菜做飯、逛街、彈不出想彈的曲子。寫作之外,也很享受翻譯,因為逐字斟酌,最能體會出作者經營一本書的布局、選字、風格、目的、想像力、用心程度,以及呈現出來的效果,是十分有趣的另類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