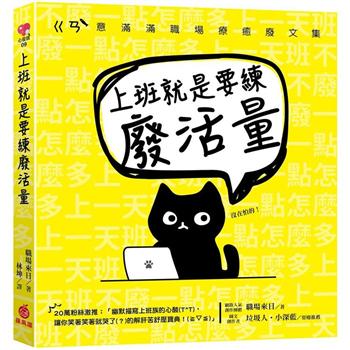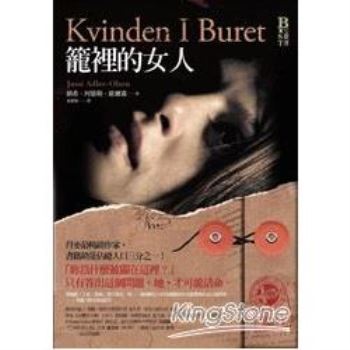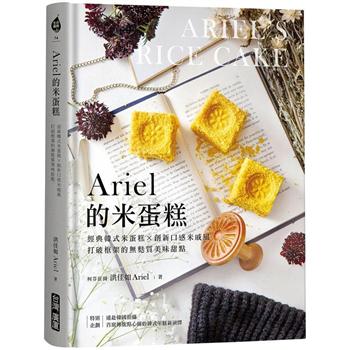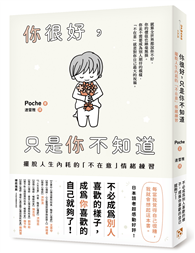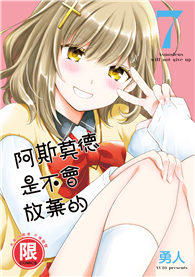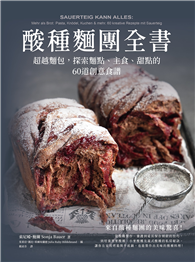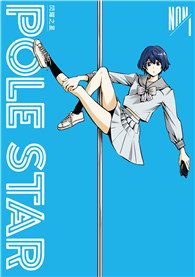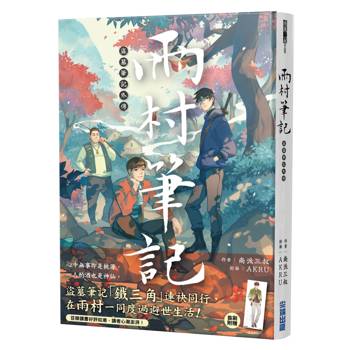很多作家試著告訴我們快樂是什麼,卻很少作家告訴我們快樂在「哪裡」、為什麼某地方的人比別的地方快樂、為什麼換地方就能換心情。
艾瑞克.魏納說自己是個鬱鬱寡歡的人,他長期擔任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的海外特派員,過去二十多年來,採訪過三十多國發生的災難與弊端,但在這本書裡,他要講另一面的故事。在新興學科「正面心理學」的引導下,魏納造訪了全球幾個最滿足的地方:快樂與悲慘比鄰而居的印度;國王把國民快樂毛額當國家首務的不丹;居民深信嫉妒是快樂最大敵人的瑞士;儘管嚴寒、偏遠、挫敗連連,卻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之一的冰島。而作者發現,這是有原因的。
探索全球的過程中,魏納藉助「自助工業集團」的集體智慧來尋找快樂之道,那些哲學家、作家和追求者的真知灼見,成了他這趟昂揚之旅的索引地圖,很少有旅遊書籍作家能把作者的心靈旅程,寫得跟外在旅程一樣意義深遠卻又有趣的。書中不時有發人深省的字句,很少書敢設下它這樣的目標,更少書能達成它所達到的目標:這本書會讓你變得更快樂。
作者簡介:
艾瑞克.魏納
擔任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海外特派員達十年之久,曾留駐新德里、耶路撒冷和東京,報導過三十多國的新聞。他也曾擔任該公司駐紐約和邁阿密特派員,目前則派駐華盛頓特區。魏納曾任《紐約時報》記者,與史丹佛大學的奈特新聞學者(Knight Journalism Fellow)。他的評論文章散見《洛杉磯時報》、網路雜誌《岩頁》(Slates)和《新共和雜誌》(The New Republic)等刊物。探訪過全世界後,他定居華府,好像挺快樂的,時間不是花在客廳,就是廚房。想找他的話,請上www.EricWeinerBooks.com網站。也請上www.TwelveBooks.com,告訴我們你覺得哪個地方最快樂。
章節試閱
第一站 荷蘭/快樂是數字
為了研究快樂,我來到了「世界快樂資料庫」。在八千多篇研究和論文裡,我找不到任何一篇提到哪個國家能從藝術汲取到快樂、能因為聽到一首大聲朗誦的絕妙好詩而愉快……。在這裡,快樂不過是統計數字,等著被分類、綜合、解析,輪入電腦程式,最後無可避免的成為電腦報表。
看別人做快樂的事,我們心裡就快樂,這是人的天性。這也解釋了何以色情業和咖啡館會大受歡迎。美國前者較發達,歐洲後者做得較好。食物和咖啡其實不是重點,我聽說以色列特拉維夫有家咖啡館連食物和咖啡都省了,服務生端給客人的雖是空盤、空杯,卻照樣收錢。
咖啡館像劇場,客人既是觀眾,也是演員。我住在鹿特丹市區的一家旅館,發現附近有家很棒的咖啡館,它寬敞、舒適、高檔,卻又破舊失修,有很棒的木質地板,樣子卻像多年沒打蠟了。那是個你能端杯啤酒,一喝幾個小時的地方,我猜當地很多人的確也這麼做。
大夥都在抽菸,於是,我也加入,點了根小雪茄。那地方會讓人感覺時間多了起來,於是,我開始注意到一些小細節。我注意到有個女人坐在吧台的高腳凳上,雙腿懸踏在旁邊的欄杆,一有人經過就抬高、放下的,像座活動吊橋。
我點了杯名叫「特拉皮斯特」的啤酒。酒是溫的。一般來說,我不太喜歡溫啤酒,但這牌子的,我喜歡。四周全是荷蘭人愉快的笑語,聽來卻有種模糊的熟悉感,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突然,我想通了,荷蘭語聽起來就像倒著講的英語。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我聽過很多倒著講的英語。在尚未數位化的年代,我曾用過電視機大小的盤式錄音磁帶機,替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剪輯過帶子,剪輯時會需要倒著播放某些段落。我坐在咖啡館,抽著小雪茄、喝著溫啤酒,心想,若我錄下某個人講的荷蘭話,然後倒著播,聽起來會不會就像一般的英語?
你一定在想,我這人一定很閒,時間很多。但歐洲的咖啡館就這麼回事:一坐就很久,而且完全沒罪惡感。難怪偉大的哲學家多數來自歐洲。他們在咖啡館閒坐,心思恣意漂蕩,然後,激進的新哲學(比如,存在主義)就在他們腦袋裡蹦了出來。我來這兒不是為了發明新哲學的,那不是我的目的。我來是為了像法國人講的:la chasse au bonheur--尋找快樂。
更明確來說,我的獵物是一個名叫溫哈文(Ruut Veenhoven)的荷蘭教授。身為快樂研究教父的溫哈文,經營一個稱之為「世界快樂資料庫」(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的組織。這不是在說笑,溫哈文把什麼讓人快樂、什麼不讓人快樂,以及最讓我感興趣的--哪些地方最快樂的相關知識,全蒐集了過來。若真有所謂的快樂地圖,溫哈文必定知道才對。
我依依不捨的離開咖啡館,回旅館用晚餐。鹿特丹這城市不美,天色灰濛陰沉,沒什麼特別的景點。這裡有很多回教移民,荷蘭本地人和移民混居,產生許多矛盾並立的有趣現象。埃及豔后情趣用品店的展示櫥窗裡,有支栩栩如生的大型陽具,巴基斯坦回教中心跟它卻只有一街之隔。我在某處聞到了一陣大麻氣味;如此芳香宜人的二手菸可是荷蘭特有的產物。往下兩條街,我看到有個人站在階梯上,正在店門前掛一隻黃色大木屐,梯子下卻見兩個臉頰紅暈的中東人在打招呼。我不曉得這兩人是哪兒來的,但我知道有些移民來自的國家禁止百姓喝酒,婦女則是從頭到腳包得密不透風。但在他們的新家裡,大麻合法,娼妓也是。難怪我在混雜著大麻味的空氣裡,嗅到了緊張氣息。
旅館的餐廳小巧舒適。荷蘭人很擅長把環境弄得舒舒服服的。我點了蘆筍湯,很好喝。服務生清走盤子,隨後問道:「餐間,您要上嗎?」
「對不起?」
「要上嗎?餐間,您可以上點別的。」
我當下以為,乖乖,荷蘭人還真開放。後來才想到,原來他講的是別的。餐間上的,也就是「兩道菜之間」(between courses)的飲品(注1)。
「好啊,好極了。」我如釋重負的說。
於是,我上了。在梵華森旅館的餐廳裡,上了餐間飲品。我很享受這種不慌不忙的用餐方式,啜飲著啤酒、望著遠處、無所事事,直到服務生端上烤鮭魚,我才知道餐間時間結束了。
***
一早,我搭地鐵到聖杯所在地:世界快樂資料庫。通常,我不會把快樂和資料庫連在一起,但這回不同。世界快樂資料庫相當於凡俗人的梵諦岡、麥加、耶路撒冷和拉薩加總在一起。在這兒,只要點下滑鼠,就可一窺快樂的祕訣。這些祕訣並非源自古老沙漠現出的短暫啟示,而是現代科學;這些祕訣沒寫在羊皮紙上,而是硬碟裡;所用的語言不是阿拉姆語,而是現代二元碼。
出地鐵後,我走了幾條街。眼前的景象,我一看就失望。世界快樂資料庫所在的大學校園,外觀像郊區的公司園區,不像人類快樂知識的寶庫。但我試著不去在乎這感覺。畢竟,我盼望要看到些什麼呢?是《綠野仙蹤》裡的巫師?還是一路興奮的狂喊「我們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快樂的祕訣了」的強哥和非洲小侏儒(注2)?不,我沒那麼盼過,倒是期待能看到沒那麼陽春的東西,至少能多些快樂、少些資料。
我經過一條單調的走廊,敲了敲一扇單調的辦公室大門。有個操荷蘭口音的男人喊我進去。面前正是愉快博士本人是也。溫哈文儀容整齊,鬍髭花白,兩眼炯炯有神。我猜,他大概六十出頭歲。他一襲黑衣,很有型,不會黑得很怪。他隱隱給人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後來我才明白,原來他是荷蘭版的羅賓.威廉斯(注3),精力充沛,臉上帶著一抹頑皮的笑容。他從椅子上跳起,伸過手來,遞上名片,名片上寫著「魯特.溫哈文,快樂學教授」。
他的辦公室跟一般教授的一樣:到處都是書和研究報告,沒特別凌亂,但照我所看過的,也不算太整齊,裡頭顯然也沒擺放笑臉圖案。溫哈文替我倒了杯綠茶後就不講話,等著我開口。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身為記者的我做過數百次專訪,訪問過國王、總統、總理,甚至是真主黨這類恐怖組織的頭子。但跟這個和藹、長得像羅賓.威廉斯的荷蘭教授面對面一坐,我卻詞窮了。我心裡的某個部分--那個渴求平靜的部分,真想大喊:「溫哈文博士,你已經統計過不少數據,你一輩子都在鑽研快樂,請把答案給我吧,把該死的快樂配方給我吧!」
但我不會這麼說。我不能偏離多年的專業訓練,這訓練告訴我,要跟訪問主題保持距離,而且,千萬不要讓人知道太多我的想法。我就像下班後帶家人上餐館用餐的警察,忍不住就想察看餐館裡有沒有埋伏槍手。
因此,我沒去管壓在心頭的重擔,而是使出記者和女人想讓約會氣氛變輕鬆所玩的一招老把戲。「溫哈文博士,談談你自己吧,你是怎麼踏入快樂這行業的?」我終於開口。
***
溫哈文向後靠著椅背,歡喜的回答了問題。他一九六○年代成年,就讀的大學裡,人人吸大麻、穿印了革命家格瓦拉(Che Guevara)的T恤、高談闊論所謂的美好社會。溫哈文也吸了不少大麻,但沒穿格瓦拉T恤,至於所謂的「美好社會」、東歐集團國家,溫哈文則聽來若有所缺。他認為,與其憑制度來評斷一個社會,何不憑其成效?它的國民快樂嗎?溫哈文心目中的英雄不是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紀一名拙於社會運動、名叫班森(Jeremy Bentham)的英國律師。班森以擁護「最多數人的最高快樂」這功利原則著稱,若有班森T恤這東西,溫哈文應該會很樂意穿在身上。
溫哈文原本念社會學,當時,這領域專研究病態和功能不彰的社會。姊妹學科--心理學,則專談病態心理。年輕的溫哈文不想研究這些東西,他對健康心理和快樂地方有興趣。有天,他膽怯卻又心意堅定的跑去敲指導教授的門,問說自己能不能研究快樂。指導教授是個嚴肅且學術資歷扎實的人,他明白地告訴溫哈文,閉上你的嘴,永遠別再提那兩個字了,快樂不是正經題目。
溫哈文被削了一頓後離開,但心中暗自竊喜,知道自己身負使命。這年輕的研究生不知道、也無從得知,但事情就這樣發生了,原來,當時世界各地的科學家也已覺察到,是時候研究快樂這門學問了。如今,溫哈文成了這方面的頂尖學者,該領域每年出產數百篇論文,舉辦多場快樂研討會,還發行一份名為《快樂研究》(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由溫哈文負責編輯)的期刊,加州克萊爾門研究大學(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則授與研究「快樂」正面心理學的學生碩士或博士學位給。
溫哈文有些同事到現在還認為他的老指導教授是對的,研究快樂乃是誤入歧途、蠢事一樁。但他們無法對溫哈文視而不見,因為他的研究就攤在眼前且廣為期刊引用,在學術界來說,這就表示他的東西有分量。
當然,大家不是現在才開始想快樂這件事的。古希臘人和羅馬人已經想過很多了,亞里斯多德、柏拉圖、伊比鳩魯和其他一些人,都曾埋首苦思那些雋永的問題:何謂美好人生?愉悅就等於快樂嗎?什麼時候才會發明室內給水管呢?
之後,膚色更慘白、來自更遠之北國的另一些人,加入了希臘人和羅馬人的行列,這些人花了無數時間泡在咖啡館裡,思索著人生難解的問題。康德、史賓諾莎、米勒、尼采率先加入,之後則是戴維(Larry David)。關於快樂,這些人也有很多話要說。
***
接著就是宗教。宗教若不在指引人得到快樂,又怎麼能稱之為宗教呢?每個宗教都教導其信眾快樂之道,這快樂有的存於今世,有的存於來生,途徑是藉由順服、冥想、奉獻,若你碰巧信奉猶太教或天主教,那就得藉由內疚來得到快樂。
這些方法或許都有幫助,甚至還能啟迪人心,但它們不科學,不過是一些關於快樂的看法而已。沒錯,儘管是有學問的看法,但看法終究是看法。當今這個世界,大家除了尊重自己的看法,是不大看重所謂的看法的。大家尊敬、看重的是硬科學,或退而求其次,軟科學。我們特別喜歡那些做得好的研究。新聞主播最清楚了,若想讓人們豎起耳朵聽,最好的辦法就是說出「新研究發現」五個字,至於後面講些什麼就不重要了,像是:「新研究發現紅酒對你有好處/會要你的命」、「新研究發現家庭作業會讓人變笨/變聰明」。我們還喜歡那些附和自己習性的研究,像是:「新研究發現書桌亂的人比較聰明」,或「新研究發現每天適度臭屁一下,人會比較長壽」。
的確,快樂這門新學問若要讓人當一回事,就得好好做出些研究來。但首先,它得要有個專有名詞、嚴肅的行話,像「快樂」這詞就不行,因為它聽起來輕挑、太容易懂,會是個問題。於是,社會科學家想出一個很棒的替代詞:「主觀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太完美了,這詞不僅念起來比較長、一般人完全聽不懂,還能縮寫成SWB這個更加撲朔迷離的字。現在,如果你想搜尋關於快樂的學術研究,就得上Google鍵入「SWB」,而非「快樂」。此外就是謎語般的行話:「正面情緒」就是感覺好,「負面情緒」(你應該猜出來了)就是感覺不好。
其次,快樂新學科需要有資料,也就是數字。沒數字,哪還叫科學,數字最好很大,要那種小數點以下很多位的。而科學家是怎麼得到這些數字的呢?因為他們會不斷做測量。
哦,不,這可難了。快樂如何測量呢?快樂是一種感覺、一種心情、一種人生看法。快樂無法測量。
要是能呢?愛荷華大學的神經科學家找到了跟心情好壞相關的大腦部位,方法是把研究對象(急需現金的大學生)綁在核磁共振造影的機器上,然後給這些人看一系列圖片,受試者一看到愉快的圖片(田園風光、海豚嬉戲),腦前額葉就活躍起來,一看到不愉快的圖片(身上覆滿油汙的鳥、被轟掉半邊臉的死亡士兵),腦部較原始的部位就亮了起來。換句話說,掌管快樂感覺的大腦部位,是新近才演化而成。這下問題可有趣了:若不從個人,而從進化的角度來談,人類是否正慢步走向快樂呢?
研究人員還用了其他方法測量快樂,比如測壓力荷爾蒙、測心搏,還有種方法叫「臉部辨識法」,也就是計算我們笑了幾次。這些技術大有可為,將來,或許科學家量起快樂,就像現在的醫生替人量體溫一樣簡單。
但目前,科學家用的主要測量技術還是不怎麼進步,這技術可想而知,就是問受試者他們有多快樂。真的不蓋你。「總體來說,你覺得自己這些日子以來有多快樂?」差不多就這樣問,而且這四十多年來,研究人員都是這麼問世界各地的人。
溫哈文和他的同僚聲稱,得到的答案準得出奇。「人可能病了還不知道,卻不可能快樂而不自知。就理論而言,你會知道自己快不快樂。」溫哈文說。
或許真是如此,但千萬別小看人自欺的能力。我們真有能力評估自己多快樂嗎?比方說,十七歲時,我自以為很快樂,非常滿足,在這世上一無牽掛。但現在想想,當時的我不過是大麻吸多了。啤酒應該也有關係,我想。
通往快樂之路的另一個減速路障: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不一樣,你認為的快樂跟我認定的不同。我最喜歡的快樂定義,出自一個不快樂的人,這人名叫韋伯(Noah Webster)。一八二五年,韋伯撰寫了美國第一本字典,當時,他把快樂定義為「享受美好事物後所生發的幸福感」。此語道盡了一切。快樂會有「幸福感」,快樂是種感覺,會讓享樂主義者興奮莫名。快樂是因「享受」而來,這表示它不純粹只是肉體上的愉悅。至於享受什麼?享受「美好事物」。這詞,我想韋伯應該用大寫強調才對。人們希望在正當理由下,獲取好的感受。亞里斯多德應該會同意這說法,因為他曾說過:「快樂是靈魂的道德活動。」換句話說,道德生活就是快樂生活。
我們人是那種到最後關頭才變的動物。有份研究發現,受試者受測前幾分鐘若在人行道上撿到一角硬幣,他們對生活的整體滿意度,就會高於沒撿到錢的人。研究人員試著透過經驗抽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來解析何以人的心理會突然改變。他們在受試者身上綁一個體積類似掌上型電腦的小機器,然後一天呼叫他們十幾次,問:「你快樂嗎?現在好嗎?」但海森伯格原理(Heisenberg principle)作祟了:觀察本身就會造成影響。換句話說,光是呼叫這舉動,都可能影響受試者的快樂程度。
此外,多數人喜歡笑臉迎人。這說明了何以面對面問出來的快樂程度,總高於郵寄問卷所得的結果。提問者若是異性,受試者自認的快樂程度甚至更高。本能告訴我們,快樂會讓人感覺性感。
但快樂學者有話要說。首先,若拉長時間來看,受試者的答案有一致性。此外,研究人員會跟受試者的親友核對答案,問說:「依你看,喬伊這人快樂嗎?」而結果發現,外人的看法跟我們自認的快樂程度相符。另外,科學家既然能測量智商、測量對種族歧視這類主觀議題的態度,測量快樂又有不可呢?或者,就如快樂研究領域的先驅希森米哈(Mihály Csíkszentmihalyi)所言:「有人若說自己『相當快樂』,旁人就不該忽視這感受,或用相反意思去解讀它。」
假如快樂研究可信,那麼,它有何發現?誰快樂?我該怎麼加入他們?溫哈文和他的資料庫能回答這些問題。
溫哈文帶我到一間樣子單調、跟校園其他地方同樣沒特色的房間,裡面六部電腦,操作員只幾個,多半是資料庫的志工,樣子看來沒特別快樂。對此,我不以為意,因為就算是胖醫生,也能在運動和飲食上給出很棒的建議。
我停下來端詳一番。眼前的電腦,收集了人類累積的所有快樂知識。這議題被忽視了幾十年,社會科學家現在正奮力彌補那段空白時光,以驚人速度量產研究論文。或許你可以這麼說:快樂成了一種新的痛苦。
其研究發現,有的吻合常識,有的與直覺相悖,有的一如預期,有的讓人意外。許多研究證實了幾世紀前偉大思想家的說法--好像古希臘人需要我們證實他們的說法似的。以下有幾項研究發現,次序無特別安排。
外向的人比內向的人快樂;樂觀的比悲觀的快樂;結婚的比單身的快樂,但有小孩的夫妻並未比沒小孩的夫妻快樂;共和黨人的比民主黨人的快樂;參加宗教活動的比不參加的快樂;有大學文憑的比沒有的快樂,但有博、碩士學位的比只有大學畢業的不快樂;性生活活躍的比不活躍的快樂;女人情緒起伏較大,但男人、女人一樣快樂;外遇會讓人快樂,但這彌補不了被抓包且配偶走人而損失的大量快樂;通勤上班的路上,人最不快樂;忙人比沒事幹的人快樂;有錢人比窮人快樂,但只多快樂一點點。
那麼,該怎麼應用這些研究成果呢?結婚,但不要生小孩?開始常上教堂?不念博士了?別猴急。社會科學家還在釐清所謂的「相互因果」,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蛋生雞或雞生蛋的問題。例如,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快樂,還是說,快樂的人通常比較健康?已婚的人比較快樂,還是說,快樂的人比較願意結婚?這一切很難有個準。相互因果這妖怪把很多研究攪得天翻地覆。
但我真正想知道的不是誰快樂,而是哪些地方的人快樂,以及,為什麼?我這一問,溫哈文嘆了口氣,又倒了杯茶給我。這計算起來,更難了。真能說出哪些國家、哪些民族比較快樂嗎?這趟尋訪世界最快樂地方的旅程,會不會沒開始就結束了?
每個文化區都有一個用來形容快樂的字,有的還好幾個。但英文的happiness(快樂)跟法文的bonheur、西班牙文的felicidad,或阿拉伯文的sahaada意思一樣嗎?換句話說,快樂這詞能翻譯嗎?部分研究證據顯示,能。瑞士有法語、德語、義大利語三大語言區,各區的受訪者自認的快樂程度差不多。
所有文化區都看重快樂,但看重的程度不同。東亞國家強調和諧及履行社會義務,較不強調個人滿足,因此,當地人的快樂程度較低或許不是巧合。這現象即所謂的東亞快樂鴻溝(East Asian Happiness Gap),而在我聽來,感覺好像某個中國大峽谷。此外,還有所謂的「社會期望偏誤」(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也就是擔心受試者填寫快樂問卷時並未照實講,而是照社會所允許的尺度在回答。例如,日本人喜歡把自己藏起來,很怕自己太突出,而儘管生活算是富裕,他們卻不算很快樂。我在日本住過幾年,從不習慣日本女人一笑就遮嘴,好像笑很丟人似的。
我們美國人卻喜歡表現出快樂的模樣,甚至還喜歡誇大滿足感,好博取別人注意。有個住美國的波蘭人曾告訴作家索克爾(Laura Klos Sokol):「美國人若說棒透了,意思就是很好。若說很好,意思就是還好。若說還好,意思就是不好。」
這可難了,若真有所謂的快樂地圖,恐怕會像塞在你汽車置物箱裡的皺地圖一樣難以閱讀。但我決定繼續往前,因為心想就算無法細分出各國的快樂程度,起碼能找出較為快樂的國家。
***
溫哈文讓我自由取用資料庫,並祝我好運。但一開頭他就警告我:「你恐怕不會樂見所看到的。」
「什麼意思?」
他說,所謂最快樂的地方,未必符合我們的預期。比如,某些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像冰島、丹麥)的同質性很高,這顛覆了美國人的想法,以為多元才會有力量、才會快樂。溫哈文最近的一項發現也讓同業很不以為然。他發現財富分配無法預測快樂程度,貧富差距大的國家並沒比貧富較平均的國家不快樂,有時,還反倒快樂些。
「我的同事不太高興。『貧富不均』是社會學系的大事,很多人的事業都押在這上面。」溫哈文說。
我客氣的接受他的建議,心裡卻想,他恐怕誇大了眼前的困難。但我錯了,找快樂的地方就算不讓人痛苦,至少讓人頭痛欲裂。每點一次滑鼠,我就看見謎團和明顯矛盾,比如:世界最快樂的國家當中,有很多同時也擁有高自殺率。還有這個:參加宗教活動的人比沒參加的快樂,但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卻都是不信神的。哦,對了:最有錢的美國雖是世界強權,卻非快樂強權,很多國家都比美國快樂。
***
待在鹿特丹的日子,既規律、又愜意。我在旅館吃早餐,有時放縱自己在餐間上一下,然後就搭地鐵到世界快樂資料庫。我在那兒看論文和資料,尋找虛無飄渺的快樂地圖。晚上,就到那家咖啡館(店名我從沒記起來)喝杯溫啤酒、抽抽小雪茄、想想快樂是什麼。這種生活方式,想得很多、飲酒量適中、實際勞務很少。換句話說,就是很歐洲,我愈來愈像本地人了。
基於某些原因,我決定先從快樂的基層著手,隨後再循著梯子往上找。哪些國家最不快樂?不出所料,很多非洲國家都歸在此類:坦尚尼亞、盧安達、辛巴威最接近快樂井的井底。少數幾個非洲國家(比如,迦納)擠上了中度快樂這層,但最好成績也僅止於此。成因似乎很清楚:太窮會快樂不起來。想當個快樂、高貴的野蠻人,不過就是神話。基本需求若沒得到滿足,人不太可能快樂。
令人好奇的是,我發現還有一組國家在快樂圖譜裡墊底:前蘇聯共和國,也就是白俄羅斯、摩爾多瓦、烏克蘭、烏茲別克和十幾個其他國家。
民主國家會比極權國家快樂嗎?未必。很多前蘇聯共和國國家現在的體制都已類似民主國家,但蘇聯瓦解後,它們的快樂程度卻降低了。密西根大學的英格哈特教授(Ron Inglehart)大半生都在研究民主與快樂的關係,他認為因果方向正好相反,民主不能提升快樂程度,但快樂的地方比較傾向實施民主制度──當然,這理論不太適用於伊拉克。
那麼,那些溫暖、陽光普照、被我們當成快樂熱帶天堂而掏出大把鈔票前去度假的地方呢?結果發現,這些地方沒那麼快樂:斐濟、大溪地、巴哈馬群島全落在中度快樂的區間。快樂的國家通常氣候適中,有幾個最快樂的國家(比如,冰島)甚至還冷到骨子裡。
信不信由你,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說自己快樂。幾乎全球所有國家都落在十分量表的五到八分之間,只有少數例外:沈著臉的摩爾多瓦人一直保持約四.五分,多明尼加共和國在一九六二年間曾短暫降到一.六分,創下全球最低分紀錄。但就如我講的,例外的很少,世界上的人多數都是快樂的。
為什麼這會讓人感覺意外?我想,該怪兩種人:記者和哲學家。媒體(我是共犯)照例只報壞消息:戰爭、飢荒、好萊塢新出爐的怨偶。我無意小看這世界的難處,老天爺知道我甚至還靠報導這些事而吃香喝辣呢,但我們記者所呈現出來的,確實是幅扭曲的圖畫。
但真正的元兇是哲學家,也就是歐洲那些成天胡思亂想的白人。他們喜歡穿得一身黑、抽一大堆菸、沒人願意跟他們約會。因此,他們獨自在咖啡館裡閒晃,在那兒思想全宇宙,然後--大驚奇!--他們斷言宇宙是個不快樂的地方。若你碰巧孤單一人、胡思亂想、又是膚色慘白的白種男性,你當然不會快樂。快樂的人(以十八世紀德國海德堡的居民來說好了)光忙著快樂都來不及了,哪還有時間故意去寫些冗長、鬆散、尖酸刻薄的文章,好折磨尚未出生、將來非得通過哲學概論課才能能畢業的大學生。
最糟糕的就是佛洛伊德。技術上而言,他不算愛沈思的哲學家,但卻是影響我們對快樂的看法最深的人。他曾說:「《聖經》〈創世紀〉裡,沒說人應該快樂。」一個奠定心理衛生系統的人說出這種話,真是不可思議。若世紀轉換之際,維也納某個醫生宣稱:「《聖經》〈創世紀〉裡,沒說人身體應該健康。」這人就算沒被關起來,至少也會被吊銷行醫執照。我們當然不會以他的說法來建構醫療體系,卻以佛洛伊德的話來建構心理衛生體系。
言歸正傳,多數人都是快樂的?但我不是。我是人,但我不怎麼快樂。於是,我想:在溫哈文這堆快樂資料裡,我的落點在哪裡?若老實說(既然費那麼大勁寫這本書,我就該老實說),應該是六分。我會因此遠不及美國同胞快樂,但根據世界快樂資料庫的數據,我在中歐克羅埃西亞會有回家的感覺。
魏茲碧(Anna Wierzbicka)是個語言學家,而且跟我一樣難搞。她一聽說多數人都快樂,立刻問了個簡單的問題:「這些所謂快樂的人,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我頭可大了。難道找不出全世界最快樂的一些地方嗎?隨後我注意到,有個國家在快樂量表上始終明列前矛,雖不是第一名,但也差不多了。這國家正巧就是我現在來到的地方。
我去了那家咖啡館,點了杯啤酒,思索荷蘭式的快樂。為什麼像荷蘭這樣單調且平淡無奇的國家,會這麼快樂?初步來看,荷蘭人是歐洲人,這表示他們不必擔心失去健保或工作,因為國家會照顧他們。他們每年有好多週的假期;此外,歐洲人在美國人面前,總會自然流露出莫名的優越感。自以為是會讓人快樂嗎?我邊想、邊喝特拉皮斯特啤酒。不,應該有別的原因。
包容!荷蘭是個獨特的「別踩我」國家。這國家好像大人不在,全由青少年在管事,而且不光週末才管,任何時候都是他們在管。
荷蘭人什麼都包容,甚至包容不包容。這幾十年來,他們展開雙臂歡迎世界各地移民,連那些沒宗教自由、不准女性工作、開車或露臉的國家的移民也是如此。荷蘭人因包容而付出代價,製片人范谷(Theo van Gogh)慘遭回教極端份子謀殺就是明證。但溫哈文的研究顯示,懂得包容的人比較快樂。
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看出荷蘭人的包容呢?我想到三件事:吸毒、嫖妓、騎自行車。在荷蘭,這三項都是合法的。這三件事輕易就能使人快樂--只要事先防範得宜,比如,騎腳踏車時,戴安全頭盔。
我必須仔細觀察其中一項活動,好瞭解荷蘭式的快樂。但哪一項呢?騎腳踏車當然值得研究,老天爺知道荷蘭人有多愛騎腳踏車,但外面好冷,冷到沒辦法蹬上車。嫖妓?這活動通常在室內進行,因此不受天候影響,而且顯然會讓某些人快樂。但問題出在我太太:她支持我做快樂研究,但支持是有限度的。我心裡明白,荷蘭妓女服務這檔事,顯然超過限度了。
那就只剩下吸毒這件事了。軟毒品(注4),也就是大麻菸和大麻膏,在荷蘭是合法的。咖啡館販售這些東西,但那種店其實也不算咖啡館,應該叫毒窟才對,只不過「咖啡館」叫起來比毒窟好聽就是了。
但我該挑哪一家來嘗試呢?選擇太多了。在鹿特丹,每隔三、四家店,就有一家「咖啡館」。我想去一家名叫「駭上天」的店,但那店名太……明顯了。其他店卻感覺太嬉皮。我大二以後就沒駭過了,我可不想出糗。
然後,我發現了「白朗黛咖啡館」。太完美了,除了店名吸引人,它還有窗、有空調,這絕對是加分。我按了門鈴,然後沿狹窄的樓梯往上走。裡頭有桌上足球台,冰箱裡有可樂、芬達橘子汽水、很多根巧克力棒、很多包M&M巧克力,顯然是當零食吃的吧。讓人驚訝的是,這咖啡館竟然有咖啡機,但樣子好像幾個月沒人用過了。我想,應該是擺好看的。
裡頭播放一九七○年代的差勁音樂,音樂大聲了點。我注意牆上有幅畫,看起來像是很有天分的小六生畫的,前景是一輛撞樹的汽車,滑行的軌跡一路延伸到地平線,底下則有一行字:「有些路只存於毒化的心。」我不知道這是要大家小心這些路、還是在稱許這些路。
大家看來都是常客,當然,我除外。我好似回到新澤西的大學宿舍,一直想保持冷靜、想融入,但卻沒辦法。
有個橄欖膚色的人走近我,用一口破英文跟我說明菜單。他說,今天的推薦商品(口氣好像在介紹今日湯品)是泰式大麻菸和兩款大麻膏:摩洛哥風味及阿富汗風味的。
我不知怎麼選,於是拿出不知如何點菜時的老招,問服務生他推薦什麼。
「你喜歡重口味還是普通的?」他問。
「普通的。」
「那麼我推薦摩洛哥風味。」
我給他五歐元(大約兩百塊台幣),他給我一個小袋子,和一枚郵票大小的灰棕色板子。
我完全不知道這些東西幹什麼用。
當下,我很想打電話給大學室友洛斯提。洛斯提一定知道該怎麼辦。他總是很冷靜,操作起吸大麻菸斗,就像馬友友在拉大提琴一樣。洛斯提現在是個企業律師、跟四個孩子住在郊區,雖然如此,我還是認定他會知道該拿這塊摩洛哥大麻膏怎麼辦。
這時,朗絲黛(Linda Ronstadt)很有默契的唱起:「你不行啊,你不行啊,寶貝,你不行啊。」
我曾想過把大麻膏塞進嘴裡,配可樂喝下去,但又想了一下,改為亂摸一通,並且盡可能裝出無助的樣子,但那種情況下,其實不必裝就很像了。終於,有個穿皮外套的大鬍子男人看我可憐,二話不說就伸手拿走大麻膏,當菲達起士那樣在手上捏碎,然後把一根普通的香菸捲開,再把大麻膏擺進去,接著熟練的搖一搖、舔一下、輕輕一敲,遞回一根摻了大麻膏的香菸。
謝過他後,我點起菸。
有幾個心得。首先,我推薦摩洛哥口味,它真的很順口。第二,違法行動的樂趣至少有一半是來自違法本身,而非行動。換句話說,在鹿特丹合法抽大麻膏的感覺,並不如我跟洛斯提在宿舍一邊偷抽、一邊擔心被逮那麼有趣。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挺棒的。摩洛哥大麻膏深入大腦皮質時,我心想:若一直保持這種狀態,會是什麼感覺?我會一直快樂下去嗎?不如就以白朗黛咖啡館為終點,結束這趟探尋全世界最快樂地方的旅程吧。這裡恐怕就是全世界最快樂的地方了。
關於這點,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有話要說,但不是要談白朗黛咖啡館(我很懷疑他到過這裡),也不是要談大麻膏(他或許抽過、或許沒有)。諾齊克花工夫想過享樂主義和快樂之間的關係,也曾設計一個名為「經歷機」(Experience Machine)的思想實驗。
先假想「超出色的神經心理學家們」想出了一套方法,能靠刺激人腦來誘發愉快經歷。這方法絕對安全、機器絕不故障、絕不會危害健康、能讓你餘生一直保有愉悅感受。若這樣的話,你願意嘗試嗎?願意插上經歷機的插頭嗎?
諾齊克說,若你不願意,就證明人生除了快樂,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事。人會希望經由努力得到快樂,而非只是去經歷快樂。人甚至會想經歷不快樂,或至少保留不快樂的可能性,好讓自己能珍惜快樂的感覺。
可惜,我發現自己贊同諾齊克的看法。我不願插上經驗機的插頭,因此,我不會搬進白朗黛咖啡館。這真是令人遺憾。我提過摩洛哥大麻膏有多順口嗎?
***
隔天,我的心智完全脫離摩洛哥大麻膏的影響,於是按照平常的行程,前往世界快樂資料庫。我跟溫哈文提到這項小實驗,當然,他表示讚許。我還跟他提到,若我在美國做荷蘭人平常做的那些事,比如,嫖妓、吸毒,恐怕會被抓,但溫哈文聽完只是笑笑的說:「我曉得。享受吧。」
溫哈文說,關於「愉悅是否等同快樂?」這老問題,資料庫或許可提供些答案。做了幾趟迂迴的數位尋禮後,我找到一篇溫哈文本人寫的論文,名稱叫「享樂主義和快樂」。我把內容摘要讀了一遍。
「快樂與消費刺激品的關連呈倒U型,沈迷運動和暴飲暴食的人比適度消費的人不快樂。」換句話說,幾千年前的古希臘人說得對,凡事要適度。我繼續往下讀,裡面寫到:「有好幾樁研究發現,『對性抱持放縱的態度』與『個人快樂』呈現正相關。」這些放縱的快樂人,想必跟常上教堂的快樂人不是同一班人。至於毒品,一九九五年有份研究發現,長期來說,使用毒品會讓人愈來愈不快樂--想也是。至於軟毒品,例如,摩洛哥大麻膏呢?結果發現,沒什麼人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我心想,乾脆別再坐在電腦螢幕前了。昨晚,在旅程的第一站,我去到了白朗黛咖啡館,做了最尖端的快樂研究。誰想到會是這樣呢?
***
這是我在鹿特丹的最後一天,這是個容易被遺忘、但我卻會想念它的城市。該跟溫哈文說再見了,但我向來不善於道別。我感謝他的協助,謝謝他提供的快樂資料。站在門口時,我臨時想到一件事,於是問他:「能在快樂研究這領域工作,感覺很棒吧?」
溫哈文面露不解之色。「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想必你堅信人類有能力快樂吧。」
「不,不盡然。」
「但你一輩子都在研究、分析快樂,不是嗎?」
「沒錯,但我不在乎大家快不快樂,只在乎有人比其他人快樂,因為這一來,我就有數字可算了。」
我愣在那兒。我以為溫哈文也是個旅人,跟我一起在尋找快樂,結果卻發現,就像南方人說的,他參加打獵活動卻沒帶狗來。換句話說,溫哈文並非快樂比賽的參賽者,他是裁判,是計分員。而且,好的計分員都是這樣,他們根本不在乎誰贏、誰輸,快樂跟難過都一樣,只要有一邊贏就好了。
我猜想,這門新興、理智的快樂研究看重的就是這點。溫哈文和其他快樂學者急於得到學術界的肯定,不想被當作只是在趕時代潮流。他們成功了,但值得嗎?在他們的世界裡,快樂不過是統計數字,資料等著被切片、切塊、解析,好送進電腦跑程式,最後無可避免的成為電腦報表。我覺得再沒什麼東西比電腦報表更讓人不快樂了。
我知道這趟來世界快樂資料庫是個好的開始,但結果並不圓滿。八千多篇研究和論文裡面,我找不到任何一篇提到哪個國家能從藝術汲取到快樂、能因為聽到一首大聲朗誦的絕妙好詩而愉快,或因為捧了桶不含奶油的爆米花,看了場好看得要命的電影而高興。此外,資料庫也沒揭露出那條繫住一家人的隱形線。有些事是無法測量的。
因此,我要根據溫哈文的資料庫,以及自己的直覺,畫一張屬於自己的快樂地圖。富有或貧窮、寒冷或炎熱、民主或極權,全不要緊,我會嗅著快樂的氣味,聞到哪兒就走到哪兒。
我握著這張圖,登上了鹿特丹中央車站的火車。火車啟動,荷蘭原野風光呼嘯而過,這時,我竟有鬆口氣的感覺,甚至感覺自由了。自由什麼呢?我想不出來。這趟訪問很棒,喝了些好啤酒、抽了些好大麻膏,甚至搞懂了一、兩樣跟快樂相關的事。
突然之間,我想通了,是擺脫自由的那種……自由。包容是件好事,但包容容易淪為冷漠,一點都不好玩。此外,我不能在太鬆散的環境過活。我太軟弱了,會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收手。若我搬到荷蘭,幾個月後,你可能會發現我四周全是摩洛哥大麻膏的煙霧,兩手則各抱一個妓女。
不行,我不適合荷蘭的生活方式,或許下個目的地會適合我吧。我將抵達的那個地方,火車會準時開、街道很乾淨,至於包容,就跟其他任何東西一樣,都會以適當合宜的方式做處理。我正在前往瑞士的路上。
譯注:
注1:服務生最初問作者餐間是否要上時,用的是「inter course」,作者誤會他指的是intercourse(有性交之意),其實服務生指的是餐間上的飲品(between courses)。
注2:電影《巧克力冒險工廠》裡的人物。
注3: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美國喜劇演員,曾以電影「心靈捕手」獲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注4:軟毒品(soft drug),相較於海洛英、古柯鹼、嗎啡等成癮性較重、嚴重影響健康的硬毒品(hard drugs),軟毒品對人體的影響較小。
第一站 荷蘭/快樂是數字
為了研究快樂,我來到了「世界快樂資料庫」。在八千多篇研究和論文裡,我找不到任何一篇提到哪個國家能從藝術汲取到快樂、能因為聽到一首大聲朗誦的絕妙好詩而愉快……。在這裡,快樂不過是統計數字,等著被分類、綜合、解析,輪入電腦程式,最後無可避免的成為電腦報表。
看別人做快樂的事,我們心裡就快樂,這是人的天性。這也解釋了何以色情業和咖啡館會大受歡迎。美國前者較發達,歐洲後者做得較好。食物和咖啡其實不是重點,我聽說以色列特拉維夫有家咖啡館連食物和咖啡都省了,服務生端給客人的雖是空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