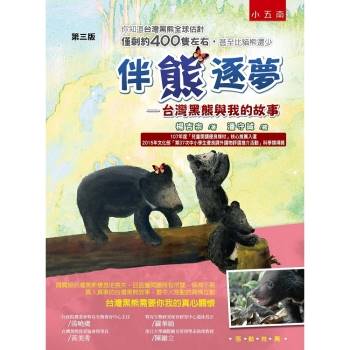導讀一
紅色暴行,黑色幽默
──曹冠龍的《沉》
王德威
旅美大陸作家曹冠龍(b.1945)七零年代末期開始創作。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傷痕文學」興起,曹以小字報形式在復旦大學校門口張貼小說《火》、《鎖》、《貓》等作,頗曾引起注意。但曹冠龍一直不能算是主流作家。他的作品透露一種「對荒謬現實的陰鬱立場」,顯然不能吻合主旋律的要求,而他在一九八七年赴美之後,也和大陸文壇逐漸行漸遠。但曹冠龍的風格畢竟啟發了一代有心的讀者。批評家朱大可最近仍回憶是曹「怪誕的色彩和批判的激情」,讓他感到「一個新的話語時代降臨了。」
曹冠龍來美後專攻藝術,卻不能忘情寫作。他的《閣樓上下》(1993)曾在臺灣出版,可惜未能得到應有的評價。這本小說以曹個人成長過程為基礎,述述一個上海下層家庭如何經歷共和國一次又一次的風暴。小說的核心是曹家一家人蝸居數十年的閣樓。曹寫侷促陰濕的空間,動輒得咎的身體,毫無私密的起居,幾乎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生活的隱喻。然而比起外面天翻地覆的變化,這閣樓一角還是曹冠龍稱之為「家」的所在,為他慘淡的青少年歲月留下最後一縷溫馨的回憶。《閣樓上下》沒有聳動的題材,曹冠龍藉娓娓家常道出一個反常的時代,自有一股動人力量。這本書能在國際文壇受到矚目,不是偶然。
曹冠龍最新的創作《沉》恰恰反其道而行。《閣樓上下》刻意以抒情救贖現實的紊亂與艱辛,《沉》則充滿了尖誚淒厲的戲謔。《閣樓上下》寫身體的禁錮,《沉》則寫身體的放縱。作家重拾他早期的怪誕色彩和批判激情,以最冷酷的笑聲來見證一個理性蕩然的時代——一個人吃人的時代。
時間回到文化大革命,「廣希省」的文攻武鬥如火如荼;革命大業如此熱火朝天,不僅殺人淪為等閒之事,甚至吃人也成了家常便飯。曹冠龍以輕佻歡樂的口吻述說這場人吃人的好戲,始於造反派吃得你死我活,終而成為全民狂歡的盛事。人性原始的飢渴欲望,老中國的進補迷信,新中國的政治狂熱全都混為一談。吃人不但要吃得狠,還要吃得巧,看看小說羅列的菜單或標題,像「紅酒腳筋」、「嫩薑脆心」、「心花怒放」、「人民肉鬆」、「人民骨酒」......,可以思過半矣。
文革時期部分地區發生吃人事件在八十年代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一九八四年作家鄭義耳聞此事,經過縝密調查,寫出《紅色紀念碑》(1993),詳細記述當時廣西的吃人暴行。除了個人探訪所得外,鄭義也涉獵了官方資料,其中尤以發生在廣西武宣縣銅嶺鎮中學的紅衛兵吃人事件最為令人髮指。造反的紅衛兵大塊朵頤的對像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校長黃文□。 曹冠龍想來對鄭義的調查不會陌生,《沉》裡那對被烹而食之的老師夫婦或許有所本,其他種種暴虐的行徑也就可想而知。
《紅色紀念碑》以報導文學形式寫出,《沉》則大肆發揮作者的想像,務以嬉笑怒罵為能事。曹冠龍顯然認為吃人事件如此背離人性,非辛辣之筆不足以狀其荒謬於萬一。但曹的筆法恐怕只點出另一層反諷:在中國歷史上,人吃人難道真的只是千古不遇的怪談?識者已經指出自公元前二世紀到一九三零年代,中國歷史至少有一百一十八個年代發生人吃人的記載,換句話說,平均每十八年就有一次大規模的人吃人事件。而這只是官方文獻所錄,至於其他時期——甚至承平時期——的犧牲就更不能聞問了。
問題是,就算吃人是中國文明古已有之的黑暗潛流,大規模的吃人多半和飢荒和戰禍有關。時至二十世紀,一九三三年的黃河水災、一九四二年河南、安徽等地的飢荒,乃至五零年代末的「自然災害」期間都有吃人的傳聞,基本動機仍不出此範圍。但發生在文革期間的人吃人事件卻有堂皇的意識形態作為前提。吃人不再只是人倫防線的違逆,反而是革命大道理的實踐。以理殺人,莫此為甚。圖騰與禁忌、野蠻與文明在此顯現了最吊詭的共謀。 這毋寧是「文化」大革命最殘酷的玩笑了。
以上的討論引領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新文學描寫吃人最有名的作品,魯迅(1881-1936)的《狂人日記》(1918)。小說裡的狂人身陷隨時吃人和被人吃的恐懼中。他發現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根本是場完不了的人肉盛宴,所有的仁義道德無非只是人吃人的藉口。更要命的,既然生長其中,狂人自己也脫不了干系:
四千年來時時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著家務,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飯菜裡,暗暗給我們吃。
我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自己,......
小說最後,狂人發出絕望的呼號:「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
《狂人日記》以寓言形式對舊社會的「禮教吃人」作出最戲劇性的控訴,魯迅也因此成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先聲。循此模式,不少三十年代作家繼續有所發揮。像汪靜之(1902-1996)的〈人肉〉寫出女性在亂世裡無路可逃,隨吃可以成為男人的俎上肉;吳祖緗(1908-1994)的〈官官的補品〉則凸現有錢人家延年益壽的妙方就是吃喝窮人的奶和血。也正因為舊社會如此恐怖,革命家乃能登高一呼:為了「救救孩子 」,吃人的禮教必須打倒,吃人的傳統必須泯除。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儼然代表了一個除舊布新的開始。
然而《狂人日記》的陰影豈真在新中國消退?曹冠龍看出了其中的吊詭。社會主義的天堂如此美好,何以狂人的詛咒卻不斷複製重生,不斷引出吃人的悲劇?狂人的呼聲——「救救孩子!」——於是有了最反諷、最野蠻的迴音。魯迅對傳統的激進的批判招致了歷史、政治上的激進實踐。為了救救孩子,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奉「革命」之名而犧牲;為了繼續革命,成千上萬的紅孩兒主導了一場又一場的吃人盛宴。《沉》描寫紅衛兵如何策動造反,如何吃盡烹絕反革命分子,卻也難逃噬人者恆被人噬的下場,讀來是要人掩卷三嘆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的吃人儀式在社會主義革命敘事裡其實有跡可循。一九四零年代末丁玲(1904-1986)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還有周立波(1908-1979)的《暴風驟雨》不約而同,都寫出了革命群眾在鬥爭高潮恨不得把造反對象吞而食之。他們憑著新天命為所欲,而且化為真正的口腔衝動。魯迅的狂人寓言落實成革命最終的詛咒,新的禮教和舊的禮教一樣吃人不吐骨頭。
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結束。過去三十多年書寫這段「十年浩劫」的作品所在多有,也不乏動人之作,大抵而言,或控訴、或悲情,多以寫實經驗入手。新世紀以來我們看到另一種風格的出現。閻連科(b.1958)的《堅硬如水》以文革一對男女積極分子作主角;兩個人壞到骨子裡,卻又是愛得死脫的地下情人,而他們的激情必須是在毛主席的口號和革命歌曲中才能達到欲仙欲死的高潮。藉此閻對革命與性的歇斯底里衝動作了最露骨的嘲諷。余華(b. 1960)的《兄弟》敘述一對同母異父的兄弟歷經文革、家破人亡後的奇遇,以及他們在後社會主義中國市場上的冒險。《堅硬如水》和《兄弟》都有匪夷所思的情節,哭笑不得的敘述,由涕淚寫到淫猥,道盡了文革創傷的後遺症那裡只是簡單的控訴或見證就能交待的。
曹冠龍的《沉》延續了這一脈絡。他筆下的廣希省和廣希湖一片窮山惡水,物種退化,人不如禽獸遠矣。而這也是個死亡嘉年華會的所在,老中青三輩無不各盡所能,為吃人大業作出貢獻。嚴格來說,《沉》的前半部寫得有點枝蔓,要到了中段以後,曹冠龍才釋放出他的能量,呈現各種可驚可笑的怪現狀。小說以萬眾歡騰的吃人盛典為高潮,但樂極終於生悲,地動山搖,一場大水淹滅了一切。這是救贖不義的洪流,也是同歸於盡的惡水,曹的義憤盡在其中。
由《沉》回顧曹冠龍的《閣樓上下》,我們看得出他的心路歷程。兩者都投射了社會主義治下中國主體——與身體——的絕對困境。如果《閣樓上下》寫出了不可言說的痛,《沉》則是痛定思痛,反而傳來陣陣陰森冷笑。而以這樣的姿態面對中國人吃人的行徑,曹冠龍難道沒有物傷其類的感慨?如此,他讓我們想起的不只是魯迅的狂人,更是是散文〈墓碣銘〉中那個自嚙其身的游魂:「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創痛劇烈,本味何能知?」
六十年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大夢,千百萬的生靈怎能就這樣沉入歷史記憶的深淵?正如《沉》的主要象徵廣希湖表面一潭死水,底下的怨毒淒厲之氣卻無從散去。紅色暴行,黑色幽默,《沉》骨子裡其實是本悼亡之書。魂兮歸來,嗚呼哀哉!
二00九年九月四日
【注】
1.朱大可,《懺悔與懷疑, 80年代的精神遺產》zhudake.idoican.com.cn/blog/6b09fff4-5e68-43df-a3d2-aaad6e68aa94.html.
2.鄭義 ,《紅色紀念碑》(臺北:華視出版社,1993)。又見《神州穿梭:文革廣西武宣縣紅衛兵吃人肉事件》 www.youtube.com/watch?v=IlrnY1H8_Bg
3.黃文雄,《中國食人史》(臺北:前衛, 2005)
4.有關西方學界對吃人的文化歷史意涵的討論,見Frank Lestringant, Cannib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導讀二
曹冠龍的《沉》和中國人的輕
李劼
曹冠龍的《沉》使我聯想起他在波士頓藝術學院裡完成的的一尊雕塑:《柬埔寨招魂舞》。一雙嫵媚而猙獰的手,吳哥窟蛇神似地扭著一束極度夸張的纖指,以一個消魂蕩魄的舞姿,召喚和引誘著那些在黑暗中漂泊的亡靈。如果柬埔寨那些波爾布特的冤魂們時時需要這麼一雙玉手的安撫,那麼廣希湖那些毛澤東的犧牲者便會夜夜聆聽《沉》為他們唱的悼亡之曲。
導讀如同導游,在進入一個崎嶇山路前,有責任提醒旅客們繫好安全帶,準備一場心理上的衝擊和顛簸:曹冠龍的《沉》裡有心曠神怡的青峰銀瀑,但也有觸目驚心的惡山黑水。一路讀去,《沉》會不時地讓你捧腹大笑,但行至尾頁,掩卷靜坐,你又會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揮之不去的憤懣和壓抑。
但曹冠龍的《沉》又是不能不讀的,就像廖亦武的《底層採訪錄》一樣。凡是想瞭解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隱史的,凡是想到中國去尋找商機的,凡是想到中國去謀求仕途的,甚至凡是想到中國去喝嬰兒湯的,或者尋花問柳,包二奶什麼的,曹冠龍的《沉》和廖亦武的《底層採訪錄》,乃是必讀之書。猶如去某個陌生的地域旅遊,有必要翻翻當地的旅遊指南,從而知道什麼事情是不可做的,知道什麼事情做了之後會有損陰德,會造成終生難以洗滌的良心譴責。
雖然《沉》不是《底層採訪錄》那樣的實地實人實錄,但這部小說所展示的畫面,所描述的細節,卻一樣的生動,一樣的鮮活。小說的整個敘事方式,乃是一種沒有結構的結構。看似漫不經心的侃侃而談,有時還有東拉西扯之嫌。然而,讀著讀著,你便會發現,整個故事從來沒有離開過那些愚昧荒蠻,又極富象徵意味的村落,始終圍繞著那群在吃人和被人吃之間掙扎的眾生。僅以那道豎於兩省間的界碑為例,就可以看出作者圍棋般的構局:成竹在胸,前後呼應,自界碑始而至界碑終。整個敘事,猶如一個巨大的漩渦,不停地打轉,將一個悲慘的人世間漸漸地吸入那深不可測的歷史河底。筆者因為沉湎於這部小說的閱讀,燒糊了一鍋稀飯。
《沉》敘事構架的宏偉,並沒有帶來細節的粗疏。在小說結構上,作者發揮了中國潑墨山水的寫意傳統,筆墨淋漓,隨意潑灑。但每一個人物,每一場情景,乃至每一次突發的聯想,卻又像絹扇蟲鳥似的,工筆細描,毫髮畢露。在小說的人物塑造和氣氛渲染上,作者常常表現出倫勃朗式的濃重,傑克.倫敦式的冷峻。小說中的諸多景物描寫,又每每令人想起德拉克羅瓦式的奔放,或者夏多布里昂式的熱烈。比如作者筆下的廣希湖的黃昏:
落日的遠征軍,閃爍著金色的盔甲,從天際滾滾而來,雄心勃勃地要在這廣希湖面濺起一片輝煌的波漣,打通那直達東方的黃金國道,卻一次又一次地在湖邊被寂水神色不動地攔腰斬斷。
湖岸上,一行光脈,如同被砍去了頭顱的巨蟒,顫抖著鱗片,漸漸地褪去血色......。
在當今的華語小說中,已很少見到如此雄健宏偉,想像奇特,銀幕感和音樂感交融滲透的文學語言。一幅幅充滿質感的歷史畫面,有如魯本斯無拘無束的放浪筆觸,潑灑著達利式的奇思異想。
小說之於歷史這種逼真的變形,與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相比,氣質上更加豪放,敘事上更加從容。這部小說所展示的芸芸眾生,對於華語讀者,當然更比那遠離千年漢文化的拉美《百年孤寂》要親近許多。就作者個性而言,也有別於馬奎斯與卡斯楚稱兄道弟的俗不可耐,曹冠龍乃是與生俱來的獨立不羈。《沉》的敘事者,頗像一個豪放的魯智深:坦蕩的詼諧之中,充滿著悲憫的情懷。正是這樣的坦蕩如砥,才使曹冠龍將《沉》寫得如此大氣磅礡。
中國八十年代的文壇,一度出現過受了《百年孤寂》影響的尋根小說。其中的著名篇幅大都是中篇短制,諸如韓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樹王》、《孩子王》,王安憶的《小鮑莊》。這些苦心經營的小說,其立意不外乎在於,試圖以文化尋根或者歸依上古的名義,對中國的歷史和當下做出一番別開生面的描述。然而,那樣的努力僅止於嘗試,並且都是淺嘗輒止。許多年以後,這些個文化尋根者,除了阿城,大都在仕場尋得了一席之地,成了大陸官方作家協會的主席、副主席什麼的。這一類的小說,更是成了文壇往事,被封存於朦朧的記憶理。唯有在大陸文壇上從不搶眼的曹冠龍,離國二十多年後,在遙遠的北美,卻悄然地將故國那段黯然失聲的文化和歷史的交響,浩浩蕩蕩地譜寫成了一部驚心動魄的史詩。
藝術家氣質極其濃郁的曹冠龍,對於人事和物象有著獨到的觀察,對於歷史和典故也有著別致的解讀。天馬行空的敘事,並不妨礙有條不紊的人物刻劃和細節描繪。天上地下,人間冥府;活人與死者,眾生和幽靈;彷彿都是很不經意地寫出,卻又一筆筆猶如刀削斧劈,渾然天成。殺人的場面,吃人的細節,驚心動魄的程度遠非魯迅的《狂人日記》可相比擬。當年喊出吃人的時候,魯迅一心控訴歷史,絕對想不到竟然成了一個陰森森的兇兆:內戰的硝煙飄散後,中國大陸將出現一個波瀾壯闊的吃人時代。
《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作者,只知道生命之輕,絕對不會知道中國人的人命,是如何的輕賤。倘若說,食素會讓人的身體感覺輕快,吃肉會讓身體變得沉重,那麼中國人也罷,中國社會也罷,中國歷史也罷,全都由於祖祖輩輩,子子孫孫吃多了人肉而變得沉重不堪,致使整個民族難以向上,只能不斷地下沉,下沉,再下沉。人命越輕賤,這個民族及其歷史就越沉重。這也許就是小說何以命名為《沉》的寓意所在吧。
這樣的小說,如一本正經地寫,便成了一冊駭人聽聞的犯罪檔案。曹冠龍筆下的悲劇,卻全然以喜劇筆法寫出。所有令人毛骨悚然之處,一一被訴諸嘻嘻哈哈的調侃和輕輕鬆鬆的說書。面對如此一個人間地獄,哭天搶地顯得膚淺,欲哭無淚又會被人懷疑矯揉造作。作者於是選擇了幽默,並且是黑色的,一如小說封面和封底濃重的油墨。
倘若有什麼不足的話,那麼無非是偶爾像花和尚多喝了點陳年花雕似的,會嘮叨個沒完。作為一個敘事者,不投入是不行的;但過於投入,作者就會情不自禁地袒胸露乳,掃開眾人,闖進小說說搶了敘事者的風頭。當作者在扮演一個敘事者的時候,必須充分尊重自己的角色。
從八十年代脫穎而出,到了二十一世紀之初才被公認為傷痕文學之巔的曹冠龍,以《沉》再一次向期待著的世界展示其獨特的文學才華和經久不衰的創作激情。以毛澤東時代為背景的《沉》, 目前只能在臺灣出版,這與其說是荒誕的,不如說正是《沉》的價值所在。偉大的文學往往在當代困頓寂寞。然而,在政治和流行的一片喧嘩中,歷史捧著桂冠,耐心等候。
二00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寫於哈德遜河畔
導讀三
Genuine & Authentic
——評曹冠龍的「《沉》的組曲」
梁雷
感動我的藝術作品,無論是小說詩歌,還是雕塑繪畫,或是庭園建築,必然內含獨特的音樂性。偉大的文學作品都有一種音樂感。中國的文學自古就很講究樂感。在曹冠龍的文學中我就能體會到一種古老又充滿當代體驗的音樂感。現在我又直接聽到了他的音樂。
曹冠龍的音樂很特別,就像他的文學作品一樣,既沸騰著原始粗獷的生命力,又凝聚著精致細膩的筆觸。文學家能作曲演唱的,古時候不少,現在幾乎滅絕了。但曹冠龍忽然復古,或返古。但仔細一想,這對他來說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的文學作品本身就具有強烈的音樂感,有一種天然的韻味與律動。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寫長篇小說推敲平仄的。我想,直接用歌聲來表達感情也許是曹冠龍的一種本能的衝動吧。
曹冠龍譜寫和演唱的「《沉》的組曲」共有三首歌。其中的〈撒了我一頭的花〉和〈一句大白話〉的旋律都是陜北民歌,特別是〈信天遊〉的變奏。黃土高原萌生出來的那種高亢、空曠、悲壯的呼號與《沉》深重的悲劇氣氛構成了天籟的和音。〈峽谷的風〉則明顯地採用了京劇中舒展從容的西皮搖板的旋律要素。
陜北民歌都是傳統地由男高音演唱的。但曹冠龍是男中音,所以他便根據自己的音域來譜寫這三首歌。犧牲了點高亢,增添了些渾厚,有失有得。
台灣是崑曲的一方淨土,相信寶島的讀者們和聽眾們一定能品味出這位老兄是一個崑曲票友。曹冠龍在演唱時摻進了不少崑曲的那種蒼勁的韻味,特別是南派的「水磨腔」,延緩節奏,放慢拍子,4/4拍,甚至8/4拍,一唱三嘆。在旋律的進行中頻頻揉入了典型的「一字數轉」的裝飾音,和「一字數頓」的挫咳音(麒派老生周信芳常用這種唱法)。不管用什麼腔調,不管是在高音區或低音區,他一概十分注意吐詞清晰, 咬文嚼字,把每個字的頭、腹、尾都交代清楚。崑曲的演唱是十分講究這一點的。
在演唱中,曹冠龍有創意地應用不同的發音共鳴,以抒發不同的感情。如在〈峽谷的風〉中,在唱「沒有一絲兒悲歡離合,榮辱得失」時,他有意減少共鳴,讓聲音變薄變細,以表達那輕飄飄的世俗價值。但一進入宇宙和神的領域,他便充分地發揮自己得天獨厚的胸腔共鳴,呈現那天宇間宏大超脫的氣氛。
曹冠龍也努力在美聲唱法和民歌唱法之間追求一個合理的平衡。太美聲了,聲道繃得太緊,共鳴過分強烈,那就會失去《沉》的地域特色。反之,太民歌了,又有點過分乾澀,缺乏《沉》的魔幻文學的現代氣息。
順便提一下,我也有幸試聽了曹冠龍近期譜寫和演唱的《遠去的市音》,那是十來首取材於老上海叫賣,而創造出來的一系列絢麗多彩清唱短歌,更將他扎實的生活基礎,豐富的想像力,奇特的作曲天賦,多變的演唱技巧表現得淋漓盡致。
提起清唱,望而生畏。清唱如同獨奏,赤裸裸的沒有掩蓋,任何一點瑕疵均暴露無遺。仔細聽,你一定會覺察出這位小說家的歌聲中有若干不夠完美的地方。如有伴奏,就不露聲色地帶過去了。但他將這些毛刺坦蕩蕩地和盤托出,臉不紅,心不跳。在我們的交談中,他曾說:「與其假而完美,還不如真而破碎。」這就是曹冠龍。我曾用兩個形容詞“genuine”和“authentic” 來評價曹冠龍的文學作品,這兩個詞也完全適用於他的音樂作品。
靜靜地聽他的歌吧!你會理解我說的是什麼意思。
二00九年十月十九日